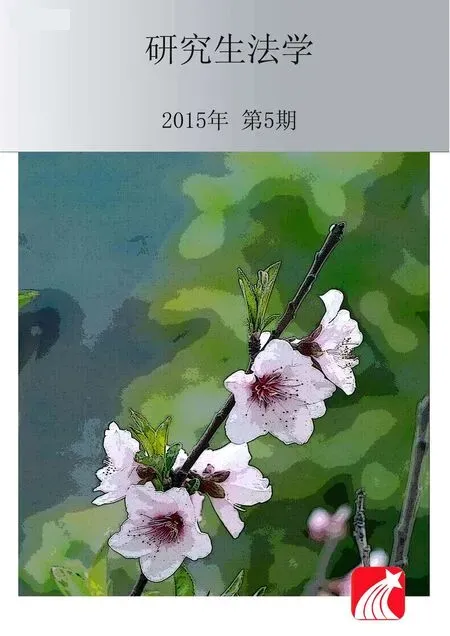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双重张力
——读哈贝马斯《事实与规范之间》
2015-02-12赵英男
赵英男
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双重张力
——读哈贝马斯《事实与规范之间》
赵英男*赵英男,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100871)。本文写作得益于“法律与正义”读书小组诸学友师长指教与本文评审意见。当然一如成例,文责自负。
“事实性与有效性”是哈贝马斯法哲学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在扬弃罗尔斯《正义论》研究偏重“规范性”而缺乏“事实性”、卢曼系统论缺乏“规范性”而偏重“事实性”的不足后,哈贝马斯提出以“沟通理性”为核心的“沟通行动”弥合二者之间的断裂。通过仔细考察哈贝马斯语言哲学基础,分析“事实性与有效性”何以成为哈贝马斯的核心关切,进而揭示“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双重张力。
有效性 事实性 沟通行动论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于上世纪90年代问世以来,即在法哲学界受到广泛地关注。学者的阅读和批评不仅丰富了对于哈贝马斯“沟通行动论”*该概念也有被译为“交往行动”或“交往行为理论”。有关该理论的中文译名辨析,参见孙国东:《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之间: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258页。于该书附录中,孙国东指出,所谓“行动”不同于“行为”是因为前者凸显了主体某一行为的内心意图,侧重于表明主体将一定意义赋予其所为之行为。而“行为”仅仅强调了主体行为的外在方面,没有考虑到做出这一行为时的心理因素。而“沟通”一词相较于“交往”,强调主体做出行动时对于共识的期待,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意味。而“交往”多为生活用语式的表达,涵义更为广泛,即使某人际互动不出于“达成共识”的期待,也可称之为“交往”。但哈贝马斯理论中的人际互动,是要以达成共识为鹄的,因而译为“沟通”更为贴切。(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Handeln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的多侧面解读,同时还推动了欧陆社会哲学、法哲学与英美法哲学之间的交流、互动。*在英美哲学界对于哈贝马斯的主要推介者是Thomas McCarthy,他不仅是哈贝马斯理论里程碑《沟通行动论》一书的译者,同时其有关哈贝马斯的研究性著作《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是西方研究哈贝马斯思想的奠基之作。在1992年有关《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的研讨会上,哈贝马斯曾说,“遇到托马斯·麦卡锡是我的福气~~我总是有这样的印象,他比我本人更理解我的文本……以至于当他在他文章中那样强调我们之间的矛盾时,我感受到了一些不安”。SeeWilliam Rehg, & Andrew Arato (eds.), Habermas on Law and Democracy, trans., J.Habermas&Benjamin 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p.390.两大传统能够借由此书而彼此照面,一大机缘在于哈贝马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与“采各家之长”的论证风格。
在该部作品中,他不仅系统性地提出了民主与商谈理论视角下法律形成、权利来源、法治国构建的宏大理论,同时也表达出了当今法哲学界的核心焦虑。这一焦虑,以哈贝马斯观点来看即是“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存在着难以舒缓的张力。借由批判卢曼自创生(autopoiesis)系统论,哈贝马斯指出从系统理论出发,对于法律的社会学研究丧失了规范性之维*哈贝马斯将社会学角度对于法律现象的研究称之为“社会科学对于法律的祛魅”。在他看来,这一进程的极端表现就是卢曼的系统理论。在卢曼的视野下,现代社会中法律形成为一个自组织、自创生的封闭性系统,法律本身是这个系统再生产的产物。法律不再与权力、政治有关,也与经济、政治系统无涉,法律就等同于判决、论辩等一系列经验性行为。但值得一提的是,哈贝马斯并不认为这一结论是系统论理论进路的必然结果~~在有关托依布纳理论的评析中,哈贝马斯认为托依布纳作为卢曼的“继承人”虽然倡导法律的“自创生性”,但是已经注重思考法律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关论述请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3~65页。;而借由对于罗尔斯先验论正义观的分析,哈贝马斯认为,哲学规范性的研究使得法律体系过于抽象而缺乏与现实经验的联系。易言之,社会学进路的研究过于关注“事实性”,而规范性角度的探索往往只重视“有效性”。在“扬弃”二者研究取向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从“沟通理性”出发兼具社会学、哲学视角研究法律现象的观点。*有关论述请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0页。
这一问题意识对于哈贝马斯提出自身理论构建价值重大,本文则拟从这一细微之处入手,首先分析“事实性与有效性”于哈贝马斯理论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并进而解释二者之间存在的两个层次的张力。
一、“有效性”概念的引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探寻“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第一步需要明确的是这两个概念的涵义。通常情况下,“事实性”并不出现于中文的学术语境之中。“有效性”也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学理论概念。本文固执于使用这两个词汇,主要是考虑到哈贝马斯原作的书名FaktizitätundGeltung。其中Geltung一词既被哈贝马斯赋予了法律效力(validity)的涵义,又被赋予了法律实效(efficacy)的涵义,因而译作“有效性”。为与之相对,Faktizität译为“事实性”。虽然英译本将之译为“事实与规范”(between facts and norms),且亦获得哈贝马斯本人首肯,*有关英译本术语探讨与中译本术语厘析,请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04~706页。在中译本后记中,童世骏也指出,英译本对于哈贝马斯该书标题的翻译也不够确切,但是考虑到在中文语境下,“事实性”一词不符合通常用法因而译作“事实”,与之相对,“规范性”或“有效性”则不得不译为“规范”。此外,他还提及虽然英译本的标题可能不符合哈贝马斯理论内容,但毕竟该版本受到哈贝马斯的修订与首肯。但是这一译法并不能够体现出Geltung一词的双重含义,也就不能彰显哈贝马斯本人书中提出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双重张力。
那么何为“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双重张力?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以研究“公共领域”为学术起点,作为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哈贝马斯,为何会在其理论成熟期逐渐转入有关法哲学的探讨。而这一学术脉络的厘清,将会使我们看到“事实性与有效性”的问题为何是哈贝马斯的核心关切。
哈贝马斯的理论成熟是以20世纪80年代《沟通行动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的。在该书中,哈贝马斯从韦伯的“行动类型”的理想型研究出发提出了“沟通行动”与“沟通理性”,藉此置换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策略性行动主宰现代社会的悲观预言。*See 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Thomas McCarthy, Beacon Press, 1987, pp. 94-101.有关哈贝马斯与韦伯理论承继关系的具体探讨,See Harry F. Dahms, Theory in Weberian Marxism: Patterns of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Lukacs and Habermas, 15 Sociological Theory (1997): 181.在本文中作者提出,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了韦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工具主义的批判和悲观态度,另一方面则继承了马克思传统中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乐观取向。其理论核心旨在倡导以言语为媒介通过公共领域中的沟通、论辩而形成共识,以此摆脱现代社会中“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殖民”,从而获得良好的社会整合形式。*有关“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二分法,See 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homas McCarthy, Beacon Press, 1987, p. 185, pp. 171-175. 所谓“系统”和“生活世界”,两个概念密不可分。“系统”特指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行政、经济领域高度发展而从生活世界本身脱嵌,并进而将以权力为主导的行为方式、以货币金钱为主导的行为方式推广到整个生活领域之内。换句话说,工具理性的行动压制了道德、政治合理性与审美、实践合理性。人们的行为准则都以金钱、权力为度量加以评价。这就是所谓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哈贝马斯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提出“沟通理性”,人民藉此达成共识对抗“工具理性”的泛滥。这一于后现代视域下明显具有“乌托邦”性质,强调话语、强调对于真理和共识追求的理论构想,一方面源于哈贝马斯本人的人生境遇——他罹患天生兔唇,童年与少年时期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哈贝马斯童年的简介,See Eduardo Mendieta, Habermas: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8, pp. 6~7.但另一面更主要的则是哈贝马斯本人的理论取向,即所谓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学转向”最早的萌芽出现在19世纪末,此时康德与黑格尔有关本质和现象的区分已经失去了说服力。认识论的问题成为科学主义主导的经验研究的领地。*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页。根据经验研究,人们普遍认为,思想与表象是有本质区别的。表象是个人的、特殊的,而思想超越于个人意识,具有普遍性和同一性。那么如何超越于表象而认识思想呢?在经验主义研究看来,思想一定要表现为一种命题或表述一个事态,这也就意味着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因而认识思想就需要分析语言的语法、结构,因为命题或语句形式是多变的,但是其结构和语法则是相对稳定的。因而,通过句子的构成语法就能够穿过复杂表象获知思想本身。*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页。
然而这一观念需要一个假设,即每一个思想都要以一定的事态作为其确定的内容,而且这种事态是可以被表述的。*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不如此,则思想无法向获知它的人主张真或假的判断。不能被识别为真或假,也就意味着这个思想不能被断定是否有效,也就不成其为思想。由此可见,所谓的“有效性”其实指的是一个思想的真值问题。而思想往往借由语言体现为一个命题。因此,有效性在此就意味着一个命题的真值。若命题为真,则可认为其是“有效的”;否则,则是无效。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否为真呢?由以上的推论可以看出,思想借由语言以命题的形式得以表达,而且思想(命题)本身是普遍的而非个别特殊的。这就意味着:当我们通过某个命题来表达p这个思想,也就是在表述p所意指的某一事态。此时不是涉及p表述的事态是否具体存在,而是表达p所表述的事态是否得以成立。以哈贝马斯的举例来讲,就是当我们借助命题“一个球是红色的”,表达的是如下思想:“至少存在一个球,它是红色的”而不是指“我们眼前有一个具体的球,它是红色的”。*有关该举例,请参见该书第16页。在此,有必要稍加澄清事实与事态的区分。所谓事实,多有“眼见为实”的涵义,是一种既定的、现存的、恒常的状态;而事态彰显一种可能性、未来性与流变性。具体些的例子可以为,语句“某人去世了”可以表现为一个事态(因为此人还活着),但当此人真的去世后,“某人去世了”成为了一个事实。由此可见,当我说“某人去世了”这个语句时表现的是一种事态,而只有根据现实情况对该语句做出真假判断后,才能确定这个语句是否表现的是事实。
从这一论述中就可以发现,有关一个命题是否为真的判断,最后其实归结于对于生活事实的判断,也即需要解决生活中是否的确存在着“一个红球”的问题。而随此而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命题作为思想的语言表现形式是普遍、同一的,那么无论是谁在何时对其做出“是与否”的判断结果也应该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既然需要根据生活事实做出有关命题是否具有“有效性”的判断,那么作出判断的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意识的特殊性,而这就与思想所主张的“普遍性”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而这种冲突反映在语言本身,就是内在于概念之中的紧张性:“概念之普遍性所具有的理想性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根据语言的规则结构来说明,同一的意义,是怎么可能在各种语言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之中保持不变的”。*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页。而这也就意味着哈贝马斯需要开拓出这样的一条道路,即对于某一命题为真的“有效性”主张,要超越于各个局限于特定共同体的诠释者本身的特殊性。*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页。
再具体些,内在于语言概念的紧张其实是有关一个命题的“有效性”所具备的两个相反的面向造成的:一方面“有效性”要求,一个“命题”(作为思想的语言表现形式,并且以生活事实作为其有效性根据的命题)必须突破每一个语境而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但另一方面,“命题”却是在此时此地的具体语境中被提出,被判断是否具备“有效性”。进一步,只有一个“命题”的可接受性是普遍的、“零语境的”(即摆脱语境束缚),那么它才能够真正具备有效性;但只有在某一具体语境中,该有效的“主张”才能够转化为行动,成为现实。*有关“有效性”这两个面向的论述,请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页。
在此我们已经基本上触碰到了“有效性”这一概念本身的意涵,在抽象层面它指的是一个命题是否为“真”。如果一个命题是“真”的,那么就具备了“有效性”。进而,我们如哈贝马斯所归纳的,将“有效性”定义为某一主张或命题的“可接受性”。这一定义就凸显了我们如上分析的内在于“有效性”这一概念本身的张力,因为“可接受性”这一语汇本身预设了被提出的主张或命题通过一定方式被证成为“真”或“假”的可能性,同时也显现出哈贝马斯个人开拓的“共识真理论”(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中“共识”的本质,亦即通过商谈达成的共识与某一主张是否为真或假具有紧密关联。*在此哈贝马斯的理论明显有别于“真理符合论”,即命题或语句的真值在于命题对于某一事态的描述符合生活实际。相反,他采纳的是“共识真理论”,即一个命题或语句的真值取决于商谈各方是否就命题或语句所表述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有关哈贝马斯的“共识真理论”,学界讨论颇多且尚无定论。围绕“共识”和“真理”之间的关系,论者大多探讨“共识是否是真理的判断标准?”“共识是否是对真理内容本身的说明?”等等问题。相关论题的讨论,SeeNocholasRescher, The Problem of a 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 in David M. Rasmussen & James Swindal (eds.), J. Habermas Vol. IV,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397. 有关哈贝马斯关于“共识真理论”这一理论的流变,SeeAlessandro Ferrara, A Critique of Habermas’s 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 in David M. Rasmussen & James Swindal (eds. ), J. Habermas Vol. IV,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327. 此外,笔者认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中西方学术语境中,有关“真理”一词的涵义可谓是大相径庭。在中文语境,“真理”所具有的真实性,具备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的意味。可以说是“绝对”的。但是在西方语境中,真理(truth)一词在很多情境下表达的是一个命题的真值为真(true)。此时它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真理的意味。哈贝马斯于《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很大程度上提及“真理”问题时,侧重于后一种涵义。不过,我们目前尚不能马上进入到对于“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之中,在此之前,还需要对“有效性”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再次澄清。这就涉及到哈贝马斯对于奥斯汀语言哲学的运用。
二、“有效性”概念的拓展:奥斯汀的语言哲学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有效性”这一概念连接着一个命题的真值。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概念不仅并非哈贝马斯的原创,对其开拓性的运用也并不能归功于他本人。对此有突出贡献的是英国分析哲学家J. L. 奥斯汀(J. L. Austin, 1911~1960)。奥斯汀在其著作《如何以言行事》中对于言语行事现象做出了著名的区分。本部分将通过回顾这一理论区分而厘清哈贝马斯理论的某些预设,并呈现出“有效性”的诸个向度。
对于语言本身,奥斯汀之前的理论多将之视为是对作为认识客体的对象的一种“描述”。*参见[英]约翰·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厄姆森、斯比萨编,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页。比如当我说“一个球是红色的”则是意味着我在描述有一个物体,它是一颗球且颜色是红的。但是这一理论并不能够穷尽语言行事现象的全部。比如,我会说“我打赌明天会下雨”,或者我在遗嘱中写道,“我把我的表赠送给你”。*有关这些例子,可以参见[英]约翰·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厄姆森、斯比萨编,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页。这些话语并不是在作出描述,而是这些话语本身即是在做某些事情(打赌、承诺等)。奥斯汀认为,对于前一种表示“描述”的话语来说,可以称之为“记述话语”,我们可以根据被它描述的现象而分析其真或假;但对于后者而言,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可以被称之为“施行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它无法被判断为真或假,只能被视为适当或不适当(happy or unhappy)。具体来说,对一场赌局而言,我们无法判定打赌这个话语行为是真是假,因为我们并不意欲描述而是真的要参与一场赌局。那么,如果我在比赛结果产生后才打赌,这就不能认为我打赌这一话语行为是“假的”,只能说我这场赌局“无效”,因为我打赌并不“适当”。*有关“赌局”的例子请参见[英]约翰·斯汀:《如何以言行事》,厄姆森、斯比萨编,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6页。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奥斯汀语言哲学中,一个语句(或命题,本文对此两个概念不作详细区分)的“有效性”有了完全不同于我们前文所分析的涵义——在此时,语句的有效与否与其真值不存在必然关联。这是因为当一个语句是作出描述时,其有效性才能够以真或假作出判断;但当一个语句是“施行话语”时,判断语句有效性的标准就是是否“适当”。
借助“描述”与“施为(施行)”这一标准,奥斯汀区分了两种言语行事现象,但是随着其理论发展和研究地深入,他发现自己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限定“施行话语”具体的界限是什么。为此,许多论者及奥斯汀本人都认为自己的区分有待改进,甚至完全是误导性的。*有关施行话语的基本标准,请参见[英]约翰·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厄姆森、斯比萨编,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7页。有关奥斯汀对于言语行为的两种区分所具备的的困难,请参见该书译者导言。在这种情形下,奥斯汀将自己的二元区分扩展为了三元区分,即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话语施效行为。由于这三个概念区分本身十分复杂,本文将通过一个例子对此三者的联系与区别加以总结。
当我说“我会在明天下午三点交作业”时,对这一句话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向度加以理解。就“话语行为”而言,我这句话是一种描述,我在表达“我明天下午需要交作业,而时间是三点”。除此之外,这句话没有其它任何意味。而从“话语施事行为”来看,这句话近似于一种承诺:我可能是在向任课老师保证,我不会迟交作业;也有可能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或自律,总之要比仅仅描述事态具有更多的意味。最后,从“话语施效行为”来看,这句话也有可能表达的是一种委婉的拒绝:比如有某个我不想见的人要在明天下午拜访我,而我将这句话告诉他,实际上就意味着委婉地表示拒绝的涵义。*有关从某一句话入手形象分析三种行为的差异,SeeEduardo Mendieta, Habermas: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8, p. 66.
而以上内容,以哈贝马斯的归纳就是,“说某事(话语行为),在说某事时做某事(话语施事行为),通过在说某事时做某事而造成某事(话语施效行为)”。*有关此表述,SeeJ. Habermas, On the Pragmatic of Communication, Maeve Cooke (ed.), The MIT Press, 1998, p. 122. 转引自[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脚注。换句话说,对于一句话而言,它很有可能兼具这三个向度的涵义。奥斯汀也持此论,同时认为每一句话都虽然未必具有“话语施效行为”向度的涵义,但是都具有“话语行为”以及“话语施事行为”两重涵义。*参见[英]约翰·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厄姆森、斯比萨编,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4页。
因而我们不难看到在哈贝马斯的眼中,一个语句(命题)具有着双重属性——它既是描述性的,又是施为(施行)性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上文中厘清的两种“有效性”的涵义都被哈贝马斯吸纳入自己的理论,认为是对于语句(命题)有效性加以判断的标准。
在此,本文暂不讨论这两个有效性标准的关系,单从施行话语角度稍作延展,以便进一步理解哈贝马斯的理论。由于哈贝马斯认为每一个语句(命题)都具有施行意义,因而“有效性”作为判断“话语施事行为”的标准,就顺理成章地扩展到了整个语言范围之内。而这也就同时意味着语言在这个世界中具有了“本体论”上的意义。借由“话语施事行为”,语言不再仅仅是本体的模拟物,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世界的描摹,而是作为行动的话语本身即在构成着世界。
由此,在语言得以成为本体的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哈贝马斯在“语言学转向”后,通过语言而达成共识、并将之视为这个世界现实本身达成共识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构建理论的基础之一是奥斯汀所区分的“话语施事行为”,因为这一行为所主张的“有效性”判定标准与哈贝马斯对于“有效性”问题的思考有密切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从语言学角度理解哈贝马斯“共识真理论”的一条进路为:既然语言构成着世界,语言的边界乃为世界的边界;那么依靠语言取得的共识也就意味着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着共识,即便现实生活中我们或许未曾察觉到。
让我们重新回到“话语施事行为”之中,奥斯汀认为要达成一个有效的“话语施事行为”,需要一定的标准,这些标准具体为:(1)必须存在一个具有某种约定俗成之效果的公认的约定俗成的程序,这个程序包括在一定的情境中,由一定的人说出一定的话;(2)在某一场合,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景必须适合所诉求的特定程序的要求;(3)这个程序必须为所有参加者正确地实施,并且(4)完全地实施。此外,还需要(5)这个程序通常是设计给具有一定思想或情感的人使用,或者设计给任何参加者去启动一定相因而生的行为,那么参加并求用这个程序的人,必须是具有这些思想和情感,并且(6)随后亲自这样做。*有关这些标准,参见[英]约翰·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厄姆森、斯比萨编,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7~18页。需要指出的是,奥斯汀将此六个条件分为三组,其中1和2为一组,3和4为一组,5和6为一组;这涉及到对于“话语施事行为”不同偏差类型的划分,于文本论述并无必然联系,因而略去不谈。这些标准也即“话语施事行为”之“有效性”的判定标准,其作用就在于保证当我做出一个“话语施事行为”时,听话者能够准确理解我的意思而不会产生误解。比如,当我在打赌时,听话者根据我言语的情境、程序等标准得以判定我的确在发出一个赌局的邀约,而非开玩笑或反讽。
不过哈贝马斯并没有直接继承奥斯汀所提及的六条标准。而是将这六条标准转化为对应其“沟通行动论”中所区分的三个世界,*很多论者已经指出哈贝马斯其实是误用了奥斯汀的语言哲学理论,但鉴于本文是追寻哈贝马斯如何使用“有效性”这一概念而非辨析哈贝马斯语言哲学理论基础恰当与否,因而这一问题姑且不论。有关这一方面的讨论,SeeMaeve Cooke, Language and Reason: A Study of Habermas’s Pragmatic, The MIT Press, 1994, pp.1-27.在该书第一章中,作者检讨了哈贝马斯同语言哲学的关系,并进而指出,由于论者的批评,是的哈贝马斯在其理论后期改变了术语的使用:从直接承袭奥斯汀的三类言语行为划分,改变为“语内行为”、“语后行为”的划分。从而将“有效性”的涵义转变为三个方面,即除了肯定性命题的有效性之外,还有主观的真诚、规范的正确。*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页。具体而言,这就表明“沟通行动”的有效性体现在三个层次上,即道德上的正确性、客观事实的真实性以及主观上的真诚性。*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哈贝马斯所区分的“三个世界”。它们分别是道德领域、伦理—政治领域、审美领域,各个领域的有效性主张分别为道德上的正确、客观上的真实、主观上的真诚。这三个“世界”是哈贝马斯对于“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做出的进一步描述。它旨在说明秉承沟通理性的行动者并非仅仅以客观化地外在视角面对自己所处的世界。相反,他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下采取不同的态度。而当行动者的态度取向与其所处领域的有效性主张相吻合时,就达成了“社会整合”;反之,就很有可能是“系统整合”,甚至是“失范”。有关论述,SeeMaeve Cooke, Language and Reason: A Study of Habermas’s Pragmatic, The MIT Press, 1994, p.21.易言之,哈贝马斯借用奥斯汀的理论,将语言不仅视为对于世界的描述,还视为对于世界的构成具有作用。通过论证话语“施行行为”具有普遍性,哈贝马斯即将讨论语句或命题的“有效性”视为其理论的核心——因为关注语句与命题即是关注世界本身。在这一意义上,奥斯汀语言哲学中所谓的“有效性”同哈贝马斯理论中的“有效性”之间形成了对接。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简要讨论,已经追踪出了哈贝马斯从何处继承了“有效性”这一概念(以语言哲学为基础),以及为何要关注“有效性”的问题(语言作为一种本体,以及包含于“有效性”之中的张力)。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到有关法律如何体现出“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张力的讨论之中。
三、内在张力与外在张力
在论述“事实性与有效性”张力之前,最后一道“关卡”是哈贝马斯有关“有效性”三个维度的主张是如何同法律现象相衔接的问题。哈贝马斯论证了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何以成为社会整合的必然纽带从而使得“有效性”问题同法律现象结合起来。这一方面涉及到哈贝马斯社会演化理论,同时又涉及到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有关其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内容,请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96页。(本书第九章“现代国家中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德]于尔根·哈贝马斯著:《合法化危机》,刘北城、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在这两部著作中,哈贝马斯提及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整合失败而导致的危机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其有关“系统与生活世界”理论的先声与补充。本文限于主题无法将之详细讨论,但哈贝马斯理论重构的结论是,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系统的高度分化,社会整合越来越依靠于个体行动者的“理解成就”,即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共识而维持社会秩序,形成社会的再生产。*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页。而作为法律现象的载体,语言,就成为了人们达成共识的重要手段。因为它一方面降低了系统运行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降低了社会协作的成本与人与人之间达成共识的负担。换句话说,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人与人之间不是说他们想要沟通,而是他们不得不沟通,因为非如此不能保证社会的存在。
在此意义上,关注法律就是关注社会得以可能这一核心问题。进而,这意味着生活世界中三个领域的有效性主张悉数被吸纳入法律本身,而对法律本身“有效性”问题的解决,就能够完成有关社会整合的任务。由此不难看出,在法哲学范畴中哈贝马斯将先前从较为一般的对于语句或命题“有效性”的探讨,转化为了对于语言的特定领域,也即法律的有效性的探讨。*本文认为这一归纳是有道理的。本文前两部分着力点便在于追踪“有效性”这一抽象概念如何进入哈贝马斯的理论视野并最终进入其有关法哲学讨论之中。
在完成这一衔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了。在此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所谓“事实性”(Faktizität)概念是“有效性”概念的对称,指的是与“有效性”概念相对反的情况。易言之,所谓“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其重点是分析“有效性”之涵义是什么。对照法律有效性与哈贝马斯理论中“有效性”主张的三个向度。显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法律,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实证法并不涉及到审美领域的“主观上的真诚性”主张。因而,法律本身有效性承袭了哈贝马斯提出的其它两个向度,即道德上的正确性与客观上的真实性。这就意味着法律本身内容在面对异议时是可辩护的,同时又是可以在社会中主张具备普遍约束力的。进一步的,将这一哲学话语转变为法学术语,就意味着法律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求它得到规范性的接受;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其平均被遵守的情况而加以衡量。哈贝马斯将前者称为“规范有效性”,后者称为“社会有效性”。*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页。
“规范有效性”描述的是法律共同体成员看待法律的态度。在法律共同体中,成员们通过交往行动将法律规范视为一种“义务期待”,*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页。在心理学意义上接受法律对于他们的拘束。此时,所谓的法律共同体不仅仅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人共同体,也包括了一个法域范围内的社会乃至主权国家。而“社会有效性”指的是当遵守或违反法律时就会产生相应的后果,这些后果的出现都是可计算的。因此,这一有效性向度针对的是社会中策略性的行动者。*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页。对于法律,这些行动者并不从内心加以认可进而承认其拘束力,恰恰相反,他们将之视为是一种对于自由的强制束缚。
在法学理论中“规范有效性”往往对应的是法律规范的正确性或可接受性,其对立面则是一条法律规范或某个法律体系的合法性或正确性受到质疑,不被认可。在现实生活中,后者是常常发生的景象,同时根据本文对于“有效性”概念引入的论证,这一现象其实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当一条法律规范主张自身“有效”时,其言下之意是在法律共同体内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地点对之是否有效的判断都是一致的;但一条法律规范,特别是实证法规,往往是立法者在法律共同体中于某时某地提出的,因而其是否对其是否有效的判断,脱离不开其创生之时所具备的特殊性。在此意义上,有人将这一重“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张力理解为“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的张力。*有关这一论述,请参见郑戈:《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导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虽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并不能够揭示出哈贝马斯理论的语言哲学基础。
而就“社会有效性”而言,在法律理论中大多对应着法律实效(efficacy),*需要指出的是童世骏教授在译著后记中认为,哈贝马斯此处的社会有效性是法律的社会效力,即efficiency。严格来讲,这是不确切的。所谓“社会效力”指的是法律规范发挥规制作用后,是否达到了立法者预期的社会作用,以及这一作用有多大。而社会实效(efficacy)指的是人们遵守法律,依照法律行为的事实。即社会成员实际上对于法律的遵循。其对立面则是法律共同体成员不遵守法律,规避或违反法律规定并因此而带来的暴力惩罚或强制。在现实生活中,法律的确需要由国家系统性垄断的暴力保证实施,这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可避免的事实属性。因此,这构成了“事实性与有效性”的第二重张力。
通览以上两种张力,可以将前者称为“内在张力”,因为这一重张力的生发源自于语句命题之“有效性”本身;其所涉及的是法律规范的证立与论证以及与此相伴的行动者基于法律的内在视角。而后者则是“外在张力”,即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是否匹配的问题。在这一层次中不涉及规范的论证,而是涉及到有关特定语境下社会政治现实的经验现实如何与抽象规范相结合的问题。其中行动者的视角是外在于法律规范的客观化态度。这两个层次相结合,就是哈贝马斯关于“事实性与有效性”张力的整体论述。而他所谓的沟通“事实性”与“有效性”就是指在上述两个方面运用沟通行动理论解决有效性与事实性之间相对反的情形。
关怀哈贝马斯对于“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法理论的性质、回应法实践对法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法学研究中,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讨论方兴未艾。这场大讨论所揭示出来的法理论与法实践的复杂关联,远远超出了先前“知识(理论)来源于经验(实践)”这一简单认知图示。
从法理学立场回应有关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问题,路径之一是承认法律命题在规范效力(validity)外尚存在社会实效(efficacy)。哈贝马斯所做的努力即是在此维度的延展。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内在、外在张力,以及阿列克西在对法概念分析中运用“观察者和参与者”双重视角提出“社会学、伦理学、法学”三重效力的区分。*有关这一分析,请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概念与法效力》,王鹏翔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9~92页。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伦理学、法学效力并非必然是等置并列的,法学效力某种程度上可以涵盖了社会学或伦理学的效力;但在狭义上,法学效力也可以不包含前两者。也即,只要某个法律是有权机关根据上位法制定,不与之冲突,就具有了法学效力。都对于我们充分理解法理论的性质、法律命题的效力以及它们与法实践的关系提供了充分的参照点。
(实习编辑:范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