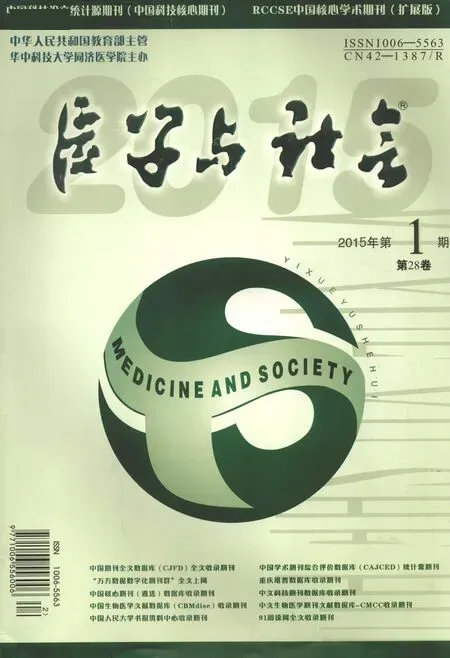基于生命质量视角的安乐死问题探讨
2015-02-12臧运森喻小勇贺云龙
臧运森 田 侃 喻小勇 贺云龙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安乐死作为一种结束生命的非自然方式,一直备受争议,2014年5月13日,苏州一夫妇申请对其8个月大的“无脑儿”实施安乐死遭到拒绝而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人们对生存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污染也随之加剧,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大陆人口为136072万人,年死亡率为7.15‰,年死亡人数约972万。《中国肿瘤登记年报(2013)》报告指出,我国每年新发肿瘤病例估计约为312万例,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死亡约270万,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癌症患者,因实施安乐死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和限定规定,许多患者是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的。
1 安乐死发展概述
1.1 境外安乐死的实施状况
安乐死(Euthanasia)源自希腊语“美好的死亡”(Eu-thanatos),意思是指舒适或没有痛苦的死亡或者是有尊严的死亡。安乐死在欧美一些国家实施相对较早,其实施的法律规范也比较完善,英国、美国、瑞典、丹麦等国家都出现过安乐死相关的法律。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安乐死自愿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但未被议会通过。1994年,美国俄勒冈州提出《尊严死亡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安乐死的合法性。澳大利亚曾经在1996年颁布第一部安乐死法律《垂危病人权利法》,但《垂危病人权利法》仅仅实施了八个月即被废止。瑞士苏黎世市政府规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医师为养老院中的老年人选择以安乐死方式结束生命时,可为其提供协助。2001年,荷兰上议院通过了《应求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法》,这是安乐死真正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得到了认可,目前荷兰有25万人加入自愿安乐死协会。2002年,比利时议会通过了安乐死法案。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等国家都有意向或正在推动安乐死立法进程。2011年1月10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对安乐死的实施进行限定。
1.2 国内安乐死的发展状况
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蒲大夫因对患肝腹水晚期的夏某实施安乐死,被公安机关起诉。6年后,该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下,蒲大夫最终被无罪释放[1]。这是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此后,安乐死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这也是安乐死引发争论的根本原因。鉴于癌症晚期、罕见病等患者及其家属对安乐死立法呼声较高。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王群等代表提案建议制定《安乐死条例》,这标志着中国安乐死的立法问题首次涉入立法机关的议事范围。此后,安乐死曾被数次提到立法议程上,但由于现实的条件限制始终未能进入立法程序。
2 安乐死问题争论的焦点
2.1 安乐死与生存质量
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QOL)又称生存质量,主要是指个体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状态评估。生命质量通常以主观条件指标,测定人们的某些人口条件、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心理状况等因素决定的生存满意度和幸福感。临终质量在生命质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生存满意度有明显的影响[2],因此产生了临终关怀和安乐死。临终阶段是生命历程的一个特殊时期,艾滋病、癌症、罕见病等诸多疾病在医疗技术尚未完全治愈的情况下,这些疾病的患者将面临治疗时间过长造成患者生命质量低下等问题,因此如何平衡死亡和生命质量的关系、如何在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减轻患者痛苦,这已成为当今医疗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安乐死有助于患者摆脱疾病的折磨,提高生命质量,符合患者临终追求生命尊严的选择,是维护患者生命质量的直接体现。但部分学者认为,安乐死在结束患者痛苦的同时,也终止了其生命,对提高生命质量并无益处[3]。
2.2 安乐死与法律规制
安乐死问题本质上就是法律规制问题,即采取何种措施来约束安乐死的申请对象,以何种方法进行实际的操作,以何种实施程序保证安乐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正常有序的开展。这些安乐死问题的研究与争议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为了理清人们对安乐死问题的认知,立法者必须对安乐死进行全局性的思考。从表面上看,安乐死实施者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实施者与真正的故意杀人犯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安乐死的实施者是有患者的要求和承诺的,而在病患对残值生命权益予以抛弃时,刑法实际上就没有对其进行强制保护的必要[4],所以必须将安乐死纳入法律的范围进行规制,才能有效的保证安乐死应有之意。像我国一样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制定一部法律规范的成本并不是很高,诸如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完全实现了安乐死的合法化,说明安乐死的技术问题已不是阻碍的因素。而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条件下,安乐死的实施可能产生一系列的纠纷和社会问题,甚至催生新形式的犯罪,所以在我国实施安乐死关键问题,是立法前必须达成社会共识和制定法律的有效规制程序,只有在兼顾两者的基础上,才能有效保障安乐死立法的正当性。
2.3 安乐死与传统观念
对死亡的认知是中国传统生存观念的重要部分,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深刻的影响着人们死亡的方式。《孝经·开宗明义章》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传统文化的影响使民众恪守着自然死亡观,倡导遵循自然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坚持自然决定命数的规则。传统的死亡观念认为,如果安乐死合法化,那么就变相的承认了杀人合法化,对生命权益的剥夺已经超越了道德和伦理的底线,严重挑战了人类的尊严和价值。但随着现代医学观念的更新,传统医学伦理学中的救死扶伤、挽救生命的医生职业操守有了新的诠释,即更加注重人的生命价值和质量。国际护士协会根据新的《护士伦理国际法》提出了“保存生命、减轻痛苦和促进康复”三位一体的原则,呼吁全世界的医学界尊重患者的尊严权、健康权和生命权[5]。此外,社会对安乐死也有着独到的认识,他们认为传统的救死扶伤、解除患者疾病和痛苦是医者必须要遵循的职业准则,但是在当前医疗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过分注重与疾病的抗争往往会导致“过度医疗”[6]。虽然,这种医疗行为在伦理上遵循了生命至上的原则,但是道义上的责任却违背了患者的生存尊严和生命的自决权益,严重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
3 安乐死与生命质量的关系
3.1 安乐死与人格尊严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尊重生命,保护人权是法律和道德的首要责任。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生存,更重要的是生存质量,法律保障公民生存权利的同时,也保证了公民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死亡作为生命的尽头,死亡的方式理应在人们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范围之中。当死亡迫近,患者无法忍受病痛折磨时,人格尊严理所应当取代生命权成为第一位阶的权利。选择死亡,是善待生命,也是维护患者最后的尊严。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亵渎,而是跳跃这个痛苦的过程,维护患者生命的质量和人格尊严,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
3.2 安乐死与生命权的关系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行为对待他人。自然人作为权利的主体,法律有保障其身体、智力、精神发展的各项权利。生命权的行使是对生命权利的尊重,而选择死亡的权利和选择理想死亡状态的权利的行使,则是对生命权的维护[5]。绝症患者在长期遭受病痛折磨又无治愈的情况下,经由严格的医学标准证明其生命在短期内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选择安乐死,是自然人作为主体对生命权益进行自主决定和处分,是合理、正当的行使权利。医疗机构尽职,家人尽责都无可厚非,但是患者的痛苦却无人分担。这种生存的状态是否理智,患者选择安乐死以平和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病痛,这也许是患者尊重和维护自身生命权的体现。
3.3 安乐死与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关系
对长期承受病痛折磨的病人来说,医疗只是延长生命时限,却不能提高生存的质量,实施安乐死终止了患者生理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是对患者生命质量的维护。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并不完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绝症患者晚期治疗,耗费家庭财力较多,这给家庭成员的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实行安乐死,一方面节省因过度医疗带来治疗费用,避免了道德上的过分责任而造成家庭成员的家庭债务,另一方面对患者和家属精神与情感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现有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13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3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73.1亿人次,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2.06人,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7.3人次和住院2.6床日;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89%,三级医院病床使用率102.9%,东部的一些地区病床使用率达137%[7]。根据《2013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显示,2012年底,我国有老年人口1.94亿人,2013年老龄人口可能突破2亿人,医疗机构面临巨大的诊疗压力。因此,对罕见病和癌症晚期诊断效果不佳的患者,实施安乐死可以有效节约卫生资源,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救护和治疗。
3.4 安乐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对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而言,时间就是生命。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保持器官的活性对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实施安乐死,一些绝症病人捐献的器官,可在最短的时间内移植到患者体内,且可有效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因此,安乐死实施,不仅使器官移值患者生命得以延续,而且也是安乐死死者家属对死者生命的尊重,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
4 安乐死实施的限制
伦理对法律有深刻影响,法律,尤其是宪法也对当代道德影响至深[5]。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的权利为宗旨。安乐死是剥夺人的生命权的行为,必须按照法律相关规定予以确认,要建立严格的,完善的制度,才能保障安乐死的顺利实施。
4.1 安乐死实施对象的限制范围
选择安乐死的患者主要集中于3类患者:第一类是绝症晚期并正忍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如艾滋病晚期患者;第二类是自我意识已经完全丧失且经专家会诊诊断不可逆的昏迷患者,如植物人;第三类是患有严重畸形或严重先天疾病的新生儿,如无脑儿、严重内脏缺失儿等。
4.2 对安乐死实施主体的限制
由于专业技术和道德水平的差异,医生的执业水平也是存在差异的。如果医疗技术被滥用,可能会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无可挽回的后果。这就要求对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职业素养加以规范和引导,提高医务人员的人文意识和道德修养,医生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应更加关注患者的诉求,考虑患者的心理和生理的承受能力;加强职业道德的修养可以使医生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坚持医务人员的道德底线,避免生命权益与利益交换等犯罪行为的产生。
4.3 对安乐死实施条件的限制
安乐死是非自然结束生命的方式,需要对实施条件加以限制。首先,必须是患者本人主动要求,在患者意识清楚的前提下,由患者提出书面申请,预防他人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患者生命而丧失保证生命质量的本意;如果患者处于无意识状态无法申请,可由3名具有主任医师资格的医师,对患者进行诊断有无恢复的可能,也可以由近亲属商定一致后提出,申请采取消极安乐死的方式[7],避免利害关系人因担心患者病程拖累家庭而违背患者意愿选择安乐死。其次,患者必须在精神和情绪稳定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8],避免患者因冲动或者其他精神因素的影响随意作出的决定。另外,必须经过严格的医疗检查证明患者正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且死亡无法逆转[9],如诊断无效,且当前的技术措施无法减轻患者生理痛苦和精神压力,其方法从伦理上看是妥当的,才可实施安乐死。
4.4 对安乐死程序的限制
安乐死决定书必须包括家属签字、诊断证明、相关治疗措施记录、主治医生签字、专家会诊意见、伦理委员会意见,决定书由当地主管卫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审查。医院成立相应的安乐死鉴定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有很高职业道德和执业资历,以保障对医生的诊断鉴定的高效性和准确性,确保安乐死不被滥用。法院可成立安乐死审查庭,专门受理安乐死的相关审查程序和继承权利的处理。在实施安乐死之前,由主治医生填写四份患者健康状况鉴定书,并附有患者或者家属签字的申请安乐死决定书。四份表一份由患者家属留存,一份由公证机关公证,一份由医院留存,一份有司法机关备案。获得卫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一致同意后,由主治医生在伦理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实施。
[1]刘建利.死亡的自我决定权与社会决定权——中日安乐死问题的比较研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5):62-71.
[2]周丽昀.安乐死的原本意义与现代意义之争[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9-104.
[3]李长兵,彭志刚.论刑法对医疗技术革命挑战的立法应对[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3(4):56-62.
[4]王瑀.生命权与安乐死出罪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2):84-87.
[5]沈婉婷.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正当性分析及其路径选择[D].西南政法大学,2012.
[6]李琤,邵军.对癌症患者过度医疗的原因与对策探讨[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3):349-351.
[7]王晶.从安乐死问题浅谈生命权入宪[J].思想战线,2013(2):44-45.
[8]刘泽刚.宪法生命权的界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3):3-10.
[9]刘三木,汪再祥.关于安乐死的若干争议问题之讨论[J].法学评论,2004(6):95-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