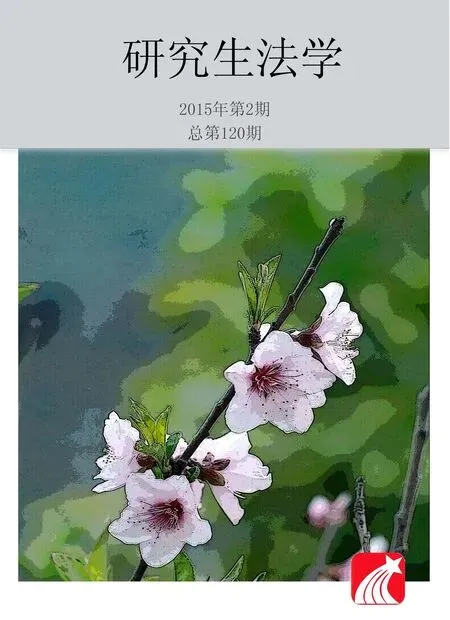功利主义抑或契约论——读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中有关司法的起源
2015-02-12赵英男
赵英男
在《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一书第二编中,波斯纳法官提出了以经济理论效率分析为基础的国家起源解释,以此挑战霍布斯以来的社会契约理论。〔1〕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由此,波斯纳法官将契约论与经济分析论调置于彼此矛盾的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或制度起源之解释学说历来纷繁复杂,虽然彼此或有攻讦,但未必针锋相对。〔2〕在此,笔者的观点可以进一步明确为,不同学说理论传统对于人类国家、法律起源这一事实的解读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性质的。因而虽然诸多学说彼此或有矛盾,但并不必然是相互替代、非此即彼的关系。很有可能是各个学说理论的“辐辏”构成了有关国家起源的完整认识。对此问题将在本文第二、三部分进一步阐释。有关不同的国家起源或制度基础的学说请参见[美]夏皮罗:《政治的道德基础》,姚建华、宋国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页。在本书中作者提供了有关制度基础的多种学说,包括古典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契约论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理论不同但并非对立。由此我们需要厘清,(一)在哪些方面波斯纳法官提供的经济学分析与契约论对于国家起源的解释构成了冲突;进而(二)这些冲突是否意味着经济学分析更具有说服力,或构成了对于契约论的替代。在明确两种学说的理论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尝试比较契约论进路下(实证法)与波斯纳经济分析进路下(习惯法)法律概念选择的特点。
一、经济分析理论vs.契约论
(一)波斯纳版本的国家与法律起源
波斯纳法官的研究方法有些近似于《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恩格斯的方法,他以荷马史诗为蓝本,分析其笔下古希腊社会作为初民社会/国家的特征,以此历史“事实”反驳契约论的理论“玄想”。在对于荷马笔下古希腊政府的描绘中,波斯纳法官提出:
真正的有限政府只有一个职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保证身体安全。对内的一方面是要保证个体的人身和财产不受谋杀或偷盗这样的强迫性入侵。如果没有某些最基本的对内公共秩序,社区福利就会衰落。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国家,人们就都成了杀人狂,就会相互厮杀和偷窃……从原则上看,对外安全也可以留给私人领域,但一般都认为由国家提供更为有效。这种国家职能的逻辑延伸就是掠夺其他地区。〔3〕[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以此,可以看到波斯纳法官反对契约论的两点核心主张:(1)前社会契约状态并非是契约论特别是霍布斯契约论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2)国家的终极目的并非在于保证国内安全维护社会秩序,而是保护社会免受外来入侵。在此基础上,波斯纳法官进一步细化了他的论证。
就命题(1)而言,波斯纳法官承认了荷马笔下古希腊政治制度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政府能力太弱以至于无法发挥有效的管理职能;同时它也无法解决最高权力的接续继承问题从而引发了持续的战乱。〔4〕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此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政府存在着结构但却没有功能,〔5〕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许多职务是荣誉性的而非职能性的。〔6〕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法律并非依赖于国家的暴力,而是依赖于习惯。习惯得以被遵循端赖于它可以满足社会的需要。〔7〕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波斯纳法官敏锐地把握住契约论核心观点加以反驳说,在已然成为国家的古希腊社会,于荷马笔下他看不到任何“公民德性”的价值存在。〔8〕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在战争中无论是参与的将士还是对之作出分析的荷马本人,都未将战争理解为一种组织化的冲突,而是将之视为一种个人荣誉的混战。〔9〕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针对以上所列举的古希腊国家/社会的缺陷,波斯纳法官对之作出了两个断言。其一,他认为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状态是混乱的,但这并不构成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因为这一社会体系中存在着调节人与人交往的机制,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10〕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其二,通过以史实列举“公民德性”的缺乏,反驳了契约论所认为的由自然状态向公民状态过渡的逻辑转变过程。接下来,波斯纳将以上命题(1)与命题(2)联合起来从正面加以证立。
首先,他提出了在初民社会中社会秩序的调节机制。他认为,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在于防范乱伦和抵抗抢劫者。对应的解决方法分别是与其他家族成员通婚以及亲属结盟。〔11〕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这两种形式得以贯彻的核心在于礼物交换。礼物交换意味着交换双方信息的流动(彼此财富多少、在战斗中是否英勇顽强)同时也具备道德评价的涵义(缺乏礼物交换的部落是野蛮的)。〔12〕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其次,与礼物交换这一机制相配合的是社会价值系统,比如社会成员好客、喜好荣耀等等。〔13〕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这就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近乎于平等的彼此交换网络,社会秩序借此机制得以协调。
但波斯纳承认,这一机制所达到的平衡是脆弱的。因为一旦一些家户发现了如何把自己组织成国家的时候,其他分散家户的成员就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他们不再能以对侵犯自己利益的人做出令人信服的报复威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此时国家就要回应外部的安全问题。〔14〕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在此,波斯纳证立了他所提出的两个命题。他总结道,契约论观点认为国家是解决内部安全问题的办法。这种说法意味着,世界上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15〕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但他的分析有力地反驳了这一点。
(二)契约论模型
波斯纳在其分析中并没有给出有关契约论的完整图景,这不仅让契约论在其攻击下显得支离破碎,也使得波斯纳本人的论述凌乱琐碎。〔16〕当然,这未必不是后现代法理学的一个特征。See Gary Minda,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s:Law and Jurisprudence at Century’s End,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6,pp.84 -88,237.为了彰显波斯纳经济分析与契约论之间的差异,在此有必要略微梳理一些契约论的基本观点——当然鉴于该传统源远流长,在此只是给出一个模型化、脸谱化的简要分析。
契约论能够进入现代政治理论视野端赖于霍布斯的开创性著作《利维坦》。〔17〕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红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394、398页。在该书中,霍布斯认为,国家的诞生源始于自然状态向社会的过渡。〔18〕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9、132页。这一过渡不仅是可能的还是必要的。说其必要,是因为自然状态下人们彼此相残,为了自我保存而不得不达成契约,将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与主权者。说其可能,是因为人们受其欲望支配,自我保存的欲望与对死亡的恐惧构成了臣民对于主权者的服从。〔19〕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3~139页。但霍布斯理论的一个核心矛盾在于,既然他认为国家的诞生是为了保存个人的生命,那么个人生命在受到威胁时就有权利撤回对国家权利的让渡,也即放弃对社会契约的参与。〔20〕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9页;See also Susanne Sreedhar,Hobbes on Resistance:Defying the Leviath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81 -84.从这一角度而言,依据霍布斯社会契约建立的国家并不稳定。
继续霍布斯的思路,洛克与卢梭在两个方向上不同程度修正了霍布斯的理论。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下远非霍布斯所言必然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21〕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78页。国家应当保护臣民的财产权力。〔22〕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95页。卢梭则走得更远。他提出,自然状态下的人孤独索居,是社会与文明造成了人性的堕落。解决之道不在于回到自然状态,而是通过社会契约,所有成员让渡其所有的权利形成公意。〔23〕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19、25~26页。这也就意味着参与社会契约的所有成员既是立法者,同时也是自我立法的服从者。在这意义上,公意使得每个人获得了“自由”。〔24〕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41页。但值得注意的是,卢梭的理论既可以理解为激进的民主观点(每个公民都是立法者);同时又可以被视为是极权暴政的背书(个人因公意而得自由)。因而,其契约论依旧存在着缺陷。
在经典理论家之后,契约论又有诸多变体和更新,比如康德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的自然状态向公民宪政状态下的过渡,罗尔斯于《正义论》中提出的“原初状态”下的正义原则选择等等。但无论怎样都可以看到契约论(1)拥有一种作为前社会或前文明状态的“自然状态”;(2)“自然状态”的设定服务于理论构建的目的——霍布斯需要以社会替代上帝的位置,而认为社会的秩序高于自然状态中的混乱;卢梭出于批判社会、颂扬人性的目的提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社会的)枷锁之中”。因而二者对于“自然状态”的设定完全不同。而在这意义上,(3)契约论的基础是社会理论家对于现代人的人性假设与伦理预判。
在这一伦理意维度上,我们再理解霍布斯为什么将其“自然状态”设定为战争状态,就会发现他所提出的不仅仅是一种建构理论中的玄思冥想,而是道出了一种在现代社会平等状态下根源于人性的内在冲突。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重新回到“自然状态”中,在此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孤立而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是平等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如此,而是因为他们都一样地受到死亡的威胁。死亡的夷平效果构建了一个心理上平等的“空间”。〔25〕参见李猛:《自然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9页。在此空间中,人的幸福源自于同他人的比较。在激情欲望的驱使下,人由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这样,在人与人之间自然平等与力量比较之间就存在着固有冲突,而且这一冲突是无法化解的——正是因为人与人是自然平等的,才有了比较的前提和可能性;正是因为比较导致的不平等,进一步刺激了对自然平等的需要。〔26〕参见李猛:《自然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8页。因而,这个“空间”虽然平等但并不静止,而这种不静止性的突出表现就是战争。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契约论(4)虽然目的是分析国家与社会的诞生问题,但从伦理角度上理解,它的描述与预设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现代人的特征。通过总结以上有关契约论的四点性质,会发现契约论主要是一种理论设定,它与实际历史进程有所不同。因此可以认为,波斯纳从历史角度进行的经济学分析,虽然结论与契约论不同,但不构成对于契约论的实质性反驳。那么,经济分析理论与契约论是否就没有冲突的可能?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讨论二者之间有差别才是有意义的?
二、正当与善的争论
在以上的讨论中,本文开篇已然提出波斯纳认为经济分析理论与社会契约论处于一种对立之中。但在有关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与契约论的对比中,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波斯纳的理论与契约论并未构成实质冲突,是因为两种理论脉络一个偏重于假想,一个偏重于历史实际。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也是片面的。因为社会契约论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假想,它同时也经历了一场“历史化”的运动。
理解这一进程,就需要再从卢梭入手分析。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卢梭与霍布斯对于自然状态的假设是相反的。卢梭反驳霍布斯的关键一点在于,他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设中存在着太多的“社会”成分——是社会而非人本身导致人与人之间彼此陷入战争的状态。在这一理论下,卢梭眼中的自然状态并非如霍布斯笔下的前社会阶段,而是一个人逐渐败坏的过程。〔27〕参见李猛:“在自然与历史之间:‘自然状态’与现代政治理解的历史化”,载《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第69页。换句话说,自然状态下的人的逐渐败坏的历程就是社会得以展开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解释人从善到恶蜕变的“自然中人的历史”。〔28〕参见李猛:“在自然与历史之间:‘自然状态’与现代政治理解的历史化”,载《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第69页。通过社会契约形成公意,使得每个人得以自由则是对这种“恶”的救赎,而救赎的结果则是重返如同自然状态中一样的人的“善”。这就意味着自然状态由单纯的理论假设转变为了社会的“史前史”,是理解当下社会处境不可缺少的一环。
因而,理论假想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区分并不构成对波斯纳所认为的两种理论脉络处于冲突这一观点的反驳。也即,虽然彼此分属于不同的思想脉络之中,契约论和经济分析依旧存在彼此对立的可能性。因此我们需要确定的是,二者在什么情形下的对立才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就仿佛是如下这个例子:水与火是对立的,但我们可能没有必要在普遍意义上确定地辨析出水与火孰优孰劣。只有在火灾或者干旱的具体背景下,水与火的对立才成为了一个真的问题。契约论与注重效率的经济分析也有这个特点。
使得二者之间的对立有意义的讨论背景则是国家根本制度设计中正当(right)与善(good)的关系问题。所谓国家根本制度指的是宪法法律以及重要的经济社会安排体制。〔29〕在这一点上,笔者采纳罗尔斯于《正义论》中关于根本制度的观点。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而正当指的是社会对于某一行为的道德评价,善指的是物质或精神利益。我将从正当与善的关系出发,再次将两种理论脉络划分开来。
就波斯纳主张的经济分析理论而言,正当与善是彼此分离的,并且他将正当视作为善的最大化。这就意味着(1)何物为善并不需要以个人或社会的权利/正当加以限定。(2)从目的论出发,认为效率或功利是一种值得欲求的善,而效率或功利的最大化就是正当。〔30〕在此有关效率利益的理由分析参考了罗尔斯的有关论述。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1页。而就契约论来说,何物为善需要受到权利/正当的限制。也即,权利/正当给个人限定了某一范围,在此范围内个人选择他们的目标作为一种善。而这一权利/正当来自于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彼此约定。具体而言,就财富来说,经济分析理论效率进路可能认为“多多益善”;但契约论,特别是康德或罗尔斯的版本,会认为“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简单来看,以上两种理论其实都存在缺陷。经济分析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效率或功利的最大化就是可欲求的。这一预设其实具有任意性。我们的生活需要效率,我们也不反对功利,但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有必要最大化却是值得怀疑的。而契约论无法解决的问题则是,社会成员是否真的会就某一种权利或正当达成一致接受其约束?这种约束是否会造成一种极权主义(总体社会)?
但无论怎样,这些问题不是本文的核心。在此我们的核心关切是,通过对比两种理论对待正当与善的关系的不同态度,我们锚定了为什么波斯纳笔下这两种理论注定是一种矛盾——因为二者其实分别构成了现实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评判各种制度的判准——这一判准可以是功利主义式的,也可以是代表着契约论的“公平的正义”式的。
在这一背景下,讨论经济分析与社会契约论之间的矛盾才是有意义的。这恐怕也是波斯纳法官的本意,因为在他笔下契约论传统从霍布斯以降,直到诺奇克,在这一传统中不是每一位理论家都热衷于国家的起源,有相当部分的理论家关注现实制度的建构,比如罗尔斯与诺奇克。〔31〕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该书中诺日克应为诺奇克(Nozick)。
但这种矛盾是否导向了一种“一蹴而就”式的结论,即经济分析是否必然优于社会契约论或者相反,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首先,二者可能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其次,二者有可能都基于某些方法论上的设定而使得结论虽然有异,但在逻辑上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就第一点而言,这是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有关正义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争论的焦点。而就第二点,在本文第三部分将要从法律这个具体的概念分析入手,对之加以呈现。
三、法律的概念
回到本文第一部分的末尾,波斯纳所提供的经济分析版本的国家起源,使得他所描述的法律的概念必然是一种习惯法意义上的法律——没有国家又何以有制定法?〔32〕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波斯纳指出,“支配了初民法律的,就是习惯……习惯就像语言一样,是个复杂的、变化缓慢的、高度分散的精确地规则系统。这些精确的习惯规则是对法官通过创造先例而特定化的广泛标准体系的一个替代”。而某种意义上契约论中所分析的法律概念更侧重于实在法。〔33〕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实在法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实证主义。法律实证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坚持“分离命题”,即法律与道德是两个问题。请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李冠宜、许家馨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180页。契约论中法律的创生源自于自然权利让渡达成的社会契约,在一些理论家比如霍布斯笔下,法律具有较强的实证主义色彩。但在康德的笔下,自然权利(道德)会成为法律是否有效的判准。请参见[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张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250页。因而笔者使用“实在法”这个词,以强调成文的、国家制定的法律。如果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是政治哲学理论上的抽象讨论,本部分将进入法律理论层面分析法律的概念问题。这一分析将会呈现出如下结论,即契约论与经济分析理论在具体的制度评判上是相互冲突的,但他们共享了一套逻辑预设。
我们首先需要分析的是法律概念的来源。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分析的是概念的来源而非法律本身的来源。所谓概念的来源问题,解决的是针对一种现象理论家对之加以描述、概括的方法。而法律本身的来源则相对为人所熟知——理性发现、神创或主权者命令等等都是法律的来源。〔34〕同样需要细加分辨的一个问题是法律的来源也不同于法源或法律渊源,后两个词汇约定俗成表达的是法律的表现形式。
就“法律”这一概念而言,不同的法学理论家,特别是描述性法理学的理论家虽然都使用这个词汇,但却赋予这一词汇不同含义。但无论他们之间有何不同,他们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和方法都是相似的。就目的而言,他们可能主要是描述那些涉及到纠纷及其解决、规范的遵循/违背、惩罚等现象。〔35〕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理论家,比如德沃金,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旨在描述法现象,而是提供一个判准来识别什么是法律(论证法律的有效性基础)。请参见德沃金有关“哈特后记”的批判,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著:《身披法袍的正义》,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211页。也有一些理论家,比如凯尔森,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分析而非描述。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5~246页。但本文在此意在强调这些法律理论的构建都旨在使理论概念能够涵摄涉及到秩序、纠纷、规范等问题的现象。也即,通过概念指称这些社会事实。在此意义上,虽然不同理论家旨趣(构建理论的目的)不同,但可以说他们使用概念的目的都是一样。就方法而言,他们将以上诸现象中的某一种划归为法律这一概念的“核心涵义”,而将其余现象划入概念的“边缘情形”之中。〔36〕持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是哈特,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李冠宜、许家馨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125页;参见[美]比克斯:《法理学:理论与语境》,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但是,在何种标准下理论家选择某一现象作为概念的“核心涵义”是合适的呢?就韦伯看来,这种标准可能是不存在的。因而,理论家的选择也就是相当主观的。〔3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在本书中描绘理想类型方法论的段落中,韦伯提出了任何一种理论认识是无法摆脱主观因素的。这一过程也是菲尼斯于《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中的分析,“描述性理论家选择概念,然后用它们来对中心情形进行描述,接着对作为特殊社会制度的法律的所有其他情形进行描述……”〔38〕[英]约翰·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董娇娇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而这种方法引发了菲尼斯的疑问,“(这一过程)是否意味着描述性法理学必不可免地受每个理论家对什么是善和实践上合理的这个问题的设想或者偏见的制约”?〔39〕同上注。这个疑惑与描述性法律理论的本旨有关。所谓“描述性理论”指的是理论家关注行动者实际对待法律的态度。比如一个行动者是将法律视作行动的准则,还是视为对于投机行为后果的预测标准,这是秉持描述性理论的理论家所需要加以区分的。在此区分的基础上,他需要将某一类态度归为“法律”的核心涵义。而这一“归类”的判断在菲尼斯以及韦伯看来缺乏客观的标准,会受到理论家本身的认识条件制约。
在此,再度思考契约论所偏重的实在法概念与波斯纳于经济分析中所倚重的习惯法,当然两个“法律”所指涉的实在完全不同,而且波斯纳也并非是满足于描述性理论的法学家,〔40〕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波斯纳指出,经济学的解释力是独立于经济活动者的清醒意识的。可见,他拒绝相对诠释性的、主体视角化的“描述性理论”。也即,波斯纳并不关心行动者在施行社会行动时的自我态度。但这两个“法律”概念被使用的方法却是一致的:即理论家将某一类现象划入这一概念之下,进而对之展开分析。“描述性理论”所面临的质疑同样会在波斯纳的经济分析理论中出现。这一论断在波斯纳对法律概念的分析中更为清晰地表达了出来。他指出:
……支配了初民法律的,就是习惯。正是习惯规定了因杀了某人而应支付的赔偿、指定合同的手续、继承的规则、亲属关系的责任、结婚必须遵循的限制以及其他……这些精确的习惯规则是对法官通过创造先例而特定化的广泛标准体系的一个替代。……一个规则越是精确,它就越难顺应变化的环境。因此,我们也就可以预料,一个由精确规则构成的体系会提供某些方法来迅速修改规则。习惯法体系没有这样的方法。但是,在一个禁止社会这并不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41〕[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从上揭引文中可以看出,波斯纳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完全重新定义了“法律”概念,使得这一概念主要“对焦”于习惯法本身。而这种理论方法其实也就是波斯纳对于法理学经典问题——习惯法是否属于法律(制定法)——的隐秘回答:习惯法当然是法律,但在此时的法律出于分析初民社会的需要,其核心涵义已经不再是由国家或主权者命令构成的制定法而是经由日常习惯形成的规则。就我们借以认识对象的媒介——概念而言,其所涵盖的实在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无论是契约论角度还是经济分析方法,二者虽然观点相异,但都分享了法律概念运用上的这一任意性。它们各自选择了一些现象、事实作为理论的解释重点,但同时又忽略了一些现象、事实。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讲,每一种“洞见”的背后都是一种“不见”。〔42〕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三讲题目“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因而,可以说契约论与法律经济分析这两种方法虽然观点往往相左,但我们无法一蹴而就地判定孰优孰劣。我们需要的是在具体情境中加以选择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