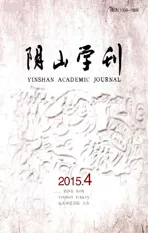挣脱桎梏,追求自由
——论《天香》中女性乌托邦的建构*
2015-02-12储阿敏
储 阿 敏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挣脱桎梏,追求自由
——论《天香》中女性乌托邦的建构*
储 阿 敏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王安忆的《天香》描画了一幅明清时期世外桃源图景,更重要的是发出女性主义与女性意识的呼喊。小说通过对各类女子形象的描写,解构传统的男权社会,关注女性精神的解放,为女性的未来勾画出理想的乌托邦世界。探讨乌托邦精神和女性主义的关系,并从王安忆创作意图出发,见出《天香》在女性文学中的特殊价值与重要意义。
乌托邦;女性主义;颠覆男权;女性声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意识萌芽,经由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倡导,女性意识被大众接受并认同。自此,受到西方女性文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作家不同程度地将目光放置在宣扬女性主义和女性意识的创作。有别于传统意义上托马斯·莫尔虚构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理想的美好世界,女性乌托邦重在文本中建立一个平等、民主、富有人道主义的以呼吁女性自尊、独立为目的的理想世界。“女性乌托邦小说创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千年圣殿》。”[1](P164)它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背景,体现了对男权社会的抵抗,也说明女性主义在长期的文学话语中虽被重视,却未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应得的价值与影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常态背景之下,女性主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天香》表明王安忆对于女性和乌托邦关系的热情关注和勇敢尝试。王安忆将故事背景设定为女性意识处在荒芜愚昧的明清时期,并在笔墨处全力构建以女性为主导的与实际文化背景背道而驰的世界,不得不说是对中国自古以来男权意识的一次全面颠覆。
一、抵抗男权的叙事策略
(一)解构男性至上的性别意识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人的性别认知并未在出生时就被主体正视,而是在今后的生长环境中由父母、老师、朋友等被告知性别差异,指导性别行为,形成性别意识。[2](P9)女性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生理等的影响,被社会认定不如男性,被迫遵守男性社会创造的游戏规则,这也是女性自从认识自身以来产生自卑心理、盲目崇拜男性的根源。
《天香》塑造的人物表面上看存在性别差异,实质上男女同性,有力地打破了性别观念。希昭于观音日在杭州一大户人家诞生,得观音恩赐天赋非凡、样貌出众,却拥有一副男人面相。阿潜自幼命途多舛,得到大伯母小绸的悉心照顾,故长得眉清目秀,性格温顺,具有明显的女性倾向。这两个人物的性别界限模糊,男性与女性的特征展现在同一个个体中,两者的婚姻结合更证实了王安忆有意拆解常规的性别认识,说明男女在未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前处于相同相等的地位,达到呼吁男女平等的目的。
申家第二代与第三代男性形象存在缺失的现象。镇海与柯海继承了申家第一代男性的生活习惯,一个出世,一个入世。天香园的故事就侧重写出世一方的后代,对于入世一方没作多少交待。一方面是违背男性竞争规则的有意为之,另一方面是突出出世一方虽然存在男人好强的天性,却没有能力使天香园延续繁华。镇海抛弃功名出家、阿昉抛弃功名开豆腐店;柯海与阿潜不爱读书,喜爱交游。虽然性别决定了他们应担负起传承香火与振兴家业的责任,却未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完成性别赋予的使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香园的女性大都拥有一门特殊技艺,凭借小小的女红就能够拯救天香园陷入衰败的境地。阶级观念在女性世界消失,她们都只为了绣而组成一个大集体,并使天香园名扬四海,重获昔日辉煌。男性并不一定强过女性的描述颠覆了男权话语,揭示传统的性别意识被消解。
王安忆对爱情婚姻的理解,打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观念。小绸与柯海两情相悦、情意绵绵,后经阮郎的牵线,柯海移情别恋娶了闵女儿为妾。小绸与闵女儿同是这场婚姻的受害者,却同时主动选择在精神层面抛弃柯海。自从娶了闵女儿,小绸决然不再与柯海见面。闵女儿意识到柯海对她没有真感情,只当她是佣人,遂也与柯海保持距离。名存实亡的婚姻让柯海饱受内心的煎熬,这显然是对三心二意男子的最佳惩罚。婚姻的失败预示柯海一家之主地位的崩塌,而后家中大小事都是由小绸掌管。女性从男人附庸品变成家庭顶梁柱,这种突破牢笼的女性意识是对夫权父权体制的强烈抵抗和控诉。
(二)建立和谐融洽的女性关系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又尴尬,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世界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正房与偏房、庶出与嫡出、小姐与丫鬟、婆婆与媳妇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关系,这种服务与被服务、欺负与被欺负的对立状态俨然能够谱写成一部勾心斗角、险象环生的女人争宠记。女人之间为何争宠?男人、金钱、地位才是女人一生要牢牢把握与苦苦追求的目标。《天香》的女性人物反其道而行,她们不仅与自己等级不同的女人成为知己好友,而且也挣脱了爱情婚姻的束缚,获得自主独立的生活。
小绸是柯海的妻,闵女儿是柯海的妾。小绸与闵女儿心意互通,一个擅长舞文弄墨,一个善于引线绣画,二者并没有为了争取得到丈夫柯海的爱而仇视憎恶,反因为爱好兴趣的相通成为好姐妹。与母亲地位相对应的孩子本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颉之、颃之和采萍之间却不存在地位高低的概念,她们都将对方看成自己亲密的家人、玩伴,互相照顾、相互学习。
戥子原是蕙兰母亲身边的丫鬟,后被蕙兰相中帮忙刺绣。“戥子”本是指金银、药材等贵重物品的微型称,引申为微不足道的人或事物。小说中戥子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吗?此言差矣!戥子地位低下,却敢与主人蕙兰顶撞,更敢向蕙兰提出传给她天香园刺绣技艺的要求。经过重重阻碍和困难,蕙兰终于答应将具有家族特征的刺绣教给戥子等外人,她们之间因为绣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名字含义与行为表现的相悖再次显示出王安忆的别具匠心,正是小人物身上具有更明显的自由自立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表现在她对于婚姻和男人的极度厌恶,也表现在她对不平等女性关系的质疑和抵抗。
蕙兰下嫁到张家生下灯奴后,她的丈夫和公公相继离世,哥哥与嫂子另觅去处。张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只留下年幼的灯奴、蕙兰和年迈的婆婆相依为命。为了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蕙兰同希昭、小绸一样凭借天香园的刺绣技艺担当起家庭重担。婆婆感激蕙兰并未改嫁,蕙兰也把婆婆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来赡养。二人相互怜惜,齐心协力将张家的血脉灯奴抚养长大,并让张家的境况日益好转。丈夫和儿子的角色体现在同一个男人身上时,往往会让两个女人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蕙兰本就与婆婆没有什么矛盾,当这个角色一旦缺失,两个女人只会更加珍惜对方,这是王安忆笔下融洽的婆媳关系。
二、呼吁平等的女性声音
(一)作者型声音
女性乌托邦文学的建构是由作家提起,通过作家的所思所想所感发出声音,然后将这种概念传递给社会。王安忆说:“我必须要着重地强调女性作家在新时期文学里的极其关键的作用。”[3](P174)这表明女性作家为了争取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必须凭借文学作品叙述自己的观点,表达女性主义的观念。作者型声音这一概念,借助了苏珊·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提出的“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概念而又有所不同。“作者型叙述被理解为虚构,但其叙述声音又显得更具有可信度。”[4](P22)
王安忆既是创作文本的人物,又是独立于文本人物之外的人物。作者型声音运用了全知视角的叙述,虽然没有经历真实事件的发生,却将文本中的背景、人物、情节用自己独特且乐意的方式刻画出来。王安忆曾经谈及《天香》的创作时,道出她用很长的时间才掌握了小说中展现的各种文化,如明清时期上海的“顾绣”、上海的园林建筑、民俗、音乐、书画、饮食等,为读者描画了一个庞杂丰富的图景。香花桥、法华镇、三牌楼路等地名再现了当时上海的市井,带有浓厚的历史感。明清时期的园林又以繁丽为主要特点,功能全、形式多,又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再谈到当时的婚俗,王安忆谨遵“媒妁之言”的规矩,由家里长辈为小辈物色合适的人选。天香园的绣融合了书与画的才气和美感,有别于一般的绣艺,呈现出大放异彩的艺术特色,具有非常高的遗承价值。
小绸、希昭、戥子、落苏、采萍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各具特色又有相似性。她们身上都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但是各自表达女性主义的方式却不同。小绸一类的正妻形象的女性意识更多的是展现在对男人失去依附性以及对男人决绝的态度。闵女儿一类的小妾形象的女性意识则展现在她熟练地掌握了独一无二的刺绣才能,冲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天香》的情节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在明清时期,女性拯救了一个个行将没落的大家族。情节的发展为主题的凸显铺设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明显的“绣”的线索,另一条是隐形的女性反抗男权社会的线索。为了建构一个以女性为主导,主张自由女性意识的理想世界,虚构的这些事物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王安忆“我手写我心”之才能的充分发挥。
(二)文本型声音
“我深知第三人称叙事的奥秘。第三人称……比第一人称‘我’能为她(叙述者)本人招来更多的现实感。这是用‘我’来言说所难以企及的。”[4](P161)作者赋予文本中的人物以生命,并依靠文本完成真实人物的虚构,推动故事的发展,突出故事的主题。这种文本声音又侧重在男女主人公身上体现出来,但是二者发声的目的都是为了表达女性主义。隐含在文本中的声音与被文本遮蔽的声音,都是作者表达声音的有效工具。
柯海与小绸刚刚成亲时,感情甜蜜稳定。柯海首先选择主动搭讪小绸,柯海问小绸乳名:“怎么叫你?”得不到小绸回答的柯海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怎么叫你?”“你娘怎么叫你?”“是我问你!”[5](P17)柯海对小绸充满了好奇,急于想知道小绸的名字,以拉近两人的关系。男性语言的典型特征是:“能动、直接、理智、强健、有力度、有效率、直率粗犷、有权威感、严肃实效、简明威严”。[4](P12)柯海的这一连串疑问具有明显的男权意识,是男人天性的使然,又刻画了柯海新奇、爱玩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导致了后来柯海陷于对小绸不忠的境地。
典型的女性语言应该是“温柔,富于情感与激情,说短道长,话多而不实在。”[4](P10)且看小绸回答柯海疑问时的反应。“柯海以为还是不答,不料那边的人脸一埋,被窝里发出瓮瓮的声音:你娘怎么叫你!那声腔有些耿。”[5](P17)小绸还未与柯海熟识,就反问柯海,说出如此大不敬丈夫的话语,以此抵抗柯海的男权声音。与传统的女性声音截然不同,小绸的发声充分体现了她是个不一样的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甚至对男性的不恭敬带有厌恶的情绪,浑身散发着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文本话语中刻画的人物性格为后面的故事情节作了铺垫,柯海一时头脑发热、移情别恋,企图想得到小绸的谅解,却不料被小绸毅然决然的态度伤害并一直带有愧疚的心理。如果小绸没有做出抛弃柯海的举动,那么柯海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错。影射到男性世界,他们认为自己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不会想到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对女性身心的严重伤害。小绸的声音既呼吁了女性主义,同时也启蒙了男性,消解了社会对男性以及男权的认识。
三、结 语
王安忆孜孜不倦地追求对精神家园的创建:“我追随这些思潮只是快乐的旅行,而我自己的朴素的观念则是我真正的家园。”[6](P10)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越来越强烈,直至建构了一个女性乌托邦。《天香》集结了众多的元素,历史与文化的集合,民俗与人情的集合,物质与精神的集合,集大成的作家风范让这部作品堪与《红楼梦》相媲美,让读者领略了来自古代的闺阁秀情,酣畅淋漓地接收到女性主义与女性意识的呐喊。
[1]佘立华.英美文学创作中女性乌托邦小说的解构分析[J].学术交流,2013(S1).
[2]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王安忆.女作家的自我,情感的生命[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4]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王安忆.天香[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王安忆.乌托邦诗篇[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张 伟〕
(英文摘要
Discuss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Utopia in “Tian Xiang”
CHU A-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Wang Anyi’s “Tian Xiang” painted a picture of a heavenly pla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more important is that the issue of feminism and feminist consciousness cries. Based on all kinds of women’s image description, the novel de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male dominated society, concerns the spirit liberation of the women, draws an ideal utopia for the female futur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irit of Utopia and feminism, and from Wang Anyi’s intention of writing,“Tian Xiang” shows special valu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female literature.
Utopia; feminism; subversion of male; female voice
2015-05-14
储阿敏(1989-),女,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004-1869(2015)04-007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