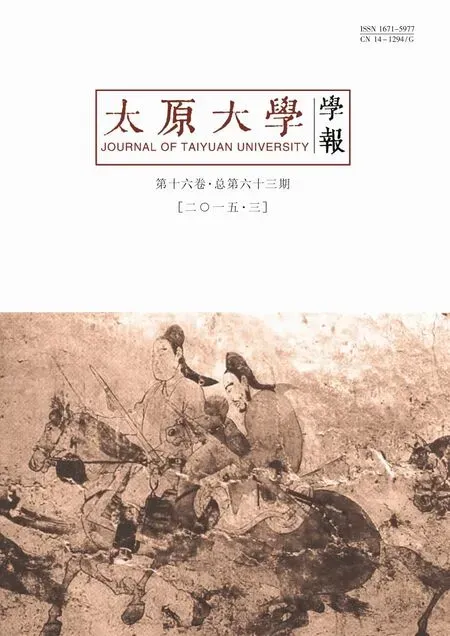生命的理想与超越
——论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中的个体成长历史反思
2015-02-11刘建军
刘 建 军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生命的理想与超越
——论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中的个体成长历史反思
刘 建 军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反思个体成长历史,她一方面反思先祖“英雄”成长历史,另一方面反思自身成长历史。在反思先祖“英雄”成长历史时,她认为先祖缺乏理性态度以及对道义与责任的担当,并以具有稳定的精神家园和和谐文明的生命状态为理想。与此同时,她反思自身的孤独与“无根”的生命状态,表达对允许较高精神境界和精神需求存在的物质生活的期待,以及对建立在优秀传统基础上的生命状态的期待。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生命;理想;超越;反思
王安忆对人的历史的审视表现为对先祖追逐王者身份的历程的审视和对自身成长历史的审视。作家将眼光聚焦于他人历史与自身历史中的一个方面:成长过程。她着意于成长中失败的一面,反思先祖的非理性的生存状态。她表达了建设文明而高贵、具有精神家园、与世界紧密结合的生命状态的愿望。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照她的反思态度,可以发现她所期待的事物其实就是先祖生命状态中所缺乏的事物。与此同时,王安忆又对自身成长历史中的孤独与“无根”状态进行了反思,并表达了对精神与物质和谐并置的、建立在优秀传统基础上的生命状态的期望。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理想生命状态就是一种能极大地满足精神需求、愉悦身心的生命状态。王安忆反思先祖“英雄”史和自身历史,是为了找到过去与现在的连接点,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未来幸福的祈愿。
一、面对“英雄”:在审视王者中期待文明与和谐
王安忆审视先祖“英雄”史,认为他们在追逐“王者”身份的过程中,缺乏理性态度,缺乏对道义与责任的承担。不仅如此,先祖过于追求物质欲望满足,而没有精神家园,并且刻意与世界为敌。王安忆在反思的同时表达了对文明与和谐关系的期待,并期待一种稳定的精神家园。
张新颖说:“《纪实与虚构》交叉写成长与寻根,客观上即形成两种生存的对照。”[1]471我认为这部作品以“寻根”的方式实现对个体成长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对于王安忆在这部作品中提出的诸如理想、生命、道义、责任等命题,都可以以“个体成长”作为一条线索去贯穿,从而能够以“对个体成长的反思”作为对这部作品主题的一种解读。王安忆追溯自己的血脉根源,并将一种强烈的英雄情结投射在先祖身上,渴望自己能是英雄的后裔,并力图在作品中将自己的先祖历史赋予英雄的色彩。同时,对先祖的“英雄”角色成长经历,作家能以理性的态度去回顾与反思。“英雄”成长经历作为个体成长的一种方式,与带有自传色彩的另一种个体成长方式作为作家对个体成长的两种向度的并列式叙述,同时构成王安忆对个体成长的观照系统,它们都体现了作家的理性态度与理想追求。正如王德威所说:“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共和国中的成长纪录,终于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活动的反省与反思。”[2]109但是,王安忆的反思的领域并不局限于自身创作活动,而是涉及理想与道义、生存与责任等诸多范畴。
王安忆反思先祖在追逐“王者”身份、“英雄”角色与最终成为堕民的过程中,在处理个体生存、发展与所背负的道义、责任之间的冲突时的非理性态度,崇尚一种建立在文明信仰与和谐关系基础上的高贵、强有力的生命状态。在这里,个体成长的表现是从英雄到堕民的过程,是英雄的失败成长史。王安忆饱含热情地叙述了先祖颇有英雄色彩的金戈铁马的征战生活,正如王德威所说:“王安忆的想象驰骋在历史荒原上,历经木骨闾、车鹿会、成吉思汗、乃颜等辉煌时代,堪称‘考证’细密,臆想淋漓。”[2]110但这并没有减弱作家对先祖“英雄”成长史的反思力量。在《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在多处以冷静的语气表达了自己反思的态度。“他们的背信与挑衅,与强大的拓跋魏仅是一个虫蚁般的骚扰,他们内部分裂,头脑简单,缺乏战略战术。”[3]90这是对先祖缺乏道义的反思。“我祖先柔然是在一个单纯凭武功决出胜负的人类早期历史中兴起的,当历史走向文明期之后,我的祖先们便理所当然地退出了舞台。”[3]165这是对祖先缺乏文明与教化的反思。“草原上因为抢劫马匹、械斗身亡的事件屡见不鲜,和解、惩治的方法千千万万,何况安答和安答之间,更要互相谅解,彼此相让。”[3]67这是对祖先缺乏和平精神的反思。“照理说,他们应该负起汗室的责任,开怀大度,抚恤臣民,不让族中任何一个人受欺伤心。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3]167这是对祖先缺乏负责任的胸怀的反思。“英雄”的失败成长史与堕民的身份形成史因果互应,我们可以看出,对他们失败的成长史的反思中,王安忆的主要指向是他们对道义的背叛与对责任的放弃。在作家带有深厚情感的追溯性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她并没有因为“英雄情结”而使自己的情感带上“英雄史观”的意味,去歌颂英雄对于世界的决定力量和业绩,而是以一种理性的客观的态度去叙述和反思。这种叙述也不同于新历史主义小说对历史带有自然主义意味的叙述。曹文轩说:“新历史小说则将所有的人物首先放置到‘吃喝拉撒睡’的琐碎的平常状态,让他们再也无法雅致,无法产生英雄气概,从而也使阅读者在面对这些先人时再也无法产生英雄感。”[4]296王安忆带有深厚情感的叙述与她理性的反思态度并不矛盾。正是对先祖的深切热爱使作家以负责任的态度观照他们的成长历史,并反思他们的失败成长经历,从而以理性态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体现出王安忆对先祖在文明与和谐的追求中失败和沉沦的失望,希望在文明与和谐的基础上建立“王者”般的高贵而强有力的生命状态。
王安忆反思先祖在频繁流徙的生活中过于追求欲望满足的生存状态,期待一种建立在稳定的精神家园之上、与世界紧密结合的生存状态。新时期小说中有以欲望为叙事主题的现象。比如,余华的《兄弟》中的李光头、林红、宋钢等人对金钱与欲望的追求,小说叙述由此导致的生命状态的恶化:宋钢精神与身体的分裂与走向死亡、林红美好人性的丧失、李光头游戏人生。方方的《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写武胜松对婚外恋情的新异刺激的迷恋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无着状态。莫言的《丰乳肥臀》中一系列具有抗日分子与土匪双重身份的人物追逐权力与性,这是用血与火去挥霍生命的幸福感。曹文轩说:“在文学界普遍认同‘人性是最为根本’的思想、认为文学的最深(也是最后)的层面便是人性之后,新历史小说非常自然地找到了‘阶级斗争’的替换物,这便是‘人的欲望’。”[4]286曹文轩指出了新历史小说欲望叙事的特征,这也体现在以上几篇小说中。新时期小说在叙述人物的欲望追求史中多具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意味。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同样如此。王安忆在小说中对先祖追逐权力、金钱与性的生活状态是持一定程度的批判态度的。因为批判的是与自己有血脉关系的先祖,所以因感情与身份的因素而具有反思的性质。她的叙述表明先祖的奋斗史就是欲望史。先祖为了欲望的奋斗导致了家族成员的生离死别,骨肉分离,同室操戈,流徙不定。他们在伤害他人的同时也自我伤害。
没有固定的精神家园可供后代休养生息,没有与世界保持紧密结合的状态,漂泊成了世世代代后人的生存状态。王安忆以此表达自己对建立一种有稳定的精神家园,并且与世界紧密结合的生存状态的期望。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精神家园”是湘西世界,翠翠独守河边,萧萧回归夫家,无论是翠翠还是萧萧都是一种包含了深刻的文化精神家园的主人,也成为沈从文精神家园的构成因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叙述:“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5]277沈从文的精神家园追求以“人性和谐美”为特征。王安忆追求的精神家园是建立在对先祖漂泊生命状态的反思的基础上,以与世界紧密联系为特征。与沈从文相同,王安忆追求的精神家园也是具有“和谐美”的特征的。这种追求不仅体现在《纪实与虚构》中,在《长恨歌》和雯雯系列小说中也有体现。如果说《长恨歌》是一幕戏,那么主角王琦瑶与众多的配角演绎的就是美与青春战胜丑与腐朽的过程。雯雯美妙的心灵世界是雯雯的,也是王安忆的。王安忆以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寓示自己的追求:建立一种具有有力的、深刻的灵魂美与实体美的精神家园。因主体的生存摒弃了漂泊流离、现实的平庸琐屑,这种精神家园达到了稳定状态。
二、面对自我:在缓释孤独中溯源彼岸
王安忆在面对自我时有更深的内心体验。对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作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观照。这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而从“无根”的心理状态转向积极地建构身份根柢,这体现了作家实现自我超越的愿望。建立在物质和精神和谐关系以及优秀传统基础上的生命状态成为作家的期待。
王安忆反思自身在失却和谐生活环境时形成的孤独状态,表达对建设一种允许较高精神境界和精神需求存在的物质生活的期待。戴锦华说:“《纪实与虚构》……其意义不仅在于它以女性自传与男性英雄的历史的并置打破了经典的等级制,不仅在于她于这一并置中呈现了女性在文明中的地位,而且在于她在这一特定的寻根写作中,不期然地揭示了整个80年代寻根及历史反思运动中不言而喻的汉文化中心主义倾向。”[6]234戴锦华是以女性地位和文化历史的多重视角观照《纪实与虚构》这部作品的,其中“女性自传”部分即王安忆在作品中对自身成长历史的回顾,当然在这种回顾中,作家表达了自己的反思态度。我认为这部作品有一种揭示人的生存状态的孤独性质的主题,作家采取的是个体成长与孤独相克相生这一视角。如果说整个作品都在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一系列问题,那么这个从源头到方向的整个成长过程中的孤独感是王安忆生存状态的一种特点。在《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这样叙述:“我有时觉得我也沾染上了他们的坏毛病,我会有疯狂的念头涌上我心,我的心脏常常无来由地加速跳动。我是那样无可解释地孤独,我有时不知在想念什么,心里非常忧伤。我很小的时候,一觉醒来,就感到四下里茫茫然,不知身在何处。”[3]268除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外,王安忆还曾说到下放生活中的孤独感:“我在个人的小圈子里,和我生存的环境联系,我插队到安徽是一个人,我老是处于一个个人化的处境里边。”[7]35在另一部作品《姊妹们》里,她表达了自己与乡村生活的隔离感:“它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它世故的表情隔离着我的心。”[8]227互为因果的忧郁和孤独形成了王安忆的生存状态。她反思了自身的理想的力量的匮乏,理想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孤独感。理想的力量不足是因为在插队生活中缺乏理想或者为理想奋斗的精神不足。作为插队知青,王安忆在仅能依靠几本外国书籍充实心灵的情况下,精神的疲弱是可想而知的。幸好她有写小说、写日记的爱好,她得以取得生命的支撑。作家在《纪实与虚构》中写到爱情经历时,回顾了自己的婚姻生活:“我们在这世上,所能缔结的深刻关系,只有这一桩了,而这一桩关系最终依然使我们孤独。”[3]268作家对婚姻生活中因争吵与分歧而产生新的孤独感与插队生活中的孤独感表现相同,实质不同。前者是个体成长面临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哲学困境: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后者是个体成长的力量与要求之间的对立。王安忆反思了精神和物质的对立造成的理想遇挫的现实状况。戴锦华说:“王安忆开始治愈,至少是开始正视她对理想主义无尽的饥渴,以及因理想主义匮乏而产生的深刻的焦虑与自卑。”[6]219实际上,王安忆在作品中叙述的她与孤独抗争的种种努力,都是向理想生命状态接近的尝试。无论是“焦虑”还是“自卑”都将消解在一种对生命状态的理性思考之中,都将消解在努力建设理想生命状态的实践中。王安忆保存理想精神的火种,试图融化处于坚硬状态的生活的物质坚冰。也许,这是一个永远延伸的不可终结的过程,但是它没有西西弗斯的带有悲剧意义的行动的冷酷面目。希望其实就在身边,它融化在孤独状态向和谐状态运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王安忆反思了自身身份历史的“无根”状态,表达了对建立在优秀传统基础上的当前生命状态的期待。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表达了一种“无根”的焦虑。张新颖说:“无根的焦虑好像是个人的,作品也是从此出发:在上海,她是外乡人,是随着革命家庭一起进驻城市的,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渊源,没有亲戚串门和上坟祭祖之类的日常活动。”[1]469可以说,王安忆“寻根”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王安忆的自我发现开始是带着伤感的情绪色彩——她自觉是“孤儿”,并被孤独感和“无根”感包围。后来她开始转向积极地建构,并在这种建构中获得了梦想中的满足。张新颖在论述王安忆的创作时说:“虚构一个世界与当下世界相对照,满足一下人生的各种梦想,尤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病。”[1]472其实王安忆的虚构并不是这样。因为这种“文化病”状态是一种虚幻的满足,而王安忆“寻找起源”的梦想则具有现实的构成因素,那就是“优秀传统”,其表现除了“英雄”家族神话中先祖的刚烈与勇猛的精神血统与基因外,就是革命家庭的精神熏陶与文化“贵族”般的社会关系因袭。王安忆希望通过建立在优秀传统基础上的身份历史起源,实现一种理想生命状态的精神意义上的建构。
八十年代小说出现“寻根”主题。张承志《北方的河》中有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力与美的赞叹,这是寻找“力与美”的“根”的作品。在韩少功的《归去来》中,有原始性文化的朴素、自然特征的描述,这与现代文明的象征的“我”的造作、虚伪形成鲜明对比,作家借此表达寻找“原始与自然”的“根”的愿望。作家对“根”的寻找往往寄托了自己的某种愿望。王安忆也不例外。但她在《纪实与虚构》中对自身身份的“根”的寻找有别于张承志、韩少功等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寻根”。因为张承志、韩少功等作家的寻根视角是包括传统、现代在内的诸多领域,具有外倾性;而王安忆的寻根视角是自身身份历史,具有内倾性。她努力通过对生命之根的寻找改变自身城市“孤儿”身份,努力消解生命的平庸状态。
王安忆反思了自身身份历史上的“无根”状态,认为这种“无根”状态是先祖的流徙不定的生活状态造成的。但她并没有沉浸在“无根”的焦虑中。她力图通过重建“家族神话”的方式实现对自身身份根柢的确认,并超越了自我,实现了心灵的极大满足。她希望有一种确定的根柢,这就是“优秀传统”。这种根柢具有精神血统和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的优越性,这使她摆脱了因平庸与弱小造成的情绪困扰,造就她无比的勇气和力量。她希望在这种“优秀传统”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生命状态。
王安忆通过对个体成长历史的反思,表达了建设理想生命状态的期望。这是建立在对自身的生命状态的反思基础上的。这有别于她通过对他人的成长史、生活经历的观照,通过宽容、批判、同情、肯定等方式作出的理想生命状态设想。因为她对自身生命状态的反思采取的是“反观自身”的视角,而对他人的成长史、生活经历的观照采取的是外部视角。但是,不管王安忆自身生命状态还是他人生命状态,都共同构成了王安忆的“心灵世界”意义上的理想生命状态系统,成为王安忆观照历史生命状态、建设理想生命状态的参照物。
王安忆以个体成长历史为视点的反思体现了她的生命理想。这建立在作家独特的生命体认基础上。无论是先祖的“英雄”成长历史还是作家自身成长历史,对此进行反思都是为了建设,都带着理想精神的光芒。作家已经在绵密繁复的叙事中实现了超越。通过被阻断的岁月超越了历史的藩篱,并通过理想生命状态的精神建构超越了自我,从而表现了积极自信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2]王德威.如此繁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3]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4]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8]王安忆.悲恸之地[M].北京:文汇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何瑞芳]
Ideal and Transcending of Lives——On Reflections on Individual Growing History in Wang Anyi’s “Record and Fabrication”
LIU Jian-jun
(School of Liberature, Anqing Normal College, Anqing 246133, China)
Wang Anyi rethinks of individual growing history in her “Record and Fabrication”. On the one hand, she rethinks of the growing history of the ancestral “heroes”: on the other hand, she rethinks of her own growing history. When she rethinks of the growing history of the ancestral “heroes”, she thinks that the ancestors lacked rational attitude and the responsible bearing, and they took stable spiritual home and harmonious civilized life status as their ideal. Meanwhile, she rethinks of her own loneliness and “rootless” life status, and she expresses her expectance for the material life which allows the existence of higher spiritual realm and spiritual needs, she also expresses her expectance for the life status based on the fine tradition.
Wang An-yi;“Record and Fabrication”; life; ideal; transcending; reflection
2015-07-22 作者简介: 刘建军(1976-),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1671-5977(2015)03-0088-04
I24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