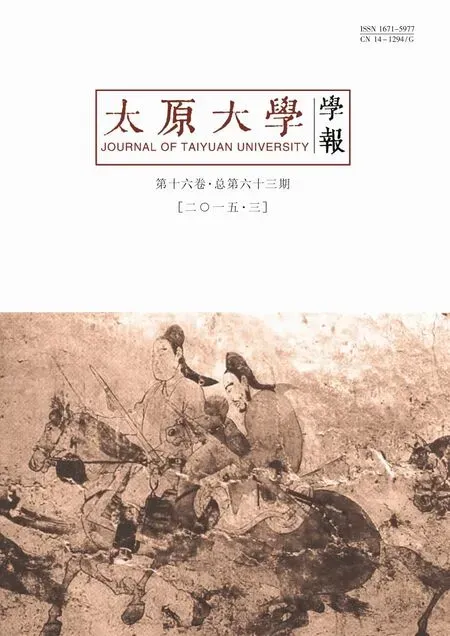徐大椿及其唱法艺术
——以其《乐府传声》为研究的重点
2015-02-11王辉斌
王 辉 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徐大椿及其唱法艺术
——以其《乐府传声》为研究的重点
王 辉 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徐大椿《乐府传声》二卷,是清代初、中期之际的一部著名戏曲论著。全书主要是对唱法艺术的探讨与总结,但重点却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口法艺术的初步总结,对阴阳调的区分与处理,对宫调与曲情的具体阐述。《乐府传声》对这些内容的论述,具体细致而深入透彻,特别是在所“传”之某些“声”与“法”方面,极具引领性与可操作性之特点,因而多为时人所称道。
徐大椿;《乐府传声》;唱法艺术;传声宗旨
在清代前期的几种重要戏曲论著中,徐大椿《乐府传声》一书,既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专论唱法艺术的著作,因其所论深入透彻,发明良多,而为时人多所称道。对此,《集成》本《乐府传声》前后共附有7篇序文的实况,又可为之佐证①《集成》本《乐府传声》所附之序,除徐大椿之自序,另有“前序”三篇,“后序”三篇,其作者依次为:刘彦颖、刘绍祖、黄之隽、无我道人、王保玠、李瀚章。《乐府传声》所附序如此之多,实为明、清两朝47种戏曲论著之绝无仅有者。。如黄之隽序有云:“细读数过,真发千古歇绝之密籥,而昭明疏析之。虽瞢于音律如弟之顽石,亦辄点头微悟,实天生神解之人于盛朝,审定律吕之时,非因源流家学而已。”[1]又如李瀚章之序认为:“徐灵胎(即徐大椿——引者注)氏生长吴会,稔其遗法,著为《乐府传声》二卷,为知音者所宗。”[2]二序中的“真发千古歇绝之密籥”、“为知音者所宗”云云,不仅对《乐府传声》评价甚高,而且也是其颇具影响的一种具体反映。徐大椿之前,在唱法及其艺术技巧方面多有所获者,乃首推明代魏良辅《曲律》与沈宠绥《度曲须知》二书,而徐大椿的《乐府传声》二卷,则在继承二家之所获的同时,又有所创新与发展,从而使得对唱法艺术的探讨,在清代的戏曲论著中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徐大椿“传声”的宗旨
徐大椿(1693-1772),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今江苏苏州人。《清史稿》卷五○七、彭启丰《徐君大业墓志铭》、袁枚《徐灵胎先生传》,均载有其生平事迹。徐大椿多才多艺,不仅工诗词,擅声律,而且还以医学闻名于当时,为“举国知名”的一位“神医”,并有《徐氏医书八种》行世。在戏曲论著方面,则有《乐府传声》二卷。据附于《乐府传声》卷首的徐大椿、胡彦颖二《序》可知,《乐府传声》的成书在“乾隆甲子”,即公元1744年,而刻印则在“乾隆十三年”,即公元1748年,二者相隔4年。以《乐府传书》的成书之年“乾隆甲子”计,是年徐大椿52岁,越4年为56岁,则《乐府传声》为徐大椿晚年所撰并梓行者,即可肯定②《乐府传声》卷首所附徐大椿《序》落款为“乾隆甲子”,所记为《乐府传声》成书之年(公元1744年),胡彦颖《序》之落款为“乾隆十三年二月”,后前者4年,知其乃为《乐府传声》的刻印之年(公元1748年)。。此则表明,晚年时期的徐大椿,对于“乐府”的唱法艺术,乃是相当关注的。以“神医”的身份撰著《乐府传声》,这在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作者中,徐大椿而外,别无第二人,正因此,“神医”论“乐府”之“传声”,即成为清代戏曲论著中的一段佳话。
作为一位“举国知名”的医学家,徐大椿之所以撰著《乐府传声》者,诚如此书名之所示,即主要在于“传声”,也就是要使其所制定的一系列“传声”之法,得以广为歌者所知、所识与所用。这一实况表明,徐大椿对于当时戏曲界之“传声”种种(如优与劣等),已是早有所观察且又了然于胸的。正因此,其即在卷首的《序》文中,将清初以来的“传声”之况,作了如下之描述:
若今日之南北曲,皆元明之旧,而其口法亦屡变。南曲之变,变为“昆腔”,去古浸远,自成一家。其法盛行,故腔调尚不甚失,但其立法之初,靡慢模糊,听者不能辨其为何语,此曲之最违古法者。至北曲则自南曲甚行之后,不甚讲习,即有唱者,又即以南曲声口唱之,遂使宫调不分,阴阳无别,去上不清,全失元人本意。又数十年来,学士大夫全不究心,将来不知何所底止,嗟夫!乐之道久已丧失,犹存一线于唱曲之中,而又日即消亡,余用悯焉,爰作传声法若干篇,借北曲以立论,从其近也;而南曲之口法,亦不外是焉[3]。
这一段文字的描述,主要包含了这样几方面的内容:(1)由于“今日之南北曲”在“口法”上的“屡变”,致使“听者不能辨其为何语”,即如具有地方特色的“昆腔”也不例外;(2)唱北曲者因为“不甚讲习”,而“以南曲声口唱之,遂使宫调不分”,以至于“全失元人本意”;(3)作者“爰作传声法”者,主要是欲“借北曲以立论”,“而南曲之口法,亦不外是焉”。总起来说,前二者虽然是对北、南曲(戏)唱法之不良现状的勾勒,但其中所蕴含的却是徐大椿对这种现状的深感忧郁;而后者,则为徐大椿依据前二者的实况所开出的一剂药方。徐大椿撰著《乐府传声》的宗旨,仅此即可见其端倪。由是而观,作为“神医”的徐大椿,欲藉《乐府传声》以疗治“唱曲”之“伤痕”者,已是甚为清楚。
重视对唱法艺术的探讨,自元人燕南芝庵《唱论》始,便成为了戏曲论著者所关注的一个戏曲学命题,而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者,又尤为重视之,并因此推出了有关这方面的一批重要成果,如朱权《太和正音谱》、王骥德《曲律》、魏良辅《曲律》、沈宠绥《度曲须知》、李渔《闲情偶寄》(此所例举者,仅就其中所涉之“唱法”而言,非指全书所论内容,特此说明)等,即皆为其例。其中,又以沈宠绥《弦索辨讹》、《度曲须知》二书最为著名。沈宠绥论唱法艺术,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口法,一即唱法。对于“口法”,《弦索辨讹凡例》所论之“撮口”、“开口”、“闭口” 、“鼻音”,以及“开口张唇”、“穿牙缩舌”等,即皆与其密切相关;而《度曲须知》所论之“出字总诀”、“收音总诀”、“入声收诀”、“收音谱式”、“收音问答”、“字母堪删”、“鼻音抉隐”等,亦属如此。“唱法”的重点是字音,即歌者在具体的演唱过程中,对每一个字所唱时之“出音”、“转音”、“收音”、“顿音”、“送音”等,都要作具体的把握与处理,如“高唱”与“低唱”的区别,“出音”与“送音”的分辨等,即都在其列。沈宠绥《弦索辨讹》、《度曲须知》对唱法艺术之所论,于徐大椿《乐府传声》则产生了较为直接之影响。徐大椿《乐府传声》论唱法艺术,从总的方面讲,主要是倾向于“发声”二字,且以“四声唱法”为重点,如认为:“平自平,上自上,去自去,字字清真,出声、过声、收声,分毫不可宽假,故唱入声,亦必审其字势,该近何声,及可读何声,派定唱法,出声之际,历历分明,亦如三声之本音不可移易,然后唱者有所执持,听者分明辨别。”[4]所论虽然是承续沈宠绥二书而来,但却较其更为具体与精细,因而也就更具理性色彩。
徐大椿认为,传声”的关健性技巧,主要在于“正字音”与“审口法”两个方面。在论“乐之成”时,徐大椿即将这两个方面,列入了其所言之“七大端”(另“五大端”依序为“定律吕”、“造歌诗”、“正典礼”、“辨八音”、“分宫调”),以表明二者在“乐”中的重要性。之后,徐大椿即着眼于可操作性的角度,对“字音”与“口法”作了如下之解释:“何谓字音?一字有一字之音,不可杂以土音;又北曲有北曲之音,南曲有南曲之音是也。何谓口法? 每唱一字,则必有出声、转声、收声,及承上接下诸法是也。”并于专论“口法”时,又作了如下之认为:
口法则字句各别,长唱有长唱之法,短唱有短唱之法,在此调为一法,在彼调又为一法,接此字一法,接彼字又一法,千变万殊…全在发声吐字之际,理融神悟,口到音随[3]。
“口法”虽然具有“千变万殊”的特点,但其关键则“全在发声吐字之际”。可见,“发声”之于“口法”与“传声”,乃是相当重要的。由“发声”而“口法”,再由“口法”而“传声”,表明了徐大椿对于“传声”的认识,乃是由此及彼,并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之情状的。所以,从总的方面讲,徐大椿所“传”之“声”,所论之“法”,主要是重在“发声”的技巧与方法方面,而“口法”,即为其中之大端。
二、对口法技巧的初步总结
徐大椿将“审口法”列为“乐之成”的“七大端”之一者,表明了其于“口法”乃是相当重视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从《乐府传声》有半数以上的篇什论“口法”者,即略可获知。在徐大椿以前的明、清两朝戏曲论著中,专论“口法”者,以沈宠绥《弦索辨讹》、《度曲须知》二书最具代表性,但对于什么是“口法”,二书却并没有讲明(实际上是不曾涉及,只是多次提到“口法”)。徐大椿《乐府传声》则不然。如在《乐府传声·序》中,徐大椿即明确指出:“口法”是指“每唱一字,则必有出声、转声、收声,及承上接下诸法是也”。这实际上是徐大椿为“口法”所下的一条定义,其要旨则在于告诉人们,“口法”与“声”乃密切相关,也即“口法”是关于歌者“发声”的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艺术。换言之,凡与“声”相关者,即属于“口法”的范畴,或者说,凡关于“声”之类的演唱技巧,如“出声”、“收声”、“转声”等,便皆为“口法”之属。至此,“口法”作为一个戏曲学概念,即为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进行了首次定义。
而实际上,所谓“口法”,是指歌者从音韵学与声律学的角度,对一个单音汉字的双重演绎,即“长唱有长唱之法,短唱有短唱之法”,不同的字在“出声”、“转声”、“收声”等方面,有着不同的“发声”要求与技巧性处理。以“出声”为例,《乐府传声》之“出声口诀”一节, 即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认为“欲改其声,先改其形”,“形改而声弗改也”。徐大椿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形”在“出声”中的作用。至于什么是“出声”中的“形”,徐大椿的解释则为:“大、小、阔、狭、长、短、尖、钝、粗、圆、扁、斜、正之类是也。”[5]这里所言之“大”、“小”、“斜”、“正”等13端,其实指的就是歌者发声的强弱、高低、长短等要素。而此,即涉及到了“五音”、“四呼”诸问题。“五音”(即“唇”、“舌”、“齿”、“牙”、“喉”)与“四呼”(即“开”、“齐”、“撮”、“合”),是北曲(戏)与南曲(戏)口法艺术的核心所在,对此,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中已有所涉及(具体参见该书卷上“字母堪删”等条),而徐大椿则在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之开拓与深化。如论“五音”时,徐大椿不仅在《乐府传声》中专设了“五音”一节,以显示其在口法艺术中的重要性,而且还首次对“五音”的“传声”之法也进行了具体而系统的总结,使之更具戏曲学价值。徐大椿之此举,在戏曲唱法艺术史上,实属为一次可操作性的深化推进。其具体为:
最深为喉音,稍出为舌音,再出在两旁牝齿间为齿音,再出在前牝齿间为牙音,再出在唇上为唇音。虽分五层,其音万殊,喉音之深浅不一,舌音之浅深亦不一,馀三音皆然。故五音之正声皆易辨,而交界之间甚难辨[6]。
“口法”之于歌者来说,不仅极为复杂多变,而且须在瞬间演绎完成,方可收恰到好处之审美效果。所以,徐大椿即在这段文字中,将具有“五层”之音特点的“唇”、“舌”、“齿”、“牙”、“喉”等,着眼于“口法”的角度,首次进行了操作层面上的论述与总结,如对“稍出”的体验与“再出”的理解,以及对三个“再出”之间关系的具体把握等,均使之更具示范性特点。而其论“四呼”者,亦属如此:“开口谓之开,其用力在喉。齐齿谓之齐,其用力在齿。撮口谓之撮,其用力在唇。合则谓之合,其用力在满口。”所论均简洁明了,极便于歌者把握与练演。与此同时,徐大椿之于《乐府传声》中,还曾将“五音”与“四呼”结合起来考察,认为“五音为经,四呼为纬”,二者缺一不可。徐大椿的这种认识,从“口法史”的角度言,乃是极具关联与演进之特点的。而在此基础上,徐大椿又根据发音位置的不同,提出了一种新的“经纬”说:“喉舌齿牙唇为经,上下两旁正中为纬,经纬相生,五五二十有五,而出声之道备矣。”所谓“二十五音”之说,即因其中的“五五二十有五”而始。故其乃又认为:“此千古之所习而不察者也。”(“喉有中旁上下”语)此则表明,徐大椿对其所持之“经纬相生”说,乃是相当自信的。
而尤为可贵的是,《乐府传声》还对“五音”与“四呼”之间的依承关系进行了具体讨论,并就其“唱字”之法作了更深层次的探究,如“四声唱法”中的“去声唱法”一节,即为其例。在这一节中,徐大椿针对“去声”字的“唱法”与不同地区的“曲唱”特点,首先作了如是之认识:“南之唱去,以揭高为主,北之唱去,不必尽高,唯还其字面十分透足而已。”继之,则举出了一个个的具体例子,以说明“一字三音”在“去声”字“唱法”中的重要性,例说深刻而方法独特,颇值称道。如其认为:
如唱冻字,则曰冻红翁,唱问字,则曰问恒恩,唱秀字,则曰秀喉沤,长腔则如此三腔,短腔则去第三腔,再短则念完本字即收,总不可先带平腔。盖去声本从上声转来,一著平腔,便不能复振,始终如平声矣。非若上声之本从平声转出,可以先似平声,转到上声也。…况去声最有力,北音尚劲,去声真确,则曲声亦劲而有力,此最大关系也[7]。
在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中,王骥德《曲律》、沈宠绥《度曲须知》、李渔《闲情偶寄》等著作,虽然于“去声”均有所论及,但以“一字三音”为切点论“去声唱法”者,徐大椿《乐府传声》则堪称为第一书。仅此,即可见出《乐府传声》所“传”之“口法”,在其唱法艺术中的独创性与重要性。
不独如此,徐大椿还在《乐府传声》中采用同样的论述之法,于“平声唱法”、“上声唱法”、“入声派三声法”等篇什中,分别对“平声”、“上声”、“入声”字的“唱法”,亦进行了具体而细微的探究,这种形式的探讨,完全是以作者对“口法”的洞悉程度为基础的,即其所获之种种,乃皆属于作者对口法技巧的总结与归纳所致。因之,其较他人之所论所析,更具有戏曲学意义,也就不言而喻。虽然沈宠绥在《读曲须知》中也曾对“平声唱法”等有所探讨,但从总的方面讲,其在系统性与深度感等方面,则是明显地不如《乐府传声》之所论的,对此,徐大椿自称其之所论“乃千古未发之微义”(“声各有形”语)的认识,又可为之佐证。
三、对阴阳调的区分与处理
这里所说的“阴阳调”,是指“阴调”与“阳调”的合称,而不是说在戏曲音乐中有一种调名为“阴阳调”。在《乐府传声》中,有两节的内容是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为“阴调阳调”,一为“高腔轻过”,其所论均属唱法艺术的范畴。而“阴调阳调”,指的即是唱法艺术中的“阴调”与“阳调”,所以,《乐府传声》论此乃云:
古人唱法,所谓阴阳者,乃字之阴阳,非人声之阴阳也。字之阴阳者,如东为阴,同为阳,二字自有清浊轻重之别。至人声之阴阳,则紧逼其喉,而作雌声者,谓之阴调;放开其喉,而作雄声者,谓之阳调[9]。
这段文字之所论,重在对“字之阴阳”与“人声之阴阳”进行区分。徐大椿认为,“字之阴阳”,“自有清浊轻重之别”,而“人声之阴阳”,则主要是指歌者对唱法技巧的处理,“紧逼其喉,而作雌声者,谓之阴调”,“放开其喉,而作雄声者,谓之阳调”。相比之下,后者更为重要,因而也更注重唱法的技巧性。所谓“字之阴阳”,实际上指的是四声平仄中的阴平与阳平,这是歌者应注意的一个方面。而“人声之阴阳”,则为歌者所要注意的另一个方面,且其技巧性更为复杂。正因此,徐大椿乃指出,对“人声之阴阳”的处理,全在于歌者的勤勉演练与细心把握,并认为,唱法艺术中所谓的“阴调”与“阳调”,即因此而产生、而存在。而且,由于口法技巧的不同,声型特征的不同,歌者所发出的“声之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就又有了“雌声”与“雄声”。对于“字之阴阳”的认识,前人如王骥德《曲律》、沈宠绥《度曲须知》等,都曾进行过程度不同的论述,而于“人声之阴阳”的涉笔,则只有《乐府传声》一家。不仅如此,《乐府传声》之于“雌声”、“雄声”的提出,还使得唱法艺术在声型与音质方面更为丰富,也更为精细了。
“阴调阳调”是徐大椿针对“乐府”所“传”之一大法门,其技巧的关健性,主要在于歌者要“善用喉”,而“善用喉”的重点,则是要求歌者拿捏自然,把握好分寸,而“非一味紧逼”,或者“逼紧”。对此,徐大椿乃有独到的见解,故其于“阴调阳调”中乃认为:“唱正大雄豪之曲,而逼紧其喉,不但与其人不相称,即字面断不能真。盖喉间紧逼,则字面皆从喉间出,而舌齿牙唇,俱不能着力,开齐撮合,亦大半不能收准,即使出声之后,作意分清,终不若即从舌齿牙唇之亲切分明也。唯优人之作旦者,欲效女声,则不得不逼紧其喉,此则纯用阴调者。然即阴调之中,亦有阴阳之别,非一味紧逼也。”在徐大椿看来,“逼紧其喉”,是导致“字面断不能真”的关键,因之,所发之声,也就“终不若即从舌齿牙唇之亲切分明也”。由是而观,可知徐大椿是反对歌者在演唱中“逼紧其喉”的。正因此,其于“阴调阳调”中又说:“近日之所谓时曲清曲者,则字字紧逼,俱从喉中一丝吐出,依然讲五音四呼之法,实则五音四呼何处著力,以至听者一字不能分辨,此曲之下贱,风流扫地矣。”在这里,徐大椿对那些“字字紧逼”且又“依然讲五音四呼之法”的世俗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乃“曲之下贱”,而致使“风流扫地”。
值得注意的是,徐大椿在论述“阴调阳调”时,还在“高腔轻过”一节中,将“阴调”、“阳调”与“声高”、“音高”互为关联,交融以论。首先,徐大椿于“高腔轻过”中对“声高”与“音高”进行了具体把握,认为“声高”不仅不等于“音高”,而是与“声高”大有区别的。因而说:“盖所谓高者,音高,非声高也。音与声大不相同。用力呼字,使人远闻,谓之声高;揭起字声,使之向上,谓之音高。”这实际上是对“声高”与“音高”的定义。这一定义表明,“用力呼字”与“揭起字声”,乃为其关键所在。而不同音质的声音,其审美效果也是不相同的,所以又说:“凡高音之响,必狭、必细、必锐、必深;低音之响,必阔、必粗、必钝、必浅。如此字要高唱,不必用力尽呼,推将此字做狭、做细、做锐、做深,则音自高矣。”其次,则是围绕“今人”将“狭、细、锐、深”处理不当而使之变成“阴调”且“似是而非”的情况,进行了具体讨论与批评。认为:
今人不会此意,凡遇高腔,往往将细狭锐深之法,变成阴调,此又似是而非也。盖阳调有阳调之高低,阴调有阴调之高低,若改阳为阴谓之高,则阴之当高者,又何改耶?且调有断不可阴者,若改阳为阴,又失本调之体矣。能知唱高音之法,则下之喉,亦可进入中等,中等可进入上等。凡遇当揭高之字,照上法将气提起,吹着按谱顺从,则听者已清晰明亮,唱者又全不费力。…是调以人分,而一人之声,只可限以一调,略高即属勉强矣[9]。
在徐大椿看来,“不会此意”的“今人”,只要遇到“高腔”,就会“将细狭锐深之法,变成阴调”,而不知“阳调有阳调之高低,阴调有阴调之高低”,二者既不可混用,也不可“改阳为阴”,或者“改阴为阳”,而是应该在唱法上下功夫。这里所说的“唱法”,就是歌者“唱高音之法”,也即“高腔轻过之法”。而“高腔轻过之法”的重点,则是“调以人分”,且“一人之声,只可限以一调”。
以上所述表明,无论是“阴调阳调”,抑或“高腔轻过”,甚或是“低腔重煞”,徐大椿于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均是深有体悟的。而尤其是所论之后者,对于歌者正确把握“阴调”与“阳调”的区分、唱法(重点在“善用喉”),以及歌者对“必狭、必细、必锐、必深”(“高音之响”)与“必阔、必粗、必钝、必浅”(“低音之响”)之音在技巧上的操作和把握等,都是极具引领性作用与指导意义的。徐大椿撰写“阴调阳调”一节的动机,主要在于对世俗“高字唱阴”、“低字唱阳”现象的批评,并于“高腔轻过”与“低腔重煞”两节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处理之法,以希望歌者能多加揣摩,灵活运用,一改“今人”之陋习。由是而观,可知其之所论所析,乃是具有相当的目标性与现实性的。而还应注意的是,徐大椿在“阴调阳调”一节中,所言之“阴调”、“阳调”与“雌声”、“雄声”等,实际上已涉及到了现代声乐学中的“真假声”(或称“真假嗓”)问题,这在当时的条件来说,乃是极难能可贵的。
四、关于宫调与曲情的阐述
“起调”在唱法艺术中至为关键,故深谙此中之道的徐大椿,乃于《乐府传声》中设置了专节以论。除“起调”一节外,徐大椿还在“宫调”、“字句不拘之调”两节中,对“乐府”之“宫”之“调”也进行了阐述。总体而言,徐大指论“乐府”的“宫调”抑或“起调”,主要是希望歌者在演唱时,应严格遵守宫调的规律,而不得擅自处理,因为古人分宫立调,乃“各有凿凿不可移易之处”。如在《宫调》一节中,徐大椿于元人燕南芝庵《唱论》的基础上,就宫调的有关特点,以及其在唱法上与平仄阴阳的关系等,均进行了程度不同之讨论。认为:“黄钟调,唱得富贵缠绵;南宫调,唱得感叹悲伤之类。其声之变,虽系人之唱法不同,实由此调之平仄阴阳,配合成格,适成其富贵客缠绵,感叹悲伤,而词语事实,又与之合,则宫调与唱法得矣。”其中的“黄钟调,唱得富贵缠绵”云云,实际上是对《唱论》的引录*燕南芝庵《唱论》原文为:“仙吕调唱,清新绵邈。南吕宫唱,感叹悲伤。中吕宫唱,高下闪赚。黄钟宫唱,富贵缠绵。正宫唱,惆怅雄壮。道宫唱,飘渺清幽。大石唱,风流蕴藉。小石唱,旖旎妩媚。高平唱,条物滉漾。般涉唱,拾掇坑堑。歇指唱,急并虚歇。商角唱,悲伤婉转。双调唱,健捷激袅。商调唱,悽怆怨慕。角调唱,呜咽悠扬。宫调唱,典雅沉重。越调唱,陶写冷笑。”这就是六宫十一调的特点之所在,兹录以供参考。,表明其于《唱论》之“宫调论”,乃是相当钦服的。但徐大椿论宫调,也有其自己的特点,如认为古人之宫调,“各有凿凿不可移易之处”,不可随便移易更改,并要求歌者“宜依本调如何音节,唱出神理,方不失古人配合宫调之本”云云,即为其例。此外,徐大椿还提出了宫调与戏曲作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唱者从调则与事违,从事则与调违,此作词者之过也”。这里所说的“作词者”,即为戏曲作家。在徐大椿看来,一位好的戏曲作家,是颇善于处理“事”与“调”的关系的,否则,即相反,也即成为了有“过”之“作词者”。这是提醒戏曲作家对宫调的注意。
“起调”是徐大椿论宫调的重点。正因此,其于开首乃如是写道:“唱法之最紧要不可忽者,在于起调之一字。通首之调,皆此字领之;通首之势,皆此字蓄之;通首之神,皆此字贯之;通首之喉,皆此字开之。”在这里,徐大椿将“起调”在唱法中的重要性,已讲得非常清楚,目的则是要引起“唱者”的注意,对其予以重视。“起调”在唱法中虽然很重要,但却更很复杂,有时甚至是复杂得令人难以措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转变之法,盖无穷尽焉”。对于“起调”的这种“无穷尽”的“转变之法”,徐大椿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乃举出了六端以为例说。其具体为:
有唱高调,而此字反宜低着;有唱低调,而此字反宜高者;亦有唱高宜高,唱低宜低者;有宜阴起翻阳者;有宜阳起翻阴者;宜有先将此字轻轻蓄势,唱过二三字,方起调者[10]。
所举的这六端,是足以说明“起调”的复杂性的。所以,徐在椿之于“起调”之末,又特地作了如是之强调:“此字一稉,则全曲皆稉,此字一和,则全曲自和。故此一字者,造端在此,关键在此。其详审安顿之法,不可不十分加意也。”仅就这段文字而言,徐大椿撰著《乐府传声》的匠心与用意,即皆寓其中。在《乐府传声序》中,徐大椿曾坦言,其撰著《乐府传声》的宗旨,主要在于“爰作传声法若干篇”,由“起调”一节观之,其“爰作传声法”的动机与目的,乃是既具强烈的一面,而又有着循循善诱之特点的,而后者对于歌者来说,又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福祉!
徐大椿论“曲情”,从戏曲论著史的角度言,应是与李渔《闲情偶寄》不无关系的,因为《闲情偶寄》中的“解明曲意”,即乃先其而为。虽然如此,但《乐府传声·曲情》与《闲情偶寄·解明曲意》毕竟是有区别的。在“解明曲意”一节中,李渔认为:“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之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此种神情。”[11]很明显,李渔所强调的“曲意”(“曲情”),主要是指“曲中之情节”,故而大力提倡“变死音为活音,化歌者为文人”的有情之曲,而反对“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无曲”的“无情之曲”。而《乐府传声》中的“曲情”,则是重在指“曲中之意义”,也即蕴藏于曲(戏)中的那种“感人动神之微义”。因而认为:
声者众曲之所同,而情者一曲之所独异,不但生旦丑净,口气各殊,凡忠义奸邪,风流鄙俗,悲欢思慕,事各不同,使词虽工妙,而唱者不得其情,则邪正不分,悲喜无别,即声音绝妙,而与曲词相背,不但不能动人,反令听者索然无味矣…使听者心会神怡,若亲对其人,而忘其为度曲矣”[13]。
徐大椿在这里所反复强调的,是歌者(演员)对于剧中人物情感的具体把握,并要求歌者“设身处地,摹仿其人之性情气像”,即与剧中人物同喜同忧,同悲同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动人”的审美效果,才能“使听者心会神怡,若亲对其人,而忘其为度曲矣”。不独如此,徐大椿还明确指出,“若世之止能寻腔依调者,虽极工亦不过乐工之末技,而不足语以感人动神之微义也”。 而此,即为徐大椿论“曲情”的意旨所在。可见,徐大椿之论“曲情”,虽然是对李渔《闲情偶寄·解明曲意》的继承,或者说是受其影响所致,但其之所论所析,却较《闲情偶寄》之“曲意说”更为具体,更为深刻,因之,其后来者居上的特点,也就更为鲜明亮丽。
从戏曲文本的语言到音韵、声律,再由唱法艺术到对曲意、曲情的注重,这就是明、清两朝戏曲批评家所开垦出的一条戏曲批评路途,而作为医学家的徐大椿,则以其《乐府传声》二卷,为这一路途的拓宽与夯实,做出了极具特点的奉献,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1]黄又隽.乐府传声·序 [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51.
[2]李瀚章.乐府传声·序 [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87.
[3]徐大椿.乐府传声·序[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53.
[4]徐大椿.乐府传声·入声派三声法[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67.
[5]徐大椿.乐府传声·声各有形[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60.
[6]徐大椿.乐府传声·五音[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61.
[7]徐大椿.乐府传声·去声唱法[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66.
[8]徐大椿.乐府传声·阴调阳调[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72.
[9]徐大椿.乐府传声·高腔轻过[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78.
[10]徐大椿.乐府传声·起调[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74.
[11]李渔.闲情偶寄:卷五 [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98.
[12]徐大椿.乐府传声·曲情[C]//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73-174.
[责任编辑:岳林海]
Xu Da-chun and His Singing Art——Taking “Yuefu Chuansheng” as Study Subject
WANG Hui-bin
(Hube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441053, China)
Xu Da-chun’s “Yuefu Chuansheng”(two volumes) is a famous dramatic works during the earlier and middle periods of Qing Dynasty. It is the exploration and summary of singing art. It includes three factors; the preliminary summary of singing art: the distinguishing and handling between yin and yang tunes: and the specific exposition of music tunes and song contents. The dissertation about the above contents in “Yuefu Chuansheng”is not only specific and detailed but also deep and thorough. Especially, some singing skills are leading and operable: so they are very popular at that time.
Xu Da-chun;“Yuefu Chuansheng”;singing art;singing purpose
2015-05-28 作者简介: 王辉斌(1947-),男,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辑佚学的研究与乐府文学批评。
1671-5977(2015)03-0074-06
I207.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