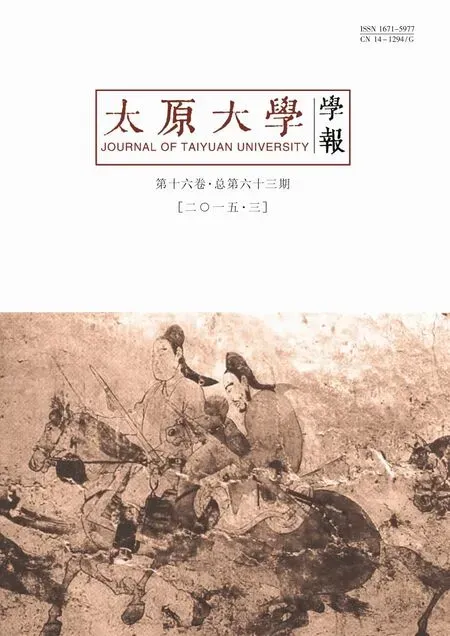司法中的宪法适用方式及其实证分析
2015-02-11武静
武 静
(太原学院 政法系,山西 太原 030032)
司法中的宪法适用方式及其实证分析
武 静
(太原学院 政法系,山西 太原 030032)
宪法具有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双重属性,而其规范性、制度化、强制性特征决定了其可以在司法中予以适用。囿于现有政治体制的要求,合宪性解释成为宪法适用的最佳选择。这是因为合宪性解释是解释方法与解释材料的结合,而且现有制度并未明确排除宪法适用的可能性。通过相关司法解释及案例的佐证,最终明确司法适用中合宪性解释的可行性。
宪法;宪法适用;合宪性解释
宪法与法治紧密联系,它成为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基础。人们谈论宪法,既是为国家存在寻找正当性的基础,也是为国家政权运行建立合法性的过程。“‘宪法’(constitution)一词的现代意义生成过程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在表达政府体制的总体安排这层意思上的演变过程;另一条是作为一个法律术语用以表达根本性法律的含义的确定过程”。[1]宪法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根本法,与国家政治结构联系最紧密,其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对国家机关的权力进行分配,因此它常常“被用作不同机构之间关于其他宪法管辖权限政治争论的背景,而不是作为这些机构之一的法院确定其他机构权限的权威来源”。[2]宪法的政治权威性光辉掩盖了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功能。对宪法两种功能的不同重视程度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我们历来强调立法机关的宪法监督,却很少论及司法机关的宪法监督。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是宪法权威的政治因素影响了人们对其法律性的思考。
一、宪法的法律性
借鉴拉兹有关法律规范的理论,法律应当具有规范性、制度化和强制性的特征。宪法的内容和性质均具有明显的法律特征,具体表现为:
(一)宪法内容的多样性和法律性
当代宪法主要内容为对国家政体、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分配等根本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中属于建构性规定的主要是对于权力分配的规定,如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的性质、职权及其范围。通过这些规定可窥见一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除赋予构设的权力框架以权威之外,宪法对各机关如何行使职权进行规范;同时予以规范的还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及国家对此的保护方式,从而使人权保护能够有章可循。此外,宪法规定对违反其内容的行为可通过有权机关进行制裁,从而约束违宪行为。
宪法规范既有构建性规范,也有规制性规范和制裁性规范,①参见欧阳景根.理解宪法[J].晋阳学刊,2006(5):34.其中规制性规范与制裁性规范在国家政治体制的框架内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的需求:国家机关应当依据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应当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承担宪法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概念,其实现既需要仰仗作为根本法的宪法规定,还需要其他法律的具体规制。其他法律的规制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并应接受宪法的监督,在保持与宪法一致的前提下,法律才具有有效性。宪法和其他法律一起,构筑起规范机关行为、人权保护的屏障。
(二)宪法属性的多重性和法律性
宪法所规定的是一国最基础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宪法论证了国家存在的正当性、政权运行的合法性,都依据宪法而获得正当性的存在;而宪法又借助于国家的存在和政权的运行获得权威性。宪法规定了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并对二者予以平衡。宪法的内容既关涉国家政治体制,又关涉法律制度的整体设计、运行,对社会文化、经济均有影响。宪法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
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表示:“本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们可以看到,宪法对政治体制的规定、对国家机关权力的分配,均是基于法律性做出的。法律性是宪法的根本属性。国家的各种组织、个人均应遵守宪法的规定,也就是说,各种组织、个人都可以依据宪法维护自身的利益,宪法为权利的保护提供最高权威的法律依据。
二、宪法的可适用性
凯尔森曾言法律只有获得实际适用才是有效的法。宪法的法律性决定其具有可适用性。“宪法适用是指宪法条文被专门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机关用来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过程”。[3]当今世界宪法适用的主体可以是立法机关或专门机关,也可以是司法机关。宪法适用模式主要分为附带的宪法司法审查模式、宪法法院模式两类。宪法适用方式即违宪审查制度,包括附带的司法审查和宪法法院两种,但这并不代表宪法适用只有这两种方式。
法律适用是一个法律发现和法律评价的过程。它要求回溯到法律渊源以表明所适用的法律具有正当性,并将其适用于待决纠纷以实现其实效。法律渊源是表明裁判依据权威出处的实践性概念,“首先,在决定该体系是否具有效力,是否得到实践方面;其次,通过它们作为识别体系的身份标准的作用,决定何种规范属于该规范体系”,[4]这两方面的功能使法律渊源成为法律体系的效力保证和身份标准。宪法可以适用,也就表明,宪法是法律适用视角下的一种法律渊源,可以成为裁判的权威性依据。
通观世界较有代表性的有关宪法的适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规律:第一,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政体基础上实行违宪审查;第二,宪法的适用多来自本国宪法的直接授权;第三,宪法司法审查具有直接的法律后果。
以上三点在我国都无法实现。首先,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我国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制度,在政治体制上无法与美国模式或德国模式接轨;其次,宪法并未规定法院或者某一特设机构对宪法的审查权,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国没有对宪法的解释和监督,*宪法的解释、监督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性质为全国人民的常设机关,享有立法权。只能说明宪法并未授权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力;最后,我国法院如果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适用的法律、法规有违宪法时,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无权直接作出认定。
但是根据宪法的法律属性可知,宪法不仅是文本的法,也是实践的法,宪法具有实际的法律效力。“宪法是人们根本的活动准则,应该像其他法律一样,作为衡量和判定是非曲直的标尺”。[5]除既有的立法机关的宪法监督之外,违反宪法的行为应受到司法追究。宪法是追究违宪责任的权威依据,是判断违宪与否的法律渊源。
三、宪法适用方式的可行性
实践中,典型的宪法适用方式是宪法的司法审查制度,但具体的宪法适用方式因国家体制而存在不同。我国学者在宪法是法律渊源的问题上态度一致,在其适用路径上有两种观点:宪法司法化和合宪性解释。
(一)宪法司法化
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有限政府、宪法至上、权力制衡。法院由此获得对有违宪法的法律、法规宣布其为无效的权力。广义的司法审查有两个指向:对法律法规的宪法监督、依据宪法监督而产生的宪法诉讼。我国学者借鉴宪法的司法运用这一特征,建议将司法审查制度引入我国。司法审查属于法院的审理职能,我国有学者称其为宪法的司法化。*一般认为,胡锦光在“宪法司法化的必然性与可行性探讨”(载于《法学家》,1993年第1期)一文中最先使用此概念,王磊在《宪法司法化》一书中将司法审查制度称为“宪法司法化”并扩大了其影响力。参见王磊《宪法司法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在宪法司法化的具体路径上,学者们的主张各有千秋:有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的重点是在法无明文规定时直接引用宪法裁判案件;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主要是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相关观点参见潘佳铭,“宪法司法化中的违宪审查制度及其模式选择”,《文史哲》,2004年第3期,144页;张心向,“我国‘宪法司法化’路径问题之思考”,《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2期,55页;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第B01版;蔡定剑,“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119页在划定宪法司法化适用范围时,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蔡定剑认为宪法司法化可以对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进行裁定,也可以对私权受损的私人侵害进行裁决;[6]而张千帆则认为宪法不宜直接适用于私法领域。[7]
对宪法司法化的多样化理解使宪法司法化备受争议。许崇德教授认为“宪法司法化”的提法是晦涩的,其所要表达的作为法院判案依据和法院对规范性文件及行为作出解释的意思,准确的说法早已被“宪法适用于审判过程”和“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涵盖。[8]借由许崇德教授的批评,有学者用“宪法诉讼”、“宪法的司法监督”等概念代替宪法司法化的内涵。[9]此种定义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宪法诉讼(如齐玉苓案以及王禹在《中国宪法司法化》中所举的33件案例等),尽管数量有限。从本质上来讲,这两种新的提法与宪法司法化具有一致性,是对宪法司法化更精确的描述。
也有学者根据我国宪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推定,我国适合坚持立法机关的审查模式,即认为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议行合一制国家,法院没有遵从判例的传统,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宪法监督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因此,现阶段并不存在违宪的司法审查制度。[10]的确,以立法者视角去看,现有成文法的规定难以为司法审查找到明确的依据。但最高法院推出的案例指导制度以及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成文法制度并不是固步自封和无法撼动的。
(二)合宪性解释
合宪性解释是宪法的适用方式之一,这种适用模式由于并未要求直接引用宪法而有别于宪法司法化,正因如此也有学者认为其不属于宪法的适用而只是解释方法的原因。[11]支持合宪解释是宪法适用路径的学者们则认为,法律的抽象性使对其的正确适用必须经过解释,“解释法律实在就是适用法律的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审判机关或执行法律机关欲确定某一抽象法律,应适用于某一事件,自然非经过这一过程不可”。[12]违宪审查的司法化路径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潜藏的司法冲动难免受到政治哲学的诘问,合宪解释的路径避开了正当性难题。合宪性解释意识到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所规定的制度尤其是权力分配的制度具有最大的稳定性需求,在宪法规定的权限内,法院通过合宪解释的方式保障宪法的实施,体现了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法治要求。这也意味着,合宪解释是站在内部视角看待违宪审查的,它的权力触及的最远点就是宪法所划定的法律范围。
(三)两种方式的可行性比较
1.宪法司法化的制度性局限
宪法司法化自提出以来就受到颇多质疑,其中最主要的是针对法院的职权范围与宪法司法化的衔接问题。表现在,第一、宪法监督权的行使主体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实施和修改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与宪法抵触的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改变或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时,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交审查要求。第二、法院的职责范围问题。依据宪法,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运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在这些规定中,我们无法在宪法和法院之间找到直接的关系:宪法的监督和解释权归立法机关;法院审判依据是法律;最高法院可以解释法律在审判中如何运用;即使发现违宪的法规,最高法院也只是有权提交书面审查要求。概括而言,基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法院应当遵守宪法(即“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适用法律进行审判活动;而违宪审查权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这是一幅由现有的宪法及相关法描绘的权力分配画轴,任何变动都会影响画面的布局平衡。
既存的事实无法兼容宪法的司法化路径。但是同时,法院的审判活动应当遵守宪法,意味着宪法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存在着实际的影响。法律适用的视角为法院遵守宪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合宪性解释。宪法不得作为法院据以裁判的直接依据,但法院据以裁判的法律依据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就是,“宪法也应通过合宪解释的方式在法院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得到适用”。[13]这是由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决定的,也是由法院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必须作出裁判的职责决定的。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合宪性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必然结论。
2.合宪性解释的可行性
合宪性解释是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为正确适用法律,依据宪法进行论证获得权威裁判依据的司法性解释。“因为宪法解释从来都是对政治原则的理解。……法律政策学的主张不仅应当通过修宪的方式变成宪法的一部分,而且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变成宪法的一部分”。[14]合宪性解释使宪法的适用建立在了司法谦抑的基础上,克制了司法能动主义易对政治问题冲动的倾向,使实施宪法的实践得以合法性延续,是宪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实现。
(1)合宪性解释是解释方法
合宪性解释首先是解释方法,是在出现法律漏洞或“法律本身——特别是应用诸如‘善良风俗’之类须填补的概念”[15]时以“以高位阶之规范,阐释低位阶法规之含义”的方法;[16]合宪解释也是法律适用方式,“所谓合宪性解释,是指在出现复数解释的情况下,以宪法的原则、价值和规则为依据,确定文本的含义,得出与宪法相一致的法律解释结论”,[17]进而确定正确的裁判依据。法律方法与法律适用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合宪解释恰如其分地对此作了注解。
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自身规定了自己的最高权威,这种规定的效力来自于“人们共同缔造了政府,而宪法表达了人们之间的共识”。[18]201法院应当遵守宪法,宪法为法院“提供虽然是次要的关于承认法律对公民和对法院具有拘束力的标准”,[19]法院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的方式维护和实施宪法。合宪性解释是当代中国宪法进入司法的符合宪法精神的方式,也是宪法实施对法院提出的要求。“合宪性解释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宪法解释,当然也就不是依据宪法裁判具体个案,但却依然是在具体案件中对宪法所确立的价值的贯彻,这个贯彻所凭借的就是法律解释的方法”。[20]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在法院审判工作中,不得突破宪法原则和规定。
(2)合宪性解释是解释方法与解释材料的结合
典型法律解释方法的形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评价解释和跨类型的意图解释四种。[21]142解释方法除具有形态以外,还须通过解释材料得以表现。合理合法的裁判依据通过恰当的解释方法方能达成。对解释材料按解释规则以不同的形态进行解释,是为具体案件寻找正确的裁判依据的过程。由于解释材料权威程度不同,对法官的解释活动影响随之不同。这也意味着,解释材料的权威性对于确定裁判依据、决定裁判后果都有影响。对一个解释论点的形成而言,“解释材料具有权威性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这些材料将被纳入它们所影响的解释论点的内容之中”。[21]132宪法作为一种解释材料,与这四种解释方法均有关联。
首先,当可以直接适用某一具体法律时,宪法不在论证过程中出现,然而法官的解释必须以宪法为最终标准;其次,当可适用的法律有两种以上的法律意义时,首先将法律作为法律有机体的一部分,选择与法律体系最接近的解释方案。宪法居于法律体系的塔尖,作为论证的一部分,可以引入宪法对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论证;再次,当运用目的——评价解释论点、以及参考立法准备材料或参与立法者的思想的跨类型的意图解释时,“在宪法上适当的、尊重立法者权威的唯一做法就是,尽可能地实施立法者在审议、通过法案时所设想的目标”。[21]137因此,据此对有关法律进行解释时,宪法作为体现人民意志的成文法形式,应当引入论证过程以证成其结论的权威性。
(3)宪法是法律适用中的法律渊源
正如惠廷顿讲原旨主义时提到的,它“有助于推进基于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的实现。……为获得正确的解释提供了一种最直接和最一致的路线”。[18]3宪法的权威性不在于必须作为直接的裁判依据,而在于法律适用必须遵循宪法的规定,在于宪法具有解决法律冲突的效力,在于任何一种解释方法都无法挣脱宪法限定的四至。“宪法进入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最现实的路径,是宪法本身就是各部门法律的重要制定法法源。一方面,宪法是各部门法律的最重要的立法依据;另一方面,宪法作为法源被纳入了各部门法律之裁判规范的建构过程,进而成为了具体案件的裁判规范”。[22]法院适用法律时,无法绕开宪法的约束力。宪法是法律适用的权威渊源,甚至可以进一步,是权威渊源的权威。“一个实现良好的宪法之治的国家,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好的宪法文本和保障宪法实施的各种具体制度,同样也需要来自法律人共同体的法律技术层面的保障”。[23]
(4)合宪性解释的制度基础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法释第[2009]14号.第一条规定法院裁判文书应当引用相关法律、法规作为裁判依据,第六条规定,对其它规范性文件,法院审查认定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结合以往有关裁判依据方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宪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无法作为直接引用的裁判依据;同时可以推定的是宪法未被排除出裁判说理的论证过程。这种默示的安排一方面回避了违宪司法审查制度蕴含的司法高于立法并可监督立法的理念对既有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冲击,另一方面又保证了宪法对司法过程的关照,排除了宪法进入司法程序的障碍,确立了宪法的适用性。
宪法司法化与合宪性解释作为宪法适用的两种方式均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但囿于我国政治体制的要求,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宪法实施方式,合宪性解释不失为最佳的方式。
四、合宪性解释的实证分析
合宪性解释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实践可能性,而且一直以其润物无声的方式实际推进着我国法治改革的进程——以司法解释为例,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具体个案的多个司法回复充分说明了作为宪法适用方式的合宪性解释的可行性及重要性。
(一)“八二宪法”之前
1955年在对新疆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最高院明确指出,刑事判决不宜引用宪法作为判案依据。*本篇法规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79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八批)的决定废止,理由是定罪科刑以刑法为依据,复函不再适用。
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兄弟民族离婚纠纷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法行字第2606号,1955-02-18中,最高院同意湖南省人民法院有关民族离婚纠纷的处理原则。湖南省高院在请示中认为根据宪法,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对于民族婚姻纠纷,应当耐心调解,不宜硬性判决。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私合营企业股权问题的函*最高人民法院,(56)法研字第8020号,1956-08-14.中,最高院认为对于土改时未予没收的地主股东的股权,按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对待。云南省高院在请示中,认为这一部分股权的法律依据来自宪法规定的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所有权的内容。
在195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过去由地方法院审理而以军事法庭、军管会、军法处等名义判决的土匪、特务、反革命案件,现在有的罪犯表示不服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法研字第22829号,1957-11-27.所附江苏省高院的请示中,引述了最高院曾对南京军区军事法院作出的批复,批复内容为“根据宪法关于国家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的原则,如果被告要求上诉的,也可以准许他上诉于上级法院”。
总之,“八二宪法”之前的制定法体系尚未充实到支持实际出现的各类纠纷,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只能因循原则性较强的宪法进行论证。实际,以宪法作为直接裁判依据进行判决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另外,我们在1957年后几乎很少再见到法院依宪法论证裁判的情形,这并非由于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只能说它间接印证了在特定历史时空法制建设几成空白的事实。
(二)“八二宪法”之后
1.1985年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法民复[1985]17号.
批复针对的案情:吴天爵之父生前有134号、136号、138号三间房,解放前134号被炸仅剩残墙。为安全,吴家人将断墙围建成院墙。1947年,林世布、肖其祥征得吴父同意,依托134号的地基搭盖铺面。房屋材料和资金由林、肖出资,其中使用了吴家桁条5根和6000多块砖,并对134号的墙面进行了改动。由于未对使用134号地基、桁条和砖的性质言明,林、肖主动给吴家2担谷子。1948年后房屋由林一人使用。1951年林将铺面的上盖(不含垒墙)折价卖给黄玉全。吴父对此无异议。1952年吴父领取了134号房屋的《房基契证》,但由于房屋天面不是吴家所盖,故不能领《房产契证》;而黄玉全因砖墙为吴家,亦不能领取《房产契证》。黄每年因使用房屋向吴家交一担谷子,1952年黄在征得吴父同意后,翻新房屋,并每年向吴家交2担谷子。1955年黄将房屋转租给新宾供销社,房租4担谷子,黄收取后向吴家转交两担。1962年黄又将房屋转租新宾镇集体餐饮服务店,房租给黄、吴各交一半。1966年后餐饮店只向黄家交付租金。1972年黄未征得吴家同意背着吴家将房屋全部材料转卖给餐饮服务店。1979年,吴天爵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原告方借工作人员疏忽于1981年取得了涉诉房屋的《房产契证》。
最高院采纳了广西省高院三种意见之一,即涉诉房产为吴家和餐饮店共有。广西高院提供的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涉诉房产的宅基地依据宪法规定,即城镇所有土地为国家所有,因此,吴家并不享有产权,房产应归餐饮店所有。在这一裁判意见中,法官认为宪法是其得出这一结论的直接依据。
2.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李理河与潘继伙宅基地租赁纠纷一案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法民复[1985]11号.
批复针对的案情:李理河与潘继伙诉争的宅基地原系李理河之父李司保的产业,其上盖于抗战期间被日寇炸毁,仅留残墙。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潘继伙的父亲潘李、伯父潘允林和潘允德三兄弟承租了该宅基,与李司保订立的租赁契约载明:从一九四七年起该宅地与残墙租给潘家使用,年租谷为二百斤,租期二十年。租赁期间任由承租人加建上盖使用,租期届满铺屋业权归出租人所有。潘家承租后,在该宅基残墙上建房居住,交过两年租谷,解放后,只按期向政府交纳房地产税,不再向李家交租。一九六七年租赁期满,李理河要求按约收回宅基和房屋,并向英德县人民法院起诉。
法院援引1950年《土地改革法》和1954年宪法规定,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认定纠纷双方的宅基地关系受当时的法律保护;后由1962年中共中央《从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1982年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归集体所有,因此纠纷双方的宅基地租赁关系依法解除,原订契约不受法律保护。类似案例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董文忠与郑明德宅基地纠纷案的电话答复,最高院认为,自1982宪法公布实施之后,必须按照宪法规定处理有关土地纠纷。
3.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88)民他字第1号。该解释已被废止.
批复针对的案情:天津市塘沽区张学珍、徐广秋开办新村青年服务站,于一九八五年六月招雇张国胜(男,21岁)为临时工,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次年十一月十七日,该站在天津碱厂拆除旧厂房时,因房梁折落,造成张国胜左踝关节挫伤,引起局部组织感染坏死,导致因脓毒性败血症而死亡。张国胜生前为治伤用去医疗费14151.15元。为此,张国胜的父母张连起、焦容兰向雇主张学珍等索赔,张等则以“工伤概不负责”为由拒绝承担民事责任。张连起、焦容兰遂向法院起诉。
法院针对“工伤概不负责”的约定是否有效时认为,张学珍等作为雇主,理应对雇员予以劳动保护。这种以招工登记表明“工伤概不负责”的行径,是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的无效的民事行为。
在1982年宪法实施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发展转型,政策变化,集中显现的具有政策导向因素的问题急需获得正当性的证明,法院以宪法规定对此加以说明,一方面是因为具体法律的规定尚未成形;另一方面也是从根本上认定相关问题的正当性。但是,我们依然难以找到直接以宪法为依据的裁判,直到齐玉苓案的出现。
4.齐玉苓案以后
宪法的司法适用案件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齐玉苓案。对于本案的性质,学者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即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审查案件。但该案引发了学者们对宪法司法实践的关注,对宪法适用路径的正当性与可行性的思考,因此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在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25号,该解释已废止。具体案情参见本文第一章,4.5.1.对权威性法律渊源的反思.中认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方式,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应承担民事责任。该案促使我们重新用法律视角审视宪法的实施,将其纳入法治的实践领域,是改变过于强调宪法政治属性、维护宪法根本法地位、实现宪法法律权威的需要。
齐玉苓案的意义并不在于对宪法司法化可行性的启发,而在于在现有体制下,它开启了宪法是否可以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的实践议题。宪法不能作为直接的裁判依据并不代表宪法不可适用。学者们的研究和法官们的实践证实,从宪法作为法律渊源的角度,宪法已然实现了其在司法领域的权威,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具体观点参见肖蔚云,“宪法是审判工作的根本法律依据”,《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张千帆,“我国法院是否可以释宪”,《法学》,2009年第4期;韩大元,“以《宪法》第126条为基础寻求宪法适用的共识”,《法学》,2009年第3期等
正如塞勒所言,“我们的法律对合法性的诉求也取决于道德价值,这些道德价值中的很多价值蕴含在我们的宪法体制中”,[24]合宪性解释以其根本、权威的方式保障着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着法治建设。有关宪法适用的司法解释影响着后来案件的审理。如保山地区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上诉杨朝富定劳动教养案[25]38-46,本案终审法院以宪法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为依据,结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认为行政机关适用规章不得与其上位法冲突,鉴于法院不具有违宪审查权,因此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由上诉人重新做出行政行为的方式维护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在另一类似案件(林树朝不符海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决定案[25]76-81)中终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海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被上诉人(林树朝)“作出劳动教养一年决定,意为平息当事人上访,却未考虑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受国家宪法保护的最根本的权利。处劳动教养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行政触犯最高等级,本应是慎重、公正。本案被上诉人是受害者,反被处劳教不慎重、不公正”。故认定对被上诉人处劳动教养,于法无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本案中,宪法成为公民人身自由获得保障的最权威的理由。
上述两件案例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据宪法相关规定,论证劳动教养决定是否符合劳动教养制度体系的精神。在现行制度既存且法院无违宪审查权的前提下,法院因宪法授予其审判权这种救济权利的最权威的方式,运用针对具体个案的合宪性解释方法,督促劳教管理机关以最接近合理性合法性的方式作出劳教决定。应该说,即使我国法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司法审查权,但其亦可运用合宪性解释等方式,在保持其司法克制的性格的同时,援引宪法规定无声地对有违宪法权威的事实予以纠正。正是司法在确保宪法实施方面无可替代的功用,公民在权利受侵害时才会求助司法程序,即使这种救济带有滞后性,但其不可不存在。
五、小结:合宪性解释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方式
与宪法相关,需要宪法作为终局性、权威性、合法性支持的案件并不在少数,尤其对于个体公民而言,宪法是其维护自身利益的最重要的武器。法院审理案件遇有法律冲突、法律规定模糊、需要依靠公序良俗等情况时,宪法是其获得审理案件依据的最重要法律渊源,对此不得有任何突破。在对比国外宪法违宪审查制度、国内82宪法前后宪法的适用情况后,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宪法的司法化不宜采用违宪审查制度,因为我国没有此制度所需要的政治土壤,但不能因此否认宪法具有可适用性。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通过合宪性解释而得以实现,实践中也有相应案例加以佐证。尽管齐玉苓案并非典型的宪法案例,但其蕴含的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司法过程中适用宪法的思考却具有强烈的理论探讨性和实践指导性。借此案的启发意义,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宪法作为法律适用语境下的权威法源,通过司法实践的合宪性解释,实现其“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宪法宣言。
虽然合宪性解释无法像违宪司法审查制度那样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但仍然以法律渊源的方式提供裁判权威,影响宪法的实施效果。如果拒绝承认它也是一种宪法的司法实践,那么我国司法领域对宪法的遵从便只剩空洞的口号而无实际的行动了。法律实践中“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26]通过合宪性解释,实现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为制度设计和人权保护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1]王人博.宪法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J].江苏社会科学,2006(5).
[2]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16.
[3]蔡定剑.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施行之道[J].中国法学,2004(1).
[4]约瑟夫·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M].朱学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143.
[5]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885.
[6]蔡定剑.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J].法学研究,2005(5).
[7]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J].比较法研究,2004(2).
[8]许崇德.“宪法司法化”质疑[J].中国人大,2006(11).
[9]谢维雁.宪法诉讼的中国探索[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172-181.
[10]韦宝平,李丰.理论与现实的碰撞:当代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困境[J].江苏社会科学,2004(3).
[11]谢维雁.论合宪性解释不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方式[J].中国法学,2009(4).
[12]韩忠谟.法学绪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93.
[13]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J].现代法学,2008(2).
[14]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3(2).
[15]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8.
[16]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9.
[17]王利明.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57.
[18]基思·E·惠廷顿.宪法解释:文本含义原初意图与司法审查[M].杜强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1.
[19]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M].周叶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24.
[20]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J].中国法学,2008(3).
[21]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2]张心向.我国“宪法司法化”路径问题之思考[J].政治与法律,2011(2).
[23]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
[24]罗杰·塞勒.法律制度与法律渊源[M].项焱,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81.
[25]王禹.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评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8-46.
[26]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J].中国法学,2008(6).
[责任编辑:岳林海]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s Appling Methods and Some Practical Cases
WU J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Taiyuan College, Taiyuan 030032, China)
Constitution has dual properties of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legal authority. It is applicable in judicature for its normality,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mandatory.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best way as the Constitution’s application in our political surroundings becaus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connection of interpretational method with explanatory material. And the present system has not excluded the constitution’s application. We can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a feasible way by the evidence from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cases.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s applicability;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2015-02-08 作者简介: 武静(1980-),女,山西盂县人,太原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司法理论与制度。
1671-5977(2015)03-0033-08
D92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