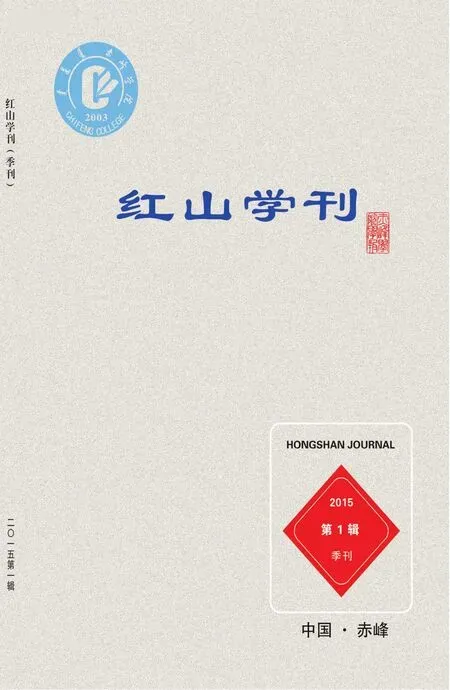赤峰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
2015-02-07乌兰
●乌兰
赤峰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
●乌兰
从地缘角度观察,赤峰这个大兴安岭余脉与燕山山脉合围成的巨扇形半独立地理单元,在历史时期一直是南面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可以从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之间的缺口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因为西拉木伦河流域不仅包括大兴安岭以西、蒙古高原的部分高地,还衔接着大兴安岭东侧的广阔的丘陵和平原地带。而燕山北麓平坦、肥沃的老哈河下游流域则是来自华北平原的华夏农耕民族与东北渔猎民族必争之地。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先民在赤峰地区留下了农耕的印迹,5000年前的红山先民在这里创建了最早的红山古国,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库莫奚、蒙古族先后从这里出发,逐鹿中原,登上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以纷呈的文化异彩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辉煌。
一、赤峰地区史前文明的考古发现及意义
自1906年起,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就已在赤峰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工作,1911年用法文写成一部考察报告《蒙古旅行》,首次向世人披露了中国赤峰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信息。1909年外国传教士在林西县创办教堂,许多传教士也开始在赤峰地区陆续展开考古调查,如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在红山一带就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于1930年寒冬在赤峰地区开展了38天的考古调查,并撰写《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一文,强调这一中国南北文化接合部的重要历史地位。同年,日本人亦开始了赤峰地区的调查采集工作。其后一直有日本考古团体在赤峰地区活动,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赤峰红山后遗址”,1938年出版的《赤峰红山后》介绍了蒙古高原史前人类丰富的遗物及生活遗迹。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尹达先生在其论著《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以“红山后遗址”为论述基点,将其定名为“红山文化”,并认为红山文化是“草原细石器文化同仰韶文化在长城接触地带而形成的一种新文化”。赤峰地区的史前第一支考古学文化的确立,揭开了赤峰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新篇章。
20世纪50年代,随着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展开(1956—1960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汪宇平先生的带领下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及赤峰市红山附近调查,发现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始建于1958年,自1959年起文物工作站在苏赫先生的带领下,在赤峰地区开展广泛调查工作,首次将考古调查工作拓展至敖汉旗孟克河、敖来河流域,发现并清理了距敖汉旗新惠镇北1公里的石羊石虎山上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内蒙古昭乌达盟石羊石虎山新石器时代墓葬》在1963年的《考古》期刊上发表,苏赫先生推测其年代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并与细石器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1960年,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成立于1959年)在赤峰地区试掘赤峰药王庙、夏家店两处遗址,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将日本人命名的“赤峰第二期文化”区分为相当于夏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相当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从田野发掘上纠正了日本人发掘工作中的混乱认识。1961—1962年刘观民、徐光翼等先生先后发掘了巴林左旗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富河沟门遗址、金龟山遗址和南杨家营子遗址。发掘者敏锐地认识到乌尔吉木伦河流域以富河沟门遗址为代表的史前文化的特殊性,并根据富河沟门遗址丰富的遗存资料,将其命名为“富河文化”。1963年,刘观民、刘晋祥先生等发掘赤峰西水泉遗址,徐光翼先生等发掘赤峰蜘蛛山遗址。西水泉遗址是一处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较丰富的遗存资料为更好地认识“红山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并进一步肯定了“红山文化的年代早于富河文化”。蜘蛛山遗址则发现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至汉初的4层文化堆积,进一步明确这4支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至此,赤峰地区在各文物机构、各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重新认识了“红山文化”,新辨识出“富河文化”及两支具有早晚关系的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并基本搞清它们的文化内涵和基本特征,初步构架了赤峰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谱系,为进一步有目的、有重点地开展田野发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3年,中断了近10年的赤峰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再次大范围展开。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敖汉旗文化馆联合对敖汉旗小河沿公社境内的老哈河、蚌河两岸进行调查。并于1974年发掘敖汉旗四棱山遗址、三道湾子遗址和南台地遗址,发掘者提出“小河沿文化”的命名,根据明确的地层打破关系,认为“小河沿文化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稍晚于红山文化”。1977—1979年,三馆再次联合发掘翁牛特旗大南沟墓地,“小河沿文化”基本确立,墓地中丰富的遗存资料鲜明显示出小河沿文化强烈的过渡特征,郭大顺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中强调其为红山文化的延续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1974年对赤峰初头郎西山根石城址进行了发掘,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1981—1985年)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与敖汉旗文化馆联合,在敖汉旗南部进行了细致而广泛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分布密集的大量史前遗存,辨识到新石器时代若干新的文化类型。80年代连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在赤峰地区展开: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1983年)、小山遗址(1984年)、赵宝沟遗址(1986年)、小河西遗址(1987年)、西台遗址(1987年)、榆树山和西梁两处遗址(1988年),翁牛特旗的小善德沟遗址(1988年)、大新井子遗址(1988年),林西的白音长汗遗址(1988年)。共发现新石器文化新类型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基本确立了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序列: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极大推动了赤峰地区先秦考古学的研究,完整而清晰的文化谱系也推动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先古秦考古学研究工作。80年代,红山文化玉器开始崭露头角,翁牛特旗海金山遗址、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和查日斯台遗址以其地表丰富的陶石器物群及地表采集的玉器,为红山文化的内涵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
20世纪90年代,新石器时代诸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聚落考古理论的指导下,遗址的大面积揭露成为发掘工作的主要工作手段。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林西水泉遗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的大面积揭露再次丰富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文化内涵。其中,兴隆洼遗址发掘面积达3万平方米,共清理出180余座房址,居室墓葬30余座,灰坑400余座,同时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陶石骨蚌玉器及兽骨、人骨、粟黍等遗物资料,由此正式提出了“兴隆洼文化”的命名。作为兴隆洼文化最重要、最典型的遗址,兴隆洼遗址是国内第一个揭露出壕沟、房址和灰坑等全部居住遗迹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址,是新石器时代罕见的保存最完整、布局最清楚的聚落。“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中,兴隆洼遗址具有学术史上的里程碑意义。”[1]
进入新世纪,敖汉兴隆沟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赤峰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2002—2003年,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兴隆洼文化中期大型聚落的大面积揭露,已为兴隆洼文化的房址、居室葬增添了新内容,为探讨赤峰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宗教观念的演变、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遗址中土样,经浮选发现少量炭化粟和黍,经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验室最终证实,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小米种子,比欧洲早2700年。兴隆沟遗址也同时被学术界定为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旱作农业的起源地。第二地点红山文化遗址是赤峰地区首次发现的重要的红山文化晚期环壕聚落。2012年,第二地点红山文化陶人的发现则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红山文化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的重大成果。2009—2011年,赤峰魏家窝铺红山文化早中期高等级聚落址的发掘,为我们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古代生态环境与生业经济、古代赤峰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热点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
二、兴隆洼文化是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距今8000年,星星点点村落的出现给北方大地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河南贾湖遗址(5.75万平方米)、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8千平方米)、赤峰兴隆洼遗址(5万平方米)及更多不到1万平方米的遗址,成为一座座地理人文景观与自然和谐一体。中国的原始先民们筑屋而居,设围壕为界,墓地与聚落比邻,聚族而葬。彩陶、骨笛、玉玦、山坡上的粟地,这些新事物出现说明社会的各方面都有了新变化。
植物考古研究证明,“大约距今8000年,北方各地分别出现发展水平相似的旱作经济文化。粟黍类农业起源与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定居社会的产生可以说是同步的。在北方新石器定居社会产生的同时,以黍类为主要类补充的植物取食结构就相当普遍,从东部的兴隆沟到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文化,再到甘肃大地湾遗址,基本上贯穿了整个北方地区;从人骨的稳定同位素数据看,北方新石器先民以C4植物为主的取食结构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这意味着黍粟类不仅相当普遍的被利用,而且是取代野生食物资源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可以推断定居聚落的出现,就是北方旱作农业的开始”[2]。
尚处于农业经济形成过程中早期阶段的兴隆洼文化,农作物虽然只是人们生计中十分次要的补充,但农业意味着人们从此拥有了一种稳定的食物来源,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食物来源在人类精心的培育下能够继续增产。而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的增长不仅为人口的增加带来的便利,还为家畜的饲养提供了契机。动植物考古学研究说明,猪的驯化似乎比粟黍类驯化时间要略晚一些。较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定居生活还让人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来改进生产和狩猎用的各种工具,发明创造更实用的生活用具,其文化上的繁荣不仅只是在陶器和石器上的改变,还扩充至居址、墓葬和装饰品。“在兴隆洼文化阶段,一种全新且明确的文化区域产生了,它比旧石器晚期的文化区域清晰多了。这意味着此时的人们有确定的可以求助的对象,他们也对有求于自己的人们作了明确的限定。”[3]
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的需要,手工制造业也在不断处于发展与变化中。石器以打制石器为多数,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各占一定比例。细石器应是一种多用途工具,它不仅是复合工具的必需之器(如骨梗石刃刀),更主要用于刮削、切割等。它是狩猎经济仍占较大比重的主要标识物。斧、锛、凿多为磨制,但多是刃部精磨,应主要用于加工木料;磨制石器中磨盘、磨棒的数量最多,说明植物类加工频率大大增加,应与农业有一定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兴隆洼文化时期是赤峰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是玉器、筒形罐和之字纹的源头,是东北文化区诸多文化因素的开创者,是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重要的奠基者之一,并对后期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影响之深远甚至是之后的任何文化都无法企及的。
三、赵宝沟文化为红山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
继兴隆洼文化而起的是赵宝沟文化,其年代为距今7000—6400年。赵宝沟文化的分布格局与兴隆洼文化大致相同,继承并发展了兴隆洼文化筒形罐、之字纹、细石器等典型文化因素,又出现了更多的新文化因素,如石耜、尊形器、斜口器、圈足钵、几何纹等,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赤峰地区极具艺术创造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后期红山文化的繁荣发达创造了重要条件。
赵宝沟文化时期,石器制作技术更为进步,与兴隆洼文化相比,细石器仍然发达,磨制石器的数量大增,打制石器的比例相对兴隆洼文化时期明显减少。磨制技术能使工具的形体更加固定,更为适用,能大幅度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石耜的出现说明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耜是古代一种装柄的农具,是由木耒(一种掘土用的尖木棒)发展而来,分耜和耜柄两部分,耜柄下部常有脚踏横木,利用深挖。土地被深翻,地力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谷物产量大大增加。结合赵宝沟遗址出土的较多猪的骨骼,动物考古学鉴定可能为家养,这就为认定赵宝沟文化农业有了一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旁证。赵宝沟文化的聚落从高度上也较兴隆洼文化有所降低,兴隆洼文化多选在坡上的林缘地带,而赵宝沟文化则多选址于坡下,也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赵宝沟先民因农耕的需要而对河谷地带的依赖性已较兴隆洼文化时期大大增强。
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反映在生产工具上,它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带来诸多变化。赵宝沟文化种类丰富的陶器群完全颠覆了兴隆洼文化时期单一的器型和单调的装饰风格。器型的多样化及盛食器数量的大为增加,说明赵宝沟文化时期的饮食方式已经有了变化,这亦是赵宝沟文化时期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直接证据。
赵宝沟文化时期,单独祭祀区及相关祭祀礼器的出现说明原始宗教有了长足的发展。“祭祀遗迹在赵宝沟遗址南部的东侧,坐落在坡地顶部凸起的平台上。台址直接建筑在生土上,堆积为黑灰土,用石块垒砌,筑成一圆角方形的平台,四面坡状,占地300多平方米。祭祀区的单独设立说明集体式祭神活动已成为重要的仪式活动,在仪式中神的世界也被人为地分成了各个等级,为宗教的统一和社会的分层铺平了道路。“赵宝沟遗址出现与居住区相对应的独立祭祀区,是西辽河流域聚落布局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为红山文化晚期远离居住区的大型祭祀中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4]
赵宝沟文化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调查所获遗址的数量明显是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数倍,遗址的面积也明显扩大,说明此时人口也得到了增加,劳动力的增长和劳动技术的提高促使手工业制造业最先发展了起来,甚至有了初步的分工和生产专门化,聚落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宗教的地位也在此阶段开始变得突出。赵宝沟文化是赤峰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为红山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
四、红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
早在20世纪红山文化发现之初,梁思永、裴文中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就将其定性为“是中原彩陶北上,与北方细石器遗存在长城地带相遇,从而形成的一种‘混合文化’”。随着发掘资料的不断丰富及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混合文化”的面貌也逐渐清晰明了。“距今6500年,随着半坡—西阴文化集团北上的压力逐渐增大,北部的后冈文化集团只能逐步退却,以至在洋河谷地失守后,一败涂地,最后在西阴文化的压迫下,只能就近窜往历史上文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燕山以北地区。当后冈文化北部集团的居民流窜到燕山北麓地区时,这里盘踞着赵宝沟文化。大批后冈文化人群的直接融入,势必会导致原有系统框架的调整或文化的重组,从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红山文化的出现应当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直接结果。随着后冈文化退出历史舞台,新生的红山文化开始直接和黄河流域面向亚洲腹地文化系统发生联系,而红山文化在阻挡住西阴文化(即庙底沟文化)北进步伐的同时也不断调整、壮大着自己,不久,兼容了三大文化系统(先后兼容了磁山文化、后冈文化、西阴文化)优势的红山文化开始迈出了奔向新时代的脚步。”[5]
红山文化的兼容,是在发扬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兼容并蓄,红山彩陶就是博采众长之后的集大成者。瓮、钵、盆、罐、豆、盘、壶、器盖和器座在精美的彩绘图案衬托下熠熠生辉,彩陶筒形器在黑彩的衬托下显得肃穆庄严。苏秉琦先生更是将红山文化居民称为“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并指出华(花)与龙的结合,是中国人自称为华人和龙的传人的历史渊源。
灿烂的文化背后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红山文化中、晚期(距今6000—5000年),农业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石耜已经被改良成磨制更加精细的宽身窄柄尖弧刃石耜,木柄与石耜的窄柄部分结合更为牢固,宽身尖弧刃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在收割工具方面,在红山文化中期以后,大量出现的磨制长方形或桂叶形双孔石刀使得收割更为容易。传统的细石器加工技术已极其成熟,除常见的细石叶和石核外,三角形石镞大量使用,助推了渔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红山文化时期,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依旧发达的渔猎—采集经济给予了有力的支撑,二者有机互补,开创出辽西地区前所未有的生业模式,为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稳定而充实的食物来源使红山文化先民过上了真正“田园牧歌”的生活,长时间的积累后,红山社会发生了一次大跃进。“考古记录发现,此时的人口突然地大幅度增加了,村落的密度数倍乃至数十倍地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时期。例如在今天赤峰市敖汉旗境内共发现了红山时期的遗址502处,是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遗址数量总和的数倍,又同在赤峰市的西部,于7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红山文化的遗址125处,也数倍于此前。人口大幅度增加,社会组织也相应复杂起来。这些红山村落一般沿河分布,不同流域范围内的村落各自聚成群落。这样的群落,在赤峰西部地区有13个,在敖汉旗有11个。一个群落内部,其村落数,有的几个,有的20余个,数量不等,其中,有的面积较大,似乎是群落的中心或核心。群落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例如赤峰西南部的6个群落,彼此距离较近,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关系要比其他群落密切得多,似乎结成了一个更大的社群集体。”[6]兴隆洼文化时期平均分布的聚落人文景观此时已经不复存在。这些大小不一且联合成群的群落的出现,说明至少统合掌控几个聚落群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聚落集群化现象的出现、聚落间等级的分化,再到一个聚落内部社会成员地位的分化在红山文化时期持续发展扩大着。红山文化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无疑已经在逐步加快。
红山文化时期,“唯玉为葬”“以玉事神”“唯玉为礼”的精神理念逐渐形成。红山玉器反映了宗教信仰在红山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唯玉为葬”的积石冢群也透射出红山社会等级化、礼制化的渐进过程,而社会的分层与分化,正是文明产生的基础。玉器正是红山文化最为核心的文明要素。红山玉器的材料主要以岫岩玉为主。勾云形佩、玉鹰、玉鸟、玉鹗、玉龟、玉鱼、玉猪龙、玉带齿兽面纹佩、玉斜口筒形器、玉刃边璧形器、玉环、玉棒形器、玉勾刀形器等,这些各形各色的玉器因使用者身份地位的差别而成了表达这一差别的媒介,玉器也被人为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
红山玉器是积石墓中唯一的陪葬品,墓主人以石为墓,以石封墓,葬于山之巅,墓室宏大壮观。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些小规模积石墓,墓主人也只随葬玉器。这些小规模积石墓或将大墓围于中心,或仅安于大墓的两侧。高规格大墓与数十个小墓形成一个冢群,整个冢群仍以石为界框,其下再以石封,形成一个积石冢。每座积石冢占地面积有三四百平方米,最大的能达一千平方米,封冢石堆高度多在1米以上,整个冢体或圆或方,高高盘踞在山岗之上。有的积石冢附近还设有圆形石砌祭坛,坛冢结合,蔚为大观。这些积石冢群星星点点分散在今天的辽宁建平、凌源、喀左三县交界处牛河梁上,牛河梁是大凌河与老哈河之间的多道呈西南—东北走向的山梁,近20处积石冢就分布这些山梁顶部的诸山岗上,冢群的分布范围广达50平方公里,没有发现日常生活遗迹。
20多处积石冢群环绕的中心区域即牛河梁第1地点,更是一个极为特别的所在。“它位于一面山坡上,坡顶是一组总占地约4万平方米的大型平台。平台分3座,排列成‘品’字形,台边皆有石块堆砌的护坡。台面上有多座土坑,内埋有陶器之类,似与祭祀活动有关。平台下方是一座面积75平方米的神秘的半地穴建筑。建筑内墙上绘着精美的朱彩图案,建筑内摆满了泥塑作品,其中人的塑像有的如真人大小,其眼睛由绿松石镶嵌而成,看上去应为女性;也有两三倍于真人的大型塑像,以及众多禽鸟走兽造型。出于谨慎,这座建筑至今还没有全部发掘清理出来,其中的秘密也远未完整昭示。但仅就已有的发现,这是一座庙宇,供奉的女性或者就是红山人的先祖。”[7]牛河梁这个面积达50平方公里的山梁,至今还没有发现日常居住生活的遗址,只有石质的冢群、土质的庙宇,冢群里只有石之精华——玉与墓主人作伴,庙宇里只有祖先与泥塑制成的飞禽走兽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圣域”。是死者想在这里得到永生,亦或是生者想要祖先永保他们兴盛不衰。
“宗教总要不同程度地反映现实社会。红山文化宗教遗存宏大的场面、高上的规格、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也应当是现实社会高度复杂化的反映。更何况如此大体量宗教建筑群的修建当要动员很大范围内的人群,没有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是难以完成的。红山文化玉器美妙天成,彩陶构图严谨规范,其制作都需要很高的工艺水平,当时应已存在专业制玉和制陶的工匠。这些都昭示红山文化晚期应该已经进入苏秉琦所说‘高于部落之上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古国’阶段,已经迈入初始文明社会的范畴。”[8]李伯谦更明确地指出:“在红山文化时期,特别是它的晚段,当时社会虽已发生分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所谓‘公共权力’已经存在,但掌握、行使这种‘公共权力’的并非世俗的‘王’,而是这些掌握着通神权力的巫师或曰‘神王’,神的权力高于一切,神的威望高于一切,社会的运转、社会矛盾的调节都靠神来解决,而神的意志和命令则统统要由能与神沟通的巫者来传达来贯彻。从其身份最高的大型墓葬墓主随葬的玉器观察,‘红山古国’有玉猪龙、箍形器(玉斜口筒形器)、勾云形佩、玦、璜、坠及鸟、蝉、龟等祭祀用玉而不见表示世俗权力的钺等兵器,红山文化古国走的是清一色的神权道路。”[9]
赤峰地区,是联结世界东西、沟通南北的文明交汇区域。凭借其相对开放的地理区位,在一次次文化撞击与兼并的大浪潮中,出色继承并发展本土文化,同时与外来文化因素互相渗透,兼容并包,逐渐形成一个独具特色又与周边文化有密切联系的考古学文化区,在全国范围内领先一步,进入初级文明社会,成为早期中国多元一统文明体系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1〕刘庆柱.玉器起源探索(序).刘国祥,邓聪,杨虎.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
〔2〕秦岭.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与展望.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
〔3〕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考古学报,2011,(1).
〔4〕刘国祥.富河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文物考古出版社,2005.
〔5〕乔梁.后冈、西阴与红山——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中国北方的态势和文明的崛起.鹿鸣集.科学出版社,2009.
〔6〕〔7〕赵辉.中华文明的初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科学出版社,2009.
〔8〕〔9〕李伯谦.从中国文明化历程研究看国家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