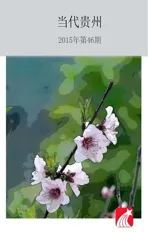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命运
2015-02-05姚源清
文丨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 程 星 姚源清
从“意”转向“真”
你曾将自己的个人艺术画展命名为“务本”。你认为中国画的“本”是什么?
陈履生:中国画包含绘画的基本定义,但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绘画。中国画是夏山烟雨、雪景寒林、曲水流觞、西园雅集……中国画还是与叠石造园、品茗畅饮、拜石书蕉等等相关联的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趣和生活理想,它们共同构成了文人艺术的内核。在中国画家和文人的文房中,除笔墨纸砚之外,还有臂搁、笔洗、书镇、砚匣、印泥、图章等等,各有各的讲究,尽显风雅。所以,中国书画也是风雅之物,是中国文人特有的品格与境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书画的意义就是通过心灵之“文”的表现而得到一种性情发挥。
我把“务本”作为展览的标题,这是我对当代中国画现状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既有理论上的,更有创作实践上的,比如我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和书画实践当中,就尽可能以中国传统绘画的品评要求来连接我们和古人,和文人画情境中表达的那份感觉。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是我多年以来的一种理想,希望中国画回归于中国画独特性的一种文人情境之中。
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画经历了世纪之交后的磨合,如何在社会形态的转换中完成历史的过渡?
陈履生:从1911到1949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具有实验性的地方性画派的出现,成为了时代的主要特色。当康有为在参观罗马教皇梵蒂冈皇宫中的拉斐尔的四组壁画后,感叹“生气远出,神妙迫真”,康有为所赞誉拉斐尔“开创写生之功”中的“创写阴阳妙逼真”,表明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绘画审美开始出现了由“意”转向“真”的变化。而这个“真”即是合乎现实的真实(形似),而此后从国外学成归国、开创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一批画家,所关注、倾心的即是这种“真”,所传授的也是这种“真”,传统国画自然也受到影响。
在绘画题材上,民国时期的中国画以1938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后一时期,因为抗战,傅抱石画《屈原》《苏武牧羊》,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不仅表现了国人的灾难和自强的信心,同时还以文人的心态表现了家国之痛,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导了传统水墨画重走现实主义的道路,将几百年来水墨画以模古而凸现的“逸”的思想,转入到关注现实和人生的新时空和新境界中。
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画尤其是水墨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不仅是水墨画,与之相应的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因为家国命运的变化所带来的审美上的变化,最鲜明地发生在中国画之上,实际上也是给传统中国画的改良以历史的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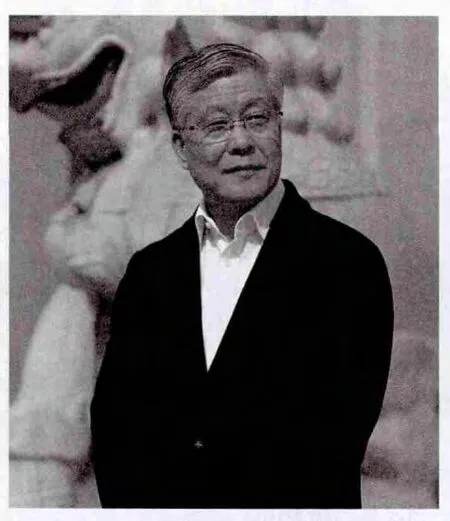
本期访谈嘉宾: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先后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建有私人博物馆“油灯博物馆”。(逄小威/摄)
从 “文人画家”到“文艺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水墨画命运如何?这一时期,中国画画家自身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陈履生:水墨画变化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带来了不断的论争,其焦点反映在绘画的本体上——文人因为时代变化而出现的选择差异。1949年以后,水墨画所面对的是一个历史的决择。
在海峡对岸,随着国民党政权移居台湾,中国的水墨画文化传统与台湾地区日据时代所形成的绘画现实形成了激烈的对抗,在日本画与中国画的争论中,确立了中国传统水墨画在50年代台湾地区的主导地位。由黄君璧、溥心畬开辟的师大艺术系的水墨画教育则成为台湾地区水墨画发展的原动力,其接续中国水墨画艺术在台湾地区的发展的同时,也在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文化特点的水墨画新传统。
而在大陆,原本属于自我的文人绘画,在1949年之后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体制的革命工作,文人画家也转变为文艺工作者,通过从思想上去除文人脱离现实的清高,行为上将画家从书斋画室引向现实,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培养与真山水、真现实的感情,从而激发起画家表现现实的激情,使艺术能够服务于现实。从1953年开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多次组织画家到北京近郊各风景名胜点写生,1954年春,吴镜汀、惠孝同、董寿平到安徽黄山、浙江富春山一带作写生旅行。李可染、张仃、罗铭赴西湖、太湖、黄山、富春山写生,并在北海公园举办了《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
在艺术服务于现实的状况下,国画如何随时代而发展?
陈履生:当电线杆、火车等新的题材,染天染水等新的画法大批出现的时候,“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的讨论应运而生。作为美术界主要领导之一的蔡若虹也在会议上明确地指出:“重新提倡写生,就是请画家们退出死胡同走上现实主义大道的第一步。”此后的第二步就是表现新的生活——表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在运动叠起的年代里,国画家以满腔的热情紧跟党的文艺方针,表现时代的主题。为了繁荣国画,也为了新的国画在新的社会中的地位,以傅抱石、李可染为代表的一批国画家努力开拓新的题材,以表现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的作品使国画得到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广泛重视。到1956年,国画的改造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发展国画艺术》,此后国画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革命,却将“新国画”的根基毁于一旦。
在1949年后的17年里,各个不同阵营中的国画家们都在努力寻求文人与现实之间的契合,他们在画面中的各种探索实际上就是解决如何用传统的笔墨表现现实的生活,如何化解文人的意境服务于政治的需求。可以说,60年代的大陆水墨画所表现的社会现实,既提升了水墨画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代表作品,并形成了一个表现现实、服务现实的新的水墨画传统。
从“新文人画”思潮到“文化自觉”
改革开放后,西方艺术思潮的涌入是否对中国画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陈履生:80年代的艺术思潮所反映出的反叛心理,一方面是回归传统文人画的情境,以期和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新国画”拉开距离;另一方面是连接西方现代艺术的潮流,以反叛传统而高举“现代”的旗帜。这一古一今两种思潮的貌离神合,推动了二十世纪末期大陆水墨画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画的发展因为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又因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更加关注中国艺术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独特性,所以,中国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一轮的回归传统的潮流。
在二十世纪末期的水墨画的表现中,既有换了名称、本质上与传统水墨画没有区别的古典型的“水墨画”,也有以西学为依托、运用水墨材料的现代型的“水墨画”,还有借助水墨概念的不是“水墨画”的另类的“水墨艺术”,例如水墨装置等等,水墨成为当代艺术的中国元素或文化符号,在当代艺术的基本格局中占有特别的比重。水墨画的时代流向从单一的主流,变成了不同流向的三条支流,显现了当代文化的多元化的背景。可以说,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画以多元的方式为二十一世纪的发展作出铺垫,这一时期已经不以反映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为成就的标志,而以某种风格获得声名的代表性画家则不断出现,并形成新时代的特色。
当代中国画存在哪些问题?你如何看待中国画的未来?
陈履生:时至今日,水墨画在要不要吸收和借鉴西法的问题上已经解决。但艺术家基于社会发展的选择,时常有着社会诸多关联的关照,一种纯粹的文人理想几乎难以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实现,而经过时代风雨的洗刷后,文人的笔墨也无法为人们展现一个正脉的体格,与之相关的批评准则的建构也如空中楼阁。
另外,多样性缺失也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要保持中国画的特色,我想一方面是我们要保留中国文化的特色,一方面要有更多的地域特色,以共同维系中国画多样化的存在。只有多元的地方文化才有可能构成一个丰富的、有独特内容的中国画的特点和特色。贵州的国画题材坚守于表现乡土,整体能看到生活气息很浓,经历多年发展,在融合民族民间文化方面有很多亮点。
水墨画在难以预料的发展历程中还将延续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未来面貌有可能是一个具有宽泛概念的复合体。但我相信,伴随着中国的强盛,中国水墨画会像“中国”这个概念一样,自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中既富有特色、又具有强势的一种绘画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