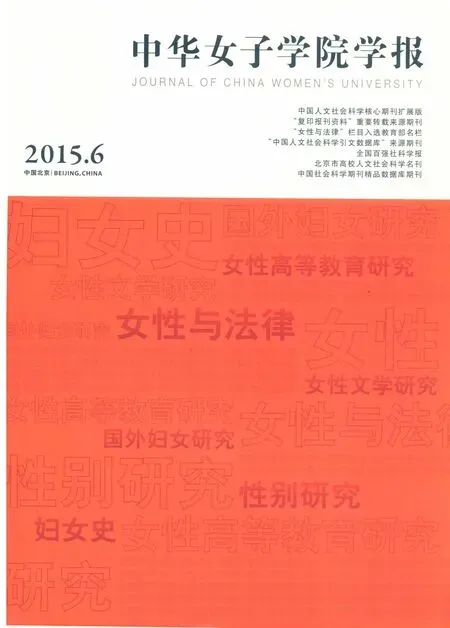“家”的隐喻
——论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后现代性
2015-01-31肖霞
肖 霞
“家”的隐喻
——论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后现代性
肖 霞
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反动,是一种社会心态和社会文化思潮,是经济发展步入大众化消费后自然形成的社会现象,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重建。20世纪后半期的日本社会,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特性,从而为女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女性文学作品具有浓厚的后现代特色,充分反映了日本现代女性作家新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生活态度。
日本女性文学;后现代性;价值取向
日本战败后经过60余年的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时已进入到了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时代。与此同时,战后民主运动推进过程中宽松的民主氛围给女性接受教育、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女作家。她们凭借女性特有的感受揭露战争,针砭时弊,抨击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从自我出发,描写现代女性的感受与不适,探讨当今社会中新型的家庭关系、母性问题,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情怀与追求。她们的作品不论从内容、题材还是从语言、形式上都突破了传统的束缚,表现出巨大的文学张力。同时,她们以自身的生活感悟去消解传统家庭的桎梏,用人性的崇高超越种族的羁绊,用现实的身体和后现代的视角去书写当代女性群体的期许、思考与焦虑。这些不断引起社会争议的作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日本现代文学的百花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代日本文学的发展方向。
一、文学解构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重建
高效的经济生产和商业销售能力,使社会蹈入信息化、复制化、雷同化以及大规模生产的发展状态之中,而由此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异化现象在对自然的压抑中试图控制人的本身。其结果导致人与人之间、事物之间界限的模糊,更大地趋向偶然性和机遇性。
在日本,社会文化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典型的后现代特性:休闲和消费优于生产,娱乐和游戏日常化,一夫一妻的基本家庭形态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其既有的结构模式不再固定不变,而是呈现出逐步松动和瓦解的状态。尤其是泛民主主义的泛滥使得公民权得到极大伸张,个人自由极端化和自律化此消彼长;同时,社会也进入一个自我解构、自我修复的后现代境遇之中。当时的日本社会出现了三个值得关注的思想倾向:一是脱合理主义,即人们对近代社会特征的合理主义价值观反感,并试图在非效率、非合理的行为中找出意义;二是脱构造化,即近现代的文化整合迟缓,在约束人们的价值观、社会规范不断变动的同时,人与人差别的界限变得模糊;三是类像的优越化,即相对于重视创造性、原创性的近现代价值观,大量的模仿与复制化盛行,其文化意义也逐渐变得深刻。[1]14-15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家庭和各种社会组织越来越松动,逐渐失去其稳定性,进而使得整个社会架构在“去中心”化的蔓延中变得松散。这种碎片化的状况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则进一步增强了社会的风险性。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范畴,作为一种心态、思维模式和文化范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类活动的新模式,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和论述策略,同时也是对新的社会和新的文化正当化方式和程度的一种质疑和挑战。”[2]3这种新的文化范畴,呈现出对现代文化和以往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以及重建人类文化的新原则。它所批判的,不是一般的普通文化,而是发自远古,经过文艺复兴、不断充实之后的现代资本主义文化。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二战后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潮,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从文艺思想与创作技巧来看,是现代主义文学在战后的延续和发展。由于其表现出诸多特征,用传统的“现代主义”无法涵盖,故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包括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黑色幽默派、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最大表现,是在后现代多元文化语境中以宽容并包的姿态追求差异性。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1)彻底的反传统。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文学和艺术应该是建立在对现有秩序的解构基础之上的,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具有反叛特色的“破坏性”文学,即所谓的“反文学”。(2)摈弃“终极价值”。后现代主义作家不愿意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道德、美学等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不仅无视对这些问题的关切,不再试图给世界以意义,而是重视生活与艺术。(3)崇尚所谓“零度写作”,将现代主义的深沉意识平面化。后现代文学关注“写作”自身,作家往往蓄意让作品中各种成分互相分解、颠覆,让作品无终极意义可寻。(4)后现代文学蓄意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出现了明显的向大众文学和“亚文学”靠拢的倾向,试图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5)作品中人物个性和事件经历可多角度解释。作者不给予任何一个人物一种特定的社会定位,而是由读者自己去定位。此外,文体上惯用矛盾、交替、非连贯性和任意性、短路、反体裁等手段,往往使人有晦涩之感。[3]
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开始,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多元文化共生与大众化消费的社会形态。在个人价值观与道德方面表现为:(1)极端个人化与利己主义。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促使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个人化日趋发展。它使“早就存在的变迁朝着个人化的方向前进,且以一种更强有力的方式出现,认为个人权力高于任何其他义务”。[4]56-61(2)对政治与权威的冷漠,重视自我发展与社会平等。丰富的社会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高度的安全感促进了个人化倾向的发展,国民不再关心政治,并表现出对政治与权威的漠视。由于强调个人主义,打破了以往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婚姻观、职业观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具体到婚姻问题上则表现出较大的自由度,女性可根据自我的意愿结婚、晚婚或晚育,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自我的价值。(3)热情丧失与反叛制度,追求自我的实现。这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年轻一代不再努力追求学习成绩与获得较好的职位,而是随心所欲,任意弃学;另一方面,具有大学文凭并进入满意公司的年轻职员,不再如父辈那样遵守职位终身与年功序列,而是要求按照智力与能力分配职位,以尽早实现人生价值。(4)个人主义的发展动摇了传统道德的基础,道德规范出现多样化趋势。现代日本人多以自我需求为中心,而不是保守地固守传统,以家国为中心。(5)极端个人主义往往导致人处于迷惘状态,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随波逐流,有的甚至有悖道德规范,出现新的社会问题。
在这种社会背景中涌现出许多富有特色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无形之中刻上了后现代主义的烙印。就女作家而言,她们除了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女性生存、女性处境,探讨女性解放的多种途径外,在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里以敏锐的感受性与独特的视角捕捉社会的聚变过程,通过自己的作品如实描写了后现代社会的各种形态,例如,家庭解体与个体自我的内心孤独,生活方式的自由带来的精神游离,解构传统的家庭形式并尝试建构新的家庭模式,忽视男女之间的恋爱描写,尝试建构新的人际关系和婚姻模式等等。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文坛活跃的女作家及其创作来看,主要可推吉本芭娜娜的《厨房》(1987)、《悲哀的预感》(1988),村田喜代子的《锅中》(1987),柳美里的《客满新居》(1996)、《家族电影》(1997),江国香织的《一闪一闪亮晶晶》(1991)、《沉落的黄昏》(1996)等。
二、“家”是悬空的月亮
“家”是悬空的月亮,照着你、照着我,也照着他。当有一天月亮不见了,不是被天狗吃了,就是被乌云挡了,或者是你自己用“五指山”把自己的眼睛遮了。当你阳光灿烂的时候,月亮默默地为你祝福。当你迷茫的时候,月亮的光辉就会在黑暗中为你呈现。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随着经济高度增长带来的就业结构的变化,家庭生活中的经济活动功能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家庭的解体和核心家庭的形成。于是,过去那种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意识,逐渐让位于个人意识;自我生活的强化使得离婚、分居以及终身不婚的社会现象司空见惯;我成为社会和家庭的“孤儿”,倍感孤独。日本现代评论家川村凑指出:“80年代至90年代的‘新文学’,其主要的主题设置的重心是从家庭崩溃向孤儿感觉转移。‘家’的解体与个人的孤立化。那也许不是今后要写的‘新文学’的主题,毋宁说应该成为那样的文学的前提。”[5]223柳美里在90年代的作品中主要描述了家庭问题。她曾在与辻仁成的对谈中阐述了自己对家庭问题的看法,“对于小说家来说,‘场所’很重要,如果一定要我举出我的场所的话,那就是自己成长的家庭。我的情况是小学五年级时家庭离散。因为是在日韩国人,不能与其他人一样共同具有国家的概念,不能构建普通的家庭。所以,相反地作为‘不具有者’,很想看看家庭这一共同体。正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它才成为社会的缩影。深究的话,它能涵盖人际关系的所有。我总这么认为,描写家庭的崩溃,就能描述世界的崩溃。”[6]
柳美里的《客满新居》发表于1996年,场景设置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欣欣向荣的都市,表现了现代社会生活场景中的家庭悲喜剧。开头部分以父亲在二十几年前刚搬到横滨西区之后,在母亲的唆使下买下百余坪的土地上“建房子”这一父亲的口头禅开始的。那时的四口之家非常幸福、和睦。父亲的这种话,我(素美)与妹妹早在16年前母亲离家出走之前就常常听到,但一直没有实现。一个月前父亲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特地将离家别居的两个女儿叫来视察新居,希望妻女能回来团聚,重温过去理想的家庭生活。这个四口之家原本十分幸福,但后来由于父亲的怪癖与不务正业,导致家庭破裂。小说这样描述道:“父亲有捡拾大型垃圾收集处的电器产品、偷盗附近邻居家盆景的毛病;所以,那个二间六叠和一间四叠的西区的家,堆满了别人用过的旧东西。”[7]13对此,母亲忍无可忍,虽然两人争吵变成了家常便饭,但夫妇两人不吵架的日子更是使人感到不安。分居的直接原因不仅是这些,父亲作为扒金库店的老板,拥有十几家分店,当时月薪就有80万,但他每个月只给家里几万日元作为生活费,其他都用在赛马或赛自行车上。对此,家人不能理解,“我”也不知道是父亲的经济观念本来如此呢?还是他想让我们体验一下他自己所度过的极为贫困的童年时代的苦难呢?作为女儿,她曾看到过从帽子、西装到手表、皮鞋等一流打扮的父亲,也了解过于吝啬的父亲的作为;而处于奢华和吝啬之间的父亲让她感到不可思议。自从被父亲叫回看了他刚建好的新居之后,素美一个多月没有再去,她不想与父亲相见,其理由主要是“自从母亲离家出走后,她从10岁到16岁的时候,就不断地在西区的家和母亲与男人同居的楼房之间往来。之后的十年间,她与双亲分居。在她看来,也许父亲为了再一次挽回已经离散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才建了新房,但在她心里,家庭早已解体了。”[7]44妹妹更是如此,自从第一次来新居时就表示不会再来。后来,父亲将流浪汉一家四口带回新居开始共同生活,重新体味家庭生活与温暖。由于流浪汉子女的恶作剧,新居最后毁于火灾。小说描写了家庭离散、希望回归的主题,同时也反映了日本9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日益浮躁的社会现实。“父亲”作为现代社会男性的代表,收入很高且有地位,但他性格扭曲,随心所欲无视家庭的存在,结果导致家庭分崩离析,致使家人疏离而各奔东西。当他随意逍遥之后忽感家庭的重要,又回归常态建造新居,期望已经离散的家人回家团聚。他那病态与随心所欲的心理状态,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人性的扭曲,以及无视传统的极端个人化对家庭的冲击。
吉本芭娜娜1988年发表的小说《悲哀的预感》中的女主人公弥生,生活在一个幸福、明快的四人家庭中,但总感到家人有所隐瞒而内心孤独。她有一个姑妈名叫雪野,是私立高中的音乐教师,30岁仍孑身一人独自生活。在她看来,这位姑妈“面孔异样地美,但身着打扮却十分土气”。在家里,她总是如同穿着睡衣那样地不修边幅,一幅悠闲自得的样子,给人一种不同于常人的俏丽的美。这位奇特的姑妈生活随意,甚至可以说毫无生活秩序。弥生总感到,她的生活方式和处事行为和她“不管干什么,看上去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和美丽动人”。这样的一位姑妈,其行为举止常常使周围的人感到不可理喻,但弥生却像得到某种启示一样,总想接近她。一天,她悄然背着书包离家来到姑妈家住下,二人一起度过的“透明的时间”,让她感到充实而又值得回忆。她甚至觉得,二人共同拥有的、由完全偶然产生的时间空隙的空间十分幸运,其后才感到其价值巨大。一天下午,当姑妈弹奏的钢琴声消失在无际的天空中时,她悄然无声地外出了。为了寻找姑妈去何处的蛛丝马迹,弥生找到了“家庭最后旅行”时去青森时的小册子以及留有父亲笔迹的“电话号码”,她潜意识地感觉到姑妈一定去东北了。为了找到神秘的姑妈,弥生坐上了去“盛冈”的新干线。在车中,弥生回想起全家人最后的温暖场景:“父亲喜欢到百货商场买盒饭,按人头买几个不同种类的来,然后在院子里扯上电灯,如同夜间野游那样大家一起吃盒饭。父亲经常在院子里睡觉,三个人要么搬动父亲,要么由母亲在院子里铺上被子,不管做什么,大家都非常愉快。姐姐常常在睡着的父亲的脸上毫不留情地变着魔法乱画,父亲毫不愠怒地照着镜子微笑着。有时候在睡着的姐姐的脸上用笔画上胡子进行反击。他,的确是那个时候,刚刚买了一辆崭新的汽车……所以,开车出去了。”[8]152过去的经历犹如梦境再现般地浮现在脑海,令她无比怀念。那时,弥生与她年龄相差不少的姐姐在一起,总感到安全与温暖。姐姐经常在傍晚时分牵着她的手走在“古老的商店街”,感受着人们亲切的问候,以及“抚摸头皮的大手和笑脸的温暖”。可是,那美丽的傍晚时分,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总伴随着一种令人感到悲哀的预感。在东北部的“恐山”,她终于见到了姑妈。她也是来追寻过去家庭温暖的最后时光,二人同时回忆起那次事故前父母的音容笑貌,感到无比欣慰。可以说,这次东北之行,弥生并非失去了姑妈和弟弟,而是用这双手发掘了“姐姐与恋人”,她“犹如寻找失去了的家庭的面影的摇动那样”。原来这位奇特“姑妈”就是她过去的亲姐姐。可以说,小说以虚幻、疏离的情节描写了失忆少女的梦幻,表达了现代人对丧失的家庭温暖的追忆。购买汽车、家庭旅行、交通事故、完好家庭的支离破碎,无不是日本人进入高度消费社会后的生活表现。成年女性的独居生活和未成年女性的寄养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人际关系,表现了现代家庭并非血亲的组合模式。
从以上的女性写作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柳里美还是吉本芭娜娜,她们描写家庭崩溃的目的和寓意非常明确,即在冥冥之中寻找因家庭崩溃而失去的弥足珍贵的东西,为心灵深处那些零碎的和破损了的美好记忆寻找安居之所。
三、“家”是血液中的遗传因子
“家”的感觉,不会因为没有婚姻关系而消失,也不会因为没有血缘关系而减弱,它是溶解到人类血液中的遗传因子。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它大而无形;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在那儿。你可以无视它的存在,但你永远不会让它消失。
村田喜代子的小说《锅中》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说描写了少女“我”(多美)和弟弟、表兄妹等四人在暑假期间来到乡村奶奶家小住期间的内心感受与自我精神世界的孤独,以及自我成长的经历。奶奶今年80多岁,骨瘦如柴,但身体矍铄,一人独居乡村。暂住奶奶家,时常与奶奶的交流,使“我”大体了解了自己的家族:奶奶的兄弟姐妹一共有13人,有的为浪漫之恋丧失性命,有的患病发疯而死,有的远走他乡思念故乡,目前健在的只有几个人了。作者以寻根的形式,让年迈的奶奶用家族故事传承历史,以此引发少年少女对自我身世的关注,从而在冥冥之中产生恐惧感。由于她年事已高,所讲故事断断续续,含混不清也不连贯,亦实亦幻充满谜团。“我”在她那凹凸不平的脸上看出了她内心的“孤独”,更加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感兴趣了。后来得知,“我”并非父母亲生,而是姨奶奶的女儿麦子的孩子。麦子生下我就去世了,“我”被奶奶的儿子(信次郎的父母)夫妇养育成人。而我的父亲,在我没有出生就已离世了。可以说,现在看上去十分幸福的家庭,其实并非是靠血缘缔结的血亲关系,而是由血缘变异后形成的“绿色豌豆粒”。明白这一切后,“我”感到十分孤独,手脚像消失在雾里一样郁闷,感觉没有依靠了。与我相同,纵男也认为自己“悬在半空中”。我为自己不幸的出生感到悲伤与孤独,深深体味到没有父母的孩子共同拥有的内心世界,感到“死者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所谓大自然是一个很深的容器”。[9]207置身乡下大自然的怀抱,感受着奶奶不连贯的家族传承,前来小住的表兄妹四人似乎长大了很多:“美奈子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信次郎发生了“一大革命”——“出去玩晒黑了,丢掉了爱看漫画的习惯”;“纵男开始坐正了吃饭”,并“可以两只手弹风琴了”;“我可以管理五个人的吃饭问题了,发现给人帮忙和管理别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9]209大家都学会了分析问题,变得“坚强了起来”,并主动学习了。我也由此感到那些不明白的事没有必要硬弄明白,相信现在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这次乡下之行给“我”的启示。作者以家族故事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引起人们的思索,感知人生的启示,表现出了浓厚的后现代文学特色。
江国香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小说《沉落的黄昏》通过描写年轻人的恋爱生活,揭示了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梨果是一名代课女教师,她拥有心爱的教育工作,传统、朴实,真诚热爱自己的恋人健吾——“厚道”、“耿直”,待人“彬彬有礼”的“小型广告公司”职员。可是,突然有一天,共同生活了8年的健吾突然提出要分手,原因是他遇到并爱上了小巧玲珑的小美人华子。华子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没有固定的住处,还特别反复无常,飘忽不定。其随遇而安的生活性格,总给人一种“不正常”的感觉。她先是与健吾的朋友——新婚不久的胜矢交往,偶然在机场与健吾相遇,后来竟在健吾不知道的情况下搬到其新租的房子里借宿。在与梨果相遇后,又悄然搬到梨果的房子里借宿(提出平摊房租)。被恋人“抛弃”的梨果对华子的言行与内心世界感到不可思议,但对这位“不正常”的美女的介入又感到无力改变,只好默默地接受,保持同居但又互不干涉的关系。后来,华子又与很多男人交往,谈笑风生,交往密切,还带着梨果到中岛先生在海边的别墅避暑。她总是来去匆匆,飘忽不定。“华子曾经一副绝望而现实的表情,说自己没有任何可以相信的东西,不相信爱情和友情,不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不相信幸福和不幸。”[10]97她说自己的人生总是在逃,逃来逃去,可最终还是逃不掉。总想逃避周围一切的华子后来干脆拿走梨果朋友凉子寄来的机票,去香港玩了一趟。由于她的随意和轻飘给人带来轻松感,从而充满魅力,导致相识的男人或是与恋人分手或是离婚,而她根本就没有爱过追随她的任何人。尽管如此,生活中的男人却被她那轻松、自如、随意、逃避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一厢情愿地与她保持着恋人关系。最后,华子在别墅浴缸里洗澡时,赤身裸体地割腕自杀了。经历了这一切的梨果深受感触,亦梦亦幻不可思议,只想回到现实中实实在在地过日子。她说:“我决定生活在现实之中,也希望健吾能生活在现实中。我不知道健吾是否明白我的用心,不管怎样,时间会一如既往地从我们身边流过。”[10]132作为传统的知性女性,她既读不懂同代人华子的生活方式与追求,也读不懂与自己一起相处8年看似老实本分的恋人,在灵魂无所寄托的煎熬中,只盼尽快结束这种不可思议的梦幻生活,回到现实生活中。传统生活中恋人的专一、安静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似乎成了一种遥远的人类记忆,风雨过后,看到的仍然是绚丽多姿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即。小说很好地描写了后现代社会年轻一代居无定所、飘忽不定的灵魂世界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反映了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年轻人的内心焦虑与莫名其妙的孤独,而这正是追求高度消费的后现代社会的产物。
四、在解构中重建新“家”
“家”的内容和内部的关系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家”的存在形式永远是“家”所表现出的那样。只要有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孩童还是老人,不管是一个、两个还是三个人,都能撑起一个实在的“家”。
《厨房》是吉本芭娜娜的处女作兼成名作,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巨大反响。具体来看,作品描写了“我”在唯一的亲人祖母死后的内心孤寂,以及“我”对过去曾经有过的温暖家庭的向往。但到别人家的借宿生活,对“我”来说也不错。在这里,“厨房”带给我内心的平静,使我找到了家的感觉,所以,不管走到哪里,都最喜欢“厨房”。“厨房”既是温饱的保障,又是家庭温暖的象征,属于女性的空间。小说从人物塑造、空间设置、故事发展、语言运用来看,具有隐喻、换喻、借喻等各种象征,从诸多方面表现了后现代文学的特色。
小说的女主人公“我”,名叫樱井美影,自幼丧失双亲,由祖父母抚养成人。中学时代祖父离世,一直与祖母二人相依为命地生活至今。而今唯一的亲人祖母也去世了,她吃惊地感到如今家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从而产生“天涯孤独”的心情。现在,我在世上最喜欢的地方是厨房。由于“厨房”是“制作食物的地方”,所以总感到惬意。对于“我”来说,“厨房”代表着“家”,是温饱和温暖的象征。而现在祖母逝去,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对于目前只剩下我和厨房的现实,“厨房”无疑变成了我的挚爱,因此,不管它是擦得放光,还是特别肮脏,我都喜欢得要命。为了感受过去曾经有过的家庭氛围,我就是“被田边家捡回家之前”,也都是“每天在厨房睡觉”。祖母丧礼时,在祖母常去买花的花店打工的田边雄一前来帮忙,诚邀其搬到他家住。美影决定搬去,在居住期间两人产生了亲密的感情(但并非恋爱),最后各自成长起来。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以丧失血亲骨肉、成为天涯孤客的女大学生的生活及命运揪住读者的心,从此以后的她将与周围的人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走向自己的生活。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部年轻人的自我“成长”物语。
回忆与祖母共同度过的日子虽然总是非常不安,但她却有家的感觉,心里总是惦记着只有祖母一个人的家。那时,“我一回到家,祖母就从有电视的房间里走出来,说你回来了。晚归的时候总是买了蛋糕回家。说是在外住宿之类的话,祖母也不生气,非常豁达。有时喝咖啡,有时喝日本茶,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蛋糕,度过睡觉之前的一段时辰。”[11]385可以说,她以往的生活舒适、平和,对失去祖母感到可怕。这次借宿雄一家,再次让她找到家的感觉,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她“按时去打工,回来后或是打扫卫生,或是看电视,或是烧制蛋糕,过着主妇那样的生活”。[11]386同时,被田边家明快、舒适的氛围所吸引,认为这里有厨房,有植物,在同一屋檐下有人,而且静静的,因而感到这里最好。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借宿的雄一家与过去的家完全不同,但她不仅没有生疏感,反而如同以前一样仍然感到惬意。在美影看来,在这个世界上,与她血缘相近的人没有,不管去哪里干什么都行,非常豪爽。雄一母亲则认为,她无处可去,尤其是受伤的时候越发痛苦。于是让她安心住在这里。这种意外的临时构成的家庭关系正是作者意欲缔造的新型家庭关系,即没有血缘支撑的人类集体(集团)的可能性。日本学者佐伯泰子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的母子、夫妇关系不同的这种适度的距离感,才给美影以安心感。与没有母子、夫妇、血缘这样密切的爱情关系所支撑的他人的同居,反倒心情愉悦——那与以往的‘家族’基础性质不同,展示了代之而来的成为安息之地的人类集体的可能性。”[12]
不仅如此,雄一的家庭也与众不同,他的家庭表面看是由母子二人构成,但实际上母亲缺席,现在的“母亲”原来是他的父亲。由于母亲去世,父亲辞职变性后变成了他的“母亲”,用“女性的双手”抚养儿子雄一。可以说,这样的设置与以往的家庭完全不同,作者有意打破传统固有的家庭形象,尝试建构家庭的多样形态。另外,在这两个家庭中,不论年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在他们的人生成长过程中,女性(祖母、母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而“厨房”又属于女性空间,可见作者的寓意之深刻。
再就是雄一与美影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之前互不相识的同一所大学的大学生,初次认识后便邀请对方到自己家同居,这在现实生活中似乎很难想象。但是,前来同居的美影不仅没有生疏感、拘束感,反倒在沙发上睡得很踏实,如同自家先前的生活。其后,两人之间经常见面并有了更深的了解,美影不仅知道雄一曾有个女朋友,还在夜晚专程去给他送盖浇饭等,可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但是,小说直到最后两人也没有发生恋爱关系,而是找到工作后各奔东西了。这种超越性爱、血缘关系的人际交往形式,无疑也是作者意欲探求的新的生活方式,即超越男女性别欲求,摒弃私心杂念,在相互理解与相互帮助中建构纯洁、和谐的人际关系。自然、舒适、平和的生活,不仅使人内心安宁,还会使人顺利跨过人生中的坎儿,并顺利成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厨房》又是一部描写当代日本青年的成长物语。作者通过对两个“残缺”家庭中青年人的心态描写,旨在探求一种新的家庭结构形式,即没有性爱的临时扶持也可构筑实质性的家庭生活,这就打破了以往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家庭或家族关系,展示了理想的共同体生活的诸多可能性。
五、母性晕轮下“家”的探索
不管是传统的还是反叛的,不管是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不管你的性格偏向男性还是中性;你说你没有母性,那是因为你掩着藏着,不敢面对而已。只要你是女人,你就永远被母性的晕轮罩着。因为,母性是一种人性,是一种天性,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容压抑的潜意识;“家”因母性而存在,因母性而精彩。日本当代女作家同样对女性拥有的母性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通过作品表现了独特的母性观。具体来看,她们否定或消解近代以来形成的家庭制度和价值观,试图建构一种新型的家庭伦理和理想的内部关系,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山田咏美、吉本芭娜娜和江国香织。
山田咏美“非常重视身体感觉”,作品中“登场人物时常用冷彻的眼光,时常以深厚的爱情观察人们,从而捕捉对方本质性的地方。其观察并不只是偏重于内面,对于身体性的感觉也投以锐敏的眼光”。[13]因此,其作品别具特色。山田咏美的《杰西的背骨》,以青年女性可可为中心,触及女性、生育与母性的关系,以此探讨日常生活中新的家庭关系的可能性。小说讲述了非洲裔美国黑人利库与日本女性可可结婚,面对其前妻留下的11岁男孩杰西而感到无法应对的困惑展开情节,最后终于与他达成和解、平和生活的故事。小说中,利库与杰西是拥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可可作为后来者进入这个家庭,从此开始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生活。小说以可可的心理、现实矛盾为主题展开,从可可的立场触及离婚后的“家庭”重构以及它所面临的问题。最初,没有血缘关系的可可与杰西对突然到来的家庭生活很不习惯,彼此之间很难接受。特别是杰西,他对取代母亲而至的女人可可激烈反抗,绝没有半点亲近,两者很难成为亲密的朋友。可可为此十分苦恼,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小说开头部分便写道:几个月使可可苦恼的11岁恶魔。可可茫然地感觉到,即使与利库分享日常生活,也要分担那个孩子的生活。作为再婚家庭的妻子,面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前妻之子,按传统思想来说,她在接受婚姻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承担“母亲”角色,但可可不同,她试图告诉人们在男女双方的爱情中,未必一定会伴随“母性”的发生。也就是说,可可在对利库产生爱情的同时,未必按传统思维无条件地爱他的孩子。对她来说,打算做母亲,这样的想法一点儿也没有,因为那个孩子是利库的孩子。也就是说,可可对杰西没有母爱,而是由于与利库的爱情使然,她才乐意给他做饭,她是非常排斥对杰西的“母爱作用”的。可可这样的感觉与困惑,无疑是对女性自然拥有母性这一近代“母性神话”的消解。
作为现代女性的可可,其行为、举止反传统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对“孩子是爱情结晶”这一固有观念的否定上。在她看来,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男女之间的爱情并非一成不变。在不断变化而又难以捕捉的现实面前,女性生育孩子是非常可怕的事。因此,她总是慎重地加以回避。小说如下描写道:“她预感到自己一生都不会生孩子。她感到生育是件非常可拍的事。相互爱慕而生育孩子,如果与那个男人相互厌恶的话那该怎么办?不是要留下相互爱恋的证据吗?”[14]250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总是将女性看作是“生育”与“母性”的化身。生育被看作是女性成熟的标志,而母性则成为女性必须具有的内在情感,它甚至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严重束缚了女性的身心自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可可不能认同这种传统思想。在她看来,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她忠实于爱情,但未必同时拥有母性。这一点从她自己的体验来看是如此,从杰西的生母来看也是如此。杰西的生母在与利库离婚后,作为看护杰西的条件向丈夫索要报酬,小说写道:“提到这孩子的母亲,就会歇斯底里。甚至说如果不付200美金的话就不会照看。那点钱不成问题。不想把孩子寄养在没有报酬就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养育的女人那里……”[14]223也就是说,杰西的母亲作为生母,她在生育杰西的同时,也没有自然而然地就产生母性。她看望杰西,但没有真心养育他的意思,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她始终不理解杰西的内心,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如何聪明,以及其聪明是由何产生的?杰西对这样的母亲也同样没有任何亲近感。最后,选择与可可同居的杰西也发现,光靠血缘关系不能成为维系同居家庭的纽带。从杰西与其生母的关系出发,可可更加坚信,即使是拥有血缘关系的母子之间,也不一定就无条件地具备“母性”。在她看来,生孩子根本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重要的是养育,是读懂孩子的内心需求,否则,就不能成为母亲。从自身来说,她没有必要苛求母亲的名分,重要的是得到一个共同生活的人。由于自己态度的变化,杰西也相应地与她亲近并喜欢她了。这使可可感动不已,因为她所希望的就是如同志愿者那样照顾杰西,对此并非受人感谢,也不像母亲那样得到他的敬慕。只是被人作为一名女性对待。她对杰西的感觉既不是憎恨,也不是爱,只是对待一个人而已。可以说,这部作品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母亲的作用,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崭新的“共同生活的人间同志”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以血缘、母子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生母、继母的界限,展示了后现代社会新型家庭关系的可能性。
可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女作家的创作,表现出对传统意识的反抗与解构,以及对新的人际关系、家族模式的建构,其中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带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具体来看:她们的作品要么强调异性之爱,探讨女性、自然与母性之间的关系,揭示女性并非生就自然地拥有母性;要么说明男女之间的相处并非都是建构在性爱基础上的,那种没有血缘关系的、和谐的集团式的生活同样具有可能性;要么解构固有的男女性别分工,以自由的生活方式为理想,否定婚后“男主外,女主内”的固有模式,尊重同性恋者的人格与权力,等等。她们通过文学创作展示现代社会的人间形态与思想追求,否定约定俗成的固有观念、生活方式,探讨家庭、婚姻以及人类生活的诸多种可能性。她们的作品,一方面展示了女性对当今社会制度的不满、解构与反抗,另一方面又表达了日本女性的精神追求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从日本现代文学的总体发展来看,她们的创作正是代表了当代日本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
[1]間々田孝夫.第三の消費文化論——モダンでもポストモダンでもなく[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
[2]高宣杨.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百变百科.后现代主义文学[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411552.htm?fr=aladdin.
[4](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变化中的价值观: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A].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C].黄语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川村凑.戦後文学を問う——その体験と理念[M].東京:岩波書店,1995.
[6]芥川賞受賞記念対談(一)柳美里+辻仁成「書くしかない」[J].文学界,1997,(3).
[7]柳美里.フルハウス[M].東京:文春文庫,1999.
[8]吉本ばなな.哀しい予感[M].東京:角川文庫,1990.
[9]村田喜代子.锅中[A].水田宗子.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作品卷)[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10]江国香织.沉落的黄昏[M].李炜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11]吉本ばなな.キッチン,于荣胜.日本现代文学选读(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佐伯泰子.現代日本の女性作家が描く家族と母性——山田詠美·よしもとばなな·江国香織が描く「近代家族」の終焉と新しい“親密性”[EB/OL]. http://www.arts.chula.ac.th/~east/japanese/files/2008news/houkokusyo/houkokusyo.
[13]島本理生.身体と文学をつなぐ世界[J].文芸,2005,(3).
[14]山田詠美.ベッドタイムアイズ指の戯れジェシーの背骨[Z].東京:新潮文庫,平成8.
责任编辑:杨春
A Metaphor for“Home”——On Postmodernityof Japanese Modern Female Literature
XIAOXia
Postmodern literary crea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counteractions to modern capitalism, and one school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sociocultural thought, occurs naturally in society af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enters mass consumption, and is also a form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The obvious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appear in the ideology,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social lifestyle and other fields in Japa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provide the women writers with abundant writing sources. The women’s literary works published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ith strongly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fully reflect the new value orientation and basic life attitudes of Japanese modern women writers.
female literature of Japan; postmodernity; value orientation
10.13277/j.cnki.jcwu.2015.06.009
2015-06-23
I106.4
A
1007-3698(2015)06-0061-09
肖 霞,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女性文学。250100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主题表达与价值取向”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JA75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