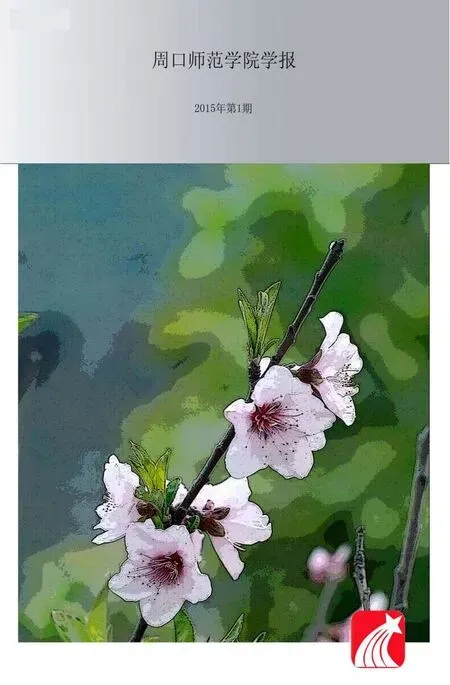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2015-01-31李琴英
李琴英
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李琴英
(华侨大学法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我国民事诉讼的基础是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贯彻落实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仅有利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且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阐述了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及其不足,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提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建议。
证明标准;一般理论;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是指在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对于当事人而言,如果了解了证明标准,就不会对诉讼进行不恰当的估计,而贸然提起诉讼或者迟迟不敢起诉;对于法官而言,只有明确了证明标准,才能正确把握认定案件事实需要具备何种程度的证据[1]。基于上述考量,本文将研究重点置于分析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建议,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构设宏观取向。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特征及其不足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或然性占优势或优势证据标准”。证明标准,是指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或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当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效果上处于优势地位,相对的另一方当事人的举证效果处于劣势地位,显然,这种明显悬殊的力量对比所形成的证明标准模式就是优势证据证明标准[2]。莫菲认为:“在民事案件中,事实审理者认为,负有法定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主张事实上的真实性大于不真实性,就是‘或然性权衡’和‘盖然性占优势’的标准。”[3]
(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相关概念之辨析
1.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存在两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证明标准和证明要求是同一概念,当事人的主张必须达到证明标准的程度。证明标准,又可以称为证明程度、证明要求、证明度,是民事诉讼当事人证明待证事实要达到的程度。第二种观点认为,证明标准和证明要求不是同一个概念,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证明要求是抽象的,而证明标准则是相对明确的。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证明标准和证明要求不是同一个概念,需要加以区分。证明要求是抽象的,其前后经过了神示真实、客观真实、法律真实的演变。证明标准是相对明确的,是证明主体的证明活动能否证明其主张成立的具体量度。不言而喻,前者更为宽泛,后者较前者相对详细、确定,如果两者分辨不清,将会导致证明标准的不确定。
2.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区别比较明显。证明责任是指“证明在法庭上主张的事项是真实的义务”。一般认为,证明责任包括两个层面:法定责任和提供证据的责任。法定责任也称为“说服责任”“最终责任”,是指证明争议中的事实为真实的义务,如果承担法定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能对证明事项履行适当的证明责任而说服审理事实审理者确认争议事实为真实,将会承担败诉的风险。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就某一特定事项提供充分的证据以使该事项在法庭上能够处于争议事态的责任[4]。证明责任强调承担民事诉讼诉讼主体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的责任,突出强调的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当事人在承担举证责任时,要承担相应的事实和法律后果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的作用是司法指引和约束,它是针对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在当事人提交证据后,法官认定事实时,司法指引作用得到发挥。
(三)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征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变革的展开,我们需要对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不断的改革,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大挑战。200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事实审理者在接受另外一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时,不得不排除另外一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这是同时站在双方当事人的立场上来看的,由一方当事人驳倒另一方当事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有以下特征:第一,法官自由心证。当双方当事人均提出证据,双方的证明强度还不足以否定对方提出的证据,则法官会根据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衡量它们之间证明力大小,而进行自由裁量。第二,当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无法确认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大小时,法官也应当依据证据规则进行裁判。第三,法官通过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证明力大小的对比,证据证明力大的一方胜诉。
在理解“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时,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它是证明标准中最低的,是判断要求的最小的置信度。法官不能以此为托词,摒弃对其他证据的审查与判断,应该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从而得到更加肯定的内心确信。第二,法官在适用证明标准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将适用的证明标准与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因和结果进行公开阐明,特别是应充分公开判决时的理由。
(四)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足
1.强化法官职权主义。在认定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大小时,法官应当依据自由心证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法官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证据与当事人所提供证据发生冲突时,公权会对私权进行干预,当事人利益受到损害。
2.证明标准过于单一,缺乏灵活性。美国的证据法把证明标准分为九等,从最高的证明等级“绝对确定”到最低的“无线索”。我国的民事诉讼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没有区分证明标准的等级。证明标准的“单一性”或“概括性”会造成不当提高或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对公正裁判产生重大的影响。
3.违背诉讼经济效用原则。民事诉讼主要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纠纷,诉讼当事人花很多的时间搜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样就能减少自己败诉的风险。如果案件事实要求的证明标准越高,当事人的举证也就越困难。笔者认为,一些简单的案件笼统地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会导致诉讼当事人耗费过高的诉讼成本。从长远看来,案件事实得不到证明,会造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不稳定。
二、域外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首先,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通常是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可以理解为:审判的过程,是一种证据的数量和质量的对比,是待证事实明确性的一种客观状态。这表明,这种证明标准需要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心证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受到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一些影响,不适用陪审员的审理方式,法官则只能依靠相关的经验法则,依据理性来综合判断相关证据,从而达到法官内心的确信。显而易见,证明标准与法官的心证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次,英美法系民事诉讼标准。由于两大法系历史发展与产生基础的不一样,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明标准模式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大多数采用优势证据。优势证据标准是民事案件传统的、基本的证明标准[5]。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一个诉讼争议事实承担说服责任,一般就会要求当事人须对该争点事实的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当事人必须说服陪审团相信“争论事实的存在比不存在更有可能”。但是优势证据标准并不是一项数量标准,证明力的大小不是以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数量进行判断。准确地说,它是一项质量标准,反映了证据的可信度和说服力[6]。尽管优势证据标准反映了事实审理者对盖然性优势的确信,但法院通常会拒绝接受统计学意义上的证据,即使这一证据所显示出来的可能性超过50%。相反,法院通常要求陪审员对事实的真实性要有“确信”,而不仅仅是对事实的真实性进行盖然性的估计。
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诉讼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法官就像体育竞赛的裁判人员,属于中立裁判者。法官的中立性决定其不得主动收集证据,其职责是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判断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是否成立。英美陪审团制度与“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也是相互联系的。美国著名学者摩根教授认为,证明标准与证据的数量直接相关,但是,它的优势度评价主要体现在陪审团内心的天平上,通过天平来衡量证据的分量。显而易见,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中立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所以,当事人只有切实履行其应负的证明责任,而后经过一系列的证明活动,最终获得诉讼主张的成立。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建议
我国的证明标准较为模糊,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笔者针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一)完善相关证据立法工作
证明标准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关键点,笔者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修改或增加与证明标准相关的法律条文。加大我国证据法的立法力度,如制定《证据法》,可以把证明标准问题在《证据法》中做出详细规定,这样对当事人还是法官,都是有益的。
(二)证明标准类型化
据笔者所知,美国的民事诉讼存在两个证明标准。在大多数民事案件中,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或者案件中的特殊事实(例如欺诈),则采用“明显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一标准。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美国证明标准,结合我国本土司法,对证明标准的类型化进行确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事案件呈现出多样化,主要表现在特殊侵权的案件中,如医疗纠纷、环境侵权案件。由于信息掌握是不一样的,证据掌握在侵权人手中,适用单一的证明标准会给举证方带来一定的负担,加重举证难的问题。如前文所述,证明标准的类型化,对于法官与当事人而言是有益的。
(三)证明标准对象化
笔者认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要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程序事实的证明标准和实体事实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前者的证明标准要低于后者的证明标准,这是由于实体事实决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程序性事实不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是全部程序事实都适用相对比较低的证明标准,只有对实体性权利没有实质影响的程序性事实,才适用比较低的证明标准。如针对不公开审判申请和回避的审查,就没必要适用较高标准的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着诸多不足,需要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借鉴域外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经验,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笔者认为,我国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笔者建议,我国应该将“高度盖然性”原则类型化、对象化上升到立法层面。
[1]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98.
[2]何家弘.外国证据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7.
[3]Peter Murphy.Murphy on evidence[M].London:Blackstone Press Limited,2000:126.
[4]特拉西·阿奎诺.证据基础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
[5]吴杰.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8.
[6]彼得.G.伦斯特洛姆.美国法律词典[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61.
[7]Jeffrey A.Segal et al.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17.
DF713
:A
:1671-9476(2015)01-0085-03
10.13450/j.cnkij.zknu.2015.01.022
2014-10-31;
2014-12-03
李琴英(1988-),女,福建龙岩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