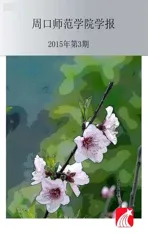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及其影响
2015-01-31高子涵
赵 勇,高子涵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科部,上海 201620)
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及其影响
赵 勇,高子涵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科部,上海 201620)
史华慈是美国学界提出“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异端”的第一人,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两次争论。史华慈并没有否认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文革”的错误会被中国共产党的后期领导人修正,不能因此而否认毛泽东是伟大的领导者这个事实。史华慈对毛泽东的研究既有成功之处,也留下诸多遗憾。史华慈的学术研究十分严谨,善于运用原始文献来解读毛泽东以及中国问题。他的研究从政策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使美国的毛泽东研究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
史华慈;毛泽东;异端论
本杰明·史华慈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学专家,是西方“自由派”毛泽东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是美国学术界最早展开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发展史的专家。他明确地指出了“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提出“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并由此引起学术界两次争论。聚焦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挖掘其现实意义,有助于深化认识史华慈学术思想的中国学意义,便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一、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
(一)史华慈的“毛泽东主义”与“异端论”
史华慈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著名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它的历史价值无法超越,是因为它在西方学术界首次提出并定义了毛主义(Maoism),从而使西方的研究转变为学术研究,不再是传记研究,这是一个转折性的标志。
当时美国人普遍认为共产党人受苏联控制,史华慈对此观点进行批驳。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机械教条地复制苏联的意识形态,它是在经历艰苦奋斗和摸索中建立起来的,这种道路是可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脱离中国当时面临的特殊历史背景来看待是毫无意义的。史华慈深入的论断目的就是要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出现的变局。
史华慈在他的文章《“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中对“毛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史华慈认为,尽管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都强调人民群众对历史的重要作用,但他们二者对“人民群众”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在马克思、列宁看来,革命的中心是夺取和占领具有中心地位的大城市,群众的核心是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在毛泽东看来,城市是反动统治的中心,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民才是群众的核心,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史华慈因为以上几点不同得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异端”这样的结论。史华慈认为如果说苏联是正统的共产党,那么中共就是非正统的,这个结论的得出,让很多美国人大为吃惊。
史华慈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革命路线。但是这种定性并没有多大的研究意义,真正应该研究的是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区别,中国道路与苏联道路的区别。马列主义原著中总有对农民革命的一种疏离,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找不到这种态度,甚至有一种对农民阶级的天然信赖。毛泽东文中流露的思想和态度不是跟从共产国际路线的,而对待农民党的态度恰好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本质差别,因此史华慈认为“毛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有差异的,他称之为行为上的异端。
史华慈认为,马克思是把工人作为革命的主体,毛泽东却是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他革命的目标从未改变。所以史华慈笔下所指的“异端”和“背离”其实可以说是一种独创和发展。史华慈认为“毛主义”实际上是以农民为群众基础,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对其革命战略进行创新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毛主义”的核心实质强调的是建立在农民阶级的认同和支持之上的中共运动,针对其具体战略路线来说,是对马列主义所持的以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为革命基础观点的“独创性异端”。
(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两次大论战:以史华慈的异端论为焦点
在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出版以后的10年间,美国学术界麦卡锡极右主义思潮泛滥。史华慈这样的理论家自然难逃麦卡锡主义者的批判。学界的第一次争论就来自于右派学者的代表魏特夫与史华慈之间,魏特夫批判和攻击史华慈提出的观点,称史华慈“已给美国与世界共产主义斗争带来无法估量的恶果”[1]。魏特夫在《中国季刊》发表文章专门来攻击史华慈的观点。魏特夫认为史华慈提出的“毛主义”根本没有任何的独创性和发展,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根本就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所指使和摆布的,不能把它定义为一个新的主义,也不能说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区别的。魏特夫抛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阴谋论”这样的观点,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受苏联控制的,毛泽东思想是莫斯科共产国际一个阴谋的产物。
从20世纪70年代持续到80年代初,哈佛学派学者与新“左”派学者激烈论战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三者的关系。佩弗和沃尔德是新“左”派的代表,他们写了大量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著作。新“左”派赞成毛泽东“文革”时期的理论和政策构想,认为其方针政策不仅仅适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西方社会也适用同样的或类似的政策。佩弗在《近代中国》杂志发表文章不赞同“毛主义”异端论这个说法,他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是存在一致性的。但他受到中国“左”倾错误观点的影响,竭力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以后来处于尴尬的境地。佩弗认为马克思和毛泽东革命理想是相同的,而马列主义并不是静止教条的,是灵活发展的随实际情况变化的,因此他坚持毛泽东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个观点。佩弗假设说,如果让马克思活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下,去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可能也会赞同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和毛泽东选择一样的革命道路,不会教条地照搬经典书籍理论,也会像毛泽东一样根据国情改变战略战术,也会在取得政权以及改造了所有制关系后,对思想政治和社会文化继续进行改造。
我们国内也已经认可史华慈的一个说法,就是毛泽东确实与马克思在对农民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地位认知不同。作为一个美国学者,虽然完全摆脱政治立场来研究毛泽东不太可能,但他仍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地评论。从具体的争论内容上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史华慈和魏特夫都是以毛泽东有关的原始文献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这种方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文本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这种依赖文本的研究方法,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的意识与存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这一点上,他们二人比佩弗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因为佩弗的立论是依靠假设和假想。但是史华慈和魏特夫的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为他们的结论都是依靠原始文献得出,这样使读者难以辨别是非。事实上,文本是客观存在的,而对于文本的理解却有很多种,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也就是为什么史华慈无法从根本上驳倒魏特夫,是源于史华慈的研究论据充足,却论证不够,分析不足。第二,魏特夫的论证在忽视“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差异性,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共性,可见他的论证是建立在主观的设定下,因此论证的逻辑无法被认可。相比较而言,史华慈既肯定了两者确实存在共同之处,又论证出二者之间的差异,这显然更容易被接受。而史华慈在这方面与佩弗相比,史华慈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略显僵硬,佩弗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教条的理论而是一种用以革命的方法,方法是会因结合实际而不断修正发展的。他既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也敏锐地察觉到了马克思主义静止和变化间的矛盾辩证关系,这是值得肯定的。第三,史华慈、魏特夫、佩弗这三派的代表,在他们的学术研究后面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美国毛泽东学研究的共同目的是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咨询。通过研究毛泽东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和建设战略,也是提供一个途径解决国内社会危机。在三者之间的反复争论中,很容易看出他们互相批判指责对方,指责彼此而带有政治色彩的研究,因为这种学术争论带有强烈的个人倾向和政治取向,一定是不完美的研究。这种政治角度会使他们在阅读文本和选取论据时剪裁为自己取向服务的片段,因而会影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评价的客观性。“对文献的利用与解释存在着主观性,甚至有的是完全错误的。”[2]史华慈并没有回避政治立场这个问题。但是他指出对待中国和毛泽东的态度,并不是只有远离和归顺两种选择。正如他曾经说过,有的人喜爱中国,有的人厌恨中国。我尊敬她。他努力在遵守政治自由的价值观,客观不带感情色彩的描述和评论中国和毛泽东思想。
(三)史华慈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定位分析
史华慈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为我们国内的研究提供很多借鉴和启示。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史华慈曾说:“无论毛泽东晚年做出怎样的举动,他多么地想要做一个理论的创始者,犯下多么致命的错误,无论他的行为有何政治性质,他都一直坚持证明他所获得的政权是他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合理合法取得的,可见他迫切想证明他是根正苗红的继承者,所以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都是一个忠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3]这说明,无论史华慈将毛泽东思想视为马列思想怎样的“异端”,毛泽东在史华慈心中依旧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伟大的政治领袖。”史华慈曾经说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是伟大的,他是20世纪伟大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他的功绩是不可因为错误而磨灭的。究其根本,是他重新统一了中国,重新组织了中国人,是他使中国人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永远都是20世纪伟大的政治领袖,他的名字必将广为传颂。可见史华慈对毛泽东的政治领导能力和政治领袖地位的肯定。
“文化大革命”会被否定。史华慈预言说,如果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这样偏激的政治运动是会被否定的。中国未来领导人会正确评价和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中国未来的发展和走向不是靠毛泽东一个人,而且许多中国的重要领导人是反对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的。这正预见了中国“文革”后的发展道路,虽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的贡献。这充分说明史华慈作为一代大师的真知灼见。
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史华慈指出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异,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得出了日后引起很大争议的“毛主义”和“异端说”的理论。改造论这个论调的提出,奠定了西方毛泽东学研究在日后的理论起点,这种论调至今仍是西方毛泽东学研究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它论证了中国不是对莫斯科进行复制模仿,这对美国学界和政界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的贡献影响
(一)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对国外学界的影响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最初的写作背景是美国社会的对华政策制定的需要,涉及政治必然会遭遇一定的政治风险。他是首位清楚提出“毛主义”这一名词的学者,而且详尽地分析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在这方面他是很出色的。如果说以前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是单纯的政策研究,那么他就是一个领头者,将之转为学理研究,使美国毛泽东研究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
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版,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主题直指中国的共产主义发展史,其中中共党史的内容占很大部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提出麦卡锡的追随者所不能接受的观点——中国不是克里姆林宫的传话筒。正因为此,这部著作在整个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弥足珍贵。尽管是史华慈早期远距离研究的成果,它却确立了一种将实证方法运用到共产主义研究的研究范式,尽可能精密地梳理复杂的历史现象,对后来的美国关于中共党史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方法论意义。研究目的的实用性决定了史华慈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不是单纯的党史研究,而是借助研究党史发掘出中共思想理论发展脉络,从而得出实用性的结论。然而,在资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史华慈的研究方法还是对后世产生了不能小觑的影响。史华慈对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独创性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更在于他的研究融入了比较分析、原始文献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在他以前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是传记类型的研究,他开启了真正的学术研究。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所做的文献工作对于后来编撰文献起到很大的帮助,这本历史文献的出版为美国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文献考证之风也日益盛行。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初,正是美国社会反共意识甚嚣尘上的时期,从各级政府官员到美国民众都普遍敌视和恐惧共产主义。这一时期有一条特别值得关注的反共内容,即认为:共产主义集团是一块铁板,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在他们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服从莫斯科的指挥,鼓动世界革命,最终统治整个世界。史华慈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尽管他未必是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共产主义,但至少是比较客观的。他大胆地否认了这么一条已为大众接受的“真理”,提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走的道路与苏联不同,中国人靠自己创造胜利。他还创造性地提出“异端说”,认为共产主义在扩张的过程中产生了异化,实际不断地修正和削弱原始的教条。尽管他的看法与我们不是完全相同,但在当时的美国却已极为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二)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首先,注重原始资料的考证与阐释是史华慈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研究最为鲜明的特点。对历史进行研究最重要的是回归原始文本,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必须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不带有感情色彩、个人喜恶。中共党史本身是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史华慈的研究也略有不足,史华慈用以研究的文献大部分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文件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原始材料的考证是许多学者容易忽视的一部分,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多次探讨深究原始资料,因为有的原始资料存在互相矛盾的情况,书中展露的这种探讨的过程,使读者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能更加深入地思索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历程,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次,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史华慈非常善用的。他作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共党史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他对于中共党史和中共领导人的评价不会带有盲目的个人崇拜情感,也不会有个人打压的情感,几乎不带有政治取向或者个人偏好,这样的判断会比较客观。人物的思想发展历程往往更能通过思想的碎片反映出来,而史华慈刚好具备这样的眼光,他的视野中有散落的思想碎片,又有形成体系的理论支撑。他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我们那种单单重视理论体系的研究截然不同。
再次,史华慈研究人物时,不光看事件的表象,也把人物所处社会环境、个人思想融入思考中,在分析历史人物时加入了对人物心理、境遇的分析,虽然这样的研究会带有一定主观判断的因素,但是却不会落入千篇一律的研究误区。史华慈的学术观点是值得借鉴的,他的研究方法是我们需要学习和予以肯定的。史华慈的见解非常独到,他提出的毛主义也可以说是大胆的。他提出的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等不同,他强调农民革命地位,我们国内的研究成果也是认同这点的;而且很有启发的是,他把毛泽东研究放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启蒙运动思想脉络中,这样比较的研究方法很新颖。《德性统治》和《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正是体现了他这种独到新颖的研究视角。因为他的启发,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美国学者的身份让他不可能摆脱政治立场和个人的价值取向来进行研究,但是史华慈仍然使自己的研究尽可能客观公正,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特别之处在于站在外国人的角度,去看待中国问题,这像一面反光镜,为我们研究毛泽东学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史华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仅在方法论上,更是在治学态度上带给我们珍贵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中国的建设,我们既需要做内部研究,研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要做外部研究,对一些非马克思和反马克思的学者的观点有所了解。这样内外兼顾的研究,我们会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才能让视野拓宽,思路广泛,这正应了那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萧延中.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250.
[2]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M].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6.
A84
:A
:1671-9476(2015)03-0095-04
10.13450/j.cnkij.zknu.2015.03.023
2015-02-10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影响与国际评价研究”(12CKS009)的阶段性成果。
赵 勇(1977-),男,山东泰安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意识形态、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高子涵(1988-),女,辽宁阜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