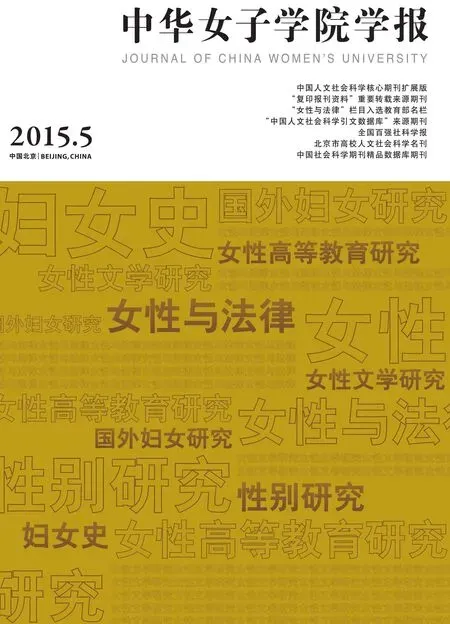抗战时期的陕西妇女运动
2015-01-31袁文伟
袁文伟
抗战时期的陕西妇女运动
袁文伟
抗日战争期间,陕西各界妇女实行了大规模的总动员。女界的抗战活动涉及很广泛,在国统区有的直接参军、参战,有的参加妇女慰劳会、工合办事处、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组织,积极支援前线。在陕甘宁边区,广大妇女也积极支援前线,参政议政,开展反封建斗争。陕西妇女既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又投身到抵御外侮的军事斗争中,她们以自己的行动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力量。
抗战时期;陕西省;妇女运动;支援前线
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陕西省各界妇女突破国民党“远离政治,塑造贤妻良母”的思想禁锢,勇敢地走上街头,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取得了巨大的影响,还摆脱了封建婚姻和家庭的枷锁,赢得了社会地位的独立和人们的尊重。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不仅仅在城市发起,也极大影响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村的妇女运动迅速展开。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广大妇女在抗日救亡、争取自身解放的革命运动中逐渐摆脱封建束缚,大胆参与政治、经济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一、陕西国统区的妇女运动
(一)陕西妇女慰劳会的活动
1937年8月16日,陕西妇女慰劳会在西安成立。陕西妇女慰劳会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中共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他们认真执行共产党坚持抗战和巩固扩大统一战线的方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动组织各界各阶层妇女做了大量的工作。
1.成立支会
陕西妇女慰劳会为了扩大组织,在成立后积极成立支会,全省37县都按章程要求按时成立了支会。在省会西安,22个学校成立支会。直属妇慰会领导的是姊妹团,主要成员主要分布在夏家什字一带,共有80个人左右。姊妹团除了参加慰劳、募捐、宣传、唱歌、演戏、为伤兵服务外,还组织了歌咏队和服务队。①参见中共西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西安党史资料》(内部资料),1988年,第19页。
组织识字班。陕西妇慰会在成立的一年时间里,在西安先后举办7个识字班,共使得100余人受到了爱国教育,除西安之外,约有20个县组织识字班,参加人数有200余人。[1]除教识字外,还教唱救亡歌曲,讲解抗日道理和如何争取妇女解放的问题。曾在夏家什字的大院里举办过几次妇女游艺晚会。除游艺节目外,还有抗日形势报告,报社记者也赶来采访。在二中召开时,前来听抗日形势报告的竟有1000多人。[2]此外,随着大批的爱国青年奔向延安,妇慰会还负责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把他们妥善安置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然后转赴延安或安吴青训班。
2.宣传救亡
创办会刊《西北妇女》。主要内容:一是报道抗日战况和时政评论,二是宣传妇女救亡运动的作用。在创办的两年多时间里,《西北妇女》共出版16期。虽然是月刊,由于时局混乱,导致出版时间不固定,所以有时两月才出版一次,正常情况下每期大约发行1000多份。[3]197同时编写《妇女抗战壁报》《杀敌壁报》等,还利用漫画和连环画等形式宣传抗日内容,印成传单四处发放。
除了刊物以外,陕西妇女慰劳会利用电台的影响,创办了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播音节目,每周一次。内容为保育儿童、优待抗属、动员家庭妇女、陕西妇女大团结、第三期抗战中陕西妇女的任务等。为了扩大妇女运动的影响,陕西各界妇女积极联合陕西妇女慰劳会和妇女抗敌后援会等团体一起举办妇女抗日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有“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怎样肃清汉奸”、“怎样动员农村妇女、家庭妇女、难民妇女”等,也有当前的抗战形势与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问题。
3.积极募捐
组织义演义卖。据统计,14个县支会募集缝制了大量的衣被鞋袜,“妇慰会成立两个多月时间就为前线募制棉被10万条”,“从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各支会募集了大量缝制的衣被鞋袜,还有现金5000多元、金银器100余件。”[4]198其中,城市知识女性捐款捐物的积极性相对较高。除参加各救亡团体的慰劳活动外,妇慰会还联合平津同学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团体组织几路慰劳队,奔赴抗战前线慰劳陕西子弟兵。
主动参加接待伤兵工作。从1937年10月开始,大批伤兵从前线来到西安。妇慰会给送去面包、饼干,为伤员募集衣被鞋袜,组织缝洗队、姊妹团等义务服务队,精心照顾伤员,使得伤兵的护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卫生条件也相应改善。歌咏队去病房为伤兵演唱和教唱救国歌曲。宣传科将壁报办在伤兵医院,制作“再接再厉”的纪念章赠送给伤愈归队的战士。据初步统计,仅1938年5月至9月,就赠出了5000余枚。[4]107
(二)中国工合西北办事处妇女部
1939年,日军向武汉方面大举进犯,大批难民流亡到宝鸡。西北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分支机构)妇女部组织难民围绕生产自救、供应战时军需民用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1.教育活动
宝鸡十里铺、罗家塄等村是工合运动的据点,妇女工作部成立初期,先后在这两处成立儿童识字班,招收12人。又在硖石村、姜城堡及城内设立了工合小学三处,均为男女生兼收。在贾村塬、永清堡、罗家楞、长寿山、益门等地办妇女识字班12个,参加学习的妇女250余名。[5]课程有国语、算术、珠算、唱歌,尤其注重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女学生进行思想启迪。还有流动妇女识字班8处,即工作人员进行家庭拜访时,临时集合3—5人上课,规定每天教会妇女们认识三个字,每个月考查一次,还要教会她们十个抗战常识。[6]
为了吸引更多的乡村妇女参加合作社,1940年创办了宝鸡工合小学,招生146名。其中,女学生62名,到1943年共存4校。[7]1940年4月,创办了妇女职业训练班,开设国文、珠算、会计、常识、唱歌、漂染、纺织等课程。1941年5月5日,创立了女子职业学校,有学生40余名,注重知识的提高、身体的锻炼、技能的学习和道德的修养。
2.社会活动
1941年三八妇女节,西北工合妇女工作部在宝鸡召开纪念大会,参加的女工、农妇达千余名。会上妇女部负责人介绍了三八节来历、妇女运动与工合运动的关系,总结了一年来妇女工作的进步和发展。《西北工合》专刊登载了喻林炎写的《纪念三八节说到妇女问题》、方愉之写的《纪念三八节想到的两件事》、张琳写的《妇女问题的发生及其他》、刘克顿写的《三八与西北妇女》等文章,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抗日救国及动员妇女学习文化技术,参加劳动生产,劝导妇女放足、求学,提倡婚姻自由等。
玉涧堡工合新村的妇女工作很活跃。这个村东靠义民村,有难胞妇女儿童200余名,北靠长寿山,有荣誉军人教养院,内有残废军人300余人。妇女部帮助这些人恢复健康,接受教育,并逐渐走上发展生产的道路。办起了妇女识字班、工合小学、妇女缝纫生产合作社、纺毛站、妇女俱乐部等。当地农民有400余户参加了纺毛生产,日纺毛线千余斤。
西北工合还在凤翔、陇县、凤县双石铺设立了事务所,各事务所设有妇女股,负责妇女抗日运动。凤县双石铺妇女股开办了纺织合作社、妇女俱乐部、纺织训练班、工合小学和附属幼稚园。
(三)西安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大批难民涌入西安。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战时工作部开办了难民职业介绍所、难民识字班、难民诊所、纺织班、缝纫班等,设身处地为难民着想,为难民服务。1939年5月20日,西安市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战时工作部的基础上成立。它的性质是一个不以传教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服务公益机构。其宗旨为:“本基督精神,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展,培养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其会训为:“尔识真理,真理释尔。”
战时工作部在抗战爆发后开办了为难民服务的各种组织,极大地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西安演出期间,尽可能帮助基督教女青年会做抗日救亡工作。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大力支持下,战时工作部把宣传抗日救亡、拥军优属、捐献支前作为主要任务来贯彻。
为了更及时地解决难童问题,战时工作部联合其他妇女团体组织难童救济委员会,为抗日军人家属分忧解难,仔细造册登记,发放优属证,先后发放2500余份。同时,军人的孩子上学、洗浴等均免费,还定期组织看电影。社会各界爱国同胞也踊跃捐款3000余元,用于救济抗日家属。
战时工作部积极组织筹办西北合唱团,经常奔赴黄河沿岸为抗战将士慰问演出。为了吸引抗日家属的参加,邀请有一定知名度的各界名人做抗日演讲,传播抗日消息,宣传抗日功绩。为了鼓舞抗战将士的杀敌士气,发动西安的广大市民给即将东征抗日的陕西子弟兵写慰问信,雪片一般的慰问信表明了西安市民高涨的爱国热情。战时工作部也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帮助来自香港、澳门、厦门的女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等等。中共党员杨玉珊、彭毓泰、秦熙垣等经常来基督教女青年会指导工作。
(四)陕西女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12月14日,西安各校学生通电否认华北伪自治,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24日,西安各校学生和教职员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学生发出通电,请求政府锄奸救国,维护并领导学生运动,释放被捕学生,保护爱国运动,表示誓做北平学生的后盾。25日,西安各校4000多名学生在西安二中操场集会,会后举行游行请愿。
1936年11月7日,西安各校5000余名学生冲破军警包围,轰走了破坏悼念鲁迅活动的省会警察局长和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和各界群众在革命公园召开追悼鲁迅大会。西安学联组织援绥募捐活动。男女学生组成宣传队、募捐队,在街头控诉日军罪行,动员民众慷慨捐献,并携带捐款和慰问品赴绥远慰劳抗日将士。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西安掀起了一个抗日救亡的民众运动高潮。1937年11月,先后有65个学生农村工作团深入关中、陕南各县宣传抗日。1938年1月,西安学生又有70多个寒假工作团出发到陕西各地以及抗战前线,进行抗战宣传工作。10月,西安学生分会动员全市学生组织伤兵安置工作,对伤兵进行了精心护理和慰劳。[8]12
安康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掀起。兴安师范和安康中学成为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西安事变后,教师们公开在课堂上介绍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八大主张,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反对卖国、追随光明、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的呼声愈益高涨。两校各种进步社团相继成立,如社会科学研究会、文艺研究会、各县旅安学生同乡会等。女学生非常活跃,她们办壁报,举行演讲竞赛,进行抗日宣传。经老师介绍,蔡启芝(王康)等女同学阅读《苏区文艺》《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1937年“红五月”里,兴安师范学生自治会联合附近学校,纷纷走出校门进行宣传。“五卅惨案”纪念日里,他们组织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做亡国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把传单、标语贴到专署和国民党县党部门前。宣传队则演唱《松花江上》等歌曲,表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
兴安师范学生利用寒假组成返乡工作团到各县城宣传。其中,岚皋旅安同学会组织的返乡演讲团,由娄文静领队,蔡启芝、娄学谦、程云等为团员,沿小河而上到乡间宣传。1938年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在兴安师范建立,女同学徐秀云、蔡启芝参加。安康民先队成立后,发展队员150余人,其中女队员50余名,约占35%。在安康民先队员中,女党员约有20多人。安康地区各学校民先队组织多种抗日活动,演唱抗日歌曲,散发抗日传单,创办抗日小报等。1938年7月,中共陕东南工委和民先队组织一批民先队员奔赴延安,其中有女队员徐秀云、蔡启芝、夏玉莲等。
西安事变以后,礼泉、咸阳、长武、永寿等县旅省学生,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和学生救国会的组织下,纷纷返回本县开展宣传活动。他们用连环画、标语等形式宣传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八大主张,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推销《解放》《西北》《民先队手册》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刊。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组织了慰问团,前往三原、泾阳红军驻地慰问,聆听贺龙等指挥员讲述红军战绩,不少同学当即表示要求参加红军。
1937年7月,三原武字区通过开办妇女识字班、女子义务学校,教妇女学文化,讲解抗日主张、方针政策,从中发现、培养骨干,发展了一批女党员。三原女子中学学生在抗日热潮的影响下,组成宣传小组,深入各家各户,动员适龄青年参军,鼓励家庭妇女阅读抗日救亡报刊,教唱抗日救亡的歌曲。
1938年2月,岐山县30余旅省同学,包括西安女师学生阎淑琴、王花如等,到青化、益店、蔡家坡、高店、枣林、罗局等乡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她们精心准备抗战简报,演唱抗日歌曲,散发抗日传单,张贴抗日标语。
1939年至1941年,中共党组织在鸡峰地区18个村庄和一些学校办起了妇女识字班和夜校,教妇女识字,唱抗日歌曲,针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给学员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并发展了一批女学员,于1940年秋建立了以妇女为主的党支部。
二、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以农村妇女为主力军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蓬勃地开展起来。1939年2月20日,为了纠正对妇女工作的轻视态度,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号召建立健全妇女组织,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9]70随后,中共中央妇委会发布了《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指出妇女运动的总方针是“坚持抗战,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更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各方面的工作”。[10]346边区妇女委员会组织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各项活动,为八路军和后方自卫军的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抗日女干部的成长
抗日女干部是抗日救亡活动的核心人物。边区各级妇女救国会、妇女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培训乡村妇女干部,扩大抗日的基础,培育抗日的骨干力量。至于正规的军事院校和专业学校等,则是以培养中高级知识女性人才为主。
1937年底,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在延安成立。陈正人、李贞先后任校长。学校设立补习科和职业科,管理非常严格,从这里毕业的学员约有300余人。1938年11月,抗大第四期招收了女生大队(第八大队),全队654人,张琴秋任大队长。1940年,又有300余名女青年进入第六期学习班学习。
1939年7月,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成立,办学方针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和做实际工作的妇女干部,组织千千万万妇女参加抗战。”[10]44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女大的校训是“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开展灵活的教学活动。女大先后培养了2000余名妇女干部,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1]228
(二)积极支援前线
在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学脱产人员相当多,1937年为四五万人,后来增加到10万以上,占边区总人口的8%。保障边区供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1938年至1939年,边区妇女克服种种困难,在物资贫乏的条件下共做袜子、手套8万双,鞋2万双。1940年,延川县妇女做军鞋5万双。1943年,延属分区又订做军鞋15000双。陕甘宁边区的妇女们不怕困难,不畏艰辛,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组成慰问队、救护队、缝衣队、洗衣队等等,为抗战刻苦工作。1937年至1938年,边区妇女共组织看护队1663个,参加妇女8415人;缝衣队825个,参加妇女5796人;洗衣队828个,参加者4160人。[5]288
边区妇女的无私奉献壮大了八路军的队伍。为了抗日大局,边区妇女舍小家为大家,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姐妹送兄弟的参军热潮。1939年底,在边区妇女的积极配合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动员任务,有3500余名青年参军。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开始到日本投降,总计参军、参政人数达44957人,约占边区总人口的3%。
为了支援前线,边区妇女担任起后方生产的重任,出现了“男子前线打东洋,妇女后方生产忙”的生动景象。她们不仅从事一般的农副业生产,还从事当时男人们才会干的开荒种地、送粪施肥等比较艰苦的体力劳动。1938年至1941年,开始有2万妇女参加纺织活动,后来增加到20万人,产量也由原来的2万余匹增至7万余匹。1939年,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的妇女有10万多名,共开荒6万多亩,植树7万余株。除了满足自己的生产外,广大妇女还组织了“帮耕队”,为抗日军属代耕。妇女广泛参加大生产,自然就涌现出了许多生产能手,马杏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由于劳动成绩突出,她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边区妇女劳动英雄称号。
(三)为抗战献计献策
在激情澎湃的抗日救亡活动中,边区妇女们积极参选参政,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一些受到训练的妇女干部纷纷深入边区各乡、县指导农村妇女参加选举。1939年1月17日,边区参议会第一届会议召开,高敏珍等19位女参议员参加了会议。在第二次边区的普选中,乡级女参议员多达2005人, 167人成为县级参议会议员, 17人是边区级参议会议员。安塞县邵清华还被选举为第一位女县长。妇女们参加选举的热情非常高,正如子长县群众自编的《乡选歌》所唱的:“边区要发展,选举要广泛,选举好人把事办,生活能改善。人口四万万,妇女占一半,国事家事全要管,事情才好办。道理说明了,妇女觉悟到,宝娃快把门照好,妈妈当代表。”[12]456
1940年1月,延安妇女界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并发出《告全国姐妹书》,为保护妇女的利益、保障妇女的参政议政权利而呼喊。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纷纷报道,为妇女的权益鼓与呼。据统计,全边区共选出乡级女参议员2005人,县级167人,区级17人,许多妇女被选为乡长、区长。[13]
为加强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妇女工作大纲》精神,做出了《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要求在乡以上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1937年9月12日,在延安抗大召开发起人与赞助人大会,选举由李坚真、蔡畅、丁玲、史秀云等15人组成的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李坚真、史秀云当选为正、副主任。
边区妇女在筹委会的领导下,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改造并成立了县、区各级妇女联合会。边区妇联筹委会与边区内各群众团体、各机关及西安、汉口等国统区的各救亡团体建立联系。1938 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正式成立,史秀云任主任。边区妇联会成立后,领导广大妇女积极投入到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边区妇联的会员由原来的17万人增加到27万人。1943年5月13日,边区妇联与边区总工会、边区青救会合署办公,组成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1944年春,边区开展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妇婴卫生运动需要有健全的妇女组织及大批妇女干部来领导,西北中央局决定,边区妇联会重新开始对外办公。1945 年3月,边区妇联会作为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发起单位,为建立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积极工作。
(四)边区妇女的反封建斗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学会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开始寻找自身的自由和解放。一是开展放足运动。1939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边区18岁以下妇女,一律禁止缠足;40岁以下缠足妇女立即放足;40岁以上妇女劝令解放,不加强制。①参见陕西省妇女联合会:《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1937—1949)》,1982年,第59页。在条例的鼓舞下,边区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缠足运动。各县妇联成立放足突击委员会,深入边区各个地区宣传缠足的弊端。并利用唱歌跳舞、漫画、板报等多种形式说明放足的好处。各地区还开展放足竞赛活动。许多放足妇女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现身说法,解释放足的好处,使人们增加了放足的信心。通过不缠足运动,80%的缠足妇女都自愿放足,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是追求婚姻自由。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规定“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禁止纳妾”、“实行一夫一妻制”等等。由此,现代婚姻制度逐步确立,妇女的婚姻自主开始成为主流,封建的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被禁止。很多饱受封建婚姻之苦的妇女勇敢站出来提出离婚,追求自身的爱情和幸福。
1942年12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和《修改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属条例》。对于抗日将士的婚姻提出了妥善的处理办法,同时详细制定了优待抗属的具体规定。此外,在妇女教育、卫生保健和儿童保教等方面,边区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有力推动了边区妇女运动的发展。1944年3月,针对不断变化的边区情况,边区政府又颁布了《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这些婚姻条例为妇女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包办婚姻极大地减少了,自由结婚开始流行。戏剧《刘巧儿告状》通过讲述青年妇女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与自己对象结婚的故事,反映了边区妇女追求婚姻自由、突破封建束缚的观念改变。
三、陕西妇女运动的特点
抗战时期,陕西各界妇女不分阶级、党派、职业、宗教、民族,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斗争,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努力争取妇女的自身解放,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以城市妇女为主导,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抗日活动普遍开展。由于陕西处于西部,教育比较落后,知识女性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最先是这些知识女性走上街头从事抗日救亡宣传。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战场形势的变化,广大农村妇女开始觉醒,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体。在城市妇女干部和进步知识女性的启发、带动下,广大农村妇女普遍组织起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陕西各级妇女爱国组织是妇女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陕西国统区普遍建立起各级妇女慰劳会分会,成立基督教女青年会,也有中国工合西北办事处妇女部的各级组织。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妇女联合会、救国会等组织也是妇女救亡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和推动者。不管是关中,还是陕北陕南,各地的妇女组织是不分阶级、党派、职业、宗教、民族的,都是陕西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妇女运动中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最先发起妇女救亡运动,制定各种政策和文件,宣传妇女运动的重要性,共产党员在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着核心的作用。通过妇女运动的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争取妇女解放。在陕西妇女慰劳会、抗敌后援会妇女分会、中国工合西北办事处等组织中,女共产党员起着骨干作用。在女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妇女运动真正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主张,从而推动了陕西妇女抗日民主运动的顺利发展。
[1]我们工作的一周年[J].西北妇女,1938,(9).
[2]本会消息[J].西北妇女,1938,(8).
[3]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军民抗战纪事[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4]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5]罗子为.西北区工业合作之回顾与前瞻[J].西北工合,1939,(7).
[6]任柱明.西北区妇女工作[J].西北工合,1939,(7).
[7]姜漱寰.四年来西北工合之社会服务工作[J].西北工合,1943,(5).
[8]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九)[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9]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49)[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10]全国妇女联合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1]增瑞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述略[A].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23)[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2]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3]马璞,赵传海.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述论[J].河南大学学报,1989,(1).
责任编辑:张艳玲
Shaanxi Women’s Movemen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YUANWenwei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re was a large- scale mobilization among women in Shaanxi Province. Activities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ere far reaching. In the Nationalist Party of China controlled area, some women joined the army and fought in various battles. Some attended organizations to support the front line, including the women’s consolation association of Shaanxi, the office of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d other equivalents. In the Shaanxi- Gansu- Ningxia border region, women also participated in and carried out an Anti- Feudal struggle. Their actions reveal the unity and strength ofthe Chinese nation.
Anti- Japanese War; women’s movement; support the front line
10.13277/j.cnki.jcwu.2015.05.013
2015-08-19
D442.9
A
1007-3698(2015)05-0084-07
袁文伟,男,西安邮电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71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