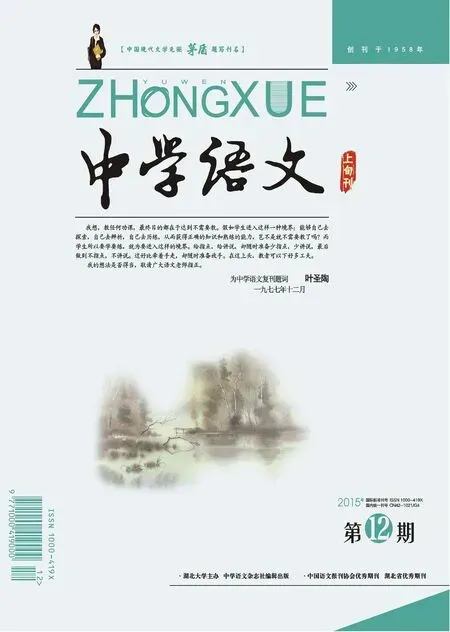形之于外,求之于内
——夏丏尊写作教育思想研究之二
2015-01-31汲安庆
汲安庆
形之于外,求之于内
——夏丏尊写作教育思想研究之二
汲安庆
对于怎么写,夏丏尊在《文章讲话》《文章作法》《文心》《国文百八课》《开明国文讲义》等著作或教材中,在《关于国文的学习》《学习国文的着眼点》等文章中,探讨不厌其详。可以说,在其写作教育思想体系中,这部分的思考,占据了半壁江山。
关于怎么写的论述虽然浩繁,但择其要,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一、勉力求通,不忘求好
“求通”“求好”主要是从写作标准的角度来谈的。
在夏丏尊看来,求通的标准可分为二:一为“明
了”;二为“适当”。“明了”包含形式上的明了和内容上的明了。形式上的明了,是指“通”,即句的构造要“合法”,不能出现病句;句与句之间的结合要能呼应——“发展这些文化的民族,当然不可指定就是一个民族的成绩”,此句便是典型的失去照应,首句的“民族”与次句的“成绩”根本不匹配;内容上的明了,是指表达无歧义,用辞要确切。前者需靠文法知识救济,后者则必须从各方面留心。
如何留心?夏丏尊谈了自己的经验——
积极的方法是多认识辞,对于各辞具有敏感,在许多类似的辞中,能辨知何者范围较大,何者范围较小,何者最狭,何者程度最强,何者较弱,何者最弱。消极的方法,是不在文中使用自己尚未明知其意义的辞。想使用某一辞的时候,如自觉有可疑之处,先检查字典,到彻底明白然后用入。(夏丏尊《关于国文的学习》)
能掌控近义词之间细微的区分度,遇可疑字词能自觉查阅字典,这是十分严谨而科学的态度。字斟句酌,避免差池,努力将最恰当的词用到最恰当的地方,不仅是对读者的负责,也是对自我精神生命形象的苛严,更是对具有极致之美的言语表现境界的执着追求。
尽管“明了”在夏丏尊的写作理论中属于“消极修辞”(怎样使文章不坏)的范畴,不属于“积极修辞”(怎样使文章更加好),但是夏丏尊从来不会将之视为“小儿科”,而是视为“修辞的第一步工夫”,并认为“一切文章的毛病,除了文法上的缺点外,几乎都可用消极的修辞工夫来医治”,还谆谆提醒学生“要养成遵守的习惯却须随时用工夫”①。因为有了这样的体认与重视,所以无论是指导学生写作,或批改学生习作,亦或自己创作,夏丏尊对文章通与不通的问题,都是极其敏感的。学生作品出现文不对题或文理不通的情况,他一般会采取总批或眉批的方式开示,但是对措辞不当的地方,他则会亲自动手,一一加以修改②。同时代的教师姜丹书盛赞夏丏尊的作品:“最注重研析字义及同类性质、作文法则等,义理务合逻辑,修辞不尚浮华,其为语体文也,简当明畅,绝无一般疵累之习,善于描写及表情,故其所译世界名著如《爱的教育》《棉被》及自撰之《平屋杂文》等,读之令人心神豁然,饶有余味,如见其人,如见其事也。”(姜丹书《夏丏尊先生传略》)简当明畅,无疵累之习,饶有趣味,这种美好的言语表现境界正是夏丏尊不懈求通的结果。
夏丏尊认为,明了是“形式上与部分上的条件”,适当则是“全体上态度上的条件”。如何适当?必须心存读者,“努力以求适合读者的心情,要使读者在你的文字中得到兴趣或快悦,不要使读者得着厌倦”。怎样具体操作呢?夏丏尊借了当时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 “六W说”,亦即①为什么作这文?(Why)②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What)③谁在作这文?(Who)④在什么地方作这文?(Where)⑤在什么时候作这文?(When)⑥怎样作这文?(How),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用他自己的概括来说就是“谁对了谁,为了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了什么方法,讲什么话”,写作中最好对之“逐一自己审究”(夏丏尊《关于国文的学习》)。
作文目的、作文题旨、作者地位、作文场合、作文时代、作文方法,一应俱全!似乎繁琐至极,甚至很无聊,可是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言语表现的整体效果和质量。夏丏尊所举的例子中,那位学生的信(“我钱已用完,你快给我寄十元来,勿误”)之所以会激怒父亲,正因为没有考虑到自己是儿子身份,反以老子自居,加以命令,怎么能不让他的父亲大光其火呢?进入民国时代,本该称“总统”“督军”,却套用前清的“元首”“疆吏”,这正是因为没有考虑到作文的历史语境问题。可见,夏丏尊对“适当”这一写作标准的设定,并非闭门造车,或多此一举,而是针对现实写作中的诸种弊病所提出的一种针对性极强的矫治方案。平心而论,在写作秘笈或宝典充斥课堂与坊间的当下,能有多少人写作时会将“6W”全部审究的呢?即使一窝蜂似地将心思花在了作文题旨“What”和作文技巧“How”上,可出现了虚假立意、新八股写作(如议论文写作中的“引-议-联-结”)等丛生的陋习,能算是“审究”吗?这样想来,夏丏尊“求通”说中所蕴含的严谨扎实的态度,精益求精的追求,真是让人感到朴素而温馨。
心存读者,让他们阅读时能得着兴趣或快悦,很容易让人将之与屈就自我,取媚他人的庸俗写作联系起来。这实是大谬。夏丏尊提倡“读者意识”,其实不为别的,只不过为了更好地锤炼字句,讲究言语表现的智慧,谋求心灵对话的通畅和快适而已,这对读者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关怀,对作者自己则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潘新和称:“在现代语文教育家中,注重培养学生读者意识的不乏其人,但能对此作周详的思考和策划,却并不多见。”③此为确评。
夏丏尊在写作教育中勉力求通,但亦不忘求好——积极修辞。
积极修辞的方式很多,夏丏尊和叶圣陶主要谈了以下几种:①调和。即整齐、相应、谐和、自然。句子要读去顺口,听去悦耳;全篇要统一有序,体式分明。②具体。即将空漠难解的无形事情用具体的方法来表达。③
增义。即用有关系的材料附加在所说的话里,使所说的话意义更丰富,如把“国事危急”说成“国事危如累卵”。这些方式都是针对了读者的心理需求,力争使表达更合情境,更加有效。
非常有意思的是,夏、叶二人还反其道行之,提出了三种对立的积极修辞方式:①奇警。主要是针对长期调和所造成的阅读倦怠。如“人有毁谤应该声辩”是调和的说法,奇警的说法就会是“止谤莫如缄默”。初看,不合情理,但是如果加以说明,也会生出说服力。②朦胧。这是具体的反面,故意将意思表达含蓄一些,如交际社会上把“撒粪”改说“出恭”。③减义。与增义相对,故意把要说的话不说尽,或不说,让对手用想象去补足,如对一个愚人说“你真聪明”,骂无用的人为“宝贝”④。将言语表现的辩证法诠释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奇警、朦胧、减义诸法,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奇异”——最能使风格既明白清晰而又不流于平凡的字,是衍体字和变体字;它们因为和普通字有所不同而显得奇异⑤,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的“陌生化”——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⑥,还有英美新批评所追求的“反讽”(irony)——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⑦,在精神本质上十分契合,却又天然地具有浓郁的中国风、个人味,独特的发现与创造能力,一样可以在理论上实现“人生的通感”,这的确令人称奇。
二、知行合一,熟能生巧
这主要是从写作实践的层面来谈的。
在“知”与“行”之间,夏丏尊颇为看重“行”。他说:“技术要达到巧妙的地步,不能只靠规矩,非自己努力锻炼不可。学游泳的人不是只读几本书就能成,学木工的人不是只听别人讲几次便会,作文也是如此,单知道作文法也不能就作得出好文章。”⑧怎样努力锻炼,他在许多方面都作了强调。
对于作文次数,夏丏尊力主多练。这与当时很多学者的意见相左。比如,肖楚女、叶苍岑等人主张作文每两周一次,短篇习作一小时可完者,每周一次⑨;胡适、梁启超等人主张每学期至多三次,因为“多做学生便要讨厌,或拿一个套子套来套去”,不如“做一次便将一种文做通。下次再做别一种文。如此便做一篇得一篇的好处。尚有补助法,使学生在课外随意做笔记,以为作文的补助,比出题目自然得多”⑩。夏丏尊是力挺每周一次的命题作文的,并且也不认为课余多做笔记、日记、通告、书札,就是“补助法”,就是主张真正的作文,“把课内外打成一片”,作文是生活的一个项目,同吃饭、说话、做工一样,或者就是生活。在尝试小品文教学时还指出:“无论如何,多作总是学文底必要条件之一。现在学校中每月二次或三次的文实嫌太少。”这的确说到了点子上。千里马是跑出来的,好文章是练出来的,光说不练,眼高手低、心手不一,自然不能出佳作。
但是,夏丏尊倡导的多作,迥异于当下的题海战术。因为多作的同时,他也很强调多看、多思、多商量。多看,从他《关于国文的学习》《阅读什么》《国文科课外应读些什么》等文,自己作文理论著作中所征引经典范例显示出来的辽阔范围,还有曾经为学生开列的85部书单中,不难一窥端倪。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学、学术,甚至连工具书,《新旧约》,还有陈望道于1920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都位列其间⑪。这与古人的“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的思想,显然一脉相承。
既要多看,也要多思。把自我放进阅读的对象中去,两相比较,“一壁读,一壁自问:‘如果叫我来说,将怎样?’对于文字全体的布局,这样问;对于各句或句与句的关系,这样问;对于每句的字,也这样问”(夏丏尊《关于国文的学习》)。这种蝎子般的自觉而坚韧的思索,自然更能解悟文本的秘妙或不足,不断提升思辨、批判和表现的能力,进而渊深自我的写作素养。他指出《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面貌的文字极忠实,却吃力不讨好,无法给人想象的空间 (夏丏尊 《关于国文的学习》);批评易卜生《娜拉》中的人物语言不切合身份,发现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作家作品中 “作者忽然现出”,文字“在形式上失了统一”⑫,莫不是多思、深思之后所下的判语。马叙伦在为夏丏尊所写的铭文中有“思通百代,焕若泉新”一句,正是对其思想力量的肯定,称得上“知音之评”。
又因为,夏丏尊能始终以形式为学习国文的着眼点,不仅关注写什么,还关注怎么写,为何这么写,所以更能把握国文的体性,使阅读、写作都能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进而较好地实现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加之,他不仅关注写作之用,也关注写作之美、之趣——“一味抒述内心生活,虽嫌虚空,然账簿式的事实的排列,也实在没有趣味。因此,最好的日记是于记述事实之中,可以表现心情的作法。”书札“不只简单的排列要事,很能使受书的爱读,而且读了增加不少的兴趣……书札中能兼述生活情趣,就能不呆滞而饶兴味。”⑬这与当时学者重应用文而轻文学的写作观(如刘半农就认为“应用文是青菜黄米的家常饭,文学却是个
大鱼大肉;应用文是‘无事三十里’的随便走路,文学文乃是运动场上大出风头的一英里赛跑”⑭),截然不同,所以他提倡的多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化作学生精神成长的自发需要,成了内在的驱力,而非外在的拉力、压力了。
更要多商量。作品写好后,与同学切磋,向师长请益,明得失,悟秘妙,从而尽可能地将文章修改完善,臻理想之境。这种思想和实践,在《文心》中有多处体现,如《一封信》中的乐华与大文共写一封信,请枚叔提意见;《推敲》中的宋有方请乐华为之修改、讲评《机械的工作》一文。朱光潜在回忆春晖中学的教学经历时说:“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与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观。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⑮范泉受内山完造之托,翻译了日本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向夏丏尊请教。夏丏尊在点明其“简明扼要”的优点时,也道出其不足:“不少外国人的观点,说得似乎不够恰切”,并语重心长地指出:“有些语句,得意译。不能完全直译。意译了,反而能够表达原作的精神。”⑯一下子解决了长期困扰范泉的翻译写作问题。文章共赏,多交流,听听他人的意见,连成人学者都觉得兴趣盎然,受益无穷,更何况学养相对薄弱的学生呢?多商量,多分享,思维洞开,想象翩跹,一如戴维·伯姆所说的那样:“我们坐到一起来互相交流,进而创造出一个共同的意义;我们既‘参与其中’,又‘分享彼此’,这就是共享的含义。”⑰如此,多作又怎么会索然无趣呢?有兴味,有乐趣,有生长,再多的写作都会化为享受;反之,再少的写作,都会感到压力重重,不胜其烦。
努力锻炼,忠于自我、有感而发是前提。在《文心》中,夏丏尊借王仰之先生的口说“题目虽由我出,却还是应付真实的生活”——这真实的生活有外在生活的真实,但本质上是内心生活的真实。因为他明确说过“作文先要有真实的‘情’,才不是‘无病呻吟’”(夏丏尊《作者应有的态度》),与叶圣陶的求诚观——“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⑱是一个道理。但是,夏丏尊也很注意系统化训练,如各体作文法则的系统探究,形式知识的无声渗透。这方面,《文章作法》《文章讲话》等理论著作就是上述探索的结晶。为了激活学生的写作兴趣,他还主张试作小品文,因为小品文有如下好处:①可以作长文的准备;②能多作;③能养成观察力;④能使文字简洁;⑤能养成作文的兴味⑲。特别是将教与学、知识与生活、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的追求,令人情不自禁地想到王国维所说的“观其会通,窥其奥窔”⑳。
这说明,夏丏尊对“知”其实也是密切关注的。在《文章作法·绪言》中,他旗帜鲜明地宣称:“专一依赖法则固然是不中用,但法则究竟能指示人以必由的途径,使人得到正规。渔父的儿子虽然善于游泳,但比之于有正当知识,再经过练习的专门家,究竟相差很远。”“法则对于技术是必要而不充足的条件,真正凭着练习成功的,必是暗合于法则而不自知的。法则没用而有用,就在这一点,作文法的真价值,也就在这一点。”
夏丏尊写作教育中的知行合一思想,有的偏于先知后行,如评改学生习作,品评作家作品,自我写作中文艺理论的悄然出之;有的偏于先行后知,如重读旧书,对语感的率先发现和对语感训练的提倡。更多的时候,似乎是且知且行,即知即行,如《读诗偶感》《阮玲玉的死》《闻歌有感》等作品的诞生,还有对作文教育改革的多方尝试——“稿上订正,当面改削,自由命题,共同命题,分文体编讲义,分别讲解教授作文法等方法”,都尝试过。“所教的学生成绩并不差,可他还是感慨于学生作文内容的空洞。为了改变学生作文的态度和国文学习效果,他经常会烦闷很久,最后就教国文与学国文问题提出了‘不要只从国文去学国文,不要只将国文当国文学’的国文教育思想。”㉑令人觉得,他的写作教育思想中,知与行似乎是一回事,阳明兼得,水乳交融,所以无论是指导学生写作,还是自己创作,都能进入化境。
三、努力修养,文从道出
这是从写作外围学养的角度来谈的。跳出国文学国文,跳出写作学写作,功夫在诗外。
“白马湖”作家群的艺术信条是“首重人格,次重文艺学习”㉒,作为班首的夏丏尊更是如此。早在写《文章作法·序言》时,他便意识到人格素养对写作的重要性:“内容是否充实,这关系作者的经验、智力、修养。至于形式的美丑,那便是一种技术。”其实,人格素养的高下,也是会影响形式的美丑的。言语人格优秀的人,从来都是将“文质彬彬”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的。在《作驳论的注意》一文中,他似乎注意到了这点:“文章真要动人,非有好人格、好学问做根据不可,仅从方法上着想总是末技。因为所可讲得出的不过是文章的规矩,而不是文章的技巧。”将好人格与好学问并列,并说会影响文章的技巧,亦即形式的美丑、优劣,显得十分允当。多年之后,在《关于国文的学习》一文中,他重新突出了言语表现人格的重要——
文字毕竟是一种人格的表现,冷刻的文字,不是浮热的性质的人所能模效的,要作细密的文字,先需具备
细密的性格。不去从培养本身的知识情感意志着想,一味想从文字上去学习文字,这是一般青年的误解。我愿诸君于学得了文字的法则以后,暂且抛了文字,多去读书,多去体验,努力于自己的修养,勿仅仅拘执了文字,在文字上用浅薄的工夫。
人格内涵中更强调“知情意”的三位一体,且培养“全人”素养的意识有所明确。将人格素养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大概是针对了当时学生偏科,学问不扎实;文风浮华,不足征信;内容空洞,矫揉造作的写作现实吧!
将人格素养视为言语表现的最高学问,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写作教育中 “修辞立其诚”(《周易·乾》)这一精神道统的忠实继承。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将言视为德的自然产物,德对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他说的“养气”其实就是“养心”,进行人格的自我修炼,知言、善言,正是善于修炼人格的结果。朱熹说得更为具体、明确:“这文皆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重申了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这里的“道”,内涵已有所扩展。有论者认为是指“事物的规律和道德原则”㉓,还有论者认为是指“宇宙原理和道德准则”㉔。但是不管偏于哪种理解,都没有缺失体现自我人格素养的道德之维。
当然,重视人格对言语表现的决定作用,也有同时代“思想共同体”的相互驰援与补充、生发。叶圣陶就特别看重作文上的“求诚”——从原料上讲,要是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征验、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讲,要是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卑鄙的态度。”㉕外求事真,内求心诚,表现出非常谨严、庄重的写作使命感。朱自清说:“古人作一篇文章,他是有了浓厚的感情,发自他的肺腑,才用文字表现出来的。在文章里隐藏着他的灵魂,使旁人读了能够与作者共感共鸣。”㉖虽然忽略了文字对情感、灵魂的规约、塑造作用,但是强调为情而写,自然成文,道出了所有优秀文章的共性。朱光潜也说:“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一个文人先须是一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这个基础,他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的独到的风格,世间也只有这种文字才算是上品文字。”㉗人格、学问、经验、文章,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但是人格起着最关键的作用,是基础,是源头,是统领。
有继承,有生发,有体认,有坚守,但是要想让这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化为学生言语表现的习惯、能力,并最终融入他们的精神生命,形成素养,乃至信念,则必须投入大量的,不倦的教育实践。
除了在著述、演讲中不断点染人格对言语表现的决定作用之外,在写作教学中,夏丏尊也是始终不渝地贯彻这一理念的。
丰子恺在《悼丏师》一文中回忆了两个细节:一是某生写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匐奔丧”,夏丏尊苦笑着问他:“你那个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二是某生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丏尊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种当头棒喝可以说是对虚伪人格,套作之弊毫不留情地抨击,对真诚言语人格的有力捍卫。针对写作中的具体病症,勇敢地亮出自己的不满,或艺术地点睛,完全可以促使学生更好地意识到真诚的言语人格对为文的重要性。有痛感,有震惊,成长才会更快。帕克·帕尔默就说过:“方法固然重要,然而,无论我们做什么,最能获得实践效果的东西是,在操作中去洞悉我们内心发生的事。越熟悉我们的内心领域,我们的教学就越稳健,我们的生活就越踏实。”㉘夏丏尊既洞悉学生的灵魂领域,也知道他们的写作缺陷,并及时、果断地矫正,不折不扣地贯彻了他教育是“英雄的事业,大丈夫的事业”的信仰㉙,这样的教育当然是稳健的、踏实的、有力的。
作文评改中,夏丏尊也始终坚守着这一信念。一个叫王炯的学生,古文背得熟,作文喜欢引经据典,连缀成篇,但是缺乏自我的思想。这种作文在前任语文老师那里,常被褒奖,并获满分,可是夏丏尊并不赞成这种写法,对之循循善诱,努力使其用白话文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位学生叫陈润堂,不爱引述经典词句,但能忠于自己的思考,时有新意出现。前任老师评之内容空洞,无据可寻,夏丏尊却对之赞赏有加,并经常将他的作文当作范文介绍。有了这种健康作文观的引领,以及不断地激浊扬清,学生的作文风貌怎能不为一变呢?
夏丏尊对于虚伪造作,视套成习的现象拍案而起,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小题大做——放在当下,甚至能被视为炒作,惹得一身骚。可是,正因为这种莫名惊诧,不以为意,从他所处的时代到当下,这些弊病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谈自强不息,学生捏造出自己残废,父母离世的事实,一点儿都不会心中有
愧。至于套作,更是风魔痴狂。据说,作家叶兆言以“禁止鸣笛”的交通标志为题,让学生看图作文,学生竟然也能玩出一度备受推崇的“文化历史大散文”来。比如,从秦始皇的“禁止鸣笛”一直说到岳飞的“吹笛”,驾轻就熟,非常流畅,却把老师扔进了五里云雾之中。南京特级教师吴非讥之为“滥抒情,口吐白沫;假叹息,无病呻吟;沾文化,满地打滚;伪斯文,道貌岸然”㉚,可谓一剑封喉。梁启超指斥当年的写作教育“奖励剿说,奖励空疏及剽滑,奖励轻率,奖励刻薄及不负责任,奖励偏见,奖励虚伪”(梁启超《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此类顽症,今日何曾消除?基于此,夏丏尊的仗义执言,显得何其珍贵!
夏丏尊的努力修养,也贯彻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教学、办刊、译书、撰文、交际,始终秉持着真诚相待,一丝不苟的为人原则。尤其是独处、自省,他竟然提到了“文艺创作的源泉”的高度,认为“在森罗万象的自然人生之中”,“最安全正当的方法,是从自己下手”去认识,但是,一个人“真正要知道自己”却并不容易,非要“自己客观地作严酷的批判,深刻的解剖不可”㉛,这使他的不少文章充满了自我批判的色彩,读来颇具发人深省的力量。芝峰法师赞其为人:“贫于身而不谄富,雄于智而不傲物,信仰古佛而非佞佛,缅怀出世而非厌世,绝去虚伪,全无迂曲。”㉜这种真诚坦荡、率真刚直的个性,在其写作教育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很好地实现了作文与生活打成一片的追求。
①④夏丏尊、叶绍钧:《国文百八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5-37页、107-132页。
②夏弘宁主编:《夏丏尊纪念文集》,浙江省上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01年版第261页。
③潘新和:《夏丏尊写作教学观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⑤[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⑥[俄]莱芒(Lemon)、里斯(Reis)编译:《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2页。
⑦赵毅衡主编:《“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⑧⑫⑬⑲夏丏尊:《文章作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133-136页,92-95页,89-90页。
⑨叶苍岑:《对中学新生谈国文学习》,《国文杂志》,1942年第1卷第2期。
⑩梁启超:《作文入门》,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⑪夏丏尊:《叫学生在课外读些什么书》,《春晖(半月刊)》,1923年第17期。
⑭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期。
⑮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文学杂志》,1948年第3卷第5期。
⑯王利民:《平屋主人——夏丏尊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⑰[英]戴维·伯姆:《论对话(OnDialogue)》,李尼科编,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⑱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58-359页。
⑳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㉑傅红英:《夏丏尊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148页。
㉒丰子恺:《丰子恺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页。
㉓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㉔潘立勇:《朱熹对文道观的本体论发展及其内在矛盾》,《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
㉖朱自清:《朱自清语文教学经验》,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㉗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㉘[美]帕克·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㉙夏丏尊:《夏丏尊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㉚吴非:《王栋生作文教学笔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㉛夏丏尊:《夏丏尊文集·文心之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㉜杜草甬、商金林编,《夏丏尊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
[作者通联: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