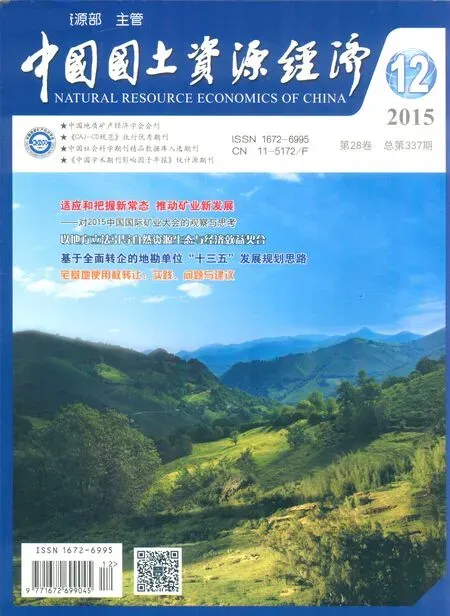以地方立法引导自然资源生态与经济效益契合
2015-01-30祁雪瑞
■ 祁雪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 450002)
以地方立法引导自然资源生态与经济效益契合
■ 祁雪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 450002)
近年来自然资源所有权行使中的生态责任凸显,治理效果却很微弱,主要原因是相关制度难以激发责任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动力。提出生态与经济两种效益契合的立法引导问题,是一个新型的立法原则倡导,也是缓解乃至消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张力的具有较高可行性的方向。这方面国家层面的立法较多空白和模糊,正是地方立法大显身手的空间和时机。文章从立法引导两种效益契合的总体思路、达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原则要求和制度途径、注意立法针对性与张力相结合、增强立法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地方立法;自然资源;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法制;契合
1 问题提出的背景及意义
1.1 问题提出的现实背景及迫切性
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保护领域存在“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现象[1]。立法理想化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徒劳无功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对法律权威性的销蚀和对建设法治国家的破坏。我国实行的是自然资源公有制,以国家所有为主,集体所有为辅。近年来自然资源所有权行使中的生态责任凸显,治理效果却很微弱,主要原因是难以激发责任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动力,内心的不认同导致行为的规避甚至是对抗,又由于行政执法方面的种种原因造成监管乏力,最终积累出空气混浊、水体污染、矿区灾害等生态环境破坏现象的呈现,致使社会濒临承受的极限。这促使决策者和研究者共同聚焦到经济与生态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以下问题:在自然资源经营权和流转权不断放宽的背景下,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有没有可能通过所有权管理和所有权实现的技术安排,大力开发生态效益,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1-3]?所谓“后发展优势”,最主要的含义应该是对发达国家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历史教训的总结和规避。
1.2 问题提出的理论背景及理论意义
当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于自然资源权利争议较大的是在其开发利用环节的制度设计,也就是对自然资源非所有利用的权利设计,有学者主张强化国有,有学者主张强化市场,设立永佃权制度。常修泽研究员创立了“广义产权论”,主张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四联动”。有学者主张采用二元立法模式,对于自然资源的非消耗性利用设立用益物权模式,对于消耗性利用则设立所有权模式[4-7]。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的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在新公共信托理论的框架下进行,最新的动态是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自然资源利用中国家的生态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用方式,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扩充国家所有权的范围和行使的有效性,所有权行使方式多采用直接行使和全权代理。有国外学者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区分为国家公产与国家私产。英美法系着重对行政管理职能与所有权行使的严格区分,以及政府对市场失灵的策略与技术调控。国内研究者针对经济发展、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明显冲突,注意到了国家所有权行使中的生态责任,但多从谁第一、谁优先的二元对立思维进行论述,认为目前到了从经济优先转变为生态环境优先的发展阶段,现行立法也肯定了“环境保护优先”的原则[8,19]。也有论及开发生态环境本身的经济价值的,但是较少有学者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与效益契合问题,以及国家所有权行使中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如何发挥的问题。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李志青教授新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生态助力于资本,还是资本让位于生态?》[9],李教授的观点可以看做是对本文思路的一次证成。他认为生态与资本不矛盾,是统一的,两者的区别仅体现在要素的价格及其配置的合理性上。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不是仅仅为了保护环境,而是为了能让中国的发展从资本——生态要素的合理配置中获得新的动力、新的效率和新的潜力。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要依靠市场力量自身,而不是政府。推进资本与生态的和平共处,或者合则两利的互动关系,需要从微观处考察,从激励机制、治理机制以及自然机制入手,找出背后的规律,然后逐步推进。
1.3 地方立法引导的必要性和功能定位
法律是法治的基本要件,立法是法治的基础性活动,市场经济一定是法治经济。立法相比政策、倡导等其他引导手段来说,强制力更高,覆盖面更广,相应地对相关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也会更有力量。行为的背后是对利益的考量,现实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张力空前巨大,不立法不足以引起重视、扭转颓势和引领趋势,法律本身的规范、评价、预测、引导等特性决定了立法是从整体上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纠偏和导向的最有效的方式。生态经济的生成必然是通过生态立法来引导的,任何其他引导手段都难当此任。立法对两种效益契合的引导是法律在规范微观经济行为中作用的显现。
地方立法相比中央立法来说,对微观经济行为的调整更具有优势,甚至可以细致到针对某一个企业的具体特点。我国的立法权模式是集权分权模式,特征是地方可以根据中央的授权行使立法权,那么根据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治理念和上位法的原则性要求,地方立法对两种效益契合的引导应致力于对生态效益思维的形塑、对生态友好经营模式的鼓励和对环境友好技术的支持。由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利用领域,所以地方立法中对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契合的引导应该以自然资源所有权行使为主要内容。
2 立法引导的可行性及生态法制的新趋势
2.1 立法空间的可能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本身就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实情是地方立法的生命力所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应在横向上考虑整个生态体系各个要素及相互关系所涉及到的法律制度的健全,也应在纵向上考虑中央和地方不同层次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协调。事实上,资源、环境、气候等生态相关的问题与地域紧密联系,地方立法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细化实施功能。地方立法能够具体细化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二是沟通弥合功能。地方立法使得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三是修补充实功能。地方立法能够及时发现现行立法的不足之处,及时修补和充实。四是创新功能。地方立法可以在解决地方事务时创立新的规则,能够为中央立法进行探索与尝试[10]。
现在我们提出生态与经济两种效益契合的立法引导问题,是一个新型的立法原则倡导,也是缓解乃至消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张力的具有较高可行性的方向。这方面国家层面的立法较多空白和模糊,正是地方立法大显身手的空间和时机,由于本文所论之问题几乎不涉及行政处罚和行政限制,因而不必担心抵触上位法,地方立法尽可以大胆尝试。对于涉及到上位法权力保留的内容,地方立法可以请求特别授权,并以立法建议的形式督促上位法的及时修改。
新一轮改革的关键任务之一是要放权于市场和社会,将过去49个较大的市才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扩大至了全部282个设区的市。这意味着这些设区的市可就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主要限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这其中的利好,是可以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及时性优势,发挥地方立法的能动性,制定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是,也可能走向反面——各种不利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发展压制生态环境保护的局面更加惨烈,这取决于作为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地方人大能否抵抗权力压力,是否具有较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
2.2 效益契合的可能性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由负相关对立关系演变为正相关双赢关系的可能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开发经济效益,挖掘生态环境本身的财产性价值也可以成为追求生态效益。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对自然资源作为生态环境要素的作用与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对自然资源的非损耗性使用方式、非破坏性利用方法不断地被发现,使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如自然保护区的绿色旅游、黄河湿地的鸟类观赏等。二是控制捕捞业、狩猎业的生产量,代之以观赏式、参与式、体验式的收费活动设计,充分挖掘获取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各类观赏性、趣味性、亲历性等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附加值,如渔业的表演性捕捞、现场加工制作海鲜食品等。三是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成本核算的前提下计算矿物质开采的适宜数量,把有形物的消耗性经济价值转换为生态环境无形的永续利用经济价值。对废弃矿场因地制宜地再利用,使其继续产生经济效益,如建设矿山公园、野外游戏型场地等。四是上述可能性实现的关键是相关部门决策者理念上有共识,行动上多沟通和配合,遇到阻碍积极协调。这需要彻底改变部门利益本位、配合消极、沟通协调不畅的流弊。必要时需进行所有权行使体制改革。
2.3 生态法制的新趋势
2015年新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关系变化的可能趋势,是生态效益话语会逐步成为主流话语,相关制度会相对完善,相关实践会趋向好转,企业终究会以生态效益为荣。自然资源具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复合性效益,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中前两种效益的矛盾最为突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传统目的主要是政府财政收入,其所有权的行使围绕利润获取展开,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略生态效益的制度设计一直延续到当下。当代中国生态环境的危机给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提出了另外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就是生态环境保护,但是从资产经营的角度来考虑,就必须用效益来引导。生态效益是生态价值中所包含的财产性部分的经济表达,这会是经营者的一个兴奋点,那么探索两种效益的一致性就成为立法研究的焦点问题,所有相关立法都将出现生态化现象。
立法生态化是指有权立法机关在遵循生态规律制定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从立法价值诉求、立法过程和立法成果上体现生态文明的理念,为保护环境和资源、防止生态危机提供法律依据的程度[11]。学界使用较多的是“法律生态化”概念,如蔡守秋教授将“法律生态化”界定为“对传统法律目的、法律价值、法律调整方法、法律关系、法律主体、法律客体、法律原则和法律责任的绿化或生态化。它以环境正义、环境公平、环境民主、环境效益、环境安全和生态秩序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以明确主体人和客体自然之间的法定关系、赋予人和非人物种的特定法律地位为特色途径”[12]。法律生态化将成为一种法律发展的趋势。
对立法生态化程度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第一,立法过程是否生态化。立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制定立法规划、立法调研、提出立法草案、审议立法议案、表决以及通过议案和公布。立法过程生态化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里贯穿生态保护理念。第二,立法是否有生态保护的价值诉求。以地方立法为样本,观察立法目的对生态价值诉求的体现,是单一追求保护生态环境,还是有多重立法目的而其中包含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追求。第三,立法成果是否体现生态化。立法的成果即各种法规范性文件。主要关注设置了哪些生态保护相关制度,是否有对应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此项内容能够反映立法生态保护的强度[11]。目前我国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立法还是地方层面的立法,生态保护的价值诉求还远未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立法价值诉求。
3 立法引导两种效益契合的总体思路
地方立法具有回应问题的及时性和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更能够把握社会问题与时代特征,在社会复杂多样而制度又大一统的国家,地方立法应该比中央立法更能发挥治理的作用。然而现实并不乐观,曾经有资深的地方人大立法专家感言,纵观过去的地方立法,90%以上都是无用的,我们的立法体制捆住了地方立法的手脚,地方立法者因为害怕越界担责而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久而久之造就了懒惰的惯性。有学者统计,地方立法重复中央立法者,约占地方立法的70% ~ 90%[13]。特别是牵涉到环境保护的地方立法,大量涉及管理相对人的义务、行政监督与行政处罚,根据立法原则,在公法领域,下位法不能加重管理相对人的责任,不能扩大行政执法者的权力,以传统的眼光来看,环保地方立法的空间是几乎没有的。然而,从专门法的立法宗旨出发,在明晰立法权力边界的基础上,还是能够找到地方立法的独特空间的。关注环境保护地方立法中对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契合的引导,是对法律实施效果的反思,同时也是对生态与经济二元对立立法理念的纠偏。
立法是对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与平衡,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变化。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240多部法律中,一半以上需要修改完善,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了法律体系形成后的大修改阶段[14]。2015年新修改的《立法法》对立法工作提出“要重视发挥地方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是发挥地方立法主动性的契机。根据《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主要可以分为地方实施性立法和地方创制性立法两大类。地方创制性立法强调的是地方创新,由于立法的动力和压力不同,广东、上海等地区在进行创制性立法时在独创性方面有明显突破,内陆省份如河南则严格遵守中央立法的精神和条文,比较缺乏独创性立法。从2007年中央推行“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地方立法的生态化进程逐步推进,在立法意向、价值诉求、内容安排方面,生态保护都有所体现,但是地方立法中对自然资源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契合的引导仍然是一个崭新的问题,目前谈论最多的是“平衡”而非“契合”。“平衡”多为舍弃和兼顾,而“契合”则强调互相借力共同发展。
资源权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整体式的,这决定了资源权中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性,既有传统民法上的占有、使用、收益等经典的利用方式,也有类似于排放、眺望、追逐、欣赏等环境法上的新兴利用手段[4]。所以,资源权是一系列属性相同的权利的总称,它比较容易生发出新的资源权类型,这给出于经济目的的生态环境非破坏性、非损耗性利用提供了契机。目前达至二者双赢的有利条件是相关立法中已经确认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又好又快”经济发展原则,不利条件是这一原则没有很好地贯彻到具体制度当中,在实践中更是遭遇重重阻碍。本文试图追随这两个效益协调发展的大方向,从所有权主体的重构,所有权权能的分离和扩展,所有权实现形式的创新,经营者效益激励,以及基于生态环境的新型权利的出现,找寻出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契合点和共同发展方向,从而设计出最适宜的法律、政策等制度规则,如此环境监督无法实现的难题也随之不攻自破。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中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制度体系,为此需要设置多层次、复合式的产权结构,设置环境产权、管理劳动产权等新型权利,明确所有权使用中关涉的各种权能、权责、权益,建立生态环境收益制度。通过所有权管理和所有权实现的技术性立法安排,变单纯生态环境保护为生态的经济价值利用,籍以平衡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达至两种效益的双赢,即立法能够切实保障“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注重发挥国家所有权行使中相对于私人所有权的生态环境保护优势,依据生态环境本身的非财产性价值与财产性价值的区分与转换,找寻到两种效益共生的理论和方法,更多重视美学价值、娱乐价值等保护性生态利用方式,缓解甚至结束经济与生态二者“你死我活”的现实困境。考虑到两大法系融合和大陆法系内部公法、私法融合的趋势,有关制度设计可不必拘泥于公法与私法、物权与产权的辨识,只注重对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行使责任、权能利益及其实现的调整即可。根据所有权权能性质的必然要求来设置权利行使、权能实现的正确途径与方式,不至于违背客观规律,欲速不达。
相关制度设计应尊重自然资源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如生态整体性、财产价值与非财产价值混合性等,重视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如一束同质性的权利和多束异质性的权利同时存在于一个标的物之上时,该怎样进行价值比较和选择,以及权利界限与责任划分。还应针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主体集合性与资源分散性、多样性,以及环境责任的加入对权利行使方式的客观要求,做出相应的制度设计。
4 立法引导两种效益契合的制度安排
4.1 立法引导两种效益契合的原则要求
达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原则要求主要有:
(1)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保护优先与合理充分利用相结合原则,注重在合理前提下的充分利用。
(2)生态效益考量要贯彻到所有权行使过程的始终,特别是在经营权市场化运作的条件下,要把生态效益理念嵌入到每一个权利行使主体的思维中,直到内化为行动自觉,这需要细致的制度性约束与激励去形塑。
(3)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中引导追求生态效益。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主要有自然资源产权界定、自然资源用途确定、自然资源监管三个方面的内容。在产权界定中照顾自然资源生态效益的整体性,在用途确定中鼓励创新生态效益开发的内容与方式,在资源监管中辨识区分并鼓励生态效益的表达。
4.2 立法引导两种效益契合的制度途径
达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制度途径主要有:
(1)对这两种效益的最佳契合点要在相关法律中给出一个阈值规定,以此指导所有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这两种效益存在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如何找准这个点,需要考虑资源的、区域的和边际的全部关联因素,建造控制模型。
(2)通过制度激励弘扬重视生态效益的经营行为。如建立企业环境友好档案,作为采矿权等经营权招投标的重要加分因素,激励的力度一定要足够抵御违法获益的诱惑。通过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划拨,如生态补偿制度,引导相关经营者重视生态效益的开发利用,遏制直接从消耗型生产活动中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和惯性。
(3)通过制度设计把全部外部成本内部化,确保相关的税费专款专用、应用尽用,确实用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效益开发。如将生态环境补偿成本、代际补偿成本、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的完善成本、城市重点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等纳入自然资源的价格构成。
(4)通过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的策略调整增加生态效益的空间机遇。也就是对所有权限制的技术性改革,通过明确限制的目的、细化限制的目标,给生态效益的释放找到确定的生存空间。
(5)区域一体化中相关地方立法协调的模式。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如火如荼,相应地对生态效益的立法引导也应该一体化,而且基于生态环境的连锁效应和广泛影响,生态效益引导更加应该一体化。从模式上看,大致包括两种: 紧密型区域地方立法协调模式和松散型区域地方立法协调模式。具体采用哪种模式,应视自然资源的具体状况而定,也可以两者结合。近些年长三角地区开展的立法协调不局限于政府之间,还包括人大之间。一般情况下,客观地理环境决定着各相邻行政地区属于同一个生态体系,自然资源也具有明显的共享性,如河南与陕西交界的天鹅湖,天鹅与游客同时在行政边界上穿梭,各自为战的管理导致了一些矛盾冲突,对于生态效益的实现造成了阻碍。可在地区范围内建立统一立法机构,也可以采用软性的地方法制协调途径,按照统一的标准和目标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法制环境。如区域环境合作倡议书、生态效益促进合作协议等[15]。
4.3 立法引导两种效益契合的重点难点
要想同时实现两种具有较强内在张力的效益,立法引导的重点主要在三个方面:
(1)对所有权管理主体主管人员和所有权各项权能行使主体管理层生态效益意识和对两种效益关系认识的制度性塑造。因为管理人员是效益达成的最核心因素,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人与技术的互动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人创新技术,技术塑造人,人只要设立了目标,就会有无限的创造力。自然资源利用的外部性和提供产品的公共性决定了其产权制度构建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对其决策者和执行者管理的复杂性。
(2)注意立法张力与针对性相结合。立法既要确定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又要确定社会关系的法律介入程度,要在二者的结合点上寻找最佳的位置,这是对立法张力的要求。要求法具有一定的张力,既包括法必须介入和调整的结合点上的张力,即程度的界定,也包括结合点之外的张力,即不要轻易介入。另一方面,立法还要尽可能具体和明确,避免歧义和模糊,这是对立法针对性的要求。由于地方的情况较之于全国来说,具有相对简单和变化快的特点,因此地方立法的针对性要求更强[16]。这是为了给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以适度的空间,既不损及秩序,又不影响其发展。在经济和生态两种效益的追求中,立法针对性和张力的把握尤为重要。
(3)增强立法的系统性和协调性。①增强相关立法的系统性。以生态保护为单一立法目的的法规数量少,更多的立法是具有多重目的诉求,然而“立法目的偏好并不具有协调性,通常每件法律都有自身的偏好,各行其是或者相互冲突,在一件法律中最优先考虑的目的,在另一件法律中则成为次要的目的。”[17]为了避免地方立法各自为战,在多重目的的立法中出现法条的相互矛盾问题,以及立法目的的排序混乱问题,应对各项立法目的做系统的关注并作出适应现状的具体权衡,后法制定之时应当注重对前法的综合利用和衔接。必须编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用规划和计划提高立法的系统性。②增强相关立法的协调性。法制协调的原则包括:共享、民主、平等原则;互惠互利原则;利益补偿原则;多数少数相结合原则;程序规范原则等[18]。协作机构拥有各成员赋予的法定职权,但需依程序规范地行使权力。
本论题的难点之一是如何调动相关决策者和执行者重视生态效益的主观能动性,变外部的约束为内在的动力;难点之二是如何激励相关人员自觉抵御违法贿赂和抑制追求即时利润最大化的习惯性冲动,走出“公地悲剧”的困境。
5 余论
在国家层面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法律体系的统一完善与政策设置,本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但这是解决本文问题的前提性工作,所以要在这里提及。国家立法需要做的工作是,通过对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章程等各位次制度资源的经向和纬向梳理,识别出与两种效益均衡追求不一致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条款,构建出有利于两种效益协调一致的制度体系。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块:
(1)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现行制度体系的生态效益贯彻程度分析,包括基本法、单行法、行政规章、国家政策等条文中明显违背生态效益要求的规定,以及因制度设置缺陷在实施过程中很可能导致明显违背生态效益要求的行为的条款。目前我国的自然资源立法强调了自然资源监督调控方面的制度设计,而对自然资源的权属制度、流转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等规定明显不够,对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规定不足,应针对性地加强。
(2)有利于两种效益协调一致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制度体系构建。针对现行制度的缺陷,根据上述达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原则要求和制度途径,构建出理想的制度体系,涵盖对所有涉及因素的关照。建议国家构建自然资源基本法,着重生态效益的实现。
[1] 邱秋,张晓京.当代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发展的新趋势[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5):102-110.
[2]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2;
[3] 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环境立法目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40-241.
[4] 姜渊.论自然性自然资源权的成本——以自然资源税为视角[J].矿产保护与利用,2012(5):9-12.
[5] 张里安.所有权制度的功能与所有权的立法[A]//孟勤国,黄莹.中国物权法的理论探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69.
[6] 左正强.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变迁和改革绩效评价[J].生态经济,2008(11):78-82.
[7] 常修泽.广义产权论的基本要义及价值追求[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6):29-36,77.
[8] 王闰平,陈凯.资源富集地区经济贫困的成因与对策研究_以山西省为例[J].资源科学,2006(4):158-165.
[9] 李志青.生态助力于资本,还是资本让位于生态?[EB/OL] (2015-10-31)[2015-11-01].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wNTYyOA==&mid=400487505&idx=1&sn=7b0f595957f5580613b156d50c9cfca9&3rd=MzA3MDU4NTYzMw==&scene=6#wechat_redirect.
[10] 葛群.论法律体系形成后地方立法的功能——基于地方立法类型的展开[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9-91.
[11] 宦吉娥,王艺.地方立法生态化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2008-2014)[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5(3):34-38.
[12] 毕晓莉.深化环境资源法学研究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J].华夏星火,2005(Z2):71-72.
[13] 孙波.试论地方立法的“抄袭”[J].法商研究,2007(5):3-10.
[14] 张维炜.立法法修改:为法治引领改革立章法[J].中国人大,2014(19):15-17.
[15] 孟涛.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立法协调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8(4):71-74.
[16] 肖辉.论地方立法的三个关系[J].河北法学,2004(11):88-91.
[17] 宦吉娥,李晓玉.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法律供给现状研究 ——以矿产资源系统安全需求为依据[J].安全与环境工程,2010(5):96-101.
[18] 陈俊.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地方立法协调初探[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2-8,161.
[19] 徐海波.20部法规竟管不住一个湖[N].经济参考报,2012-05-09(06).
The Agreement of Ecological Benefit with Economic Benefit in Respect to Natural Resources in Accordancewith Local Legislation
QI Xuerui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450002,China)
In recent years,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prominent in the exercise of natural resources ownership. Yet, governance effect is very weak. This is because relevant system has not really aroused the internal motivations of the subject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is basis, the suggestion of the agreement of both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 i ts in accordance with legislation means a new initiative of legislative principles; it is a direction with high feasibility for relieving and preven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is regard, the legisl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is in the state of emptiness and confusion. So it is the space and time for local legislation to take the spotlight.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eneral idea with regard to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 i ts in accordance with legislation, discusses win-win principle requirements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of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 i ts, engages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mbiguous pertinence of legislation and its tension, and boosts system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legislation.
local legislation; natural resources; ecological benef i t; economic benefit; agreement
F062.1;D922.6;F062.2
A
1672-6995(2015)12-0009-06
2015-11-13;
2015-11-24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BFX009)
祁雪瑞(1963-),女,河南省滑县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硕士,主要从事宪法、行政法、环境法等方面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