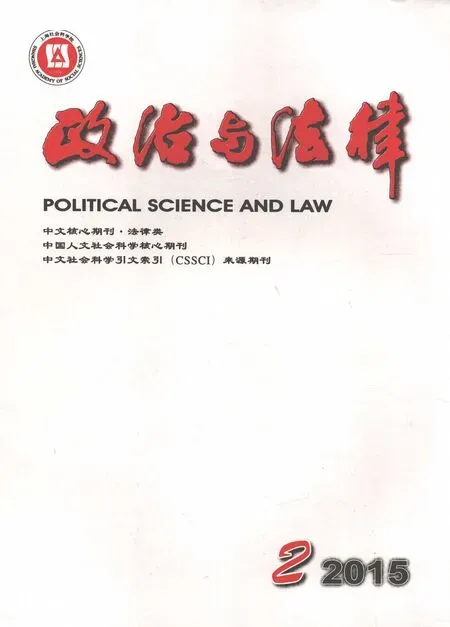美国重罪谋杀罪规则:类型归属与理论研究——与我国结果加重犯的对比及其启示
2015-01-30邓毅丞
邓毅丞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杭州311121)
在美国刑法中,重罪谋杀罪(Felony Murder)是非常重要的谋杀罪定罪规则。①根据重罪谋杀罪规则,在行为人实施特定重罪的场合,即使缺乏杀人的故意,也构成谋杀罪。我国学界对重罪谋杀罪的研究相当匮乏。②到目前为止,除了储槐植教授著述的《美国刑法》对重罪谋杀罪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专门探讨重罪谋杀罪的论文只有高长见博士的《美国刑法中的重罪谋杀罪规则评析》和郭莉博士的《结果加重犯与重罪谋杀罪原则比较研究》。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方面,通说认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重罪谋杀罪,因而没有必要对其予以过多关注;另一方面,杀人故意是故意杀人罪(谋杀罪)的构成要件,在缺乏杀人故意的场合认定故意杀人罪(谋杀罪)违背责任主义。然而,我国学界对于重罪谋杀罪的轻视与否定态度值得质疑。首先,虽然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没有重罪谋杀罪的概念,但不等于类似于重罪谋杀罪的法律现象在我国刑法中不存在。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有的犯罪在出现特定结果时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或者其他犯罪。例如,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构成故意杀人罪。如果将刑讯逼供看成是重罪,而故意杀人罪又等同于谋杀罪,那么,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规定就是典型的重罪谋杀罪。因此,关于重罪谋杀罪的研究在我国绝非没有现实意义。其次,虽然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两者在思想渊源、规范构造以及理论难题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那么,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究竟是两种平行的立法模式,还是本质相同的犯罪类型,就不无探讨的余地。再次,如果重罪谋杀罪违背责任主义,为何重罪谋杀罪能在美国刑法体系中长期存在,其法理基础是什么,有着怎样的构成要件,于此不无疑问。另外,重罪谋杀罪的相关理论能否为结果加重犯的解读提供启示,值得研究。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立足于结果加重犯和重罪谋杀罪的类型性,通过借鉴重罪谋杀罪的理论构造,反思结果加重犯的类型范围、法理基础、限制要件以及规范构造。
一、重罪谋杀罪概述
重罪谋杀罪,是指行为人在实施重罪或者企图实施重罪的过程中致使被害人死亡,因而承担谋杀罪责任的犯罪类型。③Cynthia Lee,Angela Harris,Crim inal Law:Cases and Materials,2d ed,West Press,2009:373.就此而言,重罪谋杀罪有两个基本概念:重罪和谋杀罪。
首先,美国刑法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将犯罪划分为重罪和轻罪。无论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中,这种区分都具有一定的价值。④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9页。重罪谋杀罪规则是其中一例。在实施轻罪过程中过失致人死亡的场合,不可能构成谋杀罪。关于重罪和轻罪的划分,通常以法定刑为标准。在现代的美国各州刑法典中,重罪可能被判处死刑或者监禁刑,而其他可能被判处罚金或者监禁刑的犯罪是轻罪。⑤Wayne R.LaFave,Crim inal Law,5th ed,West/Thomson Press,2010:36.美国模范刑法典将重罪和轻罪的区分予以法定化,并同时结合法定刑的轻重来进行判断。⑥See Model Penal Code§1.04.当然,并非所有重罪都可以成立重罪谋杀罪,多数州的刑法将重罪谋杀罪的重罪范围限定于特定的重罪。
其次,美国刑法根据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恶意区分谋杀罪和误杀罪。谋杀罪与故意杀人罪、误杀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不是对应概念。在英美刑法中,谋杀罪是最严重的犯罪,而恶意是谋杀罪的构成要件。预谋杀人谋杀罪被认为是具有明示的恶意;故意重伤谋杀罪和极度轻率谋杀罪被认为具有暗示的恶意。重罪谋杀罪和抗拒逮捕谋杀罪属于构建性的恶意。⑦参见前注③,Cynthia Lee,Angela Harris书,第36页。其中,预谋杀人谋杀罪和极度轻率谋杀罪均具有我国刑法意义上的杀人故意,但是,故意重伤谋杀罪、重罪谋杀罪和抗拒逮捕谋杀罪则不符合我国刑法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与之相对,误杀罪不具有恶意要件,但是,有的误杀罪则可能具有杀人故意。例如,作为自愿性误杀罪的激愤杀人罪,包括间接故意杀人的情形,⑧Joshua Dressler.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5th ed,Lexisnexis,2009:535.因而不能直接归类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在谋杀罪和误杀罪竞合的情况下,以谋杀罪处理。例如,在重罪实施过程中激情杀人,不构成误杀罪,而构成谋杀罪。
重罪谋杀罪由英国普通法所创立。通常认为,第一次明确提出重罪谋杀罪规则的判例是1535年的Lord Dacres案。⑨M ichael C.Gregerson,Case Note:Crim inal Law-Dangerous,Not Deadly:Possession of A Firearm Distinguished From Use under the Felony Murder Rule-State v.Anderson,William M itchell Law Review,2004,(31):611.在该案中,Lord Dacres和他的狩猎团队决定非法侵入一个公园进行狩猎并杀害任何抵抗他们的人。Lord团队中的一员在Lord不在场时杀害了一名看守员,Lord被认定为谋杀罪。⑩People v.Aaron,299 N.W.2d 304,307(M ich.1980).当时,Lord不是基于概括的杀人故意被认定为谋杀罪的,而是基于重罪谋杀罪规则承担刑事责任。但是,重罪谋杀罪规则没有在英国刑法中得到普遍适用。Leonard Birdsong总结道:“此规则基于法律评论家的著述而根植于英国法,而非广泛的适用于英国的刑事案件。”⑪Leonard Birdsong,Felony murder: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y which to Understand Today’s Modern Felony Murder Rule Statute,Thurgood Marshall Law Review,2006,(32):26.最终,英国《1957年杀人法》废除了这一规则。⑫See Hom icide Act,1957,5&6 Eliz.2 Ch.11& 1.
真正让重罪谋杀罪开花结果的土壤是美国各州的成文法。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许多州开始进行立法改革并修改谋杀罪规定。最早参与改革的是宾夕法尼亚州。在1794年,该州立法划分了谋杀罪的等级即一级谋杀罪和二级谋杀罪,前者只能适用于在放火、强奸、抢劫以及夜盗过程中的重罪谋杀罪。⑬参见前注⑪,Leonard Birdsong文,第17-18页。这一立法没有完全设立重罪谋杀罪规则,而只规定行为人在实施特定重罪过程中具有故意是谋杀罪的加重因素。美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规定重罪谋杀罪的立法在1827年由伊利诺斯州通过。该法规定,“非自愿杀人在实施非法行为的过程中出现,而该行为性质上倾向于剥夺他人生命,或者以重罪的故意实施,这个犯罪将被认定为谋杀罪”。⑭James W.Hilliard,Felony Murder in Illinois the“Agency Theory”vs.the“Proximate Cause Theory”:The Debate Continues,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2001,(25):355.从20世纪开始,美国大部分的州通过各种途径对重罪谋杀罪进行立法。⑮参见前注⑪,Leonard Birdsong文,第19-20页。
重罪谋杀罪在美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州直接否定了此规则的适用。例如,在1980年的People v.Aaron案中,密西根州最高法院指出,重罪谋杀罪规则在密西根州只是普通法创造的规则,而非成文法的规定,而且,“等同对待故意犯一项重罪与故意杀人、故意重伤他人、鲁莽和有意地无视行为的自然性质会引起他人死亡或者重伤的可能性”是不合理的,从而废除了此规则。⑯People v Aaron,409 M ich 672:299 N.W.2d 304(1980).另外,夏威夷州和肯塔基州则通过立法废除了重罪谋杀罪规则。⑰See Kara M.Houck,Note,People v.Dekens,The Expansion of the Felony-Murder Doctrine in Illinois,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Law Journal,1999,(30):362,n53.1962年《美国模范刑法典》,在废除和保留重罪谋杀罪的二元选择间采取了折中方案,规定只有“蓄意、明知和极端冷漠的轻率致人死亡”才能构成谋杀罪,但是,“行为人实施特定重罪可以推定其致人死亡时的轻率和冷漠态度”。⑱Model Penal Code§ 210.2.
虽然重罪谋杀罪受到不少质疑,但是,重罪谋杀罪规则仍然被美国绝大部分的司法区域(美国各州和美国联邦)所采纳。英国刑法和美国刑法对重罪谋杀罪的不同态度,大概基于以下三个现实因素。首先,重罪谋杀罪规则在美国刑法中主要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而非如英国刑法通过普通法的形式进行谋杀罪的拟制。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关于法官们通过判例法滥用重刑的疑虑。在美国目前废除重罪谋杀罪的例子来看,针对的也是普通法中的重罪谋杀罪。其次,美国刑法十分注重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重罪谋杀罪规则的立法更倾向于“社会共同体及其成员的保护,而非有利于违法者”。⑲Leslie G.Sachs,Due Process Concerns and the Requirement of a Strict Causl Relationship in Felony Murder Cases:Conner v.Director of Division of Adult Corrections,Creighton Law Review,1990(23):667.可以说,重罪谋杀罪规则是美国在人权与秩序的博弈中对后者更加偏爱的结果。最后,重罪谋杀罪规则在现实的应用中虽然存在可被诟病的地方,但总体上看,美国法院对于此规则的应用较为谨慎,没有过分地侵犯被告人的正当权利。有学者就指出,“重罪谋杀罪规则虽然没有被精确地定义,但在大部分的司法区域被公正的适用”。⑳See Guyora Binder,The Origins of American Felony Murder Rules,Stanford Law Review,2011,(97):207.可见,重罪谋杀罪的适用一方面在美国尚未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有成文法这一形式保障,因此可以维系至今。
近年来,重罪谋杀罪的发展以有限适用为主要方向。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曾反复申明重罪谋杀罪规则是一个“高度人工的概念”,“不能超出其必要的应用范围”。㉑See Andrea Rosenthal,People v.Patterson:Changing the Second Degree Felony-Murder Doctrine,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Law Review,1990,(25):126.在现实中,美国的各个司法区域为了限制重罪谋杀罪规则的适用,分别设定了不同程度的成立要件。例如,美国大部分的州都认为“独立重罪”和“平行重罪”是重罪谋杀罪的限制要件。这个要件的含义是,重罪谋杀罪只能在特定重罪独立或者平行于杀人罪(杀人结果)时成立。㉒Douglas Van Zanten,Felony Murder:The Merger Lim itation,and Legislative Intent in State v.Heemstra,Iowa Law Review,2008,(93):1571.在People v.Sm ith中,被告人在虐打孩子(重罪)的过程中致其死亡。法院认为,虐待儿童是杀人行为的组成部分,因而被告人不能构成重罪谋杀罪。㉓People v.Sm ith,35 Cal.3d 798,678 P.2d 886 Cal.Rptr.311(1984).这对限制重罪谋杀罪的适用范围有重要作用。
另外,美国法院近年来还呈现出在程序与量刑领域限制重罪谋杀罪的态势。在程序的限制方面,1989年的State v.Thomas案是典型例子。Thomas被认定指控构成重罪谋杀罪。在庭审中,检控官与Thomas分别描述了存在较大差别的案件事实并各自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如果按照Thomas的主张,其只能构成自愿性误杀罪,而不是谋杀罪。但是,审判法官只引导陪审团如何认定重罪谋杀罪,而没有提及自愿性谋杀罪的认定方法。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认为,这是一个无可否定的错误,因为审判法院达到以下两个条件时,应当引导陪审团考虑认定较轻的犯罪:第一,较轻的犯罪必须是作为法律事实被包含在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中;第二,必须存在支持以较轻犯罪定罪的证据。㉔State v.Thomas,325 N.C.at 591,386 S.E.2d at 559.有学者认为,这一判决“很可能使得较少的被告人在北卡罗来纳州被认定为重罪谋杀罪”。㉕David George Hester,A.State v.Thomas:The North Carolina Suppreme Court Determ ines that There are Lesser Included Offenses of Felony Murder,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1990,(68):1143.
在量刑限制方面,1982年的Enmund v.Florida案是典型判例。Enmund是武装抢劫杀人的被告。他作为帮助其他犯罪人逃跑的司机,被认定构成一级的重罪谋杀罪,并且被法院判处死刑。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死刑的适用,因为Enmund缺乏杀人的故意以及没有认识到在犯罪过程中其同伙会使用致命的武力,因而尚未构成以死刑来进行惩罚的必要性。㉖Enmund v.Florida,458 U.S.782,787(1982).
不过,美国法院对于重罪谋杀罪并非一味地采取限制态度。在Tison v.Arizona案中,㉗Ricky Tison和Raymond Tison两兄弟与其他亲属帮助其父亲越狱。在越狱过程中,其父亲抢劫了Lyons的林肯汽车,劫持了Lyons一家,而且,这两兄弟目睹其父亲与另一同案犯Greenawalt杀害了这些路人,但没有对杀害行为提供帮助,也没有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对此,法院判决这两兄弟在帮助作为重罪的武装抢劫、绑架等犯罪过程中致人死亡,构成重罪谋杀罪,并判处两人死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可以预见同案犯使用致命武力,而且具有“罔顾后果的轻率”以及犯行“接近主犯”,就可对其适用死刑。㉘Tison v.Arizona,481 U.S.137(1987).有学者认为Tison案与Enmund案相矛盾,并认为Tison案确立的标准没有考虑主观责任,违反了宪法第八修正案关于禁止酷刑和不正常刑罚的规定。㉙See Lily K ling,Constitutionalizing the Death Penalty for Accomplices to Felony Murder,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1988,(26):489.
美国法院的立场有所摇摆,一方面是因为重罪谋杀罪规则的适用范围蕴藏着人权保障与社会防卫之间的功能冲突,不可能表现为单向性的放宽适用或者严格限制,另一方面是基于个案具体情节的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死刑适用必要性。总的来说,美国的法院关于重罪谋杀罪的处罚总体上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可以预见,重罪谋杀罪在有限适用的范围内将长期存在。
二、重罪谋杀罪是结果加重犯的间接加重模式
结果加重犯,是指在基本行为造成法定的严重后果时,基本犯的法定刑将依法得以升格的犯罪类型。从形式上看,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之间存在诸多区别。首先,重罪谋杀罪的法律效果是按照谋杀罪来认定刑事责任,而结果加重犯的法律效果是在基本犯罪名不变的前提下,于更严厉的法定刑幅度内进行量刑。其次,重罪谋杀罪的结果要件只能是致人死亡,而结果加重犯的结果要件则可以是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法益实害结果。再次,两者的主观要件有差异。通常认为,重罪谋杀罪的主观要件不包括故意杀人(预谋杀害被害人或者极端轻率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情形,而结果加重犯的主观要件包括故意杀人。虽然有上述差别,但是,从实质的角度来考察,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应当归属于同一犯罪类型。
(一)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具有共同的思想渊源
自陷禁区原理是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共同的思想源头。自陷禁区原理是指“对于从事不正当行为的人,该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可归责于行为人”。自陷禁区原理产生于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原来是用于决定神职人员是否适合执行神职的法理。根据这一原理,神职人员必需“内心纯洁”,否则即使在发生法律上的“偶然结果”,都要对发生的结果负责。㉚[日]内田浩:《結果加重犯の構造》,信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有一著名事例:数个圣职者(助祭)和信徒在葡萄田里工作完毕后一起回家,他们因途中玩耍劳动工具而致一人受伤,这个人8天之后死亡。这一事例在当时作为自陷禁区原理的例子被列举。因为圣职者和信徒一起游玩在当时被禁止,因而他们的游玩行为被视为不正行为,并对不正行为人进行偶然杀人进行归责。
在大陆法系中,自陷禁区原理的影响十分深远。例如,在意大利刑法中,结果加重犯有三种类型:(1)作为特定犯罪目的的内容的犯罪结果(如意大利刑法典第243条);(2)在基本犯罪规范内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结果(如意大利刑法典第368条);(3)超出基本犯罪规范的犯罪结果(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72条第2款)。其中,第三种类型的结果加重犯被认为是自陷禁区原理和结果责任的体现。㉛[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31页。又如,虽然德国通说反对自陷禁区原理作为结果加重犯的正当性基础,㉜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696页。但是,不能否认德国刑法曾经继受这一原理。其中,比较明显的例证是1532年《加洛林纳刑法典》(Constitutio Crim inalis Carolina)。该法典第134条规定,理发师、射手在正当场所的理发、射箭等行为引起他人死亡的,可以免责;但是,该法典第146条规定,在不适当的场合或者人流密集的场所引起死亡结果的,可以对行为人进行归责。㉝参见前注㉚,内田浩书,第56-57页。该规定是自陷禁区原理的体现。
自陷禁区原理对于英美刑法的实践与理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㉞有学者认为重罪谋杀罪的思想来源于污点理论(Theory of“Tainting”),(See Rudolph J.Gerber,The Felony Murder Rule:Conundrum W ithout Principle,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1999, (31):765.有学者认为重罪谋杀罪的思想起源于邪恶思想理论(“Evil M ind”Theory),See Nelson E.Roth,Scott E.Sundby,The Felony-Murder Rule:A Doctrine at Constitutional Crossroads,Cornell Law Review,1985,(70):478-485.)但这些理论与自陷禁区原理本质上一致,可以说是自陷禁区原理的另一种表达。英国法官Bracton采纳自陷禁区原理,认为“行为人在非法行为过程中非故意的造成他人死亡,应承担杀人的责任,而不能被宽恕”。㉟参见前注⑳,Guyora Binder文,第75页。Coke更进一步的指出,在行为人为了盗窃而非法(用枪支)射杀公园中的一头鹿,却意外地杀害了躲在草丛中的小孩的场合,属于谋杀,因为射击行为本身违法。㊱参见前注⑨,M ichael C.Gregerson文,第611页。但是,非法行为谋杀罪规则不仅没有区分重罪和其他非法行为,也没有区分谋杀和较轻的杀人行为,还不能算是正式的重罪谋杀罪规则。非法行为谋杀罪规则的应用导致谋杀罪范围的不当扩大。直至18世纪后,为了扼制刑罚的滥用,英国的普通法确立了重罪谋杀罪规则。
从上述分析可知,结果加重犯和重罪谋杀罪的思想渊源都可以追溯到自陷禁区原理。这说明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并非两大法系的平行产物,而是在历史上具有密切的亲缘性。
(二)重罪谋杀罪与结果加重犯具有相似的规范构造
第一,两者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犯罪行为。重罪谋杀罪的前犯罪行为是特定的重罪,结果加重犯的前犯罪行为是特定的基本犯。不少犯罪既属于英美法系的重罪,也属于大陆法系的基本犯,如强奸、抢劫等。当然,重罪和基本犯的概念和范围有差异,但这不影响两者对致人死亡或者其他加重结果的意义。如日本刑法上,强制猥亵致人死伤是结果加重犯,但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没有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因此,作为加重处罚的前犯罪行为,重罪与基本犯不存在实质差异。
第二,两者都必须有一个超出前犯罪行为的加重结果。重罪谋杀罪以致人死亡为要件,结果加重犯以特定的加重结果为要件,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差异。而且,不同国家的结果加重犯有不同的结果范围。在德日刑法中,加重结果通常是致人伤害、死亡。因此,加重结果限定为致人死亡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有的结果加重犯与重罪谋杀罪一样,只能在致人死亡的场合成立。例如,绑架罪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加重结果都是致人死亡,与重罪谋杀罪的结果要件完全一样。因此,结果范围的差异与此处两者的相似性不矛盾。
第三,两者都发生加重处罚的法律效果。在重罪谋杀罪诞生之初,重罪和谋杀都被判处死刑。㊲参见前注㉞,Nelson E.Roth,Scott E.Sundby文,第765页。但是,随着英美刑法改革,刑罚得以逐步的轻缓化。在美国,通常只有谋杀罪这样的少数犯罪才会被判处死刑。㊳参见前注④,储槐植书,第385页.有学者指出,不少州设置一级谋杀罪这一犯罪类型就是为了让死刑有适用的空间。㊴George E.Dix,M.M ichael Sharlot,Crim inal Law:Cases and Materials.6th ed,West,2008:f440.在没有死刑的州,谋杀罪的法定最高刑是终身监禁。㊵戚仁广:《英美刑法的谋杀罪与我国故意杀人罪辨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其他重罪不会有如此严厉的刑罚效果。因此,从重罪转化为谋杀罪,实际上就是加重了法定刑。换言之,重罪谋杀罪的法律效果也包含了加重处罚,只不过在此以外还变更了罪名。因此,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具有相似的法律效果。
第四,两者的加重结果都以过失为归责要件。美国的主流观点认为,如果行为人对致人死亡没有预见可能性,就不能构成重罪谋杀罪。同理,大陆法系通说认为,行为人对于不可预见的加重结果不承担责任。虽然重罪谋杀罪通常不以杀人的预谋为要件,而结果加重犯可以包含故意造成加重结果的情形,但是,过失和故意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阶层关系。㊶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259页。而且,在重罪过程中谋杀他人,可以作为谋杀罪的量刑情节。例如,在1857年Robbins v.State案中,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指出,无论一级谋杀罪还是二级谋杀罪,都必须具有杀人的故意,重罪谋杀罪是一级谋杀罪的表现形式之一。㊷8 Ohio St.131(1857).再者,在绑架致人死亡等情形中,关于加重结果的主观态度亦只能是过失,因此,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的主观要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三)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面对责任主义和罪刑均衡原则的责难
部分美国学者认为,重罪谋杀罪是一项非理性的法律规则。首先,重罪谋杀罪是一种随机性的处罚,既无效益,亦不公正。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重罪谋杀罪一方面因惩罚而增大了社会成本,另一方面又没有对应的回报,因为惩罚基于故意危险行为而非故意造成的结果,就是随机的对故意行为科以惩罚。然而,应当通过提高刑罚的确定性而非刑法的严厉性来更好的预防犯罪。㊸See Guyora Binder,The Culpability of Felony Murder,Notre Dame Law Review,2008,(83):1030-1037.其次,重罪谋杀罪规则违背责任主义。有学者认为,重罪谋杀罪规则是严格责任的反映,违背责任主义。㊹See David Crump,Reconsidering the Felony Murder Rule in Light of Modern Criticism:Doesn’t the Conclusion Depend upon the Particular Rule at Issue?,Harvard Journal of Law& Public Policy,2009,(32):1160.也有学者通过重罪谋杀罪在毒品犯罪中的适用,揭示了该规则作为一种责任的推定,违反了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需由检察官举证的宪法规定。㊺See Lynne H.Rambo:An Unconsitutional Fiction:The Felony-Muredr Rule as Applied to the Supply of Drug,Georgia Law Review,1986,(20):692.再次,在罪刑均衡方面,有学者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Enmund v.Florida案中关于非实行者因重罪谋杀罪被判死刑属于违背宪法第八修正案的禁止酷刑条款的论断为例,指出重罪谋杀罪规则在罪刑极度不均衡的方面也有违宪之处。㊻参见前注㉞,Nelson E.Roth,Scott E.Sundby文,第478-485页。
部分大陆法系的学者也对结果加重犯的正当性进行了批判。首先,如果根据自陷禁区理论,结果加重犯的成立将没有任何限制,必将导致偶然责任或者结果责任。㊼:《古代刑法n re《上智法学論集》1981年第号,第256页。李斯特斥之为“古老的结果责任的残余”,“既不符合当今之法律意识,也不符合理智之刑事政策原则”。㊽[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270页。其次,即使根据责任主义要求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具有过失,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也不应如此严厉。㊾[日]丸山雅夫:《結果的加重犯の構造》,《上智法學論集》1979年第1号,第160-161页。再次,不少学者通过基本行为的危险性来肯定结果加重犯的正当性。反对意见认为,这种路径依然不能说明为什么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如此之重。以伤害致死为例,致人重伤的基本行为存在致人死亡的类型的危险,但在发生了死亡结果的情况下,法定刑却异常加重,这显然只是因为发生了加重结果而加重法定刑。㊿张明楷:《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范围与刑罚》,《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从上述种种迹象看来,重罪谋杀罪与结果加重犯同根同源,应当归属于同一犯罪类型。日本学者森井暲曾敏锐地指出:“英美法的误杀罪相当于伤害致死罪。英美法从自陷禁区原理(versari in re il lictita)出发,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结果的归责,在相当于结果加重犯的场合……1957年英国杀人罪法没有对致人死亡的情形全部规定为结果加重犯,如此等等,暗示着英美法系的进路值得重视。”[51][日]森井暲:《結果的加重犯》,《法学論叢》1961年第2卷第42号,第89页。森井教授所说的“相当于结果加重犯”的犯罪类型,包括重罪谋杀罪规则在内。其实,罪名变更与否是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最为根本的差别,但是,不能据此认为两者不属同一犯罪类型。“立法者有自由去考虑到特别的法律攻击点,来有区别地决定各种事实构成的前提。”[52][德]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结果加重犯的“法律攻击点”是基本犯以外的法定结果与基本法定刑以外的刑罚升格。而这两个特征在重罪谋杀罪中同样存在。罪名变化是重罪谋杀罪的形式特征,而刑罚加重才是其实质内容。重罪谋杀罪是在罪名变更的形式中实现法定刑的升格,相对于法定刑的直接升格,属于间接的加重刑罚。因此,重罪谋杀罪应当是结果加重犯的间接加重模式。
三、重罪谋杀罪对结果加重犯的启示
(一)类型范围的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结果加重犯不仅包括直接加重模式,还包括间接加重模式。据此,我国刑法规定的结果加重犯的范围应扩大至某些转化犯。
所谓转化犯,是指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者主客观表现的变化,而使整个行为的性质转化为犯罪或转化为更为严重的犯罪,从而应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或应按法律拟制的某一犯罪论处的犯罪形态。[53]杨旺年:《转化犯探析》,《法律科学》1992年第6期。其中,有一类转化犯以特定结果为转化要件,例如,非法拘禁又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我国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段)。我们可以称之为结果型转化犯。
通说认为,结果型转化犯是法律对特定情形的拟制性规定,因而在行为人未对特定结果持故意态度时,亦可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拟制性法条的特点在于:立法者虽然明知由法律上重要之点(构成要件上所指称的特征)论,其拟处理的案型与其所拟引用之法条本例处理的案型所涉法律事实并不相同,但仍将二者通过拟制赋予同一的法律效力。”[54]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94页。因此,如果根据法律拟制说,结果型转化犯与转化结果的故意犯的构成要件就不能相同。
然而,有的结果型转化犯不是单纯的拟制,还另有从重处罚的规定。如我国刑法第247条第2款规定,在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场合,依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根据法律拟制说,既然刑讯逼供并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形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就不适用结果型转化犯的规定,即不能按照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这便出现一个矛盾的现象:过失致人死亡比起故意杀人的刑罚还要重。这显然有失公平。
法律拟制说之所以陷入此等困境,原因在于过分关注结果型转化犯的罪名,而忽略了罪名背后所隐藏的法定刑。其实,结果型转化犯的本质在于法律对某一规定的引用来达到刑罚加重的效果。法律拟制说始终以罪名变更为中心,无法承担在结果型转化犯中贯通罪刑均衡原则的任务。
笔者认为,重罪谋杀罪和结果加重犯的类型性可以为结果型转化犯的定性提供借鉴。结果型转化犯被定性为故意伤害罪(如虐待被监管人致人伤残)或者故意杀人罪(如刑讯逼供致人死亡),实际上是为了加重法定刑。因此,结果型转化犯与重罪谋杀罪一样,都是结果加重犯的间接加重模式。
在结果加重犯的视野下,故意的结果型转化犯的罪刑均衡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结果加重犯可分为真正的结果加重犯和不真正的结果加重犯。真正的结果加重犯关于加重结果的主观态度只能是过失,而不真正的结果加重犯既可以对加重结果有过失,也可以有故意。[55][日]平野龍一:《结果的加重犯(一)》,《法学教室》1981年第10号,第58页。不真正的结果加重犯是在解释论中贯彻罪刑均衡原则的应然类型。例如,日本刑法上的强奸致伤罪的法定刑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伤害罪的法定刑只有1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50万日元的罚金或者科料。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假如本罪(强奸致伤罪,笔者注)不包含伤害故意的场合,结局是强奸罪和伤害罪想象竞合,比起较轻的强奸致伤罪的方法(强奸过失致人伤害)的处罚还要轻,是不合理的……”[56][日]西原春夫:《犯罪各论》,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76页。结果型转化犯作为结果加重犯的一种,理应适用不真正结果加重犯的理论。也就是说,结果型转化犯的行为人可以故意造成转化结果。因此,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虐待被监管人故意致人死亡的场合,亦可适用结果型转化犯的规定,对行为人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并从重处罚。
综上,以结果加重犯定性结果型转化犯是合理的,我国的结果加重犯应包括结果型转化犯。
(二)法理基础的启示
美国学者对于重罪谋杀罪的存在根据有着丰富的论述,其中,有的理论因违背刑法的基本理念而被舍弃。例如,转移故意理论认为,行为人犯重罪的故意,转移到杀人结果,因而对杀人结果便有了故意。[57]State v.O'Blasney,297 N.W.2d 797,798(S.D.1980).以转移故意理论来解读重罪谋杀罪规则,等同对待不同行为客体间的故意转移和同一客体的不同主观因素的转移,被指责为是对转移故意理论的误读。[58]参见前注⑧,Joshua Dressler书,第526页。而且,因这种观点沒有区分关于重罪的故意和关于杀人的责任,[59]参见前注㉞,Nelson E.Roth,Scott E.Sundby文,第456页。违背了责任主义,已经被抛弃。又如,减轻检控难度理论认为,重罪谋杀罪是不可推翻的推定,具有独立于一般谋杀罪的主观因素。[60]参见前注㉞,Nelson E.Roth,Scott E.Sundby文,第478-480页。根据该说,检控方不需要证明杀人的意图和对他人生命的高度危险。这显然是严格责任的体现,有违基本的程序正义原理,亦遭受否定。[61]442 U.S.510(1979).不过,不少学说对于重罪谋杀罪的解读至今具有生命力。具体而言,以下学说对于结果加重犯的加重处罚根据的理解不无裨益。
第一,关于重罪谋杀罪的存在根据,美国通说采取犯罪预防说。犯罪预防有结果预防和行为预防两个侧面。在结果预防方面,重罪谋杀罪是为了预防重罪实施过程中的杀人行为。[62]Dana K.Cole,Expanding Felony-Murder in Ohio:Felony-Murder or Murder or Murder-Felony?,Ohio State Law Journal,2009,(6)3:21.Holmes曾说:“法律不仅让重罪行为人承担其预见后果的风险,还承担一般经验不能预见而立法者认同的风险”。[63]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Common Law,Little,Brown and Company Press,1881:59.David Crump则指出,重罪罪犯与普通人一样,完全可以理解在犯罪过程中致人死亡将导致刑罚更重。[64]参见前注㊻,David Crump文,第1163页。
在行为预防方面,重罪谋杀罪的预防机能被理解为预防人们实施危险的重罪。在People v.Washington案中,法院一方面不反对通说关于重罪谋杀罪规则用于预防重罪犯过失或者意外杀人的看法,另一方面认为预防重罪犯实施含有内在危险的重罪同样是令人信服的观点。[65]People v.Washington,62 Cal.2d 777,790,402 P.2d 130,139,44 Cal.Rptr.442,451(1965).该法院指出,每个抢劫行为都具有一种被害人将会反抗以及被杀害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可以预见的。在共同持枪抢劫的案件中,如果犯罪同伙基于被害人反抗而杀害被害人,没有实施杀害行为的抢劫行为人也要构成重罪谋杀罪(一级谋杀罪)。[66]People v.Washington,62 Cal.2d 777,790,402 P.2d 130,139,44 Cal.Rptr.442,451(1965).
兼顾结果预防和行为预防的观点具有合理性。一方面,结果预防无法区分重罪谋杀罪和误杀罪,因为从结果来看,误杀罪也是为了预防杀人结果的发生。另一方面,行为预防无法解释致人死亡作为重罪谋杀罪成立要件的必要性。因此,结果预防和行为预防结合起来才算完整的犯罪预防。
犯罪预防理论对于正确理解结果加重犯的基本构造有重大意义。在大陆法系刑法中,结果和危险都是违法要素。在行为具有特殊危险且造成加重结果时,违法的程度明显增加。那么,对行为人加重处罚的范围就有可能超出故意的基本犯和加重结果的过失犯的刑罚总和。因此,以预防加重结果和基本行为的特殊危险为加重处罚根据的犯罪预防理论能避免与罪刑均衡原则相冲突。
可能有学者认为,根据大陆法系的危险性说,同样能够消解结果加重犯和罪刑均衡原则之间的冲突,没有必要引进犯罪预防理论。危险性说认为,基本行为的类型、固有危险是结果加重犯加重处罚的根据。[67][日]井田良:《結果的加重犯の理論》,《现代刑事法》2002年第4卷12号,第106页。同时,危险性说同样主张加重结果之于结果加重犯的必要性。[68][日]丸山雅夫:《结果的加重犯論》,成文堂1990年版,第218-220页。这样看来,危险性说和犯罪预防论之间似乎没有实质差别。但是,如果结果加重犯的加重处罚根据只来自于基本行为的固有危险,结果加重犯就容易被误解为以加重结果为客观处罚条件的危险犯。[69][日]山本光英:《結果的加重犯の不法内容》,《法学新报》1990年第97卷第3·4号,第261页。而危险性说将加重结果视为结果加重犯的违法要素。因此,危险性说的基本逻辑和加重结果的定位之间是有矛盾的。与之相对,犯罪预防论立足于对结果和危险的双重预防,一方面确定合理的加重处罚根据,另一方面为加重结果和特殊危险的体系定位提供理论根据,逻辑上更加完整。
第二,生命至上说认为,重罪谋杀罪规则反映了社会关于实施重罪过程中致人死亡应受更重的惩罚的判断。例如,在Commonwealth v.Almeida案中,宾西法尼亚州最高法院指出,“重罪行为人盖然的致人死亡是刑事责任,而且必须向社会回答……”[70]Douglas Van Zanten,Felony Murder:The Merger Lim itation,and Legislative Intent in State v.Heemstra,Iowa Law Review,2008,(93):1571.。也就是说,假如犯罪人被要求偿还其对于社会的债务,那么重罪谋杀罪的行为人就有偿还比没有致人死亡的重罪犯更重的债务。
这种观点倾向于等价报应的刑罚观。仅以此作为重罪谋杀罪规则的存在根据,明显是不充分的。然而,生命至上说关于为何只有在致人死亡的场合可以适用重罪谋杀罪规则的阐述,对于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完善不无借鉴可能。结果加重犯作为想象竞合犯的特殊形态,其成立范围应当受到严格限制。但是,我国的结果加重犯不仅有具体的加重结果,还有抽象的加重结果;不仅涉及人身法益,还涉及财产法益,有滥刑的嫌疑。而且,致人死亡和其他加重结果在许多场合(如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作为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加重情节,严重违背罪刑均衡原则。借鉴生命至上说,生命在法益阶梯中处于最优位阶,应属于加重结果的主要形式。重大的身体健康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因而致人重伤也可以成为加重结果的附属形式。其余后果原则上不应成为加重处罚的理由。
第三,双层归责原则理论认为,重罪谋杀罪具有两个层面的责难基础:一是心理责任,即行为人对于引起损害的期待,二是规范责任,即行为人创造风险的目的所具有的道德价值。这是美国学者Guyora Binder提出的观点。Guyora Binder认为,一方面,基于责任主义原理,在行为人对致人死亡没有认识可能性时不得成立重罪谋杀罪;另一方面,尽管刑法学者们通常只承认责任的认知层面,但在某些反映出反社会动机的情况下误杀可以升级为谋杀。重罪谋杀罪同样有这样的反社会动机,即重罪的动机。因此,重罪谋杀罪的处罚根据在于对他人生命危险的疏忽和实施重罪的动机。[71]See Guyora Binder,Making the Best of Felony Murder,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2011,(91):434.
Guyora Binder从规范责任的角度导出“重罪目的+杀人过失=杀人故意”的结论。乍看起来,此见解只注重罪过的复合性。但是,这种复合性并非对故意的拟制,而是作为规范责任的内容,不无可借鉴之处。首先,规范责任论强调责任的实质是非难可能性。[72]张小虎:《当代刑事责任的基本元素及其整合形态分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然而,大陆法系的规范责任论往往局限于关于期待可能性的讨论,[73]黎宏:《日本刑法精义(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而甚少关注责任形式本身的范围。从实质的角度来考察,等价的非难内容未必只有一种责任形式。因此,在规范责任的范围内,结果型转化犯有可能被视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以及抢劫罪的责任形式之一。其次,规范责任的理解不妨碍客观要件的必要性。Guyora Binder认为:“初审法院必需在它们(对陪审员)的指导中要求存在可预见的危险。”他同时认为:“尽管杀人罪没有要求关于有责的主观状态的独立证明,因果责任仍然要求在存在可责危险的范围内导致死亡。”[74]参见前注[71],Guyora Binder文,第435页。因此,双层归责理论并未忽略重罪对于致人死亡的客观危险。再次,双层责任理论对独立重罪的重视值得借鉴。如果结果加重犯的加重处罚根据仅在于基本行为的特殊危险,就很难理解针对结果加重犯的严厉法定刑。既遂犯的法定刑相对于未遂犯而言有从重或者加重处罚的法律效果。既遂犯和未遂犯在构造上通常以结果是否发生作为区分标准。在这一点上,既遂犯和结果加重犯有共通之处。但是,结果加重犯和基本犯的法定刑差异显然大于既遂犯和未遂犯的法定刑差异。对此种不均衡的现象,可以借鉴双层责任理论的独立重罪要件加以解决。如果将独立重罪替代为独立的基本犯,就能对结果加重犯的重刑做出解释,即以基本犯的不法作为结果加重犯的不法内容,在基本行为的危险性以外充足法定刑升格的依据。因此,故意的基本犯和加重结果的过失犯(故意犯)相结合,是结果加重犯得以加重处罚的根本原因。
(三)限制要件的启示
结果加重犯成文法中的构成要件要素非常简单,通常只有基本犯和加重结果的描述。那么,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成立结果加重犯就成为疑问。对此问题,重罪谋杀罪的限制要件不乏可供参考之处。
第一,内在危险要件对于认定基本行为和加重结果有借鉴意义。基本行为和加重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素。一方面,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未必具有造成加重结果的具体危险;另一方面,有的加重结果缺乏具体形态,如严重后果、情节严重等。那么,基本行为和加重结果的认定就会成为难题。对此,重罪谋杀罪的内在危险要件有启发意义。
通说认为,重罪应具有致人死亡的内在危险。美国许多法院都要求在行为人意图或者实施对他人生命有内在危险的重罪的情况下才能成立重罪谋杀罪。其中,包括抽象判断和具体判断两个标准。
抽象判断,是指法院忽略具体案件的事实,而通过重罪的性质来进行抽象判断。在People v.James案中,被告人Kathey Lynn James在制造甲基苯内胺(重罪)时,其中一种她使用的化学物质在制造过程中着火,她的房子被烧毁,而她三个孩子也被烧死。在法庭抗辩中,James提出的辩护理由是她在整个甲基苯内胺制造过程中严格按照制作工序,而且她也有相应安全制造的能力,因而从具体情节来看,她实施的重罪并没有致人死亡的危险。但是,法院否定了这一主张,以二级谋杀罪处罚了James。法院认为,法律中的危险判断不是数理上的概率问题,制造甲基苯内胺所需要的设备本身已经具有潜在危险。更重要的是,行为人制造甲基苯内胺不得不持有和使用一些危险物品。因此,制造行为本身就具有致人死亡的内在危险。[75]See People v.James,74 Cal.Rptr.2d 7(Ct.App.1998).
具体判断,则是指在综合考虑特定案件事实和状况的场合,作出重罪是否存在内在危险的认定。在Statev.M itchell案中,M itchell被指控因疏忽照管儿童(重罪)而致其死亡,构成重罪谋杀罪。M itchell在上诉时以疏忽照管儿童“不属于抽象的具有致人死亡的内在危险的重罪”为理由进行辩护。但是,明尼苏达州上诉法院认为,“最高法院已经反复申明诸如夜盗和盗窃等缺乏任何身体伤害(更不用说重伤害或者高度的死亡危险)的法定因素的犯罪,可以作为重罪谋杀罪的特定重罪来处理……正如最高法院所强调的那样,要求特定重罪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案件的情形中都具有危及他人生命的特殊危险,将会‘抽干特别危及他人生命标准的精华’”,从而肯定M itchell构成重罪谋杀罪。[76]State v.M itchell,693 N.W.2d 891,895(M inn.Ct.App.2005).
现在看来,片面的主张抽象标准或者具体标准,都未必妥当。美国有的法院已经尝试将两者结合。在State v.Anderson案中,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基于重罪行为必须同时符合上述标准的要求,推翻了被告人持有枪支行为作为重罪的判断,从而否定重罪谋杀罪的成立。[77]State v.Anderson,666 N.W.2d 696(M inn.2003).抽象和具体两个标准结合起来判断重罪,更具有合理性。
具体危险标准和抽象危险标准对于限定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有重要意义。首先,具体危险标准有利于限定结果加重犯的基本行为。根据具体危险标准,如果缺乏造成加重结果的具体危险,即使符合基本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不能被认定为基本行为。例如,行为人打了被害人一个耳光,被害人站不稳而摔倒在地,因大脑正好碰到地上的钉子而死亡。因为普通的打耳光行为不会有致人死亡的具体危险,所以该案行为人不构成结果加重犯。其次,抽象危险标准有利于限定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根据抽象危险标准,如果基本行为没有造成特定结果的类型危险,即使在行为时该结果的发生有具体危险,也不得被认定为加重结果。例如,司法解释将致人死亡作为诈骗罪的加重处罚情节,[78]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不妥当的。诈骗行为并没有造成致人死亡的类型危险性。基于诈骗行为直接造成的致人死亡结果,不得作为诈骗罪的加重结果。因此,诈骗致人死亡的情形原则上不属于诈骗罪升格法定刑的范围。
第二,因果关联性要件对于认定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有借鉴意义。我国司法实践认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行为和加重结果之间存在条件关系即可。[79]陈兴良:《判例刑法学(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但是,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通常较重。如果具备条件关系便认定基本行为和加重结果的因果关系的存在,无疑会过大的扩张处罚范围。对此,重罪谋杀罪的因果关系要件有启发意义。
美国通说认为,重罪与致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应具备特定的关联性。在King v.Commonwealth案中,King和Bailey用飞机非法运输毒品(重罪)。King是有驾照的飞行员,而Bailey不是。两人的飞机遇上浓雾而发生事故,致Bailey死亡。King被起诉构成二级谋杀罪。法院认为,即使King的运输毒品的行为与Bailey的死亡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但重罪谋杀罪的因果归属要求更为严格,致人死亡的行为必须用以直接促进重罪,或者为重罪所必需,才能肯定因果关系的成立。[80]King v.Commonwealth,368 S.E.2d 704,708(Va.Ct.App.1988)..学界通常将此类观点概括为近因和法律的因果关系。
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美国法院重视的往往是行为人关于致人死亡的可预见性。[81]参见前注⑤,Wayne R.LaFave书,第791页。例如,在Lew is v.State案中,亚拉巴马州的一个法院就认为,在俄罗斯轮盘中认赌服输的参与者自我枪杀,其余参与人不构成重罪谋杀罪,因为该自杀行为没有预见的可能性。[82]参见前注[71],Guyora Binder文,第489页。然而,可预见性并非因果要件的唯一基准。例如,在Phillips v.State案中,警察在与抗拒抓捕的行为人搏斗时心脏病发而死亡。阿拉斯加州的一个法院对该案拒绝使用可预见性标准,但同时认为,死亡结果必须缘于重罪犯武力的非法使用,而且,如果被害人在激烈的追赶中心脏病发而非基于暴力搏斗导致死亡,那么行为人就不用承担重罪谋杀罪的刑事责任。[83]参见前注[71],Guyora Binder文,第489页。
借鉴重罪谋杀罪的因果关联性要件,结果加重犯的基本行为和加重结果之间应当具有密切性或者直接关联性,具体而言,其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加重结果应当是直接促成基本行为的危险行为所造成的。例如,在行为人抢劫过程中不小心将地上睡觉的婴儿踩死,不应当构成抢劫致人死亡,因为踩死婴儿的行为不是抢劫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相反,假如行为人在劫取财物后,被害人紧追不舍,行为人为了抗拒被害人的抓捕行为而将被害人杀害,就应当认定为抢劫致人死亡。其次,基本行为应当高度盖然地导致加重结果的发生。例如,在被害人具有严重的心脏疾病的场合,行为人通过打击被害人的身体而导致被害人心脏病发作而死亡,应当承认因果关系的存在。但是,行为人殴打被害人,而被害人在逃跑过程中意外摔死,不应归责于袭击行为。
第三,重罪谋杀罪的主观要件对于结果加重犯的责任要件有借鉴意义。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结果加重犯所要具备的主观要素,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结果加重犯是偶然责任的表现,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无需有过失。[84]周铭川:《结果加重犯争议问题探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与之相对,美国通说认为,行为人对于致人死亡的结果应具有主观的可归责性。美国不少司法区域(包括美国联邦)都以一定的形式要求行为人对致人死亡的结果具备可责难的主观态度。例如,特拉华州要求重罪谋杀罪在轻率致人死亡时构成一级谋杀罪,在存在一般过失致人死亡时构成二级谋杀罪。[85]Del.Code Ann.tit.11,§ 636(2007).又如,亚拉巴马州限定杀人罪为至少存在过失责任的致人死亡。[86]Ala.Code§ 13A-6-2.
显然,美国通说的见解符合主观责任主义,值得我国刑法理论借鉴。首先,结果加重犯不应当是责任主义的例外。有学者认为:“责任主义原则的中国表述——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当然必须坚持,但也不能将其绝对化,尤其是不能将其解读为对每一个影响犯罪成立的条件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有故意或过失。”[87]梁根林:《责任主义原则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考察》,《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据此,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被理解为结果责任的残余。[88]许士友:《意大利刑法中的超故意》,《人民检察》2008第23期。但是,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基本人权包括行为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如果刑法在确立刑事责任的时候不顾及行为人是否对其行为产生的危害结果有否认识的可能性,就有处罚思想和禁锢行为的嫌疑,与宪法保障人权的原则格格不入。因此,行为人应当在对加重结果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其次,结果加重犯的主观责任应当是重过失责任。美国有判例要求行为人对于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重过失的责任。在Commonwealth v.Matchett案中,马赛诸州最高法院认为,陪审团在认定二级谋杀罪时必须发现“环境证据表明被告人有意识的漠视人类的生命”。[89]Commonwealth v.Matchett,436 N.E.2d 400,410(Mass.1982).以基本行为的特殊危险作为结果加重犯的特殊不法内容,应当有对应的主观要素。该判例关于行为人对特殊危险应当具有主观过错的见解是合理的。因此,行为人不仅需要对于加重结果有预见的可能性,而且应当认识到特殊危险所依赖的基础事实的存在。也就是说,结果加重犯的主观要件应当是对特殊危险事实有认识的重过失。
四、结 语
有学者认为,重罪谋杀罪在行为人没有杀人故意的情况下认定谋杀罪,而结果加重犯是规定在基本犯罪名不变的情况下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因而结果加重犯更加符合责任主义,优越于重罪谋杀罪。[90]郭莉:《结果加重犯与重罪谋杀罪原则比较研究》,《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0期。但是,罪名不变更的加重处罚未必更加正义。有的结果加重犯比起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更重。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绑架致人死亡只有死刑这一档法定刑。这比起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显然要重。因此,不能就罪名的变化确定处罚的合理与否,而必须结合具体的刑罚效果来进行判断。换言之,重罪谋杀罪的立法模式并不必然违背责任主义,相反,这种立法模式有利于反思目前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例如,如果结果加重犯像重罪谋杀罪那样以某一个故意犯罪来定性,法定刑的上限与下限就得以限定,从而缓和结果加重犯与罪刑均衡原则之间的冲突。例如,以故意杀人罪定性绑架致人死亡,可以避免绝对死刑的缺陷。而且,在结果型转化犯中,致人伤害和致人死亡的法律效果必然被区分开来,从而避免不同层次的不法结果被适用相同档次的法定刑的现实问题。当然,笔者并不认为重罪谋杀罪必然优越于结果加重犯,更不认为重罪谋杀罪本身没有缺陷。只是在我国结果加重犯大量存在的事实面前,任何有利于解释和限制这种犯罪类型的路径都不应轻易错过。美国学界和判例关于重罪谋杀罪的不少见解的确可以成为进一步深入发展结果加重犯理论的重要资源。尤其是英美刑法在处理相关问题的判例中所形成的限定规则,对于结果加重犯的理解不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