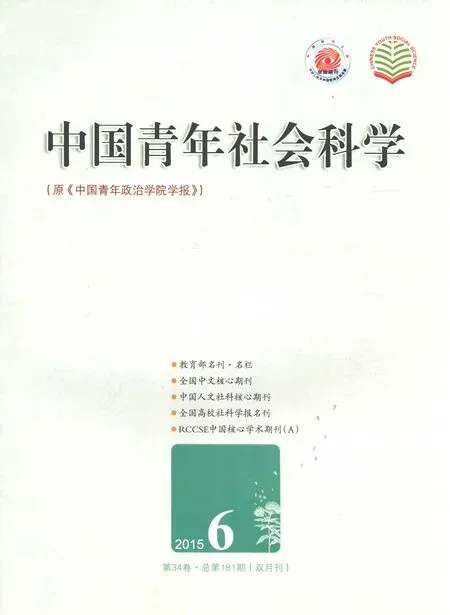美国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兴衰
2015-01-30熊贵彬
■ 熊贵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社会工作学院,北京 100089)
美国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兴衰
■ 熊贵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社会工作学院,北京 100089)
在中国社会工作学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世纪40年代早期,波士顿鞋匠(实为制鞋商)约翰·奥古斯特斯经常去法庭旁听酗酒案件的审理,后来他恳请法官对酗酒犯案人员暂缓处分,并由其保释进行感化教育。在18年中,他保释了近两千名违法犯罪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少年犯,他由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工作领域,因而被称为“缓刑之父”,也被视为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先驱。但此后,美国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并没有按部就班、顺利地进行,事实与之相反,可谓大起大落。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早期的社会工作者广泛地介入社区矫正、法院和监狱工作,为青少年犯以及受害者呼吁,使其获得至关重要的社会服务。他们关注贫困、性别、种族、残疾、家庭暴力、精神疾病、吸毒和亲子等问题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的影响。另一方面,缓刑与专业社会工作虽然具有相似的起源,但发展至今却失去了紧密的联系,当前社会工作在这个领域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监狱管理层和缓刑管理部门几乎不会优先考虑聘用社工进入一线工作,而社工教育系统很少培训学生瞄准并进入这个领域[1]。最近二三十年,该领域社工从业比例平均低于2%[2]。当前微弱的影响,与社工诞生之初及其后几十年的大发展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末以来,不断有人呼吁,社工需要重新进入缓刑管理和其他矫正领域。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必要追述和深入评析美国青少年司法社工的发展历程,吸取有益经验,避免不必要的弯路。
一、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兴起: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20年代早期
19世纪后期,很多社会改革家大量参与监狱、青少年不良行为干预和感化院工作[3]。形成青少年司法社工兴起及早期发展的大背景,除了奥古斯特推动缓刑制度的诞生,还有几个标志性事件需要提及。
第一,青少年精神病机构的成立。通过郝尔馆(美国第一个社区睦邻中心)居民Julia Lathrop的倡导,Dr. William Healy成立了青少年精神病机构,在青少年法庭审理前对涉案青少年进行诊断。一个专业团队在该机构中开展青少年不良行为研究和心理社会评估[4]。
第二,美国青少年法庭的诞生。当时,很多热心人士联合致力于把青少年法庭分离出来,1899年第一个青少年法庭诞生于伊利诺伊州。到1925年,46个州及哥伦比亚区都创设了青少年法庭,在此举行听取行为不良和受到虐待及忽视的孩子需求的听证会。在青少年法庭创设的最初几年,他们针对青少年及其家庭开展工作,处理行为不良、依赖、忽视等问题。
第三,专业化司法社会工作者的产生。最初的缓刑干警大多是自愿的,缓刑干警被分配到法庭工作的几乎所有方面,他们“会向青少年及其家庭展示友情和一些人之常情”[5],但最终让步于该领域的专业化。通过珍妮 ·亚当斯、Julia Lathrop及其他早期司法社工的不断努力,该领域实务经验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到1921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的前身)创立,个案工作成为核心方法,其中的“司法矫正治疗专家或社工”则界定为专门为违法犯罪人员提供服务的人。
早期的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凸显了明显的性别化特征。最初,男性缓刑干警在帮助行为不良青少年的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新兴的社工角色对女性具有独特的职业吸引力,因为在其他很多领域她们是被排斥的。但是,在缓刑工作中,并不是所有的岗位都向女性开放。一般情况是,“男性督导行为不良的男青年,女性督导女孩”[6]。但是,在芝加哥青少年法庭成立的前10年中 ,在14 183件青少年行为不良案件中,女孩占比不到20%[7]。于是,男性青少年缓刑工作也就成了男性工作人员的领地,女性社工开始极力争取这一领域,她们联合了一些男性呼吁立法改革。相关法案通过后,男性工作人员更多的是执行法律,而具体服务由女性提供。但是,从青少年缓刑开始之初,法律执行人员就存在于这个体系中,几乎所有人员都是男性,他们保留了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即他们向警官而不是青少年法庭法官报告[8]。因此,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带着明显的性别化特征进入接下来的几十年。
二、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20世纪20-70年代
1929年经济大萧条开始后,上述青少年司法社工岗位被砍掉。但在“新政”时期,纽约社工Harry Hopkins先后得到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任命,负责实施紧急帮助和公共岗位项目……这可以视为现代青少年行为不良预防项目的前身。而最早针对青少年犯设立的垦荒项目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由洛杉矶林业部门实施[9]。
20世纪30及40年代,大量精神干预社工被聘用,同精神病专家一起治疗有情绪困扰以及有不良行为或不良倾向的青少年。40年代年轻人帮会增长很快,于是诞生了数百个青少年成长向导机构,他们聘用社会工作者为法庭联系人。社区理事会的犯罪预防项目也纷纷设立,他们集中支持和介入一些个案,包括辍学的和被法庭标识为“问题家庭”中的青少年[10]。针对这些青少年犯罪人员开展的个案工作,使得青少年司法领域的社工逐步成为该领域的专家。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消极反应。如芝加哥青少年精神病协会把社工和缓刑干警委托给精神病专家来督导,以此来防止违法犯罪。然而,30年代,基金会发现通过精神治疗预防犯罪的实践是失败的。于是,基金会撤离了该领域,一些人开始认为在青少年法庭中不需要个案工作。尽管这个发展时期存在诸多问题,青少年矫正领域的社会工作者也有所减少,但他们在这一领域还是坚持了下来。
20世纪40-50年代,社区委员会和犯罪预防项目得到了大幅度发展。例如,波士顿Midcity项目下的社区犯罪预防和青年邻里中心、芝加哥的邻里委员会,很多其他大城市也取得了相似的成就。还有些项目聘用小组工作者(他们实际上扮演了司法社工的角色),通过外展服务接触帮派成员、辍学年轻人和一些存在“长期问题”的家庭[11]。一个成功的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项目始于50年代中期的新泽西,位于Highfields的针对青少年犯罪人员的住宿式矫正中心,该项目有效地降低了释放1年以内的犯罪人员的再犯罪率。研究发现,Highfields的假释人员当时的再犯罪率仅为18%,而控制组的再犯罪率为33%[12]。Highfields项目很快被复制到马里兰、明尼苏达、纽约、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等地。这些小型的住宿中心可以容纳15-20个青少年犯,他们接受引导性的相互作用小组工作,晚上参加由同辈领导的小组对抗活动,白天则参加社区里面安置的工作。
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任期内加强了对社工工作的联邦政策及资金支持。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一个成就是纽约市的青年动员项目,该项目由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承担的一个联邦项目而发展起来。他们奠定基础后,全国大量相似项目随之而来。这个项目中的社工主要服务于青少年帮派成员、青少年犯、吸毒人员和辍学的年轻人(很多是移民),他们大多居住在曼哈顿东边地势稍低的低收入社区。社工为这些青少年提供符合现实的工作培训和安置的机会,并教授一些适合于工作场合的交往技巧。
随后,数百万美元的联邦经费被拨付给人性化的罪犯矫正系统。州和地方机构也可以获得启动经费,开展系列项目。如警察部门的青少年社会服务、矫正服务和基于法庭的服务(包括审前转向项目、针对青少年及成年罪犯的强化式缓刑监督)。这些岗位招聘了很多司法社工,此外还招募MSW(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学生开展有偿的实习工作。这些项目还建议,需要建立专门的青年服务局,其员工主要应由社工构成,而且这些社工还需要在小组工作和社区组织中参加过培训。成立青年服务局的目的在于把青少年从司法系统转移出去,通过发展地方机构,在傍晚和周末向年轻人开放,并为他们组织娱乐活动,提供辅导、小组活动、戒毒治疗、家庭咨询和工作安置。典型的青年服务局的工作人员由五六个社工和一支经过训练的志愿者队伍构成。青年服务局的工作人员同学校、警察和缓刑部门建立了密切联系。在联邦资金的支持下,到1971年,美国成立了262个青年服务局[13]。1974年的《联邦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法案》 (P.L.93-415)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立法,伴随大量的预算拨款,产生了一个新的联邦办公室——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办公室(OJJDP)[14]。这项影响广泛的立法背后,是司法系统和社会政策方面社工的极力倡导。OJJDP的第一任主任Ira Schwartz就是社工(后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当联邦的启动经费用完后,州和地方政府就不再继续这些项目,于是青年服务局也就逐渐淡出了。到80年代早期,大部分这类项目已经停止[15]。
这一时期,司法社工加强了他们在青少年矫正领域中的地位。社工在警察部门、精神病部门、青少年司法项目中工作,并且同缓刑干警一起行动[16]。他们认为,只有经过社工专业培训的人员才最有资格成为缓刑干警[17]。美国违法犯罪委员会的执行理事长Milton Rector也是社工, 他主导了一项关于全国缓刑工作的调研,随后建议所有新的缓刑干警和督导需要具备MSW(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资格和两年的个案工作经验[18]。但是,社会工作者与青少年缓刑和矫正领域工作人员之间也显示出了一些矛盾。尽管社工在政策层面和机构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一线的青少年缓刑干警大都没有接受过社工培训。
三、社工人员大量撤离: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
1974年,Robert Martinson在评估改革项目后,发表了著名的报告《什么在起作用?(What Works?)》[19],文中指责:很少有证据显示矫正项目具有积极效果。虽然其研究面临激烈的批评,但是他的观点却导致了当时对司法社工的冷嘲热讽——在矫正项目中“什么作用也没有”(Nothing works)。这种思潮最后促使里根主政时期“对犯罪强硬”主张的产生。支持青少年转变的项目经费急剧减少,监禁的年轻人则相应地不断增加,尤其是与毒品相关的青少年。在一些州,甚至13岁的少年就可能因为某些指控而在成人法庭中被审判。大部分的青少年犯不是被送往大型的培训学校,而是被监禁。数百名青少年犯被关押在仓库,有的还因为第一次在监所打架而被单独囚禁30-90天不等。
90年代,很多青少年机构里的矫正教师和辅导员被警卫所替代。而且,在联邦和州的福利政策改革中,一些司法权力移交给了地方政府,脆弱家庭和高风险社区(由下列指标所界定:贫困、出生婴儿体重很轻、艾滋病、毒品、高失业率和高监禁率)处于崩溃和瓦解的边缘。越来越严厉的执法气候,以及随之而来的系列变革,极大地改变了青少年法庭的任务,其管辖权严重萎缩,使其工作程序更像刑事法庭。社工目标与法庭目标的冲突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比如,犯罪调查的要求同与服务对象保持信任关系的需求相冲突。同时,缓刑干警也更加关注法定程序,以确保执行法院判令,这些判令被认为更具惩罚性而不是矫正性。
当惩罚导向取代了早前对矫正恢复的强调,矫正领域中的社工和心理辅导员大幅度减少[20]。社工被八九十年代针对青少年犯罪的主导模式所震惊,其中包括强化惩罚、在大规模监所里长期监禁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00年以前,珍妮·亚当斯为青少年罪犯矫正恢复服务奔走呼吁,这一时期严厉处罚环境下似乎又再现了历史的这一幕,需要重新为青少年犯罪人员的权益呼吁。因为大部分的州已经改变了他们的青少年犯罪法律,允许青少年案件在成人法庭中审理,或者不顾青少年的隐私及犯罪记录的保护而进行审理。
除了政策强硬转向带来的外部压力,很多青少年司法社工也选择主动撤离该领域。一种较为普遍的历史解释是源于对非自愿案主开展工作的厌恶,认为该领域不可避免的强制性,玷污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21]。因为矫正系统的强制特性与社会工作强调的尊重、接纳和案主自决等原则互不相容。
但也有学者指出,社工并不是撤离了司法领域,而是转向了司法过程中的其他方面。比如,在这种强化惩罚的气候下,支持受害者权利的行动开始迅速发展。许多司法社工从监狱恢复服务转向了以社区为本的对受害者、证人的帮助,其中的工作人员约有1/3是社工[22]。而且社工也并没有完全缺席法院工作,尤其是社区法庭还纷纷求助于社工的专业力量。法庭或缓刑干警被赋予刑罚执行的任务,社工则被赋予在矫正机构之外开展预防和服务的职责,辅助法庭,提供法律援助、为家庭犯罪法庭调节、赔偿及为受害者和侵犯者调停、为青少年罪犯治疗、为虐待和青少年行为不良的家庭保全等。例如,一些司法社工主导了法庭判罚的辅导项目,主要针对青少年及成人的暴力罪犯,在小组工作中开展动手和愤怒控制、攻击行为的换位思考等训练。
四、呼吁社工重返青少年矫正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强硬措施真的有助于提升矫正效果吗?换句话说,监狱成功“修理”了犯罪人员吗?或者真正震慑了那些可能实施暴力犯罪的人员吗?没过多少年,很多学者就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转向后最初的几年,法庭并没有成功地降低青少年侵犯率,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犯率高达40%[23]。监狱建设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产业,如新的青少年拘留中心、州监狱也在增加[24]。针对青少年犯罪的“训练营”或“严厉的爱”等项目,通过对高风险青少年强制性的早期介入,以期增强其个人责任感。但是一些明显的失败会影响到对这些项目的支持。一个有名的例子是2006年14岁的案主Martin Anderson死于佛罗里达州的训练营机构[25]。可以说,依靠更长时期、更严厉条件监禁的犯罪控制措施归于失败了。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应让社工重新在矫正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一,缓刑干警没有经过专门的认知和行为矫正培训,他们不太可能判断出什么时候需要提供这些服务,或运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和技巧。一个缓刑警官谈到,他仅仅作为警察和法院之间的联系人而已,他不会对督导下的青少年开展矫正性的个案工作[26]。相反,社工则经过系统培训,能够熟练运用认知行为理论和方法、家庭干预方法等,处理卷入法庭和处于不利境况下青少年的需求。社工介入的典型特征——生态系统视角,也特别适合为面临一系列困境的青少年违法人员提供服务。
第二,很多人也认识到,司法社工并不是唯一面临强制性境遇的服务领域,其他领域的一些有益应对经验值得借鉴。其他一些社会工作分支领域也长期面临强制性带来的挑战,如儿童福利、家庭暴力、精神健康、药物滥用和一些老年照顾机构。但这些服务领域可以通过调整实务模式,或在机构中接受一个更狭窄的角色等方法进行调整,而不是抛弃这个领域[27]。因此,强制性环境也不一定排斥社工介入,需要明确的是,究竟是什么使青少年矫正社工有别于其他强制性分支领域。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政策和实务的新动向为司法社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90年代伊始,佛罗里达、明尼苏达、俄勒冈、宾夕法尼亚和德克萨斯等州的司法社工,通过挖掘基层社区和青少年司法机构的优势,扩大了恢复性司法项目。同时,出于财政的考虑以及认识到青少年犯罪中的种族比例失调,监禁替代措施得以增加,更多的青年罪犯被置于社区矫正,但这就需要更多监管和支持性服务[28]。这使很多青少年罪犯从监所矫正中脱离出来,让他们能在矫正治疗期间不与家人分离。此外,年轻的女性违法人员也引起了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采取确保妇女不离开孩子、远离殴打情景等措施,甚至在她们已经用完一生援助期限(5年)的情况下,也让她们能继续领取临时家庭援助金。
第四,社会工作教育界传来一些利好消息。十多个社工学院已经同法学院一起发起了交叉学科培养计划,包括双学位项目。此外,社工教育协会认证的120个MSW(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项目中的很多社工学院开设了青少年司法或家庭暴力等课程。大约一半的社会工作研究生院给他们的学生提供了司法社会工作领域的实习机会,如青少年司法项目、受殴打妇女避难所和成人矫正机构等。
但是即便在如此形势下,美国社工界的态度仍然是比较审慎的。如一些人呼吁进一步明确社工在司法系统中的辅助角色,担心他们在矫正工作的日常工作中被边缘化[29]。美国社工协会2003年声称社工需要重新进入矫正工作,但矫正工作已经越来越多被临床社工所主导,作为私人精神治疗师,协会成员可能很少有动机去为违法犯罪人员提供服务[30]。可见,离开司法系统之后,社工界同当前需求不断增长的矫正领域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五、美国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对中国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借鉴意义
美国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经过一百多年的坎坷发展,时至今日,毋庸置疑,社工可以在青少年矫正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这还需要不同实务领域的联合努力:包括儿童福利、青少年法庭、精神健康、教育培训和其他社会服务。重新进入司法矫正领域,社工可以利用其经验的积淀及不断更新的专业知识,更好地服务于一个被忽视的群体——青少年矫正对象。回顾美国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历史,我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到一些的有益的启示。
第一,青年司法社工并不是万能的,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避免在起步阶段过度宣传。尤其是那些案情严重、重犯、缺乏悔意和转变动机的惯犯,他们已经形成了畸形的价值观和顽固的犯罪心理结构,难以在短时间内被感化。美国司法社工在百年发展史中,历经曲折、备受争议,至今尚未完全走出低谷。但当前我国一些学者倾向于将司法社工描绘为灵丹妙药,一试就灵,这在短时间内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反而可能损害该事业的发展。
第二,过度强调专业化将损害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长远发展,可以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进行理性设计。美国青少年司法社工的高开低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多是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当前的踯躅不前则明显是专业标榜在作祟。美国司法社工的历史发展和国际经验(加拿大、澳大利亚、苏格兰等的青少年司法社工都在成功开展,立陶宛等国还在跟进)都已经证明,社工是青少年司法领域不可或缺的力量,社工界应主动适应强制性的工作背景,在这个尤其需要社工的领域,最大化的发挥“社会工程师”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威权国家的优势,避免民主国家的内耗,主动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在司法矫正领域中创立社工的岗位,如此青少年司法社工将在中国有所发展。
第三,要为中国整个社工界呼吁,使各领域的社工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渠道,这样才能引导社工事业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是影响决策。如前所述,罗斯福时期和肯尼迪、约翰逊时期,都有社工能够进入决策层,引导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带动整个服务领域的发展。尤其是,目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一份职业也是社工。另一方面是激发社工的积极性。合理的阶层流动渠道也将大大激发社工的专业服务积极性,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事业无疑也将从中受益匪浅。
[1][2][5][7][23][26][27][30]Clark M. Peters ,Social Work and Juvenile Probation: Historical Tensions and Contemporary Convergences. Social Work,2011(4),pp.355-365.
[3][10][12][13][15][16][22][24]Roberts, A. R.& Brownell, P., A Century of Forensic Social Work: Bridg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Social Work, 1999(44).
[4][25]T. Maschi and M. L. Killian, The Evolution of Forensic Soci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lications for 21st Century Practice. Journal of Forensic Social Work, 2011(1).
[6]Knupfer, A. M., Professionalizing Probation Work in Chicago, 1900-1935.,Social Service Review, 1999,pp.479-495.
[8]Weiss, H. ,The Social Worker's Technique and Probation. In S. Glueck (Ed.), Proba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 NewYork: MacMillan,1933.
[9][11][18]Roberts, A.R. , Juvenile Justice: Policies, Programs, and Services ,Belmont, CA: Wadsworth,1998,pp.110-121,122-137.
[14]McNeece, C.A., Juvenile Justice Policy. In A. R. Roberts (Ed.), Juvenile Justice: Policies, Programs, and Services,Chicago: Nelson-Hall,1998.
[17][21]Piven, H., & Alcabes, A. , A Study of Practice Theory in Probation/Parole.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1971.
[19]Martinson, R. ,What Work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Prison Reform. Public Interest, 1974.
[20]Gumz, E., American Social Work, Corrections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An Apprais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2004(48).
[28]Annie E.,Casey Foundation.,Reform the Nation's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ssue Brief]. Baltimore: Author,2009.
[29]Dane, B. O., & Simon, B. L., Resident Guests: Social Workers in Host Wettings. Social Work,1991(3).
(责任编辑:张宇慧)
2015-09-01
熊贵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教制度废止后社会工作融入社区矫正‘北京模式’研究”(课题编号:14SHB017)、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项目“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内容与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编号:1820504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