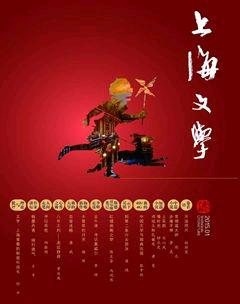中国文学与瑞典出版
2015-01-28张辛欣
到斯德哥尔摩旅游,诺贝尔颁奖地是中国文化人一大景点,而少数资深文化客知道,当地有一位“景人”值得接触。此人中文写作,翻译瑞典诺贝尔得主小说、戏剧和诗;认识诺奖秘书长并译前诺奖主席的小说;莫言获奖跟他妻子(陈安娜)瑞典文翻译有关;多年给香港《明报》写新得主快评。他叫陈迈平。经历过1978年文化解冻的文学老友更知道他另一个名字:万之。
我第一次见到万之是在墙上。我读他的短篇小说,跟北岛等人的诗在一起,都是《今天》的作品,笔名“万之”的陈迈平是《今天》的小说编辑。那些创作是手刻油印的,印在薄纸上,用浆糊刷在西单砖墙上,没有被浆糊刷到的一片小角在寒风中微微抖动。我把双手放在嘴前,哈着热气读着早春的意思,心有疑惑,小说也能这样写?我在偷偷写小说,模仿苏俄现实抒情体,我的请教留到1980年代初跟他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念本科,迈平在戏文系念硕士,攻读欧美当代戏剧。那时我用各种方式写小说,琢磨法国新小说体、侦探体、新新闻体,有点资格讨论了,而真尊现身了。墙上的小说家万之超前卫,眼前的师兄迈平很低调,说话温和,于是我得放低声音还得放慢说话节奏,假装跟他同步着斯文。学院小,学生少,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我俩什么都没有讨论,怎么写小说的问题更没有问。
不过迈平看我演戏。毕业演出我们班演易卜生《培尔金特》,我演山妖公主。万之,我发现,一直自比天涯流浪汉培尔金特。他去奥斯陆念戏剧,专攻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然后在那里教书,在北欧游荡,英文之外,挪威文和瑞典文加入他的新乡音。而我到了美国,在英语世界生活。天涯三十年,偶然地,我们写信;更偶然地,我们见面。就见过一次。那是本世纪第一年初我到瑞典去开中国女性文学讨论会。那一次见面,我们谈文学,谈戏剧,谈小说创作(我大谈他一篇小说如何修改!)。迈平听着叹气说,在学院的时候我以为你特孤傲。我回答,我以为迈平你太深沉!我们在刺骨海风中一块儿喷笑。文化天涯各自流浪,学院训练的他和我不大能遇到谈话对手,更少孤独闯荡的创作知音。那一次唯一见面,我俩的话题加入了中国当代文学与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露天集市走着,他遥测高行健会获奖,告诉我他观察的翻译与评论对西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诺奖的影响。再后来,培尔万之有一点怕妖怪师妹我了,因为我妖言预言莫言,我说了,他不答,怕我走风?
呵呵,笑在风中逝散,各自依旧独行。
几年前,他翻译《航空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与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的通信集,他译一段点我读读,他写到,没有读者能理解。我写回,不是啊,我读出诗人写散文的精彩,读出诗人的大天真,读出我走过但是被我遗漏的被我视而不见的好多感悟,好多画面。我想,孤独工作的迈平把我当作回音壁的独白?
几年前,我邮递长篇自传《我》给他,他一口气读完写来说,这是迄今他读到的中文世界第一部双语感长篇。他看封面有英文Me,似是美术设计,在他看来,那不是中文封面的时尚点缀,这部自传标题应该读为《我ME》,象征精神流浪长旅的复试音调,给了犹如内容里的我观察“我”的美学距离——我何尝不孤独,我失去任何讨论者,却有一个万之—迈平提领我再看穿自己的标题——你遥遥回了我对那堵墙的请教。
去年六月,万之告诉我,他在瑞典办了家出版社,他坚持出阳春白雪,委婉批评我不在意传统出版。是的,我做流行读物,自己做数码版小人书,在iBook网店自做商业发布。听了他说的,我人在美国拜访他的瑞典“万之”出版社——在网上拜访的。素雅的页面,看到他出版贾平凹的《高兴》(他告诉我想出版马悦然译《城南旧事》),要出版余华等人作品瑞典文版。
我们继续在电话中聊文学,聊着,我想,这是问他的新时刻?
中国作家对作品的世界出版状态很关心,诺贝尔也是作家关心的,而万之以及他的出版社在最前沿!
喝一杯红酒,我在邮件一气写了一串问题。从他为什么做出版社,从瑞典出版状态问起,包括他与诺贝尔委员会的关系,我俩说过高行健和莫言,他为什么猜对……不问则已,开问,他会用个人经验构画文化大图景?
迈平在北欧—中国文化路途中,在大学教书来去火车上,包括在生病的时候,一段段答。一改电话上我俩说话一向是我滔滔不绝,这一回,我一个个短砖头招回玉(一堆一堆)。我与读者陆续分享。
——张辛欣
(时间:2014年7月8日)
辛 欣:你怎么想起做出版社?
万 之:说来话长,我尽量长话短说。我很早就有自己做文学出版的兴趣,这个时间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978年年底。那时北岛、芒克、黄锐等人创办文学杂志《今天》,自己油印出版,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他们也邀请我参加,我就欣然加入了。北岛曾告诉过我,那时你也帮助过《今天》的出版,提供过纸张和油印机等。诗人和作家大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创作和发表自己的作品,不仅有思考和写作的自由,也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表达和出版的自由。在出版不自主的环境下,作家自己搞出版,这是比较自然的事情。所以,当时的《今天》其实不仅出期刊,也出版了几本小说和诗歌的单行本(比如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和诗集《陌生的海滩》)。我们本来是打算继续出版下去的,希望(或者梦想着)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第一家可以合法出版的民营出版社,我们到新闻出版署申请过出版登记证,但这个梦没有做成。
后来北岛和我都流落海外,又有了自己做出版的愿望,所以我们在奥斯陆恢复了《今天》,至今还在出版,而且也出版了几本书,还出版过英文版的双年选本。北岛一直是主编,主要负责编稿方面的事情,而我既当过这个杂志的小说编辑,也当过几年社长,主要负责印刷、出版和发行方面的事情,所以已经积累了一些出版经验,不过我后来辞职退出了《今天》。
《今天》主要还是针对中文的读者,希望赢得的是在中文世界里发表和出版的一定空间。而我现在的出版,则是针对瑞典文的读者,是要赢得在瑞典文世界里发表和出版的一定空间,一定的自主和自由。至今为止,在瑞典文的文学出版中,从中文文学翻译过来的书,占的比例一直很小,差不多是千分之一。就是说,比例非常低,占的空间非常小。瑞典每年出版文学类的书(包括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译作)约三千种,其中中文文学翻译过来的最多只占三本,有的年度三本都不到。瑞典人开的出版社,对出版中文文学,一直兴趣不很高,也不很了解。他们的编辑没有懂中文的,不能直接读中文原作。所以,在选择中文文学的书做出版的时候,瑞典出版商一般都是跟欧美大陆的风,是把欧美看作标杆的。那里翻译出版的中文文学译本,他们就会跟着买,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文学品味来挑选,所以他们也会出卫慧《上海宝贝》、姜戎《狼图腾》等很商业化的书。当然,欧美那边现在也会出版一些比较好的中文作家的作品,那么瑞典出版商也会跟着买,比如莫言、余华或者阎连科的作品。但总的来说,瑞典出版社对出中文文学的书非常谨慎,也不会根据我的意见来出版,我在这方面没有话语权,更没有自主权和出版方面的自由。我认为好的中文文学著作,推荐给瑞典出版社出,他们一般都未必肯。在瑞典大概只有一家出版社是个例外,这就是出版莫言著作的“鹤”出版社,因为它是由一个汉学家创办的,这个汉学家可以直接读中文,自己选择他喜欢的中文著作来翻译出版,他不跟欧美的风,不看欧美的标杆,他也会尊重我的意见。其实是我最早推荐给他苏童、余华、莫言、格非等人的作品,他当时就答应出版我搞的一个这些作家的选集,这对我教中文文学也有好处,给学生提供阅读材料。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教授是支持这个项目的,是他把我选的作品分给十来个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去翻译。但译文都交上来之后,“鹤”的老板只看中了安娜翻译的苏童中篇《舒农》,认为安娜的译文很好,而其他人的翻译他都认为太差,不接受。安娜只翻译一个中篇当然是不够出一本书的,所以他让安娜加一篇,安娜就翻译了另一个中篇《妻妾成群》,这样合起来才够一本书了。这就是安娜作为中文文学翻译家出版的第一部译作《大红灯笼》(当时张艺谋根据《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就是这个名字)。而且因为这其实是我请求这家出版社出版的,知道在瑞典做书很不容易,根本就不提要什么翻译费或稿费,人家能给你出,已经是帮大忙了,所以这本书出版后,安娜都没有拿一分钱翻译费。这个老板后来还出版了安娜翻译的莫言《红高粱》,译本也是安娜从中文直接翻译成瑞典文的,出版得甚至比其他欧洲语言的版本都早。所以这家出版社不是因为欧美先有莫言译本才翻译出版莫言的,他能听我们的判断。不过,这个汉学家后来还是因为赔本,不得不把出版社一分不收地转让给了另一个出版商。
后来的这个出版商在我看来非常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非常吝啬,比如安娜翻译完莫言的《生死疲劳》,他一直不肯出版,一直到安娜答应一分钱翻译费都不要,他才印了一千本。所以,这个吝啬的老板还能把这家出版社维持下来。他自己七十多岁,靠一个人维持这家出版社,身体还不好,确实也不容易,曾有出售的意思。其实我早就想自己收购“鹤”出版社,就是因为没有资本而只能作罢。后来我还怂恿一个移民瑞典的中国商人把“鹤”买下来,我答应买下的话,我可以帮着做编辑。我们跟这个老板面谈过三个下午,但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个老板一直不肯吐口开价,而只想要我们先开价,又不肯给我们看出版社的年度财务报告(就凭这点你也可以判断他多贪,就如你卖房子,哪有不让买主看房子又让买主先开价的道理)。他也没想到莫言很快得了奖,他靠卖安娜翻译的莫言的三本书,一下子成了百万富翁,所以现在也不肯卖了。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刺激比较大,也是促成我想自己做中文文学的瑞典文译本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数年前,我在瑞典最老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做过一个有关当代中文文学的演讲,介绍了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出现的很多作家和作品。到了听众提问的时候,有一个听众很严肃地站起来说,他认为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最好的文学著作是张戎的作品《鸿》(又名《三代女人的故事》),还有哈金和他的作品《等待》,这些作品在欧美已经非常有名,因此他还质疑我,为什么我的演讲一字都没有提到他们。相反,我提到的那些作家作品,瑞典文倒不见翻译出版。我真的哭笑不得,只能告诉他,张戎和哈金的作品,都是直接用英文写作的,原文不是中文。他们的书其实只是写了有关中国的故事,就和赛珍珠也写过有关中国的故事一样,但他们的书不属于中文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只有用中文创作的文学才是中文文学,这样的中文文学,确实只有通过翻译出版去了解,而不是直接用英文或瑞典文能写出来的。我当时就希望,会有更多的中文文学的瑞典文译本出版,让读者了解真正的中文文学。这件事情让我感到,什么是中文文学,或者什么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中文文学,好像是欧美的出版家们掌握着话语权,是他们来决定什么是中文文学,然后卖给欧美读者。也可以说,我自己办出版,是对他们的一种挑战。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告诉他们,告诉瑞典读者,告诉欧美读者,什么是真正优秀的中文文学。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个我认为比较正面的效应,就是更多人认识到了中文文学翻译成瑞典文的重要性。所以,在翻译出版方面,有了资源可以争取。毋庸讳言,这也是我现在敢自己做出版的一个原因。
我想你对西方的中文文学出版,或者说对西方的所有文学的出版也都比较熟悉。在“自由”的市场里,“市场”就要说了算,有钱的出版商,也就有权出他们认为好卖的书,也可以告诉读者,什么是中文文学,或者什么是他们认为值得读的中文文学。这跟市场决定你吃什么、穿什么差不多。按理说,我们写中文的,根本不care那些出版商。但我和你活在这么一个《我ME》的双语环境里,自然又care起来。我们得自己做东西。我觉得你自己其实就在做出版,只不过还没注册一个“辛欣书屋”而已。
(时间:2014年7月16日)
辛 欣:瑞典个人出版社有多少?
万 之:这是个看似简单其实比较复杂的问题。说简单,也许就是回答一个数字,是可以查到的统计数字。根据瑞典税务部门和瑞典出版家协会的年度报告,瑞典现有出版社大约一千家左右,股份制的大的出版社(年营业额一亿瑞典克朗以上的)只有十一家,绝大部分是我这样个人经营的小出版社。现在瑞典人口将近一千万,就是说每一万人中就有一个出版社。我听说中国现在有五百家出版社,也就是说从数字上看,这个人口不到中国百分之一的国家,出版社倒比中国还多一倍。说明在瑞典做出版,相对来说容易得多,自由得多。
说复杂,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说明,你是问职业性的个人出版社,还是业余的。上面这个数字基本上是指职业性的出版社,不包括业余性质的出版社。也就是说,那一千家里,不论出版社是大公司运作还是个人经营,都是以出版为职业,靠卖书为赢利谋生手段的。不少出版社老板还能雇佣几个人,有编辑校对等职业人员,都要为他们交个人所得税,所以税务部门可以根据交税情况来统计出哪些人属于职业出版商。而我这样的个人出版社,可以说是业余的,所以还不在上面这个数字之内。如果把我这样的业余的个人出版社也包括进去,那么瑞典出版社的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因为在瑞典,有出版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像我这样,在税务部门注册一个出版社,都可以从国家图书馆免费获得国际书号,正式出版自己想出的书。你可能一年只出一两本书,也可能十年只出一两本书,甚至注册完就出版一本书,然后就停办了。因为你不靠出版为生,出版就是一种业余活动。你可以有空的时候出书,没空的时候就不出。你也可以有钱的时候出书,没钱的时候就停下来,甚至停好几年,像北极熊一样冬眠着,等着什么时候醒过来再出版。这样你就不会出现在本年度的税务部统计数字内了。我认为,尽管我是想往职业性出版方向努力的,但我的出版社现在还不能算是职业性的,因为刚出版一本书,还没有任何赢利,我基本上不能靠搞出版谋生,还是业余做的。我估计我的出版社一两年还不能成为职业性的个人出版社,以后也不大会以出版为职业,不以此为生。而且一年也就出一两本书,即使发行销售走上正轨,基本上也不赢利。我可以靠大学教书或者做自己的翻译工作谋生,我也很快要退休了,可以拿退休金过日子了。我完全可以一直业余做书,和出版《今天》差不多。
就我所知,像我这样的业余的个人出版社在瑞典还有不少,占据图书市场相当的空间,是文化文学领域有影响的势力。所以,我倒愿意多介绍一点瑞典的业余的个人出版社的情况。比如出版安娜翻译的余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废墟”出版社,本来是几个搞现代文学的年轻人办的,没有人在出版社有全职全薪的工作,只有一两个编辑拿一点小时工资。他们出版过很多德国“废墟”文学的作品,还出版过卡夫卡,是现代派文学的出版社。他们本来还约安娜翻译余华第三部作品《中国的十个词》,安娜都已经翻译好了,可他们没钱出版,就毁约了。你也没法去找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就没钱。这部书后来就给另一家出版社出了,是家本来专做教育类书和学校课本的大出版社,叫“文化与自然”出版社,出版社自己就拥有一座楼。他们钱很多,预付给作家的版税比一般出版社都高。你可以说“废墟”现在就处在了冬眠的状态。
安娜自己也业余创办过一个儿童书出版社,所以我也可以用她办的出版社来说明情况。安娜曾在斯德哥尔摩市立的国际图书馆工作,这个图书馆主要为移民服务,出借各种语言的图书,特别是儿童书,能让移民的孩子读到母语的儿童书。比如安娜就负责中文部分,也购买中文的儿童书。在国际图书馆,安娜看到有些非欧美语言的儿童书做得非常漂亮,而翻译成瑞典文的很少,瑞典人自己的孩子反而很少能读到。安娜她们从小读的大部分是欧美的儿童书,比如安徒生童话或者唐老鸭米老鼠之类的。欧美儿童书主宰她们的儿童世界。安娜希望能改变这种状态,所以约同事玛蒂尔达一起创办了一家做这类儿童书的出版社,宗旨就是翻译出版非欧美主流的儿童书。她们自己没有什么本钱,用于购买版权和翻译、设计、印刷等等的起始资金是让“鹤”出版社先垫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出版安娜翻译的莫言小说的出版社,报税等事务也都归“鹤”来处理。所以她们的儿童书出版社也就挂在“鹤”下面,安娜也用了一个小鸟的名字做出版社的名字,叫做“鸫”(国外有些出版社喜欢用一个动物作为出版社名称,如“企鹅”)。“鹤”出版社后来的那个老板虽然小气,但非常精明,很会做生意,了解图书市场,是标准的“威尼斯商人”,所以前面那个汉学家经营亏本,而他接过来之后从来不亏反而总有盈余。他愿意为安娜她们垫出本钱,是知道这个儿童书市场里面有利可图,而且安娜她们完全是义务工作的,是业余时间做,不从出版社拿任何工作报酬,等于为他白干,卖书赚来的钱也都是归他的。
“鸫”出版社后来果然搞得比较成功,先后出版过二十多种非欧美语言翻译过来的儿童书,有非洲塞内加尔的,有亚洲菲律宾、越南、韩国、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全都是过去在瑞典儿童书市场上少见的书,对扩大瑞典儿童的视野很有帮助。瑞典报纸上的书评总是很好,有好几本还得过瑞典文化部的儿童图书奖励。所谓文化部的奖励不是把钱奖给个人或者把钱直接给出版社,而是文化部出钱,购买几百本评上奖的儿童书,分送给全国各地的托儿所和中小学。瑞典的儿童图书本来就很贵,因为关注儿童的安全,还要防止孩子撕书咬书,所以纸张一般都很讲究,封面都很硬,一本儿童书上百块是常事,所以文化部发奖,买几百本,就等于给出版社几万块奖励了。“鹤”的老板当然非常高兴,因为卖儿童书的收入不仅可以收回他垫的成本,还有赢利,所以他很愿意继续垫钱给安娜的出版社,用于后来的出版,这样她们就可以周转起来,维持这个出版社。但是这两年安娜觉得比较累,因为其他事情比较多,而这个“鸫”出版社其实是她一个人做事,另一个人只是挂了名而已,没有能力,所以这两年“鸫”就进入了“冬眠”状态。你可以说它消失了,但只要安娜愿意,又有了时间和兴趣,那么她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这就是这类出版社的好处,因为你不靠它过日子。
这类业余出版社当然也有它的弊病,往往既不职业化又不专业化,出版的书质量会很差,因为没有专业设计和专业编辑,错字和排版问题很多,纸张和装订也很糟糕。我是尽量在书的质量上往职业化靠拢的,所以马悦然也认为书做得还算漂亮。但他还是发现了错别字,是因为我请的校对不够认真。还有些这样的出版社,是自以为是的写作者搞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伟大的作家,但作品又没有正规出版社接受,于是就自己出版。这样的书,也就没有什么报纸会发表评论,也没有什么人会买。
辛 欣:我注意到你说“在税务部门注册一个出版社,都可以从国家图书馆免费获得国际书号,正式出版自己想出的书”——从国家图书馆免费得到国际书号,你们瑞典可真是福利国家啊,我们“个人主义”打拚的美国,就得自己买书号。买一个国际书号一百五十块美金,买十个二百五十块美金,我就一把买了十个。看到中国那边有出版社犯愁的,个人犯愁的,我就说:送你一个书号吧。
另外,你们收入税收是多少来着?百分之四十?你说书价上百“块”是什么货币?相当于美元多少?你再提到钱的时候请想到我,用美元“比”一下,我就明白了。你用“冬眠”和动物形容出版,形象并好玩!你家安娜用小鸟儿当社名,可爱啊。我家斯蒂夫说到北欧大怪物用trolls,这是当时我演培尔金特时候的“山妖”吗?一直想问来着。
万 之:Troll就是我们说的山妖,大怪物,但现在作为旅游商品卖。
克朗基本和人民币等值。一百克朗现在大约十五美元,是一本硬面儿童书的出版社书价。书店再往上加,那是书店赚的。瑞典的(皇家)国家图书馆给书号,不要钱,但出版社出版后必须给两本样书。他们的楼不大,但地下如一个深深的矿井,层层坑道,全都是藏书。
(2014年10月14日,继续问继续答)
辛 欣:瑞典关心中文文学的有多少人?(什么样的人?学中文的?汉学圈子?)
万 之:首先我在想,大概先要考虑回答,一般而言瑞典关心文学的有多少人?而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心?还有关心的程度如何?关心的文学是什么文学?
我知道有部分人一生从事文学,那文学就跟银行家关心股票市场一样,那是性命攸关了。这些人把文学当作自己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关心程度是像对自己女儿一般的关心,是关心她的健康成长,她的贞洁和未来。还有,我以为我们之间自然有默契,我们说的“文学”,是高品位的文学,不是一般畅销小说之类的文学。
具体说什么人关心的话,首先瑞典学院评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们,他们当然关心,而且是全世界范围的关心。瑞典作家协会和瑞典笔会的作家,他们当然也关心,因为他们要为作家服务,每年都有很多具体的事务要做,不关心也不行。比如作家协会自己也有名目繁多的大小奖项,要审批作家可以申请的资助(比如我多次申请去中国的旅费资助),这都要看作家或者翻译家拿出的作品,看这个申请人拿钱会出什么文学成果。这些都是作协或者笔会的理事会开会讨论决定的(我和安娜都曾经当过瑞典笔会的理事好多年,因为当理事,自己反而不能申请,反而拿不到资助)。还有在各家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主持文学节目的人,那些靠写书评为生的评论家,文学也涉及他们的饭碗,他们也会关心。如果有一本新书出版,尤其是一个名作家的好书出版,他们要是不知道,那就会被人当作傻子看待,可能很快就要丢饭碗了。瑞典的各地区公立图书馆的馆员自然也比较关心文学,因为他们要买好书才有读者来借阅,出借率高低也涉及他们的“政绩”。再有书商(书店老板)和出版商当然也要关心文学,不过兴趣不太一样,更有商业的考虑(所以我现在也很有点商人味道了,我不可能出赔钱的书吧),因为这也是这种人的饭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瑞典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关心文学的群体,就是读者,读书人,尤其是读文学书的人。瑞典确实还是文化很发达的国家,所以人口不到一千万,但文学方面戏剧方面电影方面都人才辈出,不少还是国际级大师,如戏剧家斯特林堡、影剧导演伯格曼、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等等。瑞典人整体上文学素质比较高,读书人比较多,他们敬重文学,也比较懂得欣赏文学,也敬重作家和诗人。加上瑞典社会福利比较好,生活水平高,有钱的人自然比较有闲,爱动的从事运动,登山滑雪,爱静的就在家看书,就是出门旅游,也必定带一本书路上读读。我想我的岳父岳母就属于这个群体,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号称瑞典“牛津”的乌普萨拉大学北欧语言系毕业生,之后当中学老师为生。他们都非常爱读书,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女儿喜欢读书肯定有很大影响。过圣诞节,我给岳父岳母送礼物常常就是书。瑞典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读者自发组织的读书会,周末时聚在一起讨论他们每周读的书,或者请作家或翻译家来演讲介绍(我和安娜都曾经应邀给这类读书会做过演讲)。我可以再举个实例:瑞典有三百多个以作家命名的民间团体,比如我翻译的瑞典诗人、也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马丁松,就有马丁松学社(瑞典文的“学社”翻译成英文也是“society”)。这类的作家学社,一般都是成名作家死后,家乡的人为了纪念他而组织起来的,也是家乡人觉得光宗耀祖的事情,把作家老宅弄个博物馆纪念馆的话还可以增加一个地方旅游项目,而且有点钱的话,还多半会设个以作家命名的文学奖,由当地政府从税收里拨点钱出来发奖。比如马丁松学会就有马丁松诗歌奖,今年还是一个日本女诗人得了,在东京的瑞典大使馆举办发奖仪式。其实钱也不多,就几万克朗(几千美金而已),但这类学社的人,自然还是关心文学的,否则还能发奖发到日本去吗?特朗斯特罗姆还没死,他老家也已经有人成立了以他命名的学社,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奖则颁发了好多年了,也是全世界发。以前奖金是几万克朗,他自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此奖现在奖金是二十万克朗了,是当地政府出的。
由此算来,瑞典关心文学的人很多了,以人口比例来算非常高。而且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瑞典文学,甚至关心国际上的文学。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从文学的兴趣上来看,上述的人都会关心中文文学,因为中文文学在他们关心的范围之内。问题是,中文文学需要进入他们关心的范围,而不是他们主动地进入中文文学来关心。简明地说,他们不是因为关心中国而关心中文文学,而是因为中文文学进入了他们关心的文学范围。那么,毫无疑问,中文文学首先需要翻译成瑞典文,需要出版,需要发行,需要得到媒体的介绍,需要得到文学界的评论,才能得到他们的关心和接受。我想,欧美很多国家的情况大概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谈主动地去关心中文文学,可能真没几个人,连汉学家里都不多。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不要以为学汉学的就对中文文学感兴趣,大多数学中文的人其实不感兴趣,也不关心,因为他们原来就对文学不感兴趣,不关心文学,是连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学都不关心和不感兴趣。我问过好几次我教的学中文的瑞典学生,看过马丁松的《阿尼阿拉号》或者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吗?回答几乎总是“没有”。证据:瑞典现在没有几个学中文的是因为写研究当代中文文学的论文而得博士硕士学位的。连安娜的博士学位都和中文文学无关,她本来不搞文学,博士论文写的是关于中国“五四时期”的社团,比如工读互助团那样的团体,是属于历史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她是因为翻译了作品,才开始对中文文学越来越有兴趣和了解的。其实学汉学的人里面,真正懂文学的凤毛麟角(!!!)。这就是现在我不断对国内朋友说的,而且也不怕得罪汉学家甚至不怕得罪安娜而说的,“千万不要把汉学家当作文学家”!比如德国那个顾彬,我就认为他只是汉学家,不是文学家。他在德国文学界根本不入流。汉学家里当然有翻译家,顾彬和安娜都可以算翻译家,但我又有一句得罪人的话,“也千万别把翻译家当作文学家”,至少不能把他们自然而然都当作文学家。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没有经过文学批评方面的训练。安娜还算不错,能听我的批评,而且她现在去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系补修了一门文学理论课,学了不少东西,最后交的分析作品的论文成绩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