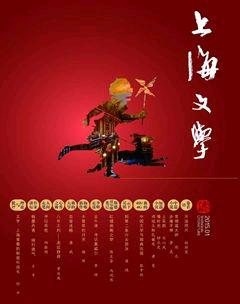翰墨丹青 隔行通气
2015-01-28王干
王干
如果不阅读汪曾祺的书画作品,是很难完整地理解汪曾祺的艺术世界的。汪曾祺被人们称之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不仅是他的精神情怀,也包含他的身手和技艺。汪曾祺是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美食家,同时还是优秀的书画家。中国书协副主席林岫先生在回忆与汪曾祺的交往时说到,“有次在军事博物馆书画院参加京城书画家公益笔会,会后席间书画家闲聊,笔者谈及汪先生的国画小品,又用了‘可亲可爱四字,大画家汤文选先生问,何以‘可亲可爱,笔者遂略述数例,举座服之,汤先生笑道,确实可亲可爱。只是汪先生低调不宣,画人大都不知……”林岫先生说的是实情,甚至直到现今汪先生的书画作品的市价也不如一些二流的书画家高,甚至一些在世的作家的书画作品也超过他。虽然市价不是衡量艺术品的标准,但在某种程度上低调的汪曾祺确实也是被高调的社会文化遮蔽了。
林岫先生作为一位当代书画大师,对汪曾祺先生的书画作品有着深刻的体味和独到的理解,“汪先生写书法作品,很随意,没这样那样繁琐的讲究,只要‘词儿好。逢着精彩的联语或诗文,情绪上来便手痒,说‘这等美妙诗文,不写,简直就是浪费。”汪先生本有散仙风度,书擅行草,虽然走的是传统帖学路子,但师古习法从不肯规循一家。其书内敛外展,清气洋溢,纵笔走中锋,持正瘦劲,也潇洒不拘,毫无黏滞,颇有仙风道骨。问其学书来路,答“一路风景甚佳,目不暇接,何须追究”;见其大字,撇捺舒展如猗猗舞袖,问“可否得力山谷(黄庭坚)行草”,答“也不尽然”;问“何时写作,何时书画”,答“都是自由职业,各不相干,随遇而安,统属自愿”。问“如何创作易得书画佳作”,答“自家顺眼的,都是佳作。若有好酒助兴,情绪饱满,写美妙诗文,通常挥毫即得。若电话打扰,俗客叩门,扫兴败兴,纵古墨佳纸,也一幅不成。”
林岫记录了当时交往的对谈,极为珍贵。汪曾祺关于文学的访谈较多,谈自己文学作品的文章也多,说自己书画作品的却很少。现在作家喜爱书画创作的不少,但都是朝着文人书画或名人书画的方向努力,也就是说书画并不是他们少年的理想。汪曾祺的书画是有童子功的,不是成名之后才对书画感兴趣的。可以这样说,汪曾祺的最早创作是书画。根据一些相关资料记载,汪曾祺在很小的时候,祖父汪嘉勋就指导他练习书法,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父亲汪菊生热爱书画,汪曾祺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看父亲画画。在高邮县立第五小学读书期间,汪曾祺遇上敬业精神强且功力深厚的周席儒先生,在他的严格要求和指导下,汪曾祺的基础打得很扎实。汪曾祺的文学天赋和书法才能,很快得到了祖父汪嘉勋与父亲汪菊生的器重,他们聘请本地两位名流指导汪曾祺。一位是张仲陶先生,指导汪曾祺学《史记》;另一位是韦子廉先生,指导汪曾祺学桐城派古文、学书法。如果不是后来在西南联大遇到沈从文先生,汪曾祺也许会成为沈鹏那样的书法大师。有意思的是,汪曾祺和沈鹏同样是江阴南菁中学的学生,而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沈鹏作为文化部的干部下放到高邮一沟乡,来到了汪曾祺的故乡,或许为他后来的艺术生涯作了神秘的铺垫。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容笔者择机再述。
书画美学对汪曾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创作的选材上。汪曾祺直接描写书画家生活的小说就有《金冬心》、《鉴赏家》、《岁寒三友》三篇。《金冬心》直接以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金农作为主人公,写出了他与袁子才等的交往,并通过一场豪宴展示当时的文人文化和饮食文化。而《岁寒三友》写市民阶层的画师靳彝甫与另外两个朋友的生存状态和仁义友情,小说的题目也是中国书画最常见的主题,且汪曾祺以松竹梅三种中国文人最爱画的意象来暗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小说一波三折,画意和文意达到了高度的融合。《鉴赏家》与其说是汪曾祺塑造了一个独特的鉴赏家叶三的形象,还不如说是汪曾祺通过小说直接来表达自己的书画美学。这篇小说写水果贩子叶三和大画家季匋民的知音之遇,是草根与精英灵犀相通的故事,也是汪曾祺的书画美学宣言。从小说的文本来看,这篇小说可以说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作家幻化成两个人物在对话,追求艺术的理想境界。画家季匋民是汪曾祺的化身,鉴赏家叶三也是汪曾祺的化身。小说中的这样一段对话很有意思:
叶三只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匋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自己负手远看,有时会问叶三:
“好不好?”
“好!”
“好在哪里?”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词: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如果看过汪曾祺的书画集,不难看出,这里面带着他自己的影子。《红楼梦》最早以篇名《石头记》传世时,曾经有署名“脂砚斋”的人,为其作批注,迷倒了多少人,也迷惑了多少人。这里的叶三就是脂砚斋式的点评。熟悉汪曾祺先生的林岫说,汪曾祺画兰草,题“吴带当风”;画竹,题“胸无成竹”;画紫藤,题“有绦皆曲,无瓣不垂”;画凌霄花,题“凌霄不附树,独立自凌霄”;画秋荷,题“残荷不为雨声留”;画白牡丹两枝,题“玉茗堂前朝复暮,伤心谁续牡丹亭”;画青菜白蒜,题“南人不解食蒜”,皆画趣盎然,语堪深味。这种题款方式,明显是汪曾祺式的,或者是汪曾祺身体力行的理想方式。
《鉴赏家》同时还传达了汪曾祺的书画价值观,金钱有价,艺术无价。小人物叶三得到了季匋民赠送的不少精品,季匋民去世后,价格疯涨,尤其在海外,在日本拥有很大的市场,但叶三坚决不出手,多少钱也不出手。虽然作为果贩的叶三生活并不宽裕,但他至死也没有贩卖季匋民的作品,而叶三死后,他的儿子将季匋民的精品放进了叶三的棺材,一起埋了。知音,热爱,艺术,遂成绝唱。这对我们今天的收藏热、鉴赏热、拍卖热仿佛是一个提前的批判。
汪曾祺的书画创作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特别是中国文人书画传统的影响。由于出生在江苏高邮,且晚清扬州八怪的艺术流韵在当地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汪曾祺的书画对扬州八怪的精神充满了向往,并潜心追随、诚心师化。在《鉴赏家》里,他通过季匋民的视角来书写自己的艺术理想:“季匋民最爱画荷花。他画的都是墨荷。他佩服李复堂,但是画风和复堂不似。李画多凝重,季匋民飘逸。李画多用中锋,季匋民微用侧笔——他写字写的是章草。李复堂有时水墨淋漓,粗头乱服,意在笔先;季匋民没有那样的恣悍,他的画是大写意,但总是笔意俱到,收拾得很干净,而且笔致疏朗,善于利用空白。他的墨荷参用了张大千,但更为舒展。他画的荷叶不勾筋,荷梗不点刺,且喜作长幅,荷梗甚长,一笔到底。”汪曾祺对季匋民的荷花分析得如此细腻和准确,不仅体现了他高深的绘画修养,同时也是汪曾祺的绘画创作的内在追求。小说人物季匋民的原型取自高邮的画家王匋民,是和刘海粟同时代的大画家。笔者曾经见过王匋民的荷花作品,也见过汪曾祺创作的《荷塘月色》,这里说的境界,就是汪曾祺的绘画境界的自我写照。与其说季匋民佩服李复堂,不如说汪曾祺佩服李复堂,这也是汪曾祺没有使用王匋民原名的原因,因为王匋民的作品有不少是山水长幅,而李复堂则以花鸟胜。汪曾祺的绘画多花鸟小品,少山水泼墨,也和李复堂一样的。如果把汪曾祺和李复堂的画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汪画对李复堂的绘画精神一脉相承,甚至连题款也与李复堂多有相似,比如林岫提到的“南人不解食蒜”,也是从李复堂那里化出来的。
扬州八怪的创新精神也深刻地影响着汪曾祺的艺术品格。打破陈规,勇于创新,是扬州八怪在书画创作上的独立品格。汪曾祺的书法喜欢用“破体”,他的书法作品喜欢隶篆行楷,混为一体,也就是郑板桥的“乱石铺街”。“破体”,在书法上属于不拘一格又暗藏章法的创新书体,就是多种字体同时出现在一幅作品中。这与汪曾祺的文学理想密切相关,他说“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诗歌的界限”,这种跨文体的写作其实也是一种“破体”。这种“破体”在绘画中干脆打破了书与画的界限。例如他本欲画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诗意,先突兀挥笔,画了一柄白荷初苞,正想下笔画蜻蜓,因午时腹饥,停笔去厨间烧水,炉火不急,水迟迟不开,便转身回来,画小蜻蜓方振翅离去,题“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汪先生说“我在等水,小蜻蜓等我,等得不耐烦了,飞走了”。林岫评价说“信非大作手不得有此雅趣,信非真性情人亦不得有此童心”。现在画家写画杨万里此句,几成模式,都画小蜻蜓站立荷苞,呆呆地,千画一律,毫无趣味,观者自然审美疲劳。汪曾祺的《蜻蜓小荷》,笔墨极简,趣味涵永,且寓文于画,破画之常规,可谓文中有画,画中有文。
中国书画美学对汪曾祺的影响还体现到艺术形式上。汪曾祺在《揉面》一文中说:“中国人写字,除了笔法,还讲究行气。包世臣说王羲之的字,看起来大大小小,单看一个字,也不见怎么好,放在一起,字的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就如老翁携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安排语言也是这样。一个词,一个词,一句,一句,互相映带,才能姿势横生,气韵生动。”我在《论汪曾祺的意象美学》一文中曾说过汪曾祺小说中,“有一种类似套装或组合的特殊结构,这就是‘组结构,‘组结构是以三篇为一个单元,形成似连还断、似断又连的组合体。三篇小说之间,情节自然没有联系,人物也没有勾连,有时候通过空间加以联系。有《故里杂记》(李三·榆树·鱼)、《晚饭花》(珠子灯·晚饭花·三姊妹出嫁)、《钓人的孩子》(钓人的孩子·拾金子·航空奖券)、《小说三篇》(求雨·迷路·卖蚯蚓的人)、《故里三陈》(陈小手·陈四·陈泥鳅)、《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幽冥钟·茶干),六组十八篇,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汪曾祺为什么对这种形式如此偏爱?或许源自他高深的书画修养。这些作品的组合方式,其实是中国书画最常见的一种摆布方式,就是“条屏”。单独放置的书画作品叫条幅,并置的几幅作品叫条屏,有四条屏八条屏等多种形式。“条屏”的创作往往是异质同构的特点,内容上似断实连,汪曾祺的这些套装的组合小说实际是书法美学的融化和变通。落实到小说创作中,则是篇与篇之间的“篇气”,每一篇作品都有自己的气息,有些作品气息是相通的,像《故里三陈》里《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表面是三个互不关联的姓陈的人物,三个人物连起来就是底层手艺人的悲惨命运,作家的悲悯之心油然而现。得注意的是,这种套装结构的方式是汪曾祺晚年的作品,在早期的创作中一篇也没有。他反复再三地实验这一小说形式,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对这种形式的喜爱和器重。再者,这种小说的组合法在其他作家身上有过类似的实验,但如此多的组合,又达到如此高的成就,可以说独此一人。因为其他作家用的是形式,没有能够体会到中国书画艺术的博大精深。
汪曾祺性情冲淡,为人更是与人为善,在文学创作上更是喜欢奖掖后生,提拔新人,对作家同行很少议论,更不会撰文批评和质疑。有趣的是,在书法上他不止一次地发出强烈的批评之声,和他一贯的温良恭谦让的风格反差巨大。在《字的灾难》一文中,他点名批评名家刘炳森、李铎的招牌字浮躁、霸悍,认为他们缺少社会责任,同时认为从北京街上的招牌字上,就能看出现在“北京人的一种浮躁的文化心理”,“愤愤不平的大字,也许会使顾客望而却步”。汪曾祺认为招牌字写得美观很重要,希望“北京的字少一点,写得好一点,使人有安全感,从容感”,并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加强绿化。汪曾祺的批评体现了一个文人的艺术情怀,但在一个与商业合谋的文化产业年代,招牌字的霸悍已经成为老板们的共同趣味。
汪曾祺在1959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时候,在沽源马铃薯研究站,曾经花了三年时间,画过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他一生画过最多的马铃薯,他先画花朵,再画果实,然后切开,再画剖面。这部画作耗了他多年时间心血,遗憾的是这本图谱画好后遗失了。如果能找到将对研究汪曾祺的书画美学和写实思想,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马铃薯的画谱是带有科研性质的,因此笔法必然是写实的素描,当时的照相技术有限。那么汪曾祺如何在科研著作中体现他的艺术禀赋,在写实的笔法中怎么体现他重意轻形的意趣?据汪曾祺自己说,当时条件极其艰难,没有印章,也没有印泥,他就自己找点红颜色画印章,画过“军台效力”和“塞外山药”等印。“塞外山药”容易理解,汪曾祺自比山药。而“军台效力”则是用典,沽源,原清代传递军书公文的驿站,又称“军台”。清代官员犯了罪,敕令“发往军台效力”。可惜的是汪曾祺花了三年心血的《中国马铃薯图谱》不知遗落何处,《中国马铃薯图谱》哪一天重见天日,将是一件重磅的艺术作品和文物。
(本文参考林岫先生的《汪曾祺的书与画》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