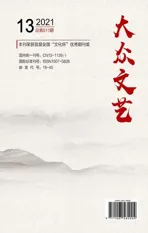当下书法创作中自我表达意识的缺失
2015-01-28陇东学院美术学院745000
王 磊(陇东学院美术学院 745000)
书法作品中的“象”是书法家实现自我表达的一种艺术手段,而“意”才是书法家需要实现的终极目的。“象”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客观存在,“意”才是书法意义上的精神高地。其实,刘熙载的《书概》中对这个问题已经作过明晰的论述,如果没有表意的需要,那么立象就是毫无意义的。刘熙载的这个观点无疑洞彻了书法创作的本质,他充分强调了书法作品的自我表达过程中和表意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抽干了书法作品中的情感因素和表意功能,那么这种书法作品的存在就是毫无意义的,同时这种书法作品就背离了书法艺术的本质。
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书法的实用功能不断退化,今天的书法似乎已经趋向于书法的艺术功能。回顾我们近三十年的书法发展历程,每一次书风的滥觞和更迭,几乎都是试图走出书法自我表达意识不断削弱的泥潭,“流行书风”“米芾风”“王铎风”“魏碑风”“写经风”“二王风”已经吹乱了我们的思想,每一次书风的滥觞中都会有一些人侥幸博得“彩头”,同时又一大批人随之“沦丧”。然而领风潮者和博得“彩头”者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书法家还是注定要被淹没。书风刮地太快了,许多人都来不及细想,就被挟裹进狂热的书风漩涡之中,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相当一部分人为了在展览中一次又一次入展获奖,不惜舍弃自己多年的艺术追求,对新起的偶像进行全方位的模仿,渐渐地失去了真实的自我。
书法是一门艺术,它不是简单的模仿,它需要书法家对自身灵魂和精神的发现和眷顾。我们学习经典法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写得和法帖一模一样,如果书法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艺术迟早都会从艺术之门中被驱逐出去。模仿是学会表达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模仿是为了得到技法,是为了寻找表达自我的方法。就像写文章一样,如果第一个人说:“女人像花一样美”,那么这个人就是创造,如果一大批人都这么说,那么毫无疑问就是模仿。我们不否认,任何步入艺术殿堂的人最初都是通过模仿来打开艺术这扇门的。书法也许特殊一些,这种模仿的过程稍微长一些,甚至是终生的。但是模仿的对象只能是经典法帖,模仿的目的也是为了寻找和发现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去重复。顾亭林《日知录》载:“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然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这段话似乎道出了模仿和创造的关系,如果没有模仿这个过程的创作那么就是野狐禅,如果始终停留在模仿的阶段,那么就不是创造。一切艺术都一样,模仿只是实现创作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我们追求艺术的目的。我们来回视当下的书法家,似乎已经找不出诗人的影子了,留下的只是匠人的互相重复的手艺了。诗人的特质在真正的书法家身上是确实存在的,我们看中国三大行书大家,王羲之也罢、颜真卿也罢、苏东坡也罢,那一个作品中流露的不是令人为之倾倒的诗性呢。《兰亭序》愉悦闲适中表达的人生况味,《祭侄稿》悲愤人生遭际中的凄楚,《黄州寒食诗》命运多舛中散发出的人生苍凉,这些诗化的境界都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大师们已经将书法艺术和自我人生的体验浑然一体地表达出来了,这种境界已经超越了书法本身,达到了艺术的至境。我们不妨盘点一下现在的书法家,有多少人身上流淌着诗人的血液呢,有多少书法作品中有诗性的因素呢,有多少书法家的作品充满着个人诗性的妙悟呢。如果我们以三大行书作参照,来衡量当下的书法创作的话,我们就会不无忧虑地发现我们的书法创作已经和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创作渐行渐远了。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书法家自我表达意识对人性中诗性的生命意蕴的呈现,而不是简单的孤立的技巧的玩弄。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的前言中就明确地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学活动。”生命意志本体的诗化就表明了在艺术创作中自我表现意识的存在,这就说明没有自我表现意识存在的艺术作品是伪艺术,不管这种作品从形式和技巧来看是多么地完熟,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这种没有自我生命意识存在的作品已经被艺术的本质所颠覆。我们当下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作品,以书法艺术的名义充斥着我们的视野,并且被许多书法人和书法爱好者盲目地追从。比如,当下泛滥的“二王”形式的作品,貌似披上了经典的外衣,其实,只是虚有其形罢了,而且这种作品更大意义上只是对“二王”书法的一种简单肢解,一种复印机式的制作,已经失去了书法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作品已经没有诗化的生命本体核心,没有活生生的创作主体的介入,我们从始至终都看不见书法家那颗跳动的诗心了。这种虚无的表达方式只不过是鹦鹉学舌般的重复着别人的话语,和制造者没有丝毫的关系。
书法不是简单的写字,它的终极目的是它的表意功能和艺术旨归。它必须依赖书法家的审美素养。当然,自我审美的觉醒是实现自我表达的前提。临帖的过程就是我们和大师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学习大师的技法,而且还要发现我们自身审美的因子。随着临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对技法的掌握和运用也会越来越娴熟,越来越游刃有余。但是这毕竟不是目的,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我们对自我审美的感知和觉醒。
自我表达意识的获得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我们对已知自我审美经验的积累和对未知自我审美经验的激活。我们常说,“外事造化,中得心源”,自我审美经验的获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在某种程度上要借助于书法以外的东西来实现。艺术是相通的,有些东西可以借助于其他艺术门类来获得。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文学阅读、美术欣赏、摄影体验、音乐激活、舞蹈感知等众多艺术形式来训练自我审美经验。有了这些积累之后,我们在创作中就会不断地强化自我表达意识,提高书法作品的艺术含量。
毫无疑问,技法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技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但是艺术创作毕竟非常复杂的,如果沉溺于技法的卖弄则是本末倒置的。如果抱着技法之上的观点不放,那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我们掌握技法是为了去表达,技法只是我们进行艺术表达的一种手段,并不是我们最后的归宿。前些年,我们有些书法家以艺术为幌子,忽略了技法的作用,把书法创作引向了玄幻的胡同。现在,好不容易把大家引到“二王”这条路上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技法的过度夸大又掩盖了书法艺术的本质,催生了一种新的馆阁体的产生。有少数书家通过自己对经典法帖的长期临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在国展上获了奖,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本来是好事情,可是过犹不及,随之一大批投机钻营者蜂拥而上,对这种作品进行生吞活剥式的重复,导致这种作品泛滥,结果违背了艺术规律,好事变成了坏事。一种表达方式的创造,只能属于一个书家个人,因为这种作品凝结了他自身对书法和自我生命意识的理解和体验,这种生命式的艺术密码别人是无法复制的。“二王”书法以降,学习“二王”的书法家风起云涌,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大师为“二王”书风填充了丰富的内涵,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梳理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李北海是一个面目,孙过庭是一个面目,颜真卿是一个面目,杨凝式是一个面目,米芾是一个面目,赵孟頫是一个面目,董其昌是一个面目,王铎是一个面目,这么多的大师他们源自“二王”,他们又都和“二王”不一样,最终都通过“二王”的学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都成就了书法艺术上的自己。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它负载的东西是非经典的东西无法比拟的,是不可能被轻易复制的。因为经典大师那种自我表达意识是任何人都无法复制的。
古人在书法学习中反复强调,要师法经典,这是我们学习书法的人必须关注的一个焦点。书法创作典中派生出来的东西,越是源的东西内涵越丰富。源是我们终生学习的核心,流只能是我们偶然光顾的风景。源是一个矿藏很丰富的所在,每个人都有可能从中挖掘出自己需要的东西,而流却不具备这种可能。我们把当下学习“二王”的优秀书家和上面列出的“二王”系列大师相比,当下的优秀书家就是属于等而下之的“流”,还不属于“二王”源下的“流”,只能是“支流”中流淌出的“小溪”。因为他们从庞大的“二王”体系中找到的是只属于个人自我表达意识中的那部分,在这种表达中他们简化和消解了许多东西,放大了一些属于个人风貌的东西,附加了自我表达意识的意蕴,所以打动了评委,打动了众多的追随者。艺术之所以能打动人,关键在于有艺术家自我的在场,它只属于艺术家个人,他的作品永远都是个体性的。王羲之的作品永远只属于王羲之个人,王献之的作品永远只属于王献之个人。经典书家的作品只能是实现我们艺术自我的媒介,而不是我们的归宿。
在书法上,我们每个人最终只能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找到的只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我们要表达的只能是属于我们生命深处的诗性的意蕴。否则,我们只能是别人的粉丝,我们只会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书风中沉沦,即使侥幸能博得“彩头”那也必将是昙花一现。
[1]蔡显良.宋代论书诗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07.
[2]秦琴,王伟.论李煜的书法艺术风格[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