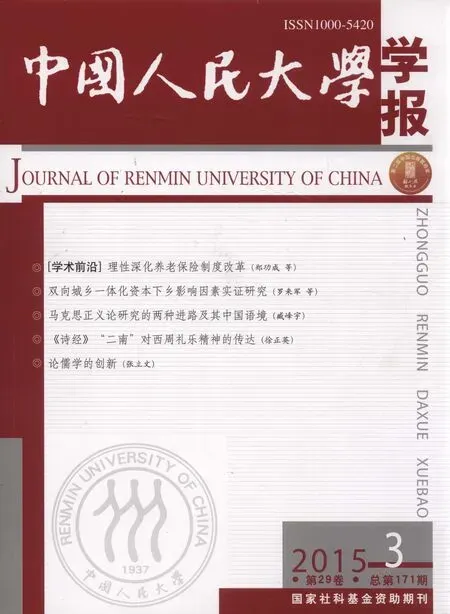论儒学的创新
2015-01-25张立文
张立文
论儒学的创新
张立文
儒学创新的内在根据是儒学文化价值系统历史觉醒的动能。对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的深刻洞察和体贴,激发了儒学从理论思维高度提出化解之道;开放包容的品德使儒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永葆青春,生生不息;唯变所适的特质使儒学随历史时代的人文语境、冲突危机、核心话题、诠释文本的变化而变化,体现时代精神。此三点是儒学在历史逻辑演变中之所以智能创新的根基动力、前提条件、支撑能量、生命活水。在当今信息革命的时代,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魂和根、体和源之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既是时代价值,也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以讲仁爱而言,仁既包“义、礼、智、信”,亦含正义、和合与大同的意思。仁爱随着儒学文化价值系统历史逻辑演变而有不同的解释,或爱人,或仁者人也,或爱人类,或推爱及物为仁,或博爱……但都是唯变所适地为每个时代所诉求。当今,为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仁爱可释为和、和合,以适应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的需求。
儒学;价值时空;信息革命;开放包容;仁爱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民族。从上古炎黄时代就初步形成民族共同体,商周时建构了“协和万邦”的联邦式的和合体,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也是理性的、合理的睿智结构机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需要唯变所适,即转古为今、转旧为新、转死为活、转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这个转化、转生是历史价值时空赋予今人的使命和职责。从儒学在历史价值时空的逻辑演变中,可以获得儒学之所以能不断转生其存在样式和连续创新其理论思维形态的借鉴、启发,为当今儒学创新提供参照。
一、觉醒动能
儒学文化价值系统具有历史觉醒的动能。每一次思想的突破创新,都是对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深刻的洞察和体贴,然后激发了从理论思维高度提出化解之道的自觉动能,从而成为时代思潮。
时代的严峻冲突和危机激烈地刺激着知识精英的神经,使他们不得不反思时代课题。东周时期,礼崩乐坏,战争连绵,杀人盈野,社会无序,协和万邦的形势被破坏,价值信仰的天命被动摇。孔子在对礼崩乐坏的反思中,重塑价值理想,重构伦理道德,重建社会秩序,祈求社会和平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儒学在元创期的文化价值系统的自觉。
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天地人“三才之道”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同归、一致的转化;董仲舒的“王道通三”道出了由战国七雄分裂向统一转变、由封建向郡县制转型以及“道术将为天下裂”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转变。在这场社会大变革、大转型中,曾经以法、道为主导思想治理社会的国家,结果是强秦的速亡和吴楚七国之乱。在面临改制、大一统和长治久安的冲突和危机的情境下,汉武帝“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董仲舒“三年不窥国”地反思,终于重新发现了孔子,重新发现了儒学,决定“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从而奠定了儒学在中华民族历史时空中重构价值的自觉。
魏晋时期,历经汉末三国的动乱分裂,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惨烈而紧张的争权夺利斗争已登峰造极,动辄滥杀,诛夷名族,朝不保夕,名教与自然分裂,名教变成砍向名士的屠刀。面对残酷的现实,人们只能将自然理想境界寄寓于精神世界;面对现实的无望,人们只能将自身无比痛苦的心情放置于纵酒之中。放浪形骸是他们反抗现实的一种方式。他们在道儒融突、自然与名教的调适中,追求精神的自由。这是儒学文化价值系统另一种发展形式的自觉。
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政治动乱,经济凋敝,人民疾苦,百业俱废,人民期盼统一和安居乐业。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鼎立,相互论争,冲突融合,佛教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中实现了中国化。佛强儒弱激发了以古文运动为先导的儒学复兴思潮,韩愈等鉴于佛教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伦常的冲突和危机,倡导道统论,重新弘扬儒学仁义之道。这不仅是中华哲学思辨的深化,也是儒学文化价值系统的又一次觉醒。
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长期混战,致使纲常失序,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惘,导致价值颠覆和意义危机。两宋面临着社会伦常冲突和价值危机、社会积贫积弱冲突和社会危机,儒学式微冲突和其生命智慧危机,为化解冲突和危机,宋代儒学家绍承孔孟道统,重整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终极关切和精神家园,使儒学起死回生,开出新的生命智慧。这是儒学文化价值系统的一次大觉醒。
当前,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与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于亡国亡种深渊已有根本的差异。在全球化、网络化的当下,地球村落化,天下如一家,世界已成为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冲突,由此带来了自然生态、社会人文、伦理道德、精神信仰和价值危机,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关系着全人类的前途与未来。和合学作为化解此冲突和危机之道,标志着儒学文化价值系统的又一次觉醒。
时代的冲突和危机是儒学文化价值系统觉醒的基础和动力,是儒学温故创新的活水和根基,更是儒学创新思想一浪高过一浪的内生增长力。
二、开放包容
儒学文化价值系统具有开放包容的品德。开放才能“致广大而尽精微”,包容才能“极高明而道中庸”。由于其开放,而能海纳百川、博收广采古今中外文化;由于其包容,而能有容乃大、融突转生中外古今文化。开放包容的品德使儒学永葆青春,生生不息。
儒学创始者孔子就是具有开放包容品德的典范。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典籍五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等。孔子收集、整理、研究旧章,“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孔安国:《尚书序》,《尚书正义》卷1)。
孔子定礼乐,明《礼》、《乐》、《诗》、《书》、《易》、《春秋》其文其义。此“六书”(后称“六经”)是中华民族关于宇宙、社会、人生、思维的存在样式或精神样式的符号踪迹,是中华民族在与宇宙、社会、人生、思维交往与反馈活动中凝聚的文化基因的遗传和文化意向的遗留,它对中华民族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实践活动的体认、生命智慧的觉解、智能创造的阐释具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看似“述而不作”,实乃综合创新。先秦诸侯国林立,百家争鸣,此“百”是为多的意思,司马谈归于六家,班固称为十家。秦汉大一统要求儒学必须创新,赋予元典儒学孔孟之道以新生命、新理念。董仲舒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明孔氏”,以孔孟仁义之道为核心价值,吸收先秦阴阳、道、法、墨、名各家思想,融突和合为新儒学,构建了化解时代冲突和危机、体现时代精神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与佛学的强势相对而言,儒学渐趋弱势。然而,正是儒学崇高而理性的开放包容的品德、儒学的慧命促使儒释道三教互相对话、交流、切磋,不仅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家,也产生了佛学化的儒家。儒学引领佛教的中国化,即佛教在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会通、融合中,特别是在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学的融突而和合中,诞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并传播于东南亚和世界各国。
儒释道三教在隋唐时论争不息,为适应中央集权统一国家“一道术”的需要,曾提出开放包容的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文化整合的方法,但由于各教之间价值观迥异,致使兼容并蓄长期不能落实。宋代儒家开放包容,解放思想,冲决“家法”、“师法”的网罗,知己知彼地出入佛道几十年,而“尽究其说”。在对儒学深刻反思和对佛道之学尽精微地研究后,把三教兼容并蓄落实到“天理”上。程颢说:“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这一体贴开创了儒学的新生命、新学说、新学风、新体系,这是以儒学为宗、道统为旨、释道为材的儒学智能创新的实践,把中华文化价值系统推向了高峰。
近代中国内外交困,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内是清王朝腐败透顶,不可救药。胸怀救国救民悲愿的知识精英们以开放包容的品德,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涌现出了一批早期改良主义者。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更是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身心情感,也更坚定了有识之士变法图强、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决心和信心,诞生了波澜壮阔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然却以谭嗣同等“六君子”的热血换来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变法维新失败后,唯有推翻清王朝一途,于是有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在西风劲吹横扫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代表的儒学及其创始人孔子,成为被痛批、打倒的对象,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口号响彻云霄。然而,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抗日战争中,爱国知识分子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悲愿,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救民的责任意识,弘扬中华文化,振兴民族精神,现代新儒家接着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体学、陆王心体学及张(载)王(夫之)的气体学讲,以抵制和抗衡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行径,而开出了儒学的新局面。
在全球化的当代,儒学更以其开放包容的品德,胸怀全球,吸收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外为中用,西为中资,马为中化,冲突融合,智能创新,开出当代和合学的新儒学文化价值系统。儒学开放包容的品德是儒学文化价值系统不断创新的前提和条件,是儒学内涵更新发展繁荣的生命力,是儒学吐故纳新、生生不息的驱动力。
三、唯变所适
儒学文化价值系统具有唯变所适的特质。《周易·系辞》曰:“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天地人三才之道是不断变迁的,社会人事、制度、王朝不断替换,历史时空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也变动不居。每个历史因素的发生,即每个历史时期的冲突和危机的出现和化解,必然推动着新的哲学思潮的诞生。新的哲学思潮既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也适应了新历史时代的需求,赋予儒学文化价值系统以新智慧生命。
在儒学文化价值系统随历史时代唯变所适的过程中,儒学的理论思维形态也随着历史时代的人文语境、冲突危机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诠释经典文本的转换而转换,随着儒学文化价值理想、精神境界诉求的转变而转变。
儒学文化价值系统的逻辑演化是系统的、有序的,其理论思维形态的创新和转生,都是对以往既定的、固化的理论思维逻辑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的冲决,这个冲决使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的元创期、两汉的奠基期、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期、隋唐的深化期、宋元明清的造极期和当代的创新期。随着此六个历史时空逻辑的变化,儒学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话题、诠释文本、理论思维形态,以及其价值理想、精神境界的追求均大相径庭。
先秦儒学以思议“道德之意”为核心话题,其依傍的文本为“六经”,其理论思维形态为人文性的元典儒学,其价值理想是追求一个没有杀戮、没有战争的和平、安定、统一的生存世界。
两汉儒学思议“天人相应”的核心话题,其诠释文本为《春秋公羊传》,其理论思维形态从人文性的元典儒学转变为独尊性的经学儒学,其价值理想、精神境界是追究人之所以生存的根源、根据,回应人为什么生存的天人感应及其相互制约问题,追求大同世界的人人安居乐业,不受社会动乱、战争之苦。
魏晋儒学在会通儒道中,思议“有无之辩”的核心话题,其依傍的文本为“三玄”,其理论思维形态从独尊性繁琐的经学儒学转变为思辨性义理的玄学儒学,其价值理想、精神境界是回应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没有意义、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人生价值等问题,追求“玄远”的自由人生。
隋唐儒学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由魏晋“有无之辨”向“性情之原”的核心话题转生,其诠释文本为佛经和道经,标志着在对人生本来面目的参悟上有了自觉,其理论思维形态亦从思辨性义理的玄学儒学向原道性复性的道统儒学转生,其价值理想、精神境界是追究人生从何而来、死了到何处去的灵魂安顿、终极关切问题。
宋元明清儒学在融突而和合儒释道三教中,由隋唐“性情之原”向“理气心性”的核心话题转变,其依傍的文本是“四书”,标志着儒学价值自觉意识、智能创新意识、历史责任意识、忧国忧民意识的大发扬和大提升,其理论思维形态随之从原道性的道统儒学向“理一分殊”性的理学儒学转生,其价值理想、精神境界是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世界。
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理学讲,而会通中西。
在全球化、信息革命的时代,核心话题由宋元明清的“理气心性”向“和合学”转变,其依傍的文本是《国语》,辅以《墨子》、《管子》,标志着儒学文化价值系统在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其理论思维形态由理学儒学向和合学儒学转生,其价值理想和精神境界是追求天和地和人和、天美地美人美、天地人共和乐和美的和合世界。
儒学唯变所适的特质,是儒学文化价值系统之所以能“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的支撑,是儒学之所以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能量。儒学唯变所适的特质使其能冲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网罗,与时俱进,随历史时空的变迁而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唯有“变则通,通则久”,儒学才能永葆其青春活力,才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四、仁的现释
儒学文化价值系统历史觉醒的动能、开放包容的品德、唯变所适的特质,是儒学之所以能智能创新的根基动力、前提条件、支撑能量、生命活水。儒学若没有创新性的超越,就没有生意化的流行,就会成为工具化的教条或僵死化的陈迹;儒学如果没有创新性的流行,就没有实质性的度越,就会沦为虚伪性的粉饰或云烟般的消散。创新是一切理论学说的生命线,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
人类文明大体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现在进入了信息革命的新阶段。当代信息革命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势不可挡,它虽不采取暴力的形式,但比之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更深入、更具影响力。它全面改变了人类在世的一切方式,如人类的生活、交往、行为、写作、购物、议政、舆论、思维、情感等,改变了人的生活、行为、心理、精神的方方面面。它突破了以往的现实性、经验性、时态性、空态性、面向性的世界,度越了现实世界,而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中,虚拟时空代替了物理时空,以虚拟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生态环境替代现实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生态环境,创造了新的时空观;在虚拟世界中,人类拥有更舒适、安逸、丰富、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创造了新的价值观。虚拟世界把不现实变成了现实、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在信息革命的严峻挑战面前,儒学文化价值系统如何创新?如何适应信息革命的诉求?如何转旧为新、转死为活?这是一个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过程,也是一个“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的历程”,因为儒学是中华民族的魂和根、体与源之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既是时代价值,也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以“讲仁爱”而言,仁既包“义、礼、智、信”*朱熹说:“仁所以包三者,盖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所以皆从仁上渐渐推出。”又说:“仁,浑沦言……义礼智都是仁。” 参见朱熹:《朱子语类》卷6,1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亦含正义、和合及大同之意。
在历史上,“仁爱”随儒学文化价值系统的演变而呈现不同的诠释,以便唯变所适。樊迟问孔子仁是什么?孔子说:“爱人。”孟子更直白地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据载,孔子有一天退朝后,家人对孔子说马厩起火,孔子只问伤人乎,不问马。在当时马的价值比人的价值要超出好几倍,足见其对人的尊重。在春秋无义战、杀人盈野的情景下,孔子高扬爱人旗帜,是对人的伟大发现,是对杀人者的抗议。换言之,要把人当人看待,这样才能尊重、关怀、体贴他人。所以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中庸》说:“仁者,人也。”人是一个人,是独立的主体。*孔子、孟子以往对仁的诠释,参见拙著《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316~3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说卦传》)。这是对人道的挺立和人道主义的发现和涌动。
秦汉时一大统,秦始皇“严刑峻法”,“以吏为师”。吕不韦主张“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吕氏春秋·爱类》),把人与人视为同类,这种同类相爱意识类似于孔子的“泛爱众”,爱类就不能杀人。“杀民,非仁也。”(《吕氏春秋·离俗》)残杀人民,便不是人,这是吕不韦对秦政严刑峻法的箴弊。汉初,陆贾、贾谊在总结强秦速亡的教训时指出:仁义不施者也。董仲舒为化解汉代所面临的社会冲突和危机,提倡“天人相应”之道,主张“仁者,所以爱人类”(《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仁之法,在爱人”(《春秋繁露·仁义法》)。如何爱人?如何“天人相应”?他对人与天的关系做了创新性的解释:“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人本于天,天是人的曾祖父,人与天同类,人的形体、血气、德行、好恶、喜怒等都是天之所化生。因此,敬畏、尊重、仁爱天,就是敬畏、尊重、仁爱人自己,反之,就是对天对人的不敬畏、不尊重和不仁爱。这是仁的进境创新,是儒学文化价值系统的一次智能创造。
魏晋时崇有论派裴頠患时俗放荡,不尊儒学。何晏、嵇康、阮籍等名士,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嵇康从自然人性的养真出发,揭露外在仁义的虚伪性,激烈批判“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于是兼而弃之”。参见《嵇康集校注》,2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于是,裴頠作《崇有论》,绍承儒术,主张“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晋书·裴頠传》),居守率行儒学仁义之道。尽管王弼与裴頠相对,属本无论派,但他作《论语释疑》,在释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时说:“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论语释疑辑佚·学而》)以自然释仁、爱,是道法自然思想的贯彻。
隋唐时儒释道三教融突,韩愈忧“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韩愈:《原道》),认为佛教乃外来的夷狄之法,并非中华文明的道统、正统,然而却加之先王之教之上。什么是先王之教?韩愈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同上)先王的仁义道德是中华文明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道统的内涵,此“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同上)。韩愈释“博爱之谓仁”似与董仲舒释“仁者所以爱人类”同,然在唐人崇佛、道德仁义“不入于老,则入于佛”的情境下,韩愈却高举儒学道德仁义大旗,振兴儒学仁义价值,接续中华文明道统。
宋代贯彻祐文政策,思想解放,各学派之间互相切磋,儒学文化价值系统“造极”,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儒学伦理道德的信仰,把仁提升至道德形上学的高度。周敦颐不仅以爱释仁,而且以生释仁。他说:“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顺化》)仁是生育天下万物的根源,义是端正万民的道德根据,这是道体学家(理体学家)的创发。二程不仅释仁为生,而且释仁为公。他们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1)“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河南程氏遗书》卷2)这是以天下为公释仁,作为儒学的价值导向。仁既生、又爱、且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原则。“是以仁者无对,放之东海而准,放之西海而准,放之南海而准,放之北海而准。”(《河南程氏遗书》卷11)仁是普遍性形式,是无对的形上学。
理体学之集大成者朱熹,释仁别有一种意味。他以理体学的观点诠释仁:“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孟子集注》卷1)仁者爱人、博爱都是仁的一种表象,“爱之理”是对仁的表象的所以然的追究,即仁爱的根据为理,赋予其形而上的意蕴。朱熹绍承周、程,亦以生释仁:“仁字恐只是生意”,“如谷种、桃仁、杏仁之类,种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得都是生意”(《朱子语类》卷6)。这是以具体事实论证仁的生意。
心体学者陆九渊和王守仁,则以心性释仁。陆九渊说:“仁义者,人之本心也。”(《与赵监》,《陆九渊集》卷1)王守仁说:“盖其心学纯明,而又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心可达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如果说朱熹之仁得于心外的天理而直贯心之德,陆王则从“心即理”出发,以本心之仁通贯天地一体之仁,而无人己、物我的分别。
气体学者从“理者,气之理也”出发释仁。王夫之说:“在天为阴阳者,在人为仁义,皆二气之实也。”(《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告子上》)仁义实为阴阳二气。戴震说:“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仁义礼智》)仁是气化流行的一种形态。
理学儒学的各派都从其价值观出发对仁做了不同的诠释,无论是“性之理”之仁,“心之理”之仁,还是“气之理”之仁,都是在天理价值观逻辑范围内的论争,这对于理学儒学的丰富、繁荣、发展大有裨益。然而,理学儒学经长期被奉为主导意识形态后,便逐渐固化、僵化,以致成为“理能杀人”之具。理学儒学在为道屡迁下,已不能唯变所适。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向西方学习,会通中西,以西方的进化论、契约论及其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诠释仁,尤其是接引自然科学释仁。康有为说:“仁从二人,人道相偶,有吸引之意,即爱力也,实电力也。人具此爱力,故仁即人也;苟无此爱力,即不得为人矣。”(《中庸注》)这是以物理学中的力解释仁的互相吸引的特性。“仁者,热力也,义者,重力也。天下不能出此二者。”(《人我篇》)仁为爱力、电力、热力,都有吸引、流通、热能的功力,试图给予已固化、僵化的仁以新的生命活力和能量。
谭嗣同自称私淑康有为,他著《仁学》,把儒家的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基督教的博爱互相融突,以仁爱救人救世,又把仁与自然科学中光热传导、电磁引力等现象的媒介体“以太”相结合,而通向自由、平等,构建了仁(心、识)——通(以太、心力)——平等的理论思维逻辑结构。他认为仁之体是不生不灭的形上学,“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1](P292)。仁具有感而遂通的功能:“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2](P291)谭嗣同站在理论思维的高度揭露清王朝闭关自守、不通而落后、落后而挨打的败局,故以通为仁的第一义。“是故仁不仁之辩,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3](P296)通才能使中外、上下、男女、内外、人我平等,这是仁的标的,亦是谭嗣同的价值理想境界。
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把进化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人类进化三个阶段,其中人类进化以互助为原则。“仁则不问利害如何,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无怨矣。仁与智之差别若此,定义即由之而生,中国古来学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据余所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4](P313-314)发扬人类博爱精神,为救中国,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这便是为革命服务之仁。
在当代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五大冲突和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信仰、价值五大危机的情境下,和合学把仁诠释为和、和合,作为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之道。其实,把仁诠释为和,并非和合学的独创,朱熹曾说:“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朱子语类》卷6)“要识仁之意识,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同上)又说:“仁虽似有刚直意,毕竟本是个温和之物。”(同上)仁具温和特质,就温和之气言,如春天温和之气生物;就温和之理言,则是天地生物之心;就伦理道德言,“试自看温和柔软时如何,此所以孝悌为仁之本”(同上)。子女对父母要孝,兄弟间要悌,体现了亲情间的温馨与和合。和合学将仁释为和、和合,既体现了儒学文化价值系统的开放包容精神、文化的自觉功能和唯变所适的特质,亦是当代世界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在化解信息革命时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过程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建构天地人共和乐、共和美的和合世界,是和合学的价值理想,亦是儒学文化价值系统一次转死为生、转旧为新、转丑为美的智能创新。
[1][2][3]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
[4]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三册,上海,上海三民公司印行,1927。
(责任编辑 李 理)
On Innovation of Confucianism
ZHANG Li-wen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How to develop Chinese traditional spirit and our forefathers’ wisdom, how to moderniz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ther words,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old to the new, the evil to beauty, is today’s people’s mission entrusted by historical value, time and space. The internal basi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on of Confucianism is the historical awakening energy of the value system of Confucian culture, which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conflicts and crisis of our times, stimulates solution from theoretical height; the open and tolerant virtue of which, embraces all, keeping Confucianism long-lasting,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while the traits of adaptive changing of which, represents the Zeitgeist of Confucianism that advocates keeping up with the changing of the times as regards humanistic contexts, crisis and conflicts, core topics, and textual interpretation.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points are the basic power, preconditions, support as well as life vitality of the intellectual innov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its historical and logical evolution. As one of the roots, soul, the main body and origi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ucianism advocates benevolence, beholds people-oriented values, observes good faith and trustworthiness, respects justice, worships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pursues universal good, all of which are not only Confucian core values but also remain the values of today’s Information Revolution era. Taking the advocating of benevolence for instance, benevolence not only contains rites, wisdom, trustworthiness, but also includes justice and universal harmony. Though the illustration of benevolence may vary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logical changing of the value system of Confucian culture, such values as loving the people, being a good man, loving the mankind, loving the goods like loving man, universal love appeal to all ages with adaption. Today, to confront the common five major conflicts and crisis faced by all mankind, such appeals can be illustrated as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that i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world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win-win, which are the major trends of the times.
Confucianism; value time and spac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pen and tolerate; benevolence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