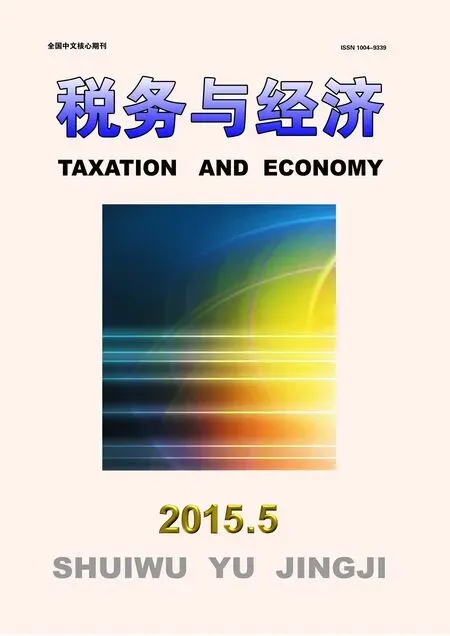幸福感、收入分配差距与税收社会福利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探讨
2015-01-16马旭东
马旭东
(内蒙古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现代化是个充满着悖论的历史进程,一方面,现代化提高了社会总产出,使得人们享受了以前未能享受的产品;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了闲暇的丧失、精神压力的增大以及健康情况的恶化。家庭问题和社交问题使得很多家庭越来越感觉到痛苦,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命题被行为经济学家Diener E.(2008)[1]所证伪,认为国民收入越大社会越幸福的观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被证实根本站不住脚。由此,经济学家不难想到幸福感的来源究竟是什么?
一、幸福感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心理学基础
幸福感一直是哲学家和普通百姓苦苦追寻的东西,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感本身是一种心理感受,因此,幸福感这一话题成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许多心理学家的关注热点,并为行为经济学研究幸福和福利问题打开了大门。心理学研究幸福感主要集中于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领域,随着经济学不断介入幸福感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幸福感这一概念得到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行为经济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
(一)幸福感受到心理参照系的影响
幸福是一种健康的主观状态,取决于我们的相对参照系,并建立在如下的进化心理上:在简单的社交愉悦与生活目的中找寻意义。行为经济学这一观点似乎与传统经济学存在着一个大悖论,传统经济学以理性选择作为分析的基础,认为人是自私的动物,追求效用和利益最大化,所以越是富有越是幸福。但这一观点似乎并不符合社会实践。
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Jeremy Bentham(1823)[2]设计出“快乐算法”来衡量幸福,用“七种要素考量愉悦或者痛苦的价值”:纯度、强度、近似度、确定度、繁殖度、范围和持久度。以此为基础,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直深信:效用的提高能增强国民整体的幸福感。就整个社会而言,只要我们按照边沁的思想“记录”和“排查”每个人,计算出表现良好倾向度的总人数,即对社会政策、目前的生活状态具有良好感觉的人数;重复此过程,再计算出“表现”不良倾向度的总人数,两相权衡,若落在愉悦的一面,则说明其认为该举动使总人口或者整个社会大体倾向于良好;若落在痛苦的一面,则说明其使整个社会大体倾向于不幸。
以中国为例,目前我国有13亿人口,每次确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应当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意调查,采用边沁的“快乐算法”。但这一般会遇到两个问题:其一,调查的社会成本可能非常昂贵;其二,幸福的主观性感觉以及与其他人比较的困难性,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快乐算法”实施起来非常困难。抛开所有的富裕和繁荣,从主观的角度来看,如今的人并不比二三十年前的人们更幸福。行为经济学将这一现象称为进步悖论或者“幸福脱节”,直接否定了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命题。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实际数据的证实。
部分行为经济学家对欧洲12国及美国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发现,1975~1992年每年向40万人提出相同的问题:“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你会怎样评价自己的状况?”27%的人认为非常满意,54%的人还算满意,14%的人不大满意,5%的人完全不满意。1994年对上述各国再进行调查,超过半数的人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钱过上满意的生活。欧洲的研究人员还发现,失业和离婚会使幸福感急剧下降。有史以来,渗透力最强、调查国家最多的幸福感研究,大概非“Word Values Survey”莫属,共包括250个问题,考察了400~800个可测变量。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具体的全球体验会暂时性地增加或者削弱人们的幸福感,但平均幸福感基本保持没变。
行为经济学认为,金钱与幸福感之所以脱节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相对价值和基因的满足度。相对价值即相对于周围人和过去的相对收入分配差距、消费差距和社会地位差距,这一理解与主流经济学中的公平与社会正义是相关的;基因的满足度与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资源的可获得性(经济自由)存在密切关系。当基因的满足度能够实现时,相对价值则成为了影响幸福感的重要标准。
(二)收入分配比经济增长更具有心理学意义的幸福
经济学家Solnick S.和Hemenway D.(1998)[3]调查了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257名学生、教员和职员,证明了幸福感的主观性和相对性特征。研究人员询问受试者,是愿意本人长的超级好看但在本地区只能排名第十,还是自己长相一般但本地区最好看?受试者大多偏好于后者,甚至可以牺牲绝对的吸引力。问到同样问题也有类似的答案:是愿意自己的孩子绝顶聪明但周围的孩子全部才华横溢,还是较之于其他孩子都聪明但孩子的智力一般,绝大多数受试者愿意选择第二种。Solnick S.和Hemenway D.(1998)[3]对瑞典18~66岁的人进行随机采访,他们发现,收入和生活必需品、高档消费品具有很强的位置性特征,即相对位置决定了其满意度和效用水平,而汽车的安全性和闲暇时间的位置性较低,其效用水平主要来源于绝对量。
收入与感知收入需求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实际收入每增加1元,“必要收入”就得提高0.4元,富人相比穷人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收入。也就是说,今年如果加薪1000元能够使你获得暂时的幸福,到了下一年你一定会有新的需求标准,这一标准一般是为了达到与现在相同的满足感,就需要提高收入400元。这一现象被行为经济学家称为“快乐水车”。随着经济增长,人们永远在追求一个达不到的目标。
由此能够看出,解决幸福感失调的主要方式是不再追求金钱,不再将之视为获得幸福感的途径。如果我们将幸福视为愉悦地享受物品的数量和多样性,因为对愉悦的渴求,使得我们陷入了“快乐水车”。如果我们仅仅追求财富的增长,认为一旦实现了增长就实现了幸福,实质上反而使得我们陷入更大的痛苦,因为周围的人享受物品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化,也就是你的参照系发生了移动。要摆脱“快乐水车”给我们带来的不幸,格雷戈里·伯恩斯(2008)[4]认为必须重新审视社会科学的关注点。由于幸福感具有非常浓厚的收入分配基础,或者说为了摆脱“快乐水车”,社会的发展应该更多关注收入分配差距而非经济增长。
二、从幸福感的构成要件上探析税收调节的作用基础
(一)幸福感的构成要件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Gilbert D.(2007)[5]提出了一个寻找幸福的办法:人不能总是寻求幸福,幸福是从偶然所得而获取。人类是考虑长远未来的高等动物,幸福感极大地受到我们事前预测的影响。通过实验Gilbert D.发现,如果我们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者接到老板的电话通知被解雇了,这样的喜悦和痛苦都不会持续太久。人类的免疫系统足够强大,可以使得我们免受挫折、失败、悔恨和侮辱带来的痛苦。
意大利神经学家Vallortigara G.(2013)[6]及其在巴里大学的同事们对狗摇尾巴进行了研究,从中找到了幸福感的进化根源。根据狗摇尾巴的规律性特征发现,动物的左脑和爱情、友谊、归属和安全等正面情绪联系在一起,而右脑与负面情绪联系在一起。行为遗传学发现,人们的情绪差异绝大多数来源于先天差异,当一个人的左脑比右脑发达时其对正面场景的反应会更好,任何人遇到正面的场景时都会感觉到自己更幸福,只是这一“幸福基准点”存在着差异。“幸福基准点”最初都是由先天的基因加以设定,后天随着环境和经历加以调整和修正。这也能说明为什么一个罪犯往往会再次犯罪或者靠赌博为生的人很难发财,而一个接受良好教育的人能够感受到幸福。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lton Freedman和Robert Lucas的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的心理学基础也正源于此。如果某人的收入产生了适应性预期,将不会改变消费者的经济行为,自然也不会改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这正是幸福基准点修正的结果。
心理学家Myers D.和Diener E.(1997)[7]确认了与幸福高度相关的特征:高度自尊;个人控制;乐观精神;外向性格。幸福的人一般喜欢自己与别人相处融洽,偏见较少,相信自己会更健康、更聪明、更具道德心。幸福的人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能自由选择和决策,并承担选择带来的结果。缺少自由的人一般士气低落,健康状况也不好,Amartya Sen(1981)[8]认为贫困是导致不自由的重要原因,贫困导致的社会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健康等方面,更为主要的是带来了不自由。Acemoglu D.(2005)[9]认为集权国家人民的幸福感较低,原因在于人们选择的范围和权利受到了制约和限制,由此带来个人控制能力的下降。幸福的人具有乐观精神,愿意以积极的心态看待人和事,通过选择和影响“幸福感基准点”来达到使自己幸福的目的。同时,幸福的人一般个性外向,喜爱社交,喜欢与周围的人相处。通过社会交往人们一般能够得到善意的鼓励、支持等社会关系,并从中实现更好的心理状态。
(二)私有产权与税收:道德秩序与社会秩序间的平衡
宗教是一种社会制度,North D.C.[10]认为,宗教是完整的人类文化机制、一种非正式的制度,鼓励人们树立互惠性利他行为、亲缘性利他行为和间接性利他行为的道德标准。宗教在国家出现以前已经存在,起到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和增进人们交往、减少敌意增强合作的功能。随着国家的出现,有的宗教为了国家利益而服务,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社会模式;有的宗教成为政府的“竞合势力”,通过政府和宗教分工地竞争与合作形成社会的道德基础。亚历西斯·托克维尔[11]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67年后,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论述了宗教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教会是旧制度这个整体庞大建筑物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因而大革命一般首先攻击的是宗教。然而法国大革命最终带来的法国社会的持续动荡正是因为大革命对整个法国道德基础的破坏性作用,托克维尔认为“尊重宗教精神是国家秩序与个人安全的第一保障”。最为原始的核心概念是最为需要发展和重新认识的东西,私有产权就是最为原始且最为需要重新认识的核心经济概念之一,私有产权的确立是人与人交往(生产关系)的最初的基础。假定A不是自己身体及其最初所分配、生产或资源获得物品的所有者,那么只有两种可能:另一个人B是A及其分配生产或者根据合约获得物品的所有者,或者A和B是双方身体和物品的共同所有者。前一种情况下,A是B的奴隶并受其剥夺,A不能够拥有B的身体及其最初分配,而B能够拥有A的身体及其最初分配,这样就出现了A和B适用于不同的法律,从而毁灭了制度的普适性原则,这样的制度并不符合伦理,即正义的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每个人。第二种情况反映了人身和财产的共同占有问题,如果所有的物品都是集体财产,那么除非获得全部共同所有人的事前同意,否则任何个人无法在任何时间使用任何物品。这样一来,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包括声带)都不能完全拥有,他又怎么能给别人这样的许可呢?集体占有会导致人的语言、财产和精神的丧失,人类也会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灭亡。
Rothbard M.N.(1982)[12]认为,国家是通过对物质的强制征收(税收)取得收入的,取得了对武装力量的轻质性垄断权以及对特定地区领土范围的最终决定权力。前者构成和确立了一种大规模的盗窃行为,而后者妨碍了政治上的自由竞争。Augustinus认为“如果没有正义,国家就无非是一群强盗。”按照Rothbard的伦理学论述,国家侵犯财产权的唯一合乎伦理的做法是为了维护正义,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目的也应该围绕着维护正义、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为准则。保护弱势群体、进行宏观经济干预等政府行为都应该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
既然税收的伦理基础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维护正义,那么税收必须在侵权(侵犯私有产权)和社会责任(寻求社会正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事实上,政府作为征税代理人存在着一个悖论:一个侵权的社会利益保护者如果被允许,将导致政府会征越来越多的税收(提高税率的倾向),而提供更少的社会正义;而且,政府垄断地位的作用会使得减少社会正义的倾向持续加剧。因此,社会正义将变得有利于国家而不断地加以扭曲,“人类行为的永恒执法最终消失,并被国家所制定的实体法的法律观念所取代。”需要保护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平衡的路径是通过政治竞争以限制国家权力的膨胀,否则,税收将沦为侵权的工具而非提升社会正义的手段。
(三)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行为理论基础
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本性指引着社会规则。人类在进化的历程中既进化出了诚实地、公平地、合作地想要为集体和社会做正确的事,同时也竞争地、好斗地、自私地想为自己和家人做正确的事。在自我进步的自私欲望和改良社会的利他欲望相冲突时,一般需要法律和正式制度的调节。私有产权即为解决这一冲突的重要制度创新,当然,私有产权制度也有着明显的进化论的印记。
制度创造出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和正式的法律规范,监督个人行为,管理人和人之间的结构性互动。North曾经因为对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开拓性研究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North(1990)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指的是诸如习惯、习俗、惯例、价值观等由下而上、自我组织、平等主体之间相互制约的制度,在人与人交互动态的过程中慢慢进化和改变。正式制度指的是法律、法规等自上而下有意识地设计的制度,正式制度的改变一般都是突然发生的,以新的法律、法规替代旧的法律、法规,正式制度的改变一般涉及到政治的动荡。Erin Ann O′Hara(2000)[13]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携手运作并携手演进和改变的。税收制度一般可以将其纳入正式的制度体系中,仅从实际税收而言,可以将税收制度分解为正式的税收制度和非正式的税收制度。预算收入可以看作一国的正式税收制度,而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可将其视为非正式税收制度。税收构成了纳税人的交易成本,降低了纳税人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社会效率损失。从税收的正义观角度,预算收入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意义,而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在社会效率损失的条件下可能进一步损害正义。因此,非正式税收制度是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
1.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特征。一国预算收入具有正式制度的特征,是一国政府自上而下确立,是暴力惩戒的手段,由特殊机构加以管理。由于正式制度具有通约性、社会统一性和社会赞同性等特征,使得一国预算收入具有平等、全面、系统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能力。平等体现在对于全部的纳税人,只要处于相同的纳税等级即需要缴纳等额的税收;全面体现在税收对于全部的公民具有统一性特征;系统性体现在税收维护社会正义的能力。
2.税收可以兼顾社会效益与社会公正。按照Rothbard的理解,税收除了维护社会正义别无它用,可见税收在维护社会正义上的本质性作用。税收能否在维护社会正义的同时不损害效率,这取决于课税对象和结构。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社会效益是一个社会的投入产出情况。例如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者征收较高的税收,虽然降低了高收入者的个人选择空间,并不一定对生产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人持有某项财产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获得长期的利益最大化,禀赋效应(Kahneman D.,1990)[14]对此做出了解释:为了捍卫自己已有的东西,我们愿意付出的资源和精力明显多于觊觎者的投入。而人一旦得到了某项资产,并不一定是为了使得资产的收益最大化。根据禀赋效应,征税一定会带来政治机构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即Rothbard所说的“盗窃”,各国采取代征、代缴政策在所有者得到前将其“夺走”,实质上降低了“税收侵权”带来的痛苦。企业所得税的多少也未必导致对生产的正向或者逆向激励,原因在于企业所得税作为企业事前的支付形成了企业的沉淀成本,减税和增税能够产生正向和逆向的激励,但对于给定的税率并不会对企业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根据“损失厌恶”原则,减税产生的正向激励一般比增税产生的逆向激励要小。因此,想通过减税来提升社会生产的目的受到了较大的限制。相反,税收的收入分配职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3.税收改变了社会的自由度。自由选择和决策是幸福感的重要构成要件,Adam Smith是经济学的鼻祖,是自由放任理论的重要倡导者。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得到了John Mill等人的发展后,获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支持。Hayek组织成立的佩尔兰山俱乐部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地,成为反对Keynes的国家干预理论的阵营,形成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新的发源地。Fogel(2000)[15]认为自由是人类福祉的本质,是决定内心体验和幸福感的重要标准,是幸福的伦理基础。古典经济学认为税收能够降低赋税者的自由度,改变了赋税者的购买力,但通过转移支付可以扩展获得转移收入者的自由度。根据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的社会福利(庇古命题)的增长实质上是社会总自由度的净增长。
4.税收对幸福感的全面影响。综合上述观点不难发现,税收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全面的。幸福的构件中,个人的控制能力(Sen将其称为可行能力集)是关乎幸福感的关键,税收的作用虽然影响了部分人的控制能力,但极大地拓展了低收入者的个人控制力。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总的社会福利还需得以相应的提升。税收也是体现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纳税额度较高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反之,在公正的税制下,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也应当缴纳较多的税款从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正义),不能承担社会责任的人自然也不应当享受较高的社会地位。税收不仅仅是调节收入分配结果的工具(结果公平),税收的调节作用更应当面向机会公平,因此,税收应当具有针对性。税收的作用不应当仅以结果调节为主注重再分配的作用,而初次分配中税收的机会均等化调节作用对社会正义的影响更为关键。初次分配的相对均等化可以避免再分配带来的损失厌恶、禀赋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创造的公平分配调节对整个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再分配会使得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对立加剧,甚至于在个别社会中,由于初次分配不公带来了很多社会矛盾,在分配中根本无法扭转。在初次分配差距较大的社会,穷人对社会的仇恨(Atkinson,1953)[16]和富人对穷人的不屑一顾使得社会处于高度的危机之中。
5.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成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隐患。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构成了经济主体的税负,在未纳入税收体系的过程中将不承担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再分配功能,但其在初次分配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原因在于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构成了产品的价格,改变了产品间的相对价格、反映了产品和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度,因此,其影响了初次分配结构。从用途上讲,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并未形成统筹预算,因此,无法起到再分配的作用。鉴于此,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成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隐患。
三、税收调节居民幸福感的方法
幸福感来自于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愉悦,当人们将大多数时间用在了他愿意继续、不想停止的活动上时,我们认为其获得了满足感。米哈里(Mihaly)将这样的全身心投入的状态称之为心流,当人们处于这一状态时,不愿意被人打扰。Edgeworth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提出了幸福与快乐的测量方法。但由于其与现代心理学相比更容易犯错误,因此并未形成真正的理论体系。
人的全身心投入带来的幸福感可以分为两大类:认识自我和经验自我(Kahneman D.,2011)。[17]早期的学者研究幸福感都是从认识自我开始的,但这样的研究可能存在较大的问题。因此,行为经济学以及后来研究幸福感问题的学者都从经验自我的角度去测度幸福感。
(一)测量经验自我的幸福感的方法
测度经验自我的幸福感是有难度的,因为人们不可能一边不停地报告自己的体验,一边正常地生活。最接近事实的测度方法是由Mihaly发明的,自Mihaly测度法发明以后,这个方法被不断改进并得出了现代的测度方法,我们称之为经验取样法。经验取样法成本较高且繁琐,Kahneman D.采用了昨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所谓昨日重现法,即不断地回忆过去的经历,通过采访、访问,给出受访者印象最为深刻的快乐、紧张、愤怒、担心、疼痛等问题,以反映受访者对经济问题与幸福感之间的感受。
如果受访者都能够非常准确地还原某个场景的典型时刻,就足以证明经验昨日重现法对幸福感测度的有效性。如果受访者能够清楚地说出各场景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此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权重。
采用DRM测度经验自我幸福感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针对时间配置来考虑人的幸福指数。例如,我们可以测量出人们在交谈、工作、与家人相处、家务、社交、看电视等问题上所获得的幸福指数。如果我们能够测量出工作中不开心的时间占总工作时间的比重,遂将这一比重称之为不愉快指数——U指数。
(二)税收如何使得人们更幸福
人们在任何时刻的心情都是由性情和幸福感所决定,情绪上的幸福感也会随着情景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人们的心情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情景,工作时是痛苦还是快乐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工作情景给其带来的情绪。除了极其例外的情况,我们的情绪绝大部分取决于我们关注的事情,我们最直接的关注是正在进行的活动和直接环境。因此,税收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应当从这两方面进行,税收可以通过改善社会环境、维护社会正义对生存环境进行改善,也可以通过扩展人们的自由度使得人们选择的经济活动空间加大从而增加其幸福感。
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做到用自己的意志使自己更为开朗、乐观,但是许多人可能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使得自己少花费一些时间交谈,多花一些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见自己喜欢的人。税收释放的时间资源可以在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例如,对高收入人群征收较高的税收对高收入人群的时间资源侵占几乎为零,而对低收入人群而言,负所得税将极大地释放其选择空间,能够使其具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想从事的工作,从而提高幸福感。经济学认为这一政策可能产生“养懒人”的结果。是否“养懒人”在于得到转移支付或者负税收补贴的人是否将其时间资源配置于享受闲暇的领域。如果转移支付、负税收与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挂钩,税收政策相当于提高了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率,只要劳动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这一税收政策不但不会产生“养懒人”的后果,反而能够提高社会的就业水平和劳动的利用率。
Kahneman D.(2011)[17]将测量经验自我幸福感的方法应用于欧美的许多国家,通过这样的访问、实验、调查和分析,证实了情境因素、生理健康以及社会接触等对经验自我幸福感的重要性。如果某人接受过更高的教育,那他对生活的评估也会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经验自我更幸福。身体健康对经验自我的不利影响比对生活方面的评估要大的多。参与宗教活动对于积极情绪与压力都具有有利影响,对生活评估的影响不大。令人惊奇的是,宗教并不会让人们沮丧或者使担心的感受有所减少。收入对经验自我幸福感的影响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别,客观的税收政策可以减少人们的痛苦,我们以降低社会的U指数为目标,解决社会抱怨和极端贫困是首要目的。增加幸福感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分配好时间,能够抽取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需要政策的指导、信息的畅通和自由度的扩展。如果收入超过满意水平,就能够拥有更多使人愉快的经历。
四、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幸福基础
税收调节的作用是提高社会幸福感,改善社会的安全系数,使得社会步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因此,税收的调节作用必须置于社会心理和现有社会发展模式下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建立在幸福感的基础上,可以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调节中的税收作用进行以下几个层次的分析。
(一)人口流动、区域差距和税收调节的心理学基础
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和企业内分配差距。虽然各类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但四种收入分配差距的突出性问题在不同的地区、经济环境下又有不同的表现。
人口流动与税收调节作用的轴向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速度和数量逐年在增加,人口流动带来的初次分配调节作用在加强,劳动力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正拉近着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这一流动也带来了另外一种问题:区域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调节越来越重要。在人口流动较小的社会形势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幸福的第四构成要件)半径较小。收入分配差距一般体现在区域内部,区域内的调节能够直接改善人们的幸福感。例如,改革开放以前,虽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但人口流动范围较小,人们的幸福感较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开放以后(下岗政策以后)和农民工进城务工带来的社会效益实质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农民工进城带来的人口流动使得区域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受到百姓的重视。我国的税收调节也应当逐渐从以前的区域内调节,转而面向区域间调节和行业间调节。
(二)城市化致使调节行业收入差距更为迫切

权利的集中垄断是人类文明史上大多数社会在人口膨胀时解决问题的途径。旧石器时代人类进化出互惠式利他的方式,建立了互惠式利他规范以及重新分配食物和日用品的规范制度。戴蒙德将二元组计算方式应用于再分配,“一对一直接解决冲突的方法,在大型社会中是不管用的,同样的道理,一对一的直接经济让渡,在大型社会也不管用。要让大型社会正常运作,除了互惠经济,还要有再分配经济。超出个人所需的物品,必须从个人手中转交给集权体制,而后再分配给有需要的人。”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际交往的复杂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模式呈现动态、多变特征。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整体收入分配制度是城市化后关乎社会稳定的更为关键的问题。
城市内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来源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和企业内收入分配差距,企业内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初次分配后形成的结果,根据公司治理理论的观点,企业外无压力是导致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垄断性企业的企业内收入分配差距将越大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主要也是源自市场的垄断力等。随着我国城市化趋势的不断显现,行业内收入分配差距将成为关系社会安定的重要问题。
(三)公共服务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提升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按照Rothbard的观点,税收的主要目的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正义。税收如何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呢?税收应当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公平,那么税收应当在提供公共物品、维护社会环境等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受教育较多的人对幸福的要求较多,但受教育较多的人更能够感受自己的经历和选择。因此,教育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手段。相同的教育水平也是实现平等就业机会的手段,虽然教育公平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果,但教育能够缩小就业机会差距,从根本上提供了公平的社会环境。
[1]Diener,E.,Biswas-Diener,R.Rethinking Happiness:The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Wealth[M].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8.
[2]Jeremy Benth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M].London,New York and Toronto: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823.
[3]Solnick, S.,Hemenway D.Is More Always Better?: A Survey on Positional Concern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98,37(3):373.
[4]格雷戈里·伯恩斯.艾客:用非同凡响的思维改造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2.
[5]Gilbert,D.Stumbling on Happiness[M].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7.
[6]Rogers,L.J.,Vallortigara,G., Andrew,R.J..Divided Brains: The Biology and Behaviour of Brain Asymmetries[M].West Nyac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7]Myers David,Diener Ed.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J].The Futurist, 1997,31(5).
[8]Amartya, Sen.Poverty and Famines[M].Oxfor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1981.
[9]Acemoglu,D.,Robinson,J.A..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10]North,D.C..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1]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3.
[12]Rothbard,M.N..The Ethics of Liberty[M].Atlantic Highlands N.J.:Humanities Press,1982.
[13]Erin Ann O′Hara.“Opting out of Regulation: A Public Choice Analysis of Contractual Choice of Law[J].Vanderbilt Law Revie,2000,53(5):1551.
[14]Kahneman D,Knetsch J.L,Thaler, R.H.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the Coase Theore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1325-1348.
[15]Fogel,R.W..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16]Atkinson,J.W..The Achievement Motive and Recall of Interrupted and Completed Task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53,46(6):381.
[17]Kahneman,D.Thinking,Fast and Slow[M].Reviewed by Freeman Dyson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1.
[18]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