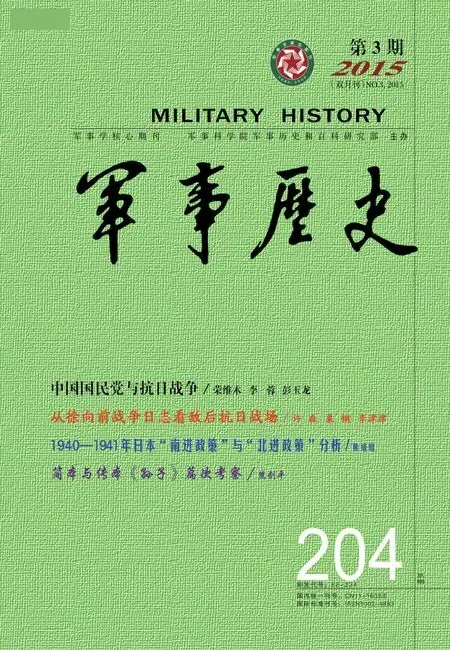简本与传本《孙子》篇次考察*
2015-01-09熊剑平
□ 熊剑平
银雀山出土的《孙子》篇题木牍,除了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孙子》古本篇题的重要信息之外,也展示了古本篇次的情况。而且,这种篇次与传本相比,有着较大差别。不同的篇次排列反映出什么样的思想差别?如何看待这些差别?究竟哪一种篇次编排更为合理?这些问题,无疑都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一、简本篇次考察
从银雀山出土《孙子》篇题木牍的残存文字可知,简本《孙子》的篇次与传本的篇次,存在着较大的出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曾就该木牍对简本篇次情况,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意见:
据此牍可知简本《孙子》十三篇篇次与今本有出入。今本《虚实》在《军争》之前,简本在《军争》之后,属下卷。今本《行军》在《军争》《九变》之后,简本在《军争》之前,属上卷。今本《火攻》在《用间》之前,简本在《用间》之后。由于木牍残缺,简本十三篇的篇次还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本书释文仍按今本篇次排列。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9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这段话先是发布在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简体横排本《孙子兵法》中,后又被原样收入1985年精装本。在这两本出版物中,相关简本的释文基本按照今本篇次排列。我们如果用这段话来对照木牍图片,便可以得知,就木牍所能提供解读的信息,整理小组的专家们已经进行了如实的归纳和总结。而他们所得出的“不能完全确定”的结论,也应该是可信的。当然,或许有人会对整理小组采取简单趋同传本的做法感到惋惜,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该是基于木牍残损现状所作出的一种无奈之举,多少也体现出专家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妄加推测,不妄下断语,未尝不是对包括木牍在内的出土文献的一种尊重和保护。
或许正是因为木牍的残损严重,导致学术界对简本篇次的研究兴趣始终不大,相关论文难得一见,只有李零等少数学者关注到这个论题。
李零曾对篇题木牍进行过深入研究,对简本的篇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三排五行的文字中,有八个篇题是可以释出或补释出,而有待确定位置的一共是五篇。于是,李零尝试对这五篇的位置进行确定,最终得出简本篇次:
一、《计》;二、《作战》;三、《埶》;四、《刑》;五、《谋攻》;六、《行军》;七、《军争》;八、《实虚》;九、《九变》;十、《地刑》;十一、《九地》;十二、《用间》;十三、《火攻》。②李零:《〈孙子〉篇题木牍初论》,载《文史》第17辑。
李零做出这样的推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也即他自己所说:第一行是书题,最后一行“七埶(势)”不是篇题,而是与“势”有关的后七篇的统称。这样,三排五行便一定只是十三个篇题,和传本及《史记》等能求得一致。李零后来否定了他所猜测的木牍第一行为书题的说法,改而认为是记《孙子》篇数,①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4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而他对于“七埶(势)”的认识似乎没有发生变化,篇题木牍仍然可视为是包含了十三个篇题,所以他当初用来推测简本篇次的前提依然存在。可能正是这个缘故,他相关篇题木牍的论文虽经几次整理出版,但他相关简本篇次的推测之论,则始终保持原样不变。
李零推测简本篇次的过程非常精妙,但也不能说是尽善尽美。愚见以为,李零至少忽视了两点:第一,“□刑”其实不能完全坐实为《地形》,把“□刑”等同于《地形》,一方面是没有注意到武经七书本尚且有《军形》这样的篇题,另一方面则是无形之中受到了传本篇次的干扰和影响。既然已知传本、简本篇次存有重大差异,我们就不能根据传本《九地》前是《地形》,而将篇题木牍中的“□刑”也坐实为《地形》。第二,篇题木牍中的“七埶(势)”也不能完全从篇题中排除出去,它可能不一定如李零所说,是七个有关“势”的统称。如果确系统称的话,《势篇》却没有被统称进来,这似乎很难让人理解和接受。如果“七埶(势)”果真是篇题,那么显然应该将其作为简本的最后一篇,而不是《火攻》或《火队》。所以,这样打量李零相关简本篇次的推测,就会觉得其中仍然有可值得商讨之处。至少是不能让我们百分之百地信服。
如果诸如李零这样对于《孙子》有着精深研究的专家,尚且不能提供一个让人完全信服的简本篇次,那么我们还不如回到当初,回到银雀山汉墓整理小组的认识上来。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整理小组的专家们在经过考察后,判断认为:“简本十三篇的篇次还不能完全确定。”基于这个态度和认识,他们在出版相关释文时,一律按今本篇次进行排列。这种态度,这种认识和结论,虽稍显保守和无奈,没有充分利用出土木牍所提供的信息,但也不失为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二、传本篇次考察
我们不妨再考察一下传本的篇次。相对于简本篇次的模糊难辨,传本《孙子》的篇次则是非常明确的。无论是武经七书本,还是十一家注本,甚或是日本出现的樱田本,虽则具体篇题有些差别,但在篇次上大致相同。
较早关注《孙子》篇次问题的是宋代的张预。在注释《孙子》时,张预对每一篇的篇题给予特别关注,尤其重视发掘十三篇之间的内在联系。下面,我们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或许可以见出张预对十三篇内在逻辑的理解和把握。
管子曰:“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也。
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
计议已定,战具己集,然后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
形因攻守而显,故次《谋攻》。
兵势已成,然后任势以取胜,故次《形》。
《形篇》言攻守,《势篇》说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两齐之法,然后知奇正;先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知虚实。盖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实由奇正而见,故次《势》。
以军争为名者,谓两军相对而争利也。先知彼我之虚实,然后能与人争胜,故次《虚实》。
变者,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凡与人争利,必知九地之变,故次《军争》。
知九地之变,然后可以择利而行军,故次《九变》。
凡军有所行,先五十里内山川形势,使军士伺其伏兵,将乃自行视地之势,因而图之,知其险易。故行师越境,审地形而立胜。故次《行军》。
用兵之地,其势有九。此论地势,故次《地形》。
以火攻敌,当使奸细潜行,地里之远近,途径之险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欲素知敌情者,非间不可也。然用间之道,尤须微密,故次《火攻》也。
张预对于传本《孙子》的篇次安排和各篇的内在联系,做出了非常精妙的解释。在张预看来,《孙子》十三篇就是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不可割裂,连各篇先后顺序的安排都是井然有序,富有深意。张预对《孙子》篇次的解读方式,获得了不少人的肯定和好评。比如蒋方震就曾发出这样的称赞:“惟张预于每篇题目之下,间记其编次之意。”①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绪言》,房西氏抄本,1915。民国时期另外一位注释家支伟成也对《孙子》的篇次安排作出了解释,但大抵都是张预之说的翻版,并不能跳出其藩篱。②详参《孙子兵法史证·孙子篇目述义》,上海泰东图书局本影印本,1934。
除了张预之外,宋代尚有郑友贤也注意到《孙子》篇次安排的精妙。郑友贤认为,从《计》篇开始,又以《用间篇》结束,其实是作者自有深意蕴含其中。《计篇》中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而《用间篇》所说正是“索其情”。所谓“计待情而后校,情因间而后知”,故此,以《计》为始、以《用间》为终的这种安排,在郑友贤看来,是“从易而入难,先明而后幽,本末次序而导之,使不惑也。”③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参见杨炳安:《孙子十一家注校理》,3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郑友贤对《孙子》篇次的解读,提及的虽然只是一始一终,但其着眼点也是在《孙子》的整体性,关注的是十三篇的内在结构。故此,这种讨论其实是很有深度的。郑友贤的这种分析之法,可能对日本的孙子研究专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学者研究《孙子》,一向非常重视《用间》,认为《孙子》十三篇其实是以“知彼知己”的情报思想贯彻始终,以《用间》作为结尾,其实是为了重视和强调情报问题。
首先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山鹿素行。他在《孙子谚义》中提出,《孙子》是一个完美的整体,而贯穿始终的就是“知彼知己”的情报思想。这一观点得到不少日本学者的认可,佐藤坚司甚至由此而称赞他“把握住了《孙子》的真谛”④[日]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等译,3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而另外一位日本研究专家德田邕兴则几乎完全沿袭了山鹿素行的观点,同样认为:“十三篇以用间而终,结其要,意在用兵之时,察敌情为第一要务,是始计也。”⑤[日]德田邕兴:《孙子事活抄》,转引自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107页。
当然,有些日本学者由此出发,认为《孙子》十三篇都是在讲用间,这就很值得商榷了。山鹿素行就是其中一位。据佐藤坚司介绍,山鹿素行曾按照他自己所找到的独特视角,对《孙子》十三篇做出这样的分析:《始计》《作战》和《谋攻》是讲“知己、知彼、知天、知地”,而《军形》《兵势》和《虚实》则是讲“知己”,《军争》《九变》和《行军》是讲“知彼”,《九地》和《地形》则是讲“知地”,《火攻》则是讲“知天”,最后的《用间》是再次回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⑥[日]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31页。用这种方法分析十三篇的结构,表面上看,似乎是抓住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但其实是对《孙子》的误读。⑦参见熊剑平:《日本的〈孙子〉研究》,载《军事历史研究》,2011(2)。《孙子》固然强调用间,但绝对不会是全部围绕用间而展开。
与日本学者有所不同,蒋方震承接郑友贤的思路,对《孙子》篇次作出另外一种解读。如前述,蒋方震对张预解读《孙子》篇次的视角进行了赞扬,同时又批评张预“不能曲尽其妙”,故此,他对《孙子》十三篇提出了另外一种解读方式:“十三篇结构缜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一篇者。计篇第一,总论军政平时当循正道,临阵当用诡道,而以庙算为主,实军政与主德之关系也。第二篇至第六篇论百世不易之战略也。第七篇至第十三篇论万变不穷之战术也。”⑧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绪言》。在蒋方震看来,《孙子》以《计》为首,又以《用间》为终,其实是反映了作者“以主德始,以庙算终”⑨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绪言》。的思想。如果我们联系蒋方震在《孙子浅说》中对《计篇》的解读——“此篇论治兵之道,在于庙算,而主孰有道”,不妨将蒋方震的前面的表述换一种说法:“以庙算始,以庙算终。”《孙子》确乎重视“庙算”思想,以“庙算”思想贯穿十三篇始终是可能的。而日本学者所看到的“用间”思想,只可以说是孙子“庙算”思想中的一个部分而已。由“五事七计”,我们可以得知孙子确是重视用间,但如果只是由此而抓住“用间”不及其余,就只能说是得其一偏,并未抓住其真正要领或精神实质,故此,我们不妨认为这是对《孙子》的一种误读。视角虽然独特,却不足称道。而相比之下,蒋方震的解读似乎是承接郑友贤而又有所发展,真正抓住了十三篇结构安排的内在灵魂。
三、简本与传本篇次差异探析
通过对简本、传本篇次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两个大致的印象:第一,就出土篇题木牍来看,简本的篇次是很难排定的。第二,传本篇次的安排是经过了精心设计,首位呼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逻辑性。
银雀山出土的《孙子》篇题木牍,除了有部分内容因字迹漫漶而无法得到确认之外,诸如“七埶(势)”这样字迹清晰可辨的也不能确定从篇题中排除,并不一定是七个与“势”有关的统称。此外,“□刑”未尝不可被解读为《军形》,至少是不能完全坐实为《地形》。在这种情况下,对简本的篇次进行排列,顶多只能算是一种猜测。要想完全地说服别人,尚且具有一定难度。就李零所推测的篇次来看,其中固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并非无懈可击。其实李零在作推测性的排列时,无形中也是受到了传本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他根据“先计后战”,将《计》排第一,《作战》排第二。这种带着先入为主之见的推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推理过程。相比之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放弃作任何的排列,出版相关释文时,只是简单按照传本篇次排列的做法,倒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因为木牍上那些漫漶之处究竟写没写东西,写了些什么,我们都无法知晓,根据木牍推测简本篇次,很可能是徒劳无功。
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对简本、传本篇次进行优劣比较,似乎也是不足取。李零在推测简本篇次过程中,也承认了相关排列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而他只是提交了在他看来是可能性更大的一种排列方式。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王正向似乎有点唯简本是从,竟然用李零推测排列的简本篇次与传本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了“传本篇次颠倒”,“严重破坏相关篇目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结论。①王正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5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这其实是沙上筑室,是一个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结论。王正向进一步认为,简本以《火攻》结尾,体现了作者“重战”“慎战”之旨,故此以“重战”始,以“慎战”终。②王正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5页。这种分析貌似有理,但其实也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从出土篇题木牍来看,《七势》更像是简本的最后一篇,③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载《孙子新探》,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只是我们目前尚且无法知道这《七势》可以和传本的哪一篇求得对应罢了,至少《火攻》并不能确定就是简本的最后一篇。
有意思的是,为王正向提供简本篇次的学者李零,在对简本、传本篇次进行比较之后,提出观点认为:“今本篇次更有条理。”④李零:《〈孙子〉篇题木牍初论》,载《文史》第17辑。这个结论应该是建立在李零本人严密考察的基础之上,也能与众多前贤的研究结论取得一致,相对王说应该更为可信。日本学者服部千春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传本篇次“无论在军事上,在逻辑上,较之木牍更胜一筹。”⑤[日]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2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前面说过,因为简本篇次尚且难以确定,贸然对简本、传本篇次进行优劣比较显得不足取。所以,我们想重点对简本、传本篇次发生差异的原因进行一些探讨。就相关论题,李零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说法。在他看来,传本篇次之所以更有条理,是因为“经刘向、刘歆父子和曹操两次整理的结果”⑥李零:《〈孙子〉篇题木牍初论》,载《文史》第17辑。。愚见以为,曹操和刘氏父子对《孙子》有没有做过整理,做过什么样的整理,都难以确考,所以李零此论未能揭示简本、传本篇次发生差异的原因。
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由于银雀山出土文献在很大程度上都能与《史记》互证,让我们对司马迁相关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多了一重信任。《孙子》十三篇出自孙武本人的说法由此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如果说《孙子》十三篇果真为孙武自著,其篇次安排更大可能也是出自孙武本人之手。那么,不能确定篇次的简本和篇次显得较为合理的传本,哪一个是出自孙武本人之手呢?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非常难以确定的。传本篇次的精妙安排可能是由于有了作者之外的人手参与,也可能出自作者本人之手,或者是孙子学派之手,而不一定要等到曹操或刘氏父子。笔者认为,《孙子》在两汉应该一直是以十三篇的规模在流传,西汉末年并没有增肥,东汉末年也不当劳曹操大驾对其进行瘦身。
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都认定《汉志·兵书略》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就是传本《孙子》最早的著录。至于“十三”和“八十二”之间篇目数之差,他们又给出一种解释,认为曹操曾经对这八十二篇的《孙子》进行过删减,恢复了《孙子》十三篇的面貌。这样解释固不失为一说,但其中的疑点很多,无法让人确信。曹操在给《孙子》作注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①《魏武帝注孙子》序,清平津馆刊顾千里摹本。从这段话中,我们应当可以得出这样两个信息:第一,曹操肯定不是第一个注释《孙子》之人,出自孙子学派的无名注释家早就注释过《孙子》;第二,我们从中并不能看到曹操删减篇目的信息。令曹操发出感慨的,只是那些“训说”《孙子》文辞的“烦富”和“失其旨要”。曹操没有批评《孙子》本身文辞的“烦富”,而是批评那些训说《孙子》的文辞的烦富,这说明曹操手里的本子,和同时期高诱所持之本应该没多大差别。曹操用“略解”为自己的这部著作命名,显然也是针对那些“烦富”的训说。②《魏武帝注孙子》尚有一题曰《孙子略解》。参见于汝波主编:《孙子文献学提要》,1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曹操对《孙子》的赞许如此之高,如果对其有删减之功,他不大可能对此只字不提。而且,假如果真是《孙子》原文“烦富”,曹操就一定不会对其发出“孙武所著深矣”③《魏武帝注孙子》序。之类的褒奖。曹操为《孙子》作“略解”的这种举动,其目的本是对着“烦富”的训说,却不幸让不少人误认为曹操曾经对《孙子》有过删减篇目的事情。造成这个误会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曹操的自序解读得不够细致,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受到了《汉志·兵书略》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某种干扰。④相关问题,笔者有两篇拙作可供参考:其一,《〈孙子〉著录考》,载《军事历史》,2010(5);其二,《曹操与〈孙子〉》,载《军事历史研究》,2012(3)。
所以,《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不一定是《孙子》十三篇的前身,曹操也未必删减过其篇目。所以,简本和传本篇次发生差异的原因,很有可能和曹操等人无关。至于简本篇次和传本篇次何时发生差异,也应当是一个暂时难以解开的谜团。它可能是由古书流传的特点所致,是在不断辗转传抄过程发生的,但其具体时间,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孙子》的流传过程一定非常复杂。简本和传本篇次之间的差异,更加说明了《孙子》流传过程中的这种复杂性。简本和传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简本是不是果真就是传本的前身,这些其实也是很难断定的。打一个比方来说,一棵沧桑的古树,有可能比埋在地下多年的朽木更加年长。所以,当我们看到简本和传本之间发生差异,就立即判断认为传本是经过了很多篡改,这种说法可能略显草率。至于《孙子》各本之间篇次发生差异的原因,也一定非常复杂。我们不如把空白还给空白,而不是轻率地下一个结论认为,简本的篇次就是如何合理,如何的首尾呼应,传本的篇次就是乱七八糟。传本的篇次安排未尝不是出自作者本人,简本也未尝不是经过了某种篡改。就兵书来说,汉代初年就开始收集整理兵书,武帝、成帝之时又进行过两次。这三次整理行动,对《孙子》有没有作过手术,作过多大的手术,我们目前并不知道。诸如韩信、张良等人是不是对《孙子》成为今本的模样产生过作用,也都是很难考证的。吴九龙认为,“传本《孙子兵法》的篇题,各篇的排列次序当是刘向、任宏排定的。”⑤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载《孙子新探》,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作者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当”字,表面了这其实也是一个推测之论。但这种推测之论,首先是把《孙子》作者参与编订篇名、篇次的可能性,完全排除了,可能也需要存疑。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曹操编订篇题篇次”的说法。如果我们认定曹操确是删减过《孙子》篇目,那么曹操必然地需要对《孙子》篇次重新作一次整理。可问题在于,曹操究竟有没有删减过《孙子》篇目,无法考证。相关出土文献证明,《孙子》在汉代一直是以十三篇的面目在流传。因此,“曹操编订《孙子》篇题篇次”的说法,同样是很难考证的。
[1]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曹操等:《十一家注孙子》,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吴九龙等:《孙子校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