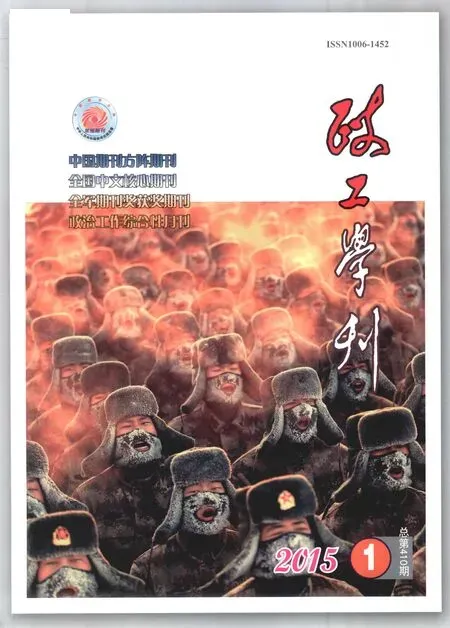想娘亲
2015-01-08杨大会
☉杨大会
想娘亲
☉杨大会
2014年10月1日是我43岁生日。往年过生日,不论是在单位,还是在漂泊的大海上,首先拨通的肯定是山东老家母亲的电话,“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孩的生日娘的苦日,记得买点好吃的,我在执行任务不能回去看您了。”然而现在,这个电话竟成了莫大的奢望,手拿电话,怅然若失,心像被掏空了一样,母亲已走了两年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也是43岁,家里一贫如洗,房子是借来的,五个孩子只有大姐刚出嫁。在以后的岁月里,母亲怕我们受委屈,始终没有改嫁,含辛茹苦地拉扯我们长大,默默履行着对爸爸临终前许下的诺言:放心吧,孩他爸,我一定把儿女们培养成人,不让他们受半点委屈。那时我才九岁,不知多少次放学回家,看到母亲独自一人躲在角落里哭泣,见我回来又装作若无其事到田里干活。生活给了母亲太多的苦水,她始终一个人默默承受着、隐忍着、吞咽着……
初中毕业那一年,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我只能辍学打工。第一份工作是玻璃厂的搬运工,在600多度高温的炙烤下,30多斤的铁模子每天要搬运三千多趟,我一干就是四年。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我兴奋地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每天1块2毛5分,共计37块5),一分不差地交到母亲手里时,母亲看着我满手的血泡和稚嫩的脸庞,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号啕大哭起来:“苦命的儿啊,妈对不起你,这么点年纪,去遭那么多罪……”我与母亲相拥而泣。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母亲几乎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过。给生产队淘粪挑粪、在医院做清洁工、在粮站卖早点、在食品厂摊煎饼、为陶瓷厂加工陶坯,有的工作既危险又辛苦,强度之大甚至连壮年男子都吃不消。记得母亲在粮站打工时,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赶过去,一年四季,天天如此。炸油条、煎油伞、蒸米糕、摊煎饼,母亲样样做得有模有样。下班后,母亲经人同意带回家的“边角余料”,总是先紧着我们解馋,自己却从来不舍得吃一口。
淄博是中国北方的陶瓷之乡,家家户户的生活基本上都与陶瓷有关。为了多挣点钱,贴补家用,母亲在医院做清洁工的同时,自己挑泥浆加工陶坯。泥浆是用家乡的青石块磨制而成,因为掺了水,比青石还要沉,两桶泥浆就有250多斤,母亲用她90多斤的单薄身体和1米58的个子,挑起泥浆要走40多分钟才能到家。每次到家,母亲浑身上下的汗像水浇了一样,衣服裤子都贴在身上,两边的肩膀透着殷红的血印。加工一个陶坯二厘钱,五个才挣一分钱。每一个都要经过沁、倒、削、刻、磨、晒等七八道工序,然后再把加工好的陶坯挑到陶瓷厂,一个星期下来最多能挣到10块钱,这份活计共持续了五年。那时放学回家,我经常帮母亲打下手,一轮做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有时我们娘俩也苦中作乐,听听收音机,哼哼小曲。母亲虽然不识字,但特别喜欢听戏唱戏,京剧、豫剧、吕剧、越剧、黄梅戏,母亲都爱听,样板戏《红灯记》《杜鹃山》《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里的精彩唱段,她样样都能哼几句。我对歌唱艺术的喜爱,就是在那段艰苦难忘的日子里慢慢养成的。后来,为了学会一首喜爱的歌曲或唱段,竟然着了魔似的到同学家、邻居家去学,有时甚至跑到县城的百货大楼去听,母亲从来不拦我。我学会的每一首新歌的第一个听众肯定是母亲,每次听完,她总是夸我:学谁像谁,唱得跟收音机里的一样,将来我儿子准能成为歌唱家。后来,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还上了中央电视台,可每学会一首新歌,依然渴望先唱给母亲听,母亲始终是我心中最信赖最忠实的听众。
家里日子过得再艰苦,在孝敬老人的事情上,母亲从来不打折扣。父亲在世时,每月给奶奶的生活费是10块钱,父亲去世后,奶奶主动减到了5块钱。别看这5块钱,常常压得母亲透不过气来,但母亲就是四处去借也从不拖欠。轮到我们家赡养奶奶时,母亲要拿出家中最好的米面,摊好煎饼,蒸好馒头,和我一起给奶奶送去。怕奶奶记性不好,母亲会细心地把钱塞到奶奶贴身大襟褂的兜里。有一次,母亲实在没辙了,打起了我的储钱罐的主意。那是我辛辛苦苦攒了近一年的零花钱,共六毛一,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看着母亲期许的眼神,我含着泪“慷慨”地砸开了储钱罐——一个残破的陶瓷茶壶,把钱交到母亲手里。母亲用她的仁慈和善良侍奉着老人,也用质朴温良的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和哥哥姐姐。
好不容易熬到姐姐哥哥都结婚成家,我也考上了军校,母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胃溃疡、冠心病、糖尿病一起向她袭来。用医生的话说,年轻时太拼命了,体力透支得厉害,把身体都累垮了。
考入军校后,每次回家,母亲总央求我一件事——着装整齐,陪她赶集。每隔五天,家乡都有一次集市,是街坊四邻、十里八村的乡亲们自发形成的。海军军装要么一身蓝,要么一身白,虽说漂亮,但我总觉得太显眼,不自在。可母亲已近乎偏执地把我和这身军装当成了她一生的骄傲。当兵24年来,由于我的演唱特长和工作需要,跟随部队出访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我在哪里,只要母亲知道了,首先看那里的天气预报,她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我的衣食冷暖。
2007年春节刚过,我把母亲从山东接到大连。由于孩子小、房间挤,单位任务又多,母亲觉得太烦劳儿媳,住了半年就回了山东。回家没两个月,母亲就大病一场,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当时在海岛执行任务,军舰靠岸后,连夜赶赴山东。第二天下午四点到医院时,母亲已昏迷20个小时。医生说,如果36个小时内,病人有反应,就有救;如果没有反应,就准备后事吧。可怜的母亲,脸肿得连眼睛都看不到了,手脚冰凉,浑身插满了各种输液管,孤独地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我让哥哥姐姐们先回家休息,自己守护着母亲。母亲在大连的半年时间里,我连续创作了十几首歌曲,发表在《解放军报》《海军文艺》和《音乐周报》上,有几首还录制成了CD。每次放给母亲听的时候,她都啧啧称赞:我以为我儿子只会唱歌呢,没成想还会写歌呢,每首歌曲的调调,好听得直往人心里钻!
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三点,我不停地在母亲耳边哼唱她喜欢的几首歌。三点半左右,恍惚间发现,母亲额头上的皱纹微微地往上一挑,母亲终于有反应了!我的眼泪奔涌而出,飞一般地冲到护士站。在医院的全力抢救下,母亲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七天,总算逃过了一劫。出院后,母亲的记忆力急剧衰退,一下子变得少言寡语起来,要说也是翻来覆去地唠叨那几件事和几句话。医生说是小脑萎缩的缘故。
从2009年开始,我连续执行国庆大阅兵和军舰出访任务,回家看望母亲的机会越来越少。2012年回家过春节,给母亲洗脚剪指甲的时候,她微笑着问我:“妈有日子不出门了,也没洗脚,你这大军官不嫌我脏啊!”我笑着回答:“嫌你脏,我就当不了军官喽!”怕母亲心里闷得慌,我给她穿上羽绒服,裹上头巾,搀扶她来到街口的集市上。在街口,母亲竟然像孩子一样央求我给她买点瓜子,我担心她的糖尿病,又怕她咳嗽,只买了半斤。回来的路上,母亲还嗔怪着买少了。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我和母亲赶的最后一次集。
2012年4月,我随舰参加环球航行任务。7月19日,当军舰行至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时,母亲竟撒手西去。母亲去世两个月后,我才回到祖国。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母亲去世前的半个月里,我竟然连续做梦,梦里母亲说自己要走,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接连从梦中哭醒,最后一次梦境依然清晰记得:母亲在村口等我放学,一遍遍唤我的乳名。当天,我拼命往家打电话,家人怕我失控,以谎言搪塞。现在回头查看自己的海上日记,时间竟然奇迹般的吻合。远隔千山万水,怎么会接二连三地做那样的梦呢?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应呢?母子连心啊!
母亲去世后的两年里,我不知有多少次从梦中哭醒,梦见在母亲的呵护下一起劳动,一起赶集。因为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总觉得母亲没有走,老人家依然活着。正如诗人所说:我相信故去的亲人,会变成星星,守望着我们,直到永远……
秋风乍起,秋雨潇潇,今天是我43岁的生日,孩的生日娘的苦日,仰望苍穹,泪眼婆娑。妈,儿想您啊……
【作者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员,
本文作于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