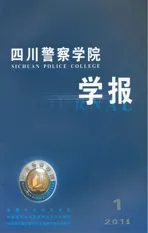中国的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
2015-01-03谭羚雁
谭羚雁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辽宁沈阳 110000)
中国的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
谭羚雁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辽宁沈阳 110000)
在中国,社区警务是依托社区建设的发展契机建立的与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相适应的警务管理新机制。社区警务与社区建设相互依托,而中国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社会性与制度性瓶颈却阻碍中国社区警务的发展。未来中国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的发展需要淡化社区的行政色彩、强化社区精神与社区意识,回归社区的本质内涵。
社区;社区建设;社区警务
20世纪80年代末,社区警务在美国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社会甚至是其他国家或地区解决犯罪问题的主导性哲学理念。从社会学意义上讲,社区警务与社区建设紧密相关,社区建设的成熟与否关系到社区警务最终的运行成效。在中国,社区警务已然成为警务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主导模式,对当前中国社区建设的现状及未来发展的思考将是关系到中国社区警务战略构建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一、社区的内涵探析
社区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的,他认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的社会团体。从滕尼斯提出社区概念到现在,学者们给出了诸多不同的解释。概括说,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概念一般分为两个维度。一是社区的地理区域内涵。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社区是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前提的。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在其所著的《社会学》一书中写道:社区是指在一个地理区域里围绕着日常交往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群人;日本社会学家横山宁夫在其所著的《社会学概论》一书中指出:社区具有一定的空间地区,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生活共同体;台湾学者龙冠海教授所著的《社会学》一书中说:社区是有地理界限的社会团体,即人们在一特定的地域内共同生活的组织体系,或称为地域团体;费孝通教授则认为,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家庭、氏族)和社会组织(机关、团体)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一个在生活上互相关联的大集体[1]。然而,上述概念简单强调社区的地理结构界限区分,而忽视了现代社会文明背景下日益强化的社区人口流动、社区成员异质性以及跨社区的文化沟通等社会结构要素。由此,社区的第二层内涵被更加关注,即社区是一种“互动网络与社会关系结构”。这种社会结构超越了纯粹的地理结构界限,具有共同的价值观、相互信任。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固性依赖非正式的社会沟通网络和强烈的社区意识。按照美国学者麦克米兰和查韦斯的观点,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必须具有以下品质:“共同的价值观、高度的社区参与、有效的公共对话、强烈的社会责任[2]”。
二、中国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的双轨运行
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警务的发展与改革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群众路线(1949-1976)、严打(1978-2001)、社区警务(2002至今)。三个阶段的警务发展演变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社区警务是随着中国社会管理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而发展起来的,新型社区管理形态的出现是中国社区警务建立与发展的重要制度载体。
(一)中国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与社区管理制度的形成。
从社区概念在中国的引入、发展与应用,到社区服务、社区发展概念的产生,再到全国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中国社区建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见表1)。

表1 中国社区建设理念的兴起历程
随着社区建设理念的不断成型,中国社会管理也逐渐从传统的单位制过渡到新型的社区管理制度。单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组织管理形态。改革开放前,基于中国总体性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背景,单位成为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管理形式,并承担着政治控制、提供福利保障等多种功能。在那个时期,人们从摇篮到墓地,都离不开单位,个人对单位具有极强的依附性。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非国家控制的社会资源急剧扩张,社会成员在职业选择、空间流动、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等方面获得了开放性的自由空间。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使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单位制途径逐渐弱化,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也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原有的单位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逐渐剥离出去,社区制超越单位制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新的组织制度。
(二)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背景下中国社区警务的兴起。
2002年8月,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动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文件精神,大力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民政部门要密切配合,根据城市社区建设的进程,统筹社区警务工作,保证与社区建设同规划、同部署、同实施,充分发挥社区警务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知还提出,“开展社区警务建设,是公安机关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提高公安机关控制社会治安能力的重大战略,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保障[3]”。由此可见,中国社区警务是借助社区建设的发展契机建立的与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相适应的警务管理新机制,社区警务与社区建设相互促进、互为依托。
三、中国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发展的理念透析与现实思考
(一)中国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的理念透析。
社区警务本质上是通过社区参与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种特殊的社区服务。有学者认为,社区警务需要同时考虑社区的地理区域性和社会关系要素。首先,社区的物质存在必须是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前提的,社区警务也必然需要以一定的空间地区或地理界限为载体。同时,社区作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组织结构,社区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构建共同的价值取向、提升社会责任、强化社区之间乃至社区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培育社区意识。改革开放后,社区代替单位成为居民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社区在居民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丁元竹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社区建设象征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进步;社区建设的发展不仅是城市生活的基础,也昭示着一个国家的文明与成熟;社区因而也逐渐成为消化改革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场所,如失业、老年护理、早期儿童保育、残疾人护理、公共安全甚至是环境保护等”[4]。毋庸置疑,中国开展社区建设的宗旨是要通过社区的自组织管理实现自我服务,为社会转型时期不断增长的居民需要提供公共服务,即“实现广泛的社会参与,在参与中实现社会互动互助,进而分享共同参与的社会成果”[5]。因此,作为对传统单位制管理形态的超越和重整,社区管理的特征可概括为:“以社区居民为主,轻管理重服务;淡化行政控制,强调社区参与;变政府单一管理为政府与社区合作治理。”同理,作为社区建设重要内容的社区警务,其根本目标是要维护社区治安、保障社区居民的安全感、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强调警察、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警务主体能够协同合作维护社区居民所需的公共安全。因此,不能把社区警务简单的理解为“在社区内搞警务”。
(二)中国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发展的现实思考。
1.中国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的地理区域要素。目前,中国的社区警务已基本形成了按照行政区划与属地管理的原则、以社区为依托、与新型社区管理相适应的一套井然有序的警务运行机制。按照地理区域划分,中国社区警务已构建了以公安基层派出所、社区警务室、社区民警为警务主体、以社区治保会、保安服务公司、治安联防组织、社区安保队等其他社会力量为辅的全方位的警务机构体系,并按照所辖地域大小、人口多少和社会治安的复杂程度合理划分若干责任区、配备充足警力、明确责任区民警职责。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的地理区域内涵清晰。
2.中国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的社会关系要素。社会关系要素主要衡量的是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美国学者帕特南从宏观视角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中的信任、规范、网络等要素,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6]。具体来讲,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的社会关系要素主要包括社区认知、社区参与、社区居民对警察的信任等维度,考察的是社区精神或社区意识层面。学术界普遍认为,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然而,随改革开放进行的中国社区建设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内涵,中国社区警务所需的社会关系要素发展缓慢。
(1)城市化发展对社区文明的“压榨”。滕尼斯早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和社会》一书中区分了社区与社会两个概念。他认为,社区好比是“简单的村落”,而社会相当于“超载的城市”。小社区就如同村落似的家庭生活,简单、亲切、私密、内敛,居民相互熟识,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在大社会中,传统的亲密关系逐渐向由价值取向不同的异质人口组成的、由分工和契约联系起来的、缺乏情感和关系疏远的社会形态过渡。滕尼斯对社区概念的认识是基于现代社会和城市化背景下对社会变迁基本趋势的深度思考,他甚至将这种小社区到大社会的转变称为“社会的病态”。在中国,随着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社区精神与社区意识仍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的发展。首先,新型社区管理让公众由行政性“单位人”向社会性“社区人”转变的同时,也使得公众由“集体人”向“理性经济人”转变。其次,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单位纽带与规范性作用逐渐消失,而新的社区规范如社区服务制度、社区居民公约、社区志愿者管理制度、社区成员代表会议制度等尚未建立或已建立却未能得到公众的认可,社区制度规范处于失范状态。再次,城市化带来的旧城区的衰落和新城区的繁荣,增加了社区网络对外来群体的排斥性,穷人社区与富人社区的分割异常清晰,社区网络关系打上了“区域性”烙印,导致社区空间的孤立与分割。最后,城市化进程中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城市社区人口异质性不断增强,城市社区原有居民往往视外来群体为影响社区安全的不安定因素,而且认为这些外来群体侵占了有限的社区资源,影响了自身的生活质量。“陌生人”关系状态有碍社区信任的形成。
(2)传统单位制的路径依赖。按照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路径依赖指的是“一种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7]。显然,尽管改革开放后新型社区管理体制日渐替代传统单位制,然而单位制已然形成了强大的管理传统与习惯,影响力依然存在。当面临新的不确定环境,人们更多地是从原有的单位组织、过去的行为规则中寻求指导,公众对单位的依赖感反而更加强烈。可以说,“单位作为一种传统的组织文化已经渗透到城市社会生活的深层领域,受这种组织文化的影响,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8]。这便是对传统单位制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性。正如吴敬琏所说,“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的方便一些[9]”。
(3)中国社区的行政色彩浓厚。中国政府开展社区建设的初衷是要通过政府权力下移实现社区自治管理,体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然而,中国开展社区建设至今,社区往往不是自我管理,而是发展为一个行政层次,新型社区制成为政府加强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替代性工具,“政府办社区”的行政化倾向可见一斑。价值理念上,中国政府接受社区自治的管理模式,然而现实是,社区制已从社区服务模式转化为服务于基层社会管理与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工具。因此,目前中国社区制并未实现完全的自治,仍停留在行政管理层次上。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社区建设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政府的干预,政府是社区发展相关政策措施的唯一合法来源。这种由行政化推动的社区建设不仅不利于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同时也阻碍了公众社区认同感和社区参与度的提升。
四、结论
当前,社区警务已经成为世界警务改革的主流模式,如何更好的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也成为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针对上述三方面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关于中国未来的社区建设与社区警务发展。未来社区警务的有效运行必须依赖于“完整”的社区建设。所谓“完整”,不仅仅指清晰的社区空间划分和明确的地域管辖,更重要的是要构建社区的社会关系要素,强化社区精神与社区意识,淡化行政色彩,回归滕尼斯所说的类似于“简单村落”、具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区本质。
[1]奚从清,沈赓方.社会学原理(第四版)[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2]M cM illan,D.and Chavis,D.(1986),“Sense of community:a definition and theory”,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Vol.14,pp.6-23.
[3]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意见的通知[EB/OL].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zcw j/ 200711/20071100002866.shtm l.
[4]Ding Yuan-zhu.(2008),“Community building in China:issues and direction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 XXIX,No.1,pp.153-154.
[5]邓 锁.社区服务研究∶近15年以来的发展与评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0,(4).
[6]Robert D.Putnam.(1995), “Tuning in,tuning out: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28,No.4.
[7][9]吴敬琏.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对诺斯教授演讲的评论[J].改革,1995,(3).
[8]武中哲.社会转型时期单位体制的政治功能与生存空间[J].文史哲,2004,(3).
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Policing in China
TAN Ling-Yan
Community policing is set up ba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new policingmanagement in China.Such a new community policing system is suitable to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However,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ommunity,the bottlenecks from society and system impeded the community policing development.Hence in the future,we must pay much attention to weake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intensify the community spirit and consciousness,recover the essence of comm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of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community policing.
Community;Community Construction;Community Policing
DF035.31
:A
:1674-5612(2015)01-0046-05
(责任编辑:赖方中)
2013年度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立项 《公民警校创新模式在我国应用的难点问题研究》(2013LLYJXJXY051);2014年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2014-10-11
谭羚雁,(1983-),女,山东临沂人,博士,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公安基础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公安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