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条上的北京(下)
2014-1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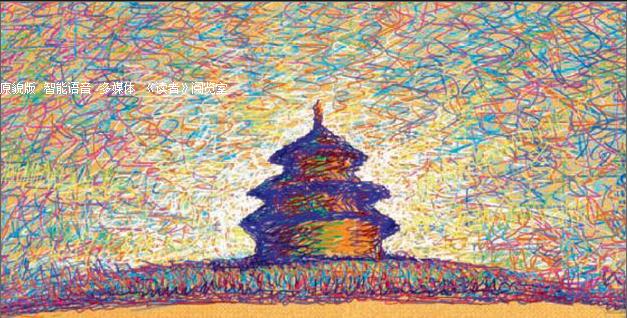


2000年元月,61岁的关庚被一家监理公司聘为工程监理,到国家大剧院工地当总监助理。
作为1960年代清华大学土建系的毕业生,他参加过北京一系列大型建筑的施工工作,如新华社、同仁堂、东方广场,以及人民大会堂的维修改造等。
早上的上班时间是8点整,关庚每天7点就准时到了。在上班前一小时的时间里,他在桌前坐下来,把厚厚的一个本子翻开,开始画画。
他画了他生活过的四合院、他家三代人的故事、街坊们的家长里短、街上的商贩、他的留连之地、北京的风物、在北京城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等等,并配上了文字。
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画满了三个本子:六百余幅绘图、五百余篇短文。
无从得知,他如何想到要画这些东西,以及画时的心情。但是那些画和文字,安静、平和,没有臧否,不掺情绪,只偶尔露出一丝淡淡的怅惘。
那三个本子后来作成了一本书,叫《我的上世纪—— 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书的腰封上写有几行字:一个平民亲历者的北京百年故事、三代人流年留影的世纪中国烟云、一幅私人手绘的“北京20世纪清明上河图”。概括精当、妥帖。
后来,他又出了一本《我的老北京》,将他记忆中的城市肌理,细细地作了描摹。
一个人的历史,一座城的历史。时代的景深,在这些充满生活质感的图和文字里清晰地、鲜活地呈现出来。这样的呈现方式、呈现角度,让城市变得可亲、可爱、可敬。
未来,倘有人也画上一本《我的上世纪》《我的老北京》,我们将能够看到怎样的画面?怎样的文字?这是个有趣的假设,让人充满想象。
本真的童年
家教
在上小学前,娘就对我进行了家教,最先学的是《三字经》。娘从头一句一句教,我一句一句学,不但认字,还讲解典故、含义,一天学八句左右,不久就能从头背到底了。后来又学《论语》,上完《学而第一》篇后,就因上小学而停止了。娘教过我的那些内容,叫我终生难忘。
抓蝙蝠
欢畅大院16号,沿街窗户的窗框和砖墙的交界处,有一条很深的墙缝,天刚擦黑,就有蝙蝠从里面爬出来,从高处往下落,趁势就飞走了。
我们几个小孩儿为了抓只蝙蝠观察了很久,最后想到一个方法:把一个人托上去,站在窗台上,拿一只鞋等着,当蝙蝠刚一露头就用鞋底子一拍,它就晕了,就能抓到它了。这方法很有效,用不了一会儿工夫就能抓十来只。抓到后,我们就拿回家养起来,捉活虫喂,可是它们不吃食,没几天就饿死了好几只。后来,这件事被大人发现了,说是破坏了家中的“福气”,只得把剩下的都放了。
萤火虫
过去,夏夜天空或草丛中,有很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发光。在院子里乘凉,看到它们飞来飞去,很是神秘。捉一两只放在小瓶子里,观察它们随着呼吸而发出淡绿色的光,趣味无穷。
小电影
在过往的隆福寺庙会,练玩意儿的台子上有一种娱乐,就是演小电影。小电影是必须有一架小型放映机,光源是用镜子反射的日光,光源过片的动力是采用手摇。当手摇动摇把以后,齿轮系统就带动片子一格格走过,片中的人物也就动了起来,走动的画面也就被阳光投射在银幕上,电影就这样放出来了。
一般电影总有几套片子,如有当时放过的动画片或从大电影中剪下来的片头,比如那时有《猩猩大闹纽约城》《探宝记》等,一段可演十分钟。看的人都坐在布围子四周的窗口前观看,一场下来得有二十人看,人多时循环上演,一天下来也得挣百八十块。
蛤蟆吵坑
过去,一出城,窑坑、草塘里都能看见很多青蛙、蟾蜍,通称为蛤蟆。一到阴雨天的傍晚,“蛤蟆吵坑”就开始了。听专家说它们是在搞“对象”,用“歌声”互相吸引对方。
其实一个蛤蟆的叫声并不大,但要是千万只齐唱,那动静儿可就大了。这时,你在河边别出声,悄悄地看,蛤蟆们半浮在水面,嘴下面的鸣囊,随着叫声鼓起一个白球,你要是出声,它们就会迅速地隐入水中,“歌声”也会戛然而止。一会儿,随着你的离去,“歌声”又慢慢地响起来,由一声、两声逐渐变成宏亮的“交响乐”。
垒球
当时,垒球是各校极为盛行的一种体育活动,各校之间经常比赛。课间,操场上“分儿包”、“奥梯”喊成一片。
童子军
我上小学时学校正组织童子军,童子军天天要穿童子军军装出操。童子军军装包括帽子,帽子分两种,一种是船形帽,一种是大檐帽。上身要配腰带,下身要配鞋和袜,腰中要带法绳、水碗,手中要拿军棍,脖子上要戴蓝白两色的领巾,好像一个小国民党兵。学校整天查上学时着装是否齐全,不全要回家带去。
素淡的青春
考上大学
1957年,我考上了清华。为了给我打点行装,娘变卖了日本投降时买的俏货,一台“胜佳”牌缝纫机、一台老式照相机、一台望远镜、一盒矿石标本,凑了一百元给我。行李用的是旧的,只买了一个带弹簧的枕头。提箱是一只放了不知多少年的大柳条箱,有的柳条已糟断了,我用布从里面糊了一下,就凑合着用上了。
香山露营
1957年“反右”时期,我们正放暑假,大家相邀去香山露营,帐篷是从清洁队借的。我们半夜出发,第二天下午才到,人困马乏,饭也没吃,倒头便睡在了香山的大门洞里。第三天,才支起了帐篷。
参加军乐队
在清华,我参加了军乐队,吹贝司。我平时吹的是降B调的抱贝司,出队时吹的是圈贝司。每次迎宾运动会游行时,军乐队都要出队,全队就属我们吹贝司的家伙分量大,累得我们个个汗流浃背。
当时还有一种出队大家愿意去,那就是给一些机关单位办的舞会伴奏。一到星期六,天刚擦黑,舞蹈队的女同学打扮完,我们也统一着装,登上接我们的大客车,直奔舞厅。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我们伴奏,女同学伴舞。午夜之后,舞会散了,犒赏我们一顿晚餐,到这时才是我们真正的重头戏。困难时期,吃上这么一顿美餐,是多么难得啊!霎时间,风卷残云,吃个盘光碗净,虽然不十分饱,但也心满意足。endprint
勤工俭学
砍 柴
勤工俭学,即是学军、学农、学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必须经过的一项劳动锻炼。暑假学校组织学生劈木柴,一个星期下来劈柴堆成了山,同学们只能落下几毛零花钱,还赔上几个大口子。
电影院领位员
还有的到电影院做引位员。刚一开始谁都抢着去,既干活又白看电影,谁不争啊?可是不久,谁都不想干了。据干过的同学称,这个工作不是什么享受而是一种折磨,一天几场电影看下来,电影台词都快背下来了,银幕上重复着上百遍同样的声音和动作,烦死人了。
拔麦子
每到五月麦收时节,就有大批劳动力下乡,帮农民拔麦子。为什么要拔?有两个原因:一是麦子被连根拔起来,地就松了一遍,地里无麦茬子,便于种下茬庄稼;二来那么多人去,镰刀不够使的,所以拔。拔要赶在露水干了之前,天没亮即起,天亮时第一拨已拔完,回去吃饭休息,下午再干到天黑,一天下来人就散架了。
群众演员
勤工俭学还有一项内容就是去“青艺”做群众演员。这是个好活,平时画好妆,在自习室内一边做功课一边等着上场。有的演二七工人,有的演群众,有的演巡警,既看戏又演戏,还常看到名演员忘记台词穿帮、闹笑话的,是一件开心有趣的事儿。
善意的玩笑
在清华期间,同学们之间常开一些善意的玩笑。因为我们每天早晨起床都有一场紧张的“战斗”——抢占好座位,所以穿衣、洗漱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同学们就利用这特殊情况大开玩笑。
比如头天晚上趁人不备,把衣服从里面用图钉钉在桌子上;把牙膏挤出一点儿,再把擦脸油抹进去一些;把裤腿或袖口缝死一只(腿或胳膊伸不进去);把棋子用糨糊贴到鞋膛里面;把糨糊薄薄地抹在擦脸油的上面等等。
做好了之后的第二天早晨,大家就等着看笑话。最损的是,牙膏内填进擦脸油,擦脸油内加糨糊,那样会造成刷牙时越刷越粘,洗脸抹一脸糨子,受害者真是又气又急。损人者一边偷着乐,还要防备第二天的报复,于是半夜起来把自己的东西都查一遍,以防到时候被弄得措手不及。但此风不会太长,因为招儿都使完了。
生活的滋味
严格保密
我与静媛谈对象时,我们两个订了一个保密条例:不得让任何局外人知道我们谈对象。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能出行的地方很少,北海故宫都关门了,公园也早早地静了园。我们没地方去就逛大街,可大街上买卖铺子极少,货物千篇一律,况且又怕被人看见,遛马路都要一人走一边。所以只有天黑了,我送她回家时,才能一块走走。
出差
在“文革”中各种商品均很匮乏,尤其是生活用品。由于文革闹得厉害,几乎不生产什么,消费产品即使有也是文革前的,几年一贯制的老样子。那个时代军服几乎一统天下,谁能去上海采购一些商品,就是很值得羡慕的事了。
临走之前,亲戚朋友闻风而至,把钱和需采购的物品清单交给出差的人,还要说上许多的好话。这时出差的人会高兴得跟当了官似的。到了上海后,利用空当儿时间采购,跟没头苍蝇似的,把东西拖回来又跟驴似的,最后累得跟孙子似的。
领结婚证
1968年4月上旬,我与静媛到东四十条民政局去领结婚证。结婚登记处的负责人对我们好一番盘问后填好了结婚证,但不立即给我们,叫我们等着。那天办证的人挺多,一会儿就好几对青年登了记,于是负责人把大家召集到毛主席像前大声说:“请大家拿起‘红宝书,让大家共同朗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朗诵完才把结婚证发到我们手里,意思是让我们的感情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
看电视
七十年代,北京已经有了黑白电视,只有两个频道,北京台与中央台。
有钱人家多买了九寸电视,我们没钱只能到静媛学校偷看十四寸的电子管电视。由于没天线,还要把扁的馈钱劈开当天线使,两手执馈线,来回调方向。找对了方向,能看到影像了,才用图钉把馈线钉在黑板上。
记得当时看了不少好的外国片子,有《罗马尼亚》《尼罗河》《三角洲的秘密》,还有国产片《三进山城》。
由于电视室没火,冬天里特别冷,到了那儿先生火暖和。看完后收拾干净再回家,那时真是苦中有乐。
第一个冰箱
八十年代初冰箱已大规模上市,买的人还不多,但过不了多久便热销起来,就得凭票供应了。开始时我觉得用途不大,只存放些剩饭剩菜,没有它那么多年不是也过来了吗?要它何用?还是先买电视、洗衣机吧!结果买的时候还费了挺大劲,票是从五金交电工地要的,货在肿瘤医院仓库,要自行提货。
我借了一辆三轮,静媛坐上头,我们俩一起去肿瘤医院仓库交款提货。
拿了票去交款时,收款员说:“您怎么手直哆嗦呀,不至于吧!”
我心想:你知道我用这么一大笔钱买冰箱,容易吗?
冰箱是单门万宝牌的,当喝上第一口冰镇的凉汽水时,心里甭提多舒服了。
裁剪衣服
改革开放前后,服装业跟不上形势,因循守旧。思想稍微开放一些的人开始自己做衣服。我也大胆地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服装设计。动手后,才体会到比画图容易多了。后来买了缝纫机更是如虎添翼,我画样子,静媛缝制,从我的衬衫、大衣,静媛的金姬领(朝鲜电影中女式汗衫领)、西服裙,到孩子的童装系列,引得街坊四邻交口称赞。
消失的背影
捏江米人
小时候,朝阳门内大街经常碰到一捏江米人的老先生,姓汤,捏的江米人逼真细腻,大的有五厘米,小的约二厘米,最让人称奇的是他可以在半个核桃壳内塑出十八罗汉的样子来,个个栩栩如生。
小孩儿看着那些造型逼真的江米人赖着不肯走,大人就让老头捏一种价格便宜又简单的胖娃娃。胖娃娃头戴绒帽穿花衣,盘腿而坐。制作绒帽、花衣比较精细,先选取不同颜色的彩色面片,后拿梳子齿在面片上压出一排一排的齿印,看上去极像衣饰的样子。最后一道工序是捏一个小茶壶,用镊子夹着往两腿中间一安就算完活,于是赢得围观人一笑。
卖铁蚕豆的
冬天晚上,西北风一吹,长街空寂,在阴惨惨的路灯下,从远处传来了悠长的叫卖声:“铁蚕豆——噢!半空儿给!”这种悲凉的声音,像叫卖人的最后呻吟,勾动着屋子里围炉而坐取暖闲话的人们的恻隐之心,觉得“买点儿吧,买点儿等于救人一命”。于是人们纷纷解囊,这个买一分的那个买两分的,回去坐在火炉旁大吃一顿,以消磨难熬的长夜。
窖冰的
上大冻后开始窖冰,北海、什刹海、筒子河等水面都要窖冰,窖起来,到盛夏供冰镇食品之用。
窖冰是苦活儿,分打冰和拉冰,窖冰的人身穿皮袄,脚踏竹板,手持冰镩,在冰面上开冰。那时拉一方冰,才不过几分钱,这一行一直持续到“文革”前才从北京消失。
卖糖葫芦的
那时每到入夜,街上就传来了“冰糖葫芦”的叫卖声,只见小贩挎着木提盒,提着灯,木提盒把儿上插满了鲜红发亮的糖葫芦。小贩一来,人们就围拢上去。
直接买糖葫芦的人很少,多是用钱先买签,一串糖葫芦的钱可买两三根签。签插在一只竹筒内,给几根签的钱就可以抽几根签,签上有点,买的人抽完签后,小贩也抽同样根数的签。然后双方比谁的点大,如果你赢了,就能拿走一串糖葫芦,输了,就什么也吃不着。在当时,此类赌输赢的小买卖还真的很多。
拉骆驼的
一到快入冬,北京人生洋炉子取暖。那时生洋炉子要烧硬煤,硬煤除了山西大同的煤外,还有就是门头沟的煤。门头沟的煤,大都是用骆驼驮进城来卖。驮煤的骆驼一来就是一大串。卸煤后,骆驼都卧在街上休息,长长的脖子、卷曲的睫毛,嘴里不断反刍,引来很多人围观。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