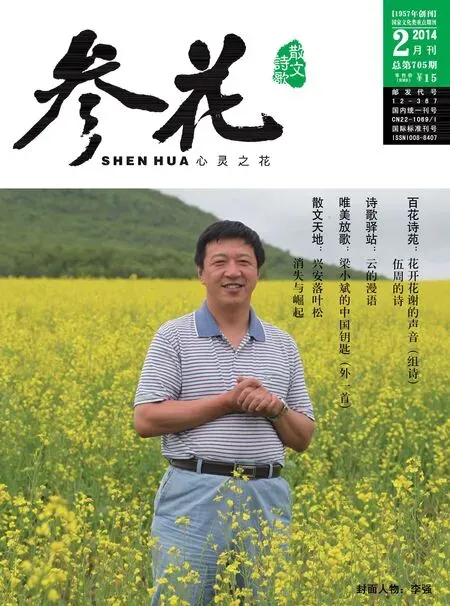中国古代人鱼文学形象的变迁考
2014-12-12光孙冬梅
◎袁 光孙冬梅
中国古代人鱼文学形象的变迁考
◎袁 光1孙冬梅2
中国有关人鱼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上,对其出典考和其现实中实际物种的考证相对成熟。本论通过探讨中国人鱼在文学上的演化过程,从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角度出发,阐述中国古代文学中人鱼形象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一、《山海经》中人鱼的神化过程
《山海经》中对人鱼的描述,首见于“其状如鱼而人面”的赤鱬。其他篇章的记叙句式多为某山有某川,其中多人鱼。松冈正子指出山川中的人鱼应为两栖类的鲵,鲮鲤(陵鱼、穿山甲)是人鱼的一种属爬虫类。其实,穿山甲是胎生动物为哺乳类。
可见,作为动物的人鱼,其种类有了扩大化的趋势。袁珂认为陵龙的音相近,所以二者应为同一所指。字音上的变化也可能引发字形的变化,所以陵鱼也是龙鱼。“龙鱼(中略)即有神乘此以行九野。”一句首次将人鱼和龙,与神这样的字眼联系起来。可以说这是人鱼从动物向神物转化的第一步。
神会变化的性质体现在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如果考虑到鲮鲤,则该变化是古人将可互化的物种归为一类,有鳞甲是互化的条件。但鱼妇的意思尚未明确。笔者推测,该词也许对后世故事中人鱼的特性做了一个伏笔。
后世有“鲛人泣珠”的典故。但《山海经》中并没有记录鲛人。中山经提到了“鲛鱼”,郝懿行云“鲛鱼即今沙鱼”。可知鲛鱼不是鲛人。海内南经提到了雕题国,郭璞认为雕题国的人是鲛人,但被袁珂否定,指出“鲛人乃人鱼之属,非雕题国人可以当之也”。笔者赞同袁珂的说法,认为鲛人属人鱼的神话范畴。
综上,《山海经》中提到的人鱼,多为山川间的真实生物,并被人逐渐神化。古人对自然的认识是有规律的,即在认知实际物种的基础上,神化其某种特性并加以崇拜,将其神奇力量与人类自身相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人逐渐摆脱“神力”,并将人类自身的品性特点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观念反作用于文学。如果说《山海经》是将人鱼神化的过程,那么后世之作就是将人鱼赋予人性的人化过程。
二、人化的鲛人
目前,有关鲛人的最早记载出自东汉郭宪著《汉武洞冥记》:“味勒国在日南,其人乘象入海底取宝,宿于鲛人之宫,得泪珠,则鲛人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此时的鲛人依旧有神性,住在海底宫殿,眼泪能变成珠子。
西晋张华《博物志》:“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绢。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此处的鲛人在继承《汉武洞冥记》之上,还增加了卖绢的行为。卖绢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表现。在河精和大禹的交流中,人鱼是高高在上的神,对人的行为动词是“授”,这里则是“寓”“卖”。可见人鱼与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人鱼基本走下神坛,与人平等交流。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人鱼以“泣”的方式送给人珠子,比起《汉武洞冥记》的“得泪珠”,更能说清珠子的来历。
东晋干宝《搜神记》“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提到了鲛人会纺织技术,能泣珠。基本是沿袭先前文艺的续作。南朝梁任昉《述异记》:“鲛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南海出蛟绡纱,泉先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以为入水不濡。”这里重点介绍了鲛人的纺织品,不提泣珠。可见后世中鲛人的生活方式逐渐向人类趋近。文学中人鱼的人化过程实则是在反映随着社会进步,古人对自身社会生活认识加深。古代中国经济以耕织为主,所以此处鲛人会纺织应该是古人将自身特性反作用于文学的表现。
三、有性别的人鱼
人鱼有性别之分应该是从唐《酉阳杂俎》开始的,“奔孚(鱼孚),一名瀱,非鱼非蛟,大如舡,长二三丈,若鲇,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取其子着岸上,声如婴儿啼,项上有孔,通头,气出吓吓声,必大风,行者以为候。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汉《异物志》记载奔孚是南方的懒妇鱼。梁《述异记》“淮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子妇,为姑所怒溺水为鱼,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鼓琴瑟博弈则灿然有光,若照纺绩则不复明”。
中国古代的淮南对应范围是指今江苏、安徽、河南境内的淮河以南的地区。长江从安徽江苏经过。
根据古籍所示,懒妇鱼应是长江江豚。九头见和夫曾指出人鱼应包含海豚一类,但尚未明确其具体所指。结合懒妇鱼的生理特点与古籍的记载,可知江豚也是中国人鱼的一种。
“雄雌阴阳类人”表明中国人鱼第一次有了性别之分。无性别之分的鲛人会纺织,懒妇鱼的传说也提到了鱼油点灯用去纺织则光线会变得昏暗。纺织总是与女子的关系较为密切。《诗·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可见在古人的观念中,纺织是代表女性的符号之一。所以,在懒妇鱼和后世人鱼的文学形象上,人鱼也就越来越女性化了。而这一问题在海人鱼的传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美丽的海人鱼
学界普遍认为海人鱼是儒艮。
有关它的记载可追溯至唐《洽闻记》:“海人鱼,东海有之,大者长五六尺,状如人,眉目、口鼻、手爪、头皆为美丽女子,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色轻软,长一二寸。发如马尾,长五六尺。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临海鳏寡多取得,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异,亦不伤人。”
到元朝,古人对海人鱼的理解和对《山海经》中人鱼的理解是相似的,基本是从其外形和功能去记录。对海人鱼更为细致的描述表现了古人对事物认识的提高。尽管如此,海人鱼依然被视作妖异的存在。而它文学形象的提升是在清李汝珍的《镜花缘》人鱼报恩的故事中体现出来的。
《镜花缘》第十五回“喜相逢师生谈故旧 巧遇合宾主结新亲”中有这样的描写:
唐敖那日别了尹元,来到海边,离船不远,忽听许多婴儿啼哭。顺著声音望去,原来有个渔人网起许多怪鱼。恰好多林二人也在那里观看。唐敖进前,只见那鱼鸣如儿啼,腹下四只长足,上身宛似妇人,下身仍是鱼形。多九公道:“此是海外“人鱼”。唐兄来到海外,大约初次才见,何不买两个带回船去?”唐敖道:“小弟因此鱼鸣声甚惨,不觉可怜,何忍带上船去!莫若把他买了放生倒是好事。”因向渔人尽数买了,放人海内。这些人鱼撺在水中,登时又都浮起,朝著岸上,将头点了几点,倒像叩谢一般,于是攸然而逝。三人上船,付了鱼钱,众水手也都买鱼登舟。
此处的“海外人鱼”啼似婴儿有四足的特征,符合《山海经》中描写的人鱼形象,而上身妇人下身鱼形,就是标准的海人鱼形象了。人鱼得救后向唐敖叩谢,这是海人鱼人化的表现。
第二十六回“遇强梁义女怀德 遭大厄灵鱼报恩”唐敖等人遇险,人鱼来报恩:
正在惊慌,猛见海中撺出许多妇人,都是赤身露体,浮在水面,露著半身,个个口内喷水,就如瀑布一般,滔滔不断,一派寒光,直向众人喷去。真是水能克火,霎时火光渐熄。
林之洋趁便放了两枪,众人这才退去。再看那喷水妇人,原来就是当日在元股国放的人鱼。
那群人鱼见火已熄了,也就入水而散。林之洋忙命水手收拾开船。多九公道:“春间只说唐兄放生积德,那知隔了数月,倒赖此鱼救了一船性命。古人云:‘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话果真不错。”唐敖道:“可恨水手还用鸟枪打伤一个。”林之洋道:“这鱼当日跟在船后走了几日,后来俺们走远,他已不见,怎么今日忽又跑来?俺见世人每每受人恩惠,到了事后,就把恩情撇在脑后,谁知这鱼倒不忘恩。这等看来:世上那些忘恩的,连鱼鳖也不如了!(后略)”
这段描写再次表现了恩报主题,海人鱼的人化过程也类似鲛人。它的存在不仅表现了古人对海洋认知的深入,也体现了古人结合当时社会宣扬的正统观念在文学创作上的应用。
综上,中国人鱼起源于《山海经》,是由多种真实动物的“整编”,并被人加以神化而形成的。《山海经》的人鱼形象对后世的人鱼故事塑造有着巨大的影响,清代小说中的人鱼依旧能看到它的影子。人鱼在从神向人的演变过程中,鲛人故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后世创作的泣珠报恩,让人鱼有了符合人类精神层面需求的形象,可看做人鱼故事的升华。随着古人对世界认知的扩大,人鱼的种类也在增多,而古人对自身关注的增加,也导致了人鱼出现了性别倾向的变化,如懒妇鱼(江豚)传说和女性形象的海人鱼。海人鱼的文学形象在清代与鲛人一样,都被提升到了恩报主题的主角,是能体现中国古代道德标准的一个经典文学形象。它的出现与演化,体现了中国古人认知世界与改造创造世界的过程,也反映了古人在文学创作上的立场与特点。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鱼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的存在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1]梁玉金 中国古代灵异报恩小说的文化学分析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1年第33卷,第1期
(作者单位:1.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
2.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