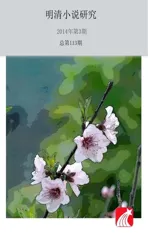魏晋以降“人鬼恋”故事流变管窥
2014-12-11··
··
魏晋以降“人鬼恋”故事流变管窥
·王庆珍·
魏晋以降,“人鬼恋”故事模式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同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诸如:鬼女身份逐渐下移,由魏晋时期的高门大族之女渐渐演变为平常人家的女儿;临别赠物也不再是价格不菲的奇珍异宝,而更多是一些日常随身佩戴之物;另外,鬼女与世人相处的时间也在逐渐延长,甚至可以作长久夫妻。这些变化让我们看到了此类故事发展的轨迹与时代、科举制度、社会思想等方面都息息相关。
“人鬼恋” 身份下移 临别赠物 世俗化
杨义先生说:“女鬼与爱情,是古典短篇小说最常见的母题之一,它沟通幽明而打破人间伦理阻隔,以怪异之笔写尽世间男女真性情。”①人鬼恋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普遍存在的母题,在漫长的小说发展历程中呈现出各异的面貌。从魏晋时期一直到《聊斋志异》,此类小说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各异的特点。
在人鬼婚恋的问题上,历代小说都有传承的痕迹。诸如鬼女出现的时间常常是日暮时分,在夕阳落去的薄暮中,她们会勇敢地敲响书生的门;抑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赶路的书生在荒山榛丛里迷失了道路,前方总是出现一豆灯火,让他们欣喜若狂,而那个房屋里必定有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在等待,等待一场如火如荼的爱情和宿命的缘分。她们虽然是鬼,但像人世的女子一样渴望真爱降临,并会为了那位深爱的情人赴汤蹈火,不避险难。这似乎已经成为冥鬼题材的小说比较固定的创作格套。但是,在历代同类题材小说的研读中,我们还会发现每一时期题材的处理、甚至细节的安排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一、鬼女身份日渐平民化
如果我们细致地去读前代流传下来的人鬼婚恋题材作品,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诸多作品里,鬼女的身份往往非常高贵,《吴王小女》中,紫玉是“吴王夫差小女”②;《驸马都尉》中的秦女是秦王的女儿;《谈生鬼妇》中鬼妇是睢阳王之女;《卢充幽婚》崔氏女为崔少府之女。
魏晋时期小说中这些鬼女几乎清一色都出身豪门,“吴王”、“秦王”、“睢阳王”,都是王侯之家;就是《卢充幽婚》中的“少府”,亦位列九卿,掌管宫中的御衣、宝货等等,可见,这些鬼女的身份都比较高贵,大都出身于王侯公卿之门。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与他们婚恋的男性在作品中却没有提及有何显赫的家世背景。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不难找到答案。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相当森严,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一个名门闺秀是无论如何不会下嫁给寒门子弟的。庶族寒士想要与大家世族联姻几乎是难于上青天,但在小说中,这种理想便可以暂时实现了,表现出在魏晋时期森严的门阀制度下,世人朦胧的对婚恋平等的期待。现实生活中,社会地位低微的世人面对高墙朱门只能望洋兴叹,而在虚拟的幽冥世界里,那些曾经出身高贵的“鬼女”们却仿佛到达了“自由王国”,可以抛却尘世的婚姻枷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选择那个虽然卑微、但却倾心相爱的男子。现实婚恋中无法企及的自由平等在“鬼女”的世界里暂时得以实现。
到了唐代传奇中,这些“鬼女”的出身较之魏晋时期明显降低。比较显赫的是《王濬》中的鬼女,为“陈朝张贵妃”③;《崔书生》中的玉姨是“后周赵王女”。还有一些是朝中或者地方官吏的女儿,如《袁洪儿夸郎》中鬼女为“晋侍中王济”之女,《王玄之》中鬼女“本前高密令女”;《刘长史女》为“吉州刘长史女”;《齐推女》为“饶州刺史”之女等等,总之,这些鬼女的身份由魏晋时期的金枝玉叶直降为普通官吏的女儿,小说也不再关注她们在世亲人与恋人之间的瓜葛,而更多的去写他们相恋过程中的情深义重,和别后刻骨铭心的相思。
宋代传奇中,这些与尘世男子萌生恋情的鬼女身份继续下移,官宦人家的闺秀也很少见,很多鬼女出身平民,甚至是优伶、歌妓。《越娘记》中越娘是“后唐少主时人”,“良人为偏将”④,只是言及她出身于丰足之家,嫁与武夫为妻。《范敏》中鬼女是“唐庄宗之内乐笛部首也”,乃宫中乐队的优伶。《钱塘异梦》中的鬼女是钱塘名妓苏小小。《吴小员外》中的鬼女生前是酒肆中的当垆女。《夷坚支甲·卷三·吕使君宅》中的鬼妇为吕使君遗孀。这些鬼女中几乎再也见不到金枝玉叶的影子,大都为市井平民的女儿,她们不顾世人的訾议,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一往无前地追逐着自己的爱情。
结合唐宋时的社会状况,由于商业的繁荣发展、市民阶级的壮大,加之唐代思想界的相对自由、宋代市民娱乐的蓬勃发展,歌楼妓馆比比皆是。这些青楼女子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能够吟诗唱词,精通琴棋书画,令当时的士子文人为之倾倒。她们不仅是现实生活中风流雅士的知己,也成为了小说中的女主角,这些出身青楼的鬼女的大量出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男性在婚姻之外的感情生活。
明代传奇小说中鬼女的身份沿袭了宋代的情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剪灯新话》中的一些作品。如《金凤钗记》的女主人公兴娘是“扬州富人”之女⑤,家境比较殷实而已;《绿衣人传》中的鬼女为“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是南宋理宗朝奸相贾似道的侍女;《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卫芳华是“已故宋理宗朝宫女”;《牡丹灯记》中的符丽卿为“故奉化符州判女”,出身下层官吏人家;《爱卿传》中的罗爱爱是嘉兴娼女。《剪灯余话》中的一些传奇小说鬼女社会地位也相对低微,《田洙遇薛涛联句记》中,鬼女是唐代名妓薛涛;《秋夕访琵琶亭记》中的郑婉娥是“伪汉国主陈友谅宫中女官”。这些小说中鬼女的社会地位和唐宋时期仿佛,或小家碧玉、或出身商贾富家、或前朝宫女侍女,前生为娼的女子也大有人在。
到了蒲松龄的笔下,鬼女的出身大都沿袭了唐宋以来小说的写法,不再像魏晋时期那样高贵了,很多鬼女生前就是平民小户家的女子。甚至对她们生前的出身根本不作赘述,如《聂小倩》中,只是言及“小倩,姓聂氏,十八夭殂,葬寺侧”⑥,关于其生前家世及社会地位等等都没有任何交代。《连琐》中,对她的身世也不过寥寥数语,“妾陇西人,随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谢,今二十余年矣”;《公孙九娘》是于七一案中连坐被诛的数百人中的一员;《小谢》中对两位鬼女的交代也不过是“妾秋容,乔氏。彼阮家小谢也”。蒲松龄着力描写她们的才华,通过鬼女的择偶态度作为这些落魄文人的安慰,藉鬼女以彰显她们所钟情的恋人的才华气度。
综上,魏晋时期的鬼女常常出身于王侯公卿之门;到了唐代,除了少数仍旧出身于豪门之外,很多为“刺史“、”县令”之女;宋代的鬼女甚至官宦小姐也很少见了,多为平民小户出身;明清时候的鬼女身份比较芜杂,但她们生前的社会地位都相对较低,宫女、侍女、娼女等大有人在,甚至有的作品对她们的出身已绝口不提了。可见,魏晋以降小说中鬼女的身份地位呈现出明显的逐渐降低的发展脉络。勃兰兑斯指出:“在文学表现的所有情感中,爱情最引人注意。而且,一般来说,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深。了解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及表现方式,对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是个重要因素……”⑦,鬼女身份的下移也让我们看到:科举取士给读书人开辟了通衢大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者大有其人,这些普通的读书人不必再通过联姻这条蹊径跻身上层社会,于是,婚恋不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而更多倾向于真情挚爱的赞歌,表现出人鬼婚恋题材小说由功利向情感的回归。
二、临别赠物趋于普通化
魏晋小说中在鬼女与男主人公经历短暂的聚首离别之时,常常有绝世无双的“信物”相赠。《搜神记》中的鬼女们在分别时常把自己随身陪葬的最珍贵的东西赠给郎君,表白情义之笃以求睹物思人。《紫玉韩重》,“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驸马都尉》辛道度与秦女分别,秦女“取床后盒子开之,取金枕一枚,与度为信”,辛“寻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恰遇秦妃东游,疑而索看,诘度何处得来”,认为女婿;《谈生鬼妇》,鬼妇离去,“以一珠袍与之”,“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是我女袍”,“复赐遗之,以为女婿”;《卢充幽婚》崔氏女分别时已经怀孕,四年后,“抱儿还充,又与金”,“充后乘车入市卖,高举其价”,“一老婢识此”,知为崔少府之女。
看到这些叙述,我们不禁会疑惑,既然女方一片痴情送了定情信物,男方必定应当珍若生命,作品也并未谈及他们生活怎样困顿不堪,既然没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压力,为什么还要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到集市上去卖掉呢?联系前文鬼女们的身份,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出身平凡的男子与鬼女结合时,大都不了解她们的真实身份,而这些信物恰到好处地成为了鬼女们身份的标识,通过这样一些东西被人世的亲人辨认,并接受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女婿”,于是,寒门子弟终于通过这种方式与高门望族结合,表现了他们在以门第高下论婚姻的社会条件下人性本能的欲望,希冀与世家豪门联姻的潜意识通过这种方式得以达成。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信物虽然珍贵,但不得不以货卖的方式作为线索,引出鬼女的家世背景,实现寒族庶民婚恋平等的理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到了唐宋文言小说中,人鬼婚恋题材的作品很多依旧保留着临别赠物的传统,与魏晋时相比,不仅是鬼女赠送物品给对方,男方也常常有回赠。“中国小说在唐宋时期,就在诗学文化的熏陶下出现了一种追求诗意的小说思维意向”⑧,关乎唐代诗歌的繁荣程度,小说中男女双方在相聚和分别的时候还大量留赠诗歌。唐人小说《王玄之》,鬼女与王玄之生活一年后分别,“女以金缕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崔书生》中,崔与玉姨“宴游欢洽”,席间博戏,“崔赢玉指环二枚”。《曾季衡》中男女主人公分别时,和诗两首,女方赠与“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男方回赠“小金缕花如意”。《李章武传》中,鬼妇临别“囊中取一物赠之,其色绀碧,质又坚密,似玉而冷,状如小叶”,“所谓靺鞨宝”,“非人间之有”,而李章武也“取白玉宝簪一以酬之”,并互赠诗歌四首。《唐晅》中唐与亡妻相会,作两首悼亡诗,相见时,又互赠三首诗作,临别,其妻“留一罗帛子,与晅为念。晅答一金钿合子”。《韦进士见亡妓》在男女恋人分别的时候已经没有物品相赠,而只是作诗悼念了。
到了宋代,由于词的兴起,就使小说中的留赠又增添了许多词作。《钱塘异梦》写了宋代才子司马槱与南朝钱塘名妓苏小小的故事,有二人互赠诗一首,词三阙。《玉尺记》中,鬼女“携一白玉尺”赠生,并作诗一首,日后为一客认出此乃“亡妹柩中之物”。《玉条脱》中,鬼女以金钗赠给蔡禋,是此女死时佩戴的。蔡因“行囊告竭”,“诣铺中售之,得钱万六千文以归”。《范敏》的故事更是离奇,鬼女李氏与范敏相处十余日分别,范敏“视其马,惟皮骨存焉;开箧,则衣服无有也”。李氏托童子致意:“人间之娼室,亦须财赂,今十余日在此,费耗兼不多”,可见留恋鬼女也要付花酒钱的。《夷坚支甲·卷三·吕使君宅》中,鬼妇临别赠给贺忠“五花骢及白金百两”,而跟随贺忠的兵卒也“各得万钱之赐”。
从这些小说中鬼女的身份来看,他们或为普通人家的女子,或为沦落风尘的歌妓,再不像魏晋时期那样出身豪门了,男方亦不必绞尽脑汁力图摇身变为某世家的乘龙快婿,所以大致已经没有了货卖这一情节。同时,分别时更多是男女双方互赠物品,而赠品也很少再像魏晋时小说中那样贵重,不过是一些随身之物或者银两罢了。其中,有一些是独一无二、用来辨认身份的东西,让男主人公事后了解女方“鬼”的身份,从而昭示人鬼婚恋的故事模式。而绝大多数赠品仅仅是留作纪念,表现双方的依依不舍,以期睹物思人罢了。在唐宋小说里,鬼女的生前的社会地位逐渐下移,信物的价值也逐渐退化,只是作为婚恋中的一种装饰品,已经不再具有魏晋时的意义了,而诗词歌赋这些传情达意的文字大量增加,使小说在叙事之余更具抒情性和浪漫主义色彩。
明代小说中的鬼女与情郎分别时有的也会有馈赠,《金凤钗记》兴娘赠与兴哥的是二人在襁褓中订婚的信物“金凤钗”,也是兴娘的殉葬之物,此物具有婚约和辨识身份的双重意义。《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卫芳华临别赠给滕穆随身佩戴的“玉戒指”。《田洙遇薛涛联句记》中,关合二人对诗歌的共同爱好,薛涛赠予田洙的东西也颇为风雅,乃“卧狮玉镇纸”和“洒墨玉笔管”,这些书斋之物显示了薛涛对文学的热爱,也与二人因诗歌联句互相倾慕而吻合。《秋夕访琵琶亭记》中,郑婉娥赠予沈韶“赤金腕钏,一对明珠首饰”,沈韶将腕钏到波斯人开的珠宝店货卖,得到万锭钱钞,设祭坛,请道士为之打醮祈福三日三夜。在明代小说里,关合鬼女生前的不同身份,她们赠送给男主人公的东西也各有特色。出身伪汉宫中的鬼女所持之物价格不菲,而才女薛涛所赠更是别具一格。明代小说中的男子也会选择将赠物卖掉,但究其目的往往是为鬼女设醮祈福,这既显示了赠物的货币价值,又流露了他们对鬼女的一往情深,希望沉沦幽冥的魂灵能够早得超生,作者的心思还是比较缜密的。
在蒲松龄的笔下,“鬼女”的形象更加丰满生动,她们与男性交往过程中大多已经没有了馈赠信物的情节,即使赠送,也不过是随身“罗袜”(公孙九娘)之类,但尚有诗词缀于其间,有的是为了表现主人公的才华,或者通过夜幕吟诗引起对方的关注,如《连琐》,杨于畏夜闻墙外有人吟诗,“悟其为鬼,然心向慕之”,以诗为媒,让男女双方通过诗歌对彼此产生好感,作为相识的纽带;也有的作为分别时的赠寄,如《林四娘》与陈公分别的时候赋诗一首,陈述了她悲哀的身世,表达挚情难舍的心情;公孙九娘与莱阳生枕上追述于七一案无数生灵无辜被戮,亦口占两绝倾诉死难者的不幸。
《聊斋志异》不再像魏晋那样,表现下层男子婚恋平等的潜意识,而是体现了女性的婚恋价值观念,这些女性绝大多数国色天香,但并非见到倜傥青年就会去拉郎配,她们以心相许的男子大多是经过谨慎斟酌的。宁采臣“帘隅自重”,不为金钱美色所动,因而获得了聂小倩的芳心;戚生“少年蕴藉,有气敢任”赢得了章阿端的青睐;陶生“夙倜傥”,明知废屋多鬼魅却寓居于此,与二鬼女小谢、秋容交往,终于抱得美人归。她们看重才学,关注人品,表现出更进步的婚姻理想。当然,作为蒲松龄自身,这些作品的创作不乏自我慰藉的成分,是为与他同命一群的失意文人去呐喊,这里绝非仅仅要求佳人配才子,更渴望当时的朝廷和社会能够睁开慧眼,看到他们的价值。因此,蒲松龄笔下的人鬼婚恋题材作品较之前代而言,不再停留在婚姻平等的简单要求上,而是扩展到文人在广阔社会人生中自我价值的体认的层面,只不过他是用婚恋问题作代言罢了。
三、人鬼婚恋逐渐世俗化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在《搜神记》中,鬼女与人的缘分都很短暂。韩重在紫玉的墓穴中“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便分别了;辛道度在秦女处“经三宿三夜后”,秦女说“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会可三宵,不可久居”。谈生鬼妇相聚的时间是这里最长的,“生一儿已二岁”,因不得复生而分别。卢充幽婚“三日毕”,鬼女称“君可归矣”,四年后送还他们的儿子。
唐代小说中人鬼的姻缘也是如此。《王玄之》“如此积一年”;《崔书生》“一住三日”;《曾季衡》“近六十余日”;《李章武传》“至五更,有人告可还”。总之,在短暂的缠绵后他们要各自回归原位,几乎没有长相厮守的可能,而且长期相伴将会给生人带来不测的祸患。正如宋代小说《越娘记》中越娘与杨舜俞分别时说:“妾乃幽阴之极,君子至盛之阳,在妾无损,于君有伤。”道士也言及:“幽明异道,人鬼殊途,相遇两不利,尤损于子”。
但小说家的观念在逐渐变化,鬼女逐渐蜕去了她们特殊身份的外衣,越来越接近世俗女性的特征,如《夷坚三志己·卷九·建德茅屋女》,筠州城民蔡五在郊外茅屋内遇到一位女子,一起生活并育有一子,后为道士所驱。这里的鬼女与生人一起生活四年多的时间,而且还生下了孩子。可见,人鬼婚恋小说在发展长河中相处时间在不断延长,更令人一新耳目的是鬼女竟然也能生下孩子留在世上。
当然,关合道家阴阳互补之说,尘世男子为阳之极,而鬼女则为至阴之质,二者的结合会使鬼女得以还阳,重见天日,有的小说也谈及这种起死回生的妙法。《夷坚乙志·卷七·毕令女》,灵壁县令的大女儿生前常被后母所生的二女儿欺侮,抑郁而死,九天玄女授以“回骸起死”的秘法。此女自荐枕席,与一士人“缱绻情通”,半年后她赠给士人的铜镜无意中被认出,二女儿执意开棺验尸,“启砖见棺,大钉皆拔起寸余。及撤盖板,则长女正叠足坐,缝男子头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肤理温软,腰以上犹是枯腊”。在小说中,鬼女与士人相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士人毫发无损,而鬼女也像那些尘世的妻子一样,常常为她的男人缝缝补补,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尽管最终前功尽弃,二人的姻缘也无奈结束,但较之魏晋小说,她们与世人相处的时间更久长,其生活画面也更世俗、更具人间烟火气息。
在洪迈笔下,鬼女也会通过与世人的交往起死回生并结为夫妇。如《夷坚乙志·卷九·胡氏子》,死去的通判之女与胡氏子结合,胡氏子使女食人间烟火之食,女形不能隐,欲归不得,还阳为人,与胡氏子永结良缘。
明代小说鬼女与生人相处的时间也呈现出逐渐延长的态势。《金凤钗记》兴娘崔郎相处一年之久。《绿衣人传》里鬼女与男子的姻缘持续了三年。《滕穆醉游聚景园记》鬼女与滕穆同归,宛如良家妇,共同生活三年后别去。总之,明代小说鬼女与生人相处的时间较之前代更显长久,而作者也没有言及她们与生人的结合会给对方带来怎样的灾难,似乎就像平常女子一样,只不过她们在人世的时间不得自主罢了。
到蒲松龄笔下,鬼女与人的结合似乎更多会作长久夫妻。鬼女们或者依靠神仙术士,或者“但得生人精血,可以复活”(《连琐》),更有甚者,干脆就到阳世与生人过正常的生活,别人也不会发现她们鬼的身份。
尽管这些文言小说中鬼女与世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久,但其结局大都是悲剧性的,或者因“数尽”而杳然离去;或者复生不得只能魂归地府;或者为道士法师所制,无可奈何。鬼女与生人阴阳有别,小说家认为其幽阴之质必然会给那些尘世的男子带来疾病和灾难,而鬼女想要与人做得长久夫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带入幽冥,让他们为爱情走向死亡。在这样的时候,道士法师们应运而生,一方面要各逞神术,各神其教。另外,“人鬼世界的悲剧,实质上是人间世界悲剧的折射。相恋相悦为情欲的体现,道士法师的介入,又体现了理学以天理灭人欲的基本原则。在作者主观上,这个描写模式是导邪入正、拯迷救溺,而在审美效果上却重现了青春与爱毁灭于道学气之间的悲剧”。
综上,基于时代特点和社会格局的不同,人鬼恋题材作品在不同时代表现方式也各异,这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
注:
①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213页。
② [晋]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下所有《搜神记》篇目均引于此,不再另行标注。
③ 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所有唐代小说篇目均引于此,不再另行标注。
④ 李剑国辑校《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以下所有宋代小说篇目均引于此,不再另行标注。
⑤ [明]瞿佑等撰《剪灯新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所有明代小说篇目均引于此,不再另行标注。
⑥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所有《聊斋志异》篇目均引于此,不再另行标注。
⑦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⑧ 吴士余《中国小说美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责任编辑:倪惠颖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