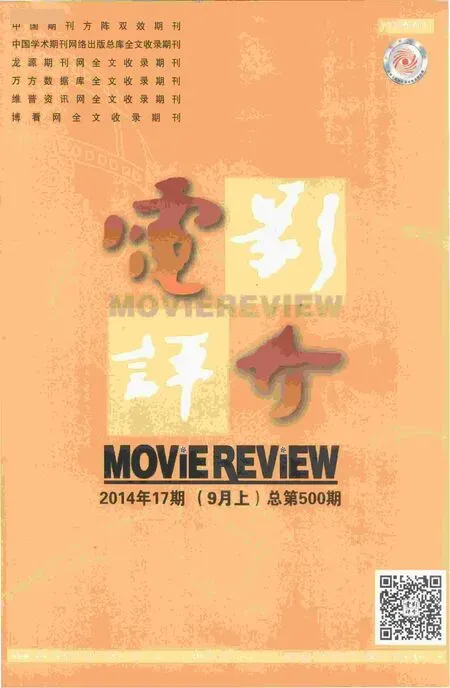社会变革影响下的女性形象——浅析明星影片公司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2014-12-10王姝
王 姝

民国时期电影明星周璇
电影诞生之初只是作为视觉影像奇观引起人们注意,不论是在咖啡馆,还是游乐场,它的娱乐性和商业性是创作的最基本动力。然而,社会前行的步伐影响着电影创作意识的变化,电影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可避免的成为各类思想的宣泄工具。尽管电影是舶来品,可它在中国的发展早已受到本土观念的“熏陶”,极具中国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国人眼中文化的社会功效极为重要。电影自引进以来,它与生俱来的娱乐性就和传统的教化思想发生碰撞,之后又因受到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中国电影的发展更具社会性。明星影片公司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王者地位可谓是无人取代,作为中国电影的早期开拓者之一,明星影片公司在十五年间留下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作品,并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却电影艺术事业上的成就,明星影片公司对近代社会发展、民众启蒙也颇有贡献。因为与其它公司相比,“明星”的创作理念随着时局的变化逐渐带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而这一理念不仅贯穿于叙事脉络中,在电影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一样影响深刻。
女性作为不可或缺的银幕形象出现在各种题材和类型的作品中。明星影片公司曾塑造过一系列经典女性形象,但由于电影是男权制度下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消减,甚至是剥夺了女性形象。尽管如此,随着创作者艺术理念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女性形象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和社会文化中仍旧呈现出多样的特点。并且,因为时代意识的不断加强,电影中的女性在摆脱父权限制下的依附形象的同时,努力探索着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本文将通过明星影片公司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主要创作理念,即娱乐追求、改良教化、宣扬革命三方面对不同时期电影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和比较,以探究人物塑造和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及早期中国电影发展中呈现出的社会功效。
一、追求娱乐下的女性形象
早期中国电影带来的商业利益是创作极其重要的目的,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初,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符号化的性别象征,是服从于电影叙事机制的一种营销策略。明星影片公司成立之初两个主要带头人就发生了分歧,郑正秋的制片宗旨是以“改良社会,教化民众”为主,他认为应该通过电影“补家庭教育暨学校教育之不及”。但是,真正的决策者张石川则倾向于“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尚无主义之足云。”于是,明星公司在初创期的电影作品以娱乐滑稽片为主,而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则处于模糊阶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强调“娱乐”的效果存在。
明星影片公司在创立之初摄制了四部系列影片,其中最为著名的《劳工之爱情》,既是明星公司现存的尚可放映的最早的一部电影,同时也是最早以爱情为主题的影片。《劳工之爱情》遵循了“娱乐至上”的宗旨,全篇随处可见夸张丰富的表情,以及不时闪现的搞笑情节。虽然剧中人物不论男女都承担了娱乐的任务,但相比于男性较为立体的形象,女性人物就略显单薄,其存在的视觉价值远大过自身的社会价值。换言之就是,女性在这一时期仅作为依附在男性形象下,满足观众视觉享受的符号化人物存在,她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只是完善叙事的手段,而女性在社会中具备的现实意义,也因当时传统文化和艺术理念的影响,被创作者几乎完全的忽略掉。剧中的女主角虽不是中国电影史上塑造的第一个女性形象,但却能视为同时期女性形象的代表。
该电影的故事情节是传统文化和五四思想杂糅下的结合体,特别是人物形象方面呈现出许多矛盾。电影开头的“本剧事略”里将女主人公称为“祝医女”,从称呼上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女性在当时社会里的地位,因为姓名是一个人基本的社会符号和标识,当时的女子均是未结婚前随父姓,婚后随夫姓,由此可见她们一生的命运都要掌控于男性手中。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典型思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祝医女伴随父亲左右,依靠父亲的医馆生活,当生意不佳时,恰逢郑木匠来求婚,父亲便将她的婚姻大事与医馆生意联系在了一起。单就祝医女和郑木匠互生情愫的事情来看,可谓是自由婚恋的大胆尝试者。但是看到祝医女面对木匠的求婚所做出的回答后,又会不自觉的质疑这种想法,她说:“这件事情要问我爹爹的。”本是两情相悦的好事,最后却仍需要父亲拍板,可见女人在争取“独立”的时候仍会有双大手钳制着自我的言行。尽管当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的格局,但对整体电影界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思想还是无法从创作者的脑海中彻底抹除,由此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就不能得到平等的诠释,她们只能活在父权社会的控制下,作为附属品和消费品而存在。
《劳工之爱情》上映后并没有创作者预计的会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现实的残酷使得人们已经对低级趣味、缺乏新意的故事失去了兴趣。这一现状也让明星公司不得不改变最初娱乐大众的制片方针,转而开始关注社会环境和民众疾苦,具有明确教化意义的“社会片”翻开了明星公司的新篇章,也令银幕里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新的特点。
二、改良教化中的女性形象
近现代中国历史极为复杂,社会大环境基本上处于不稳定时期。中国电影因其依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除却与世界电影发展的共性,自身具备的首要特点就是,不论是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中国电影受社会历史变革的影响极为突出。同时,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使得中国电影的民族性更加强烈。
以《孤儿救祖记》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片”正是处在社会动荡、思想解放时期,由一些受到五四启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创作的。他们不安于现状,并且试图寻求一条唤醒民众、救亡社会的道路,而这些怀着救国梦想的人们又或多或少的具有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因此,社会片成了这一时期的创作主流,且具有宣扬改良和维护伦理的双重功用。《孤儿救祖记》“既是一部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王汉伦、郑小秋、郑鹧鸪、王献斋主演的揭示‘遗产制’问题、有利‘家庭教育’的‘社会片’,又是第一部引起中国观众广泛兴趣并深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蕴的伦理作品。”[1]同时这部电影也诞生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位电影女明星——王汉伦。王汉伦饰演的余蔚如一角更是揭开了塑造女性形象的新篇章。剧中的余蔚如贤惠善良、忍辱负重,她的种种言行都被刻画成一个典型的受封建礼教影响的“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尽管电影在维护封建礼教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改良思想,认为人性的善恶与成长过程中的教育有关,呼吁兴办学校义务教学。但是这种批判意识仅存在于表面,并无深刻挖掘社会弊病的根源。

电影《劳工之爱情》剧照
《孤儿救祖记》大获成功后掀起了“社会片”创作的风潮,各大公司竞相模仿,一时间题材相似,模式相当的社会片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地位。为了加强电影的可看性和迎合大众的口味,更为了宣扬改良主义,剧中的女性都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在遭受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后,或是从改良中获益,或是牺牲自我使他人觉醒。我们不能排除这些社会片在赚取观众眼泪的同时,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但也不能忽视那些真心怀有责任感的创作者的一片苦心。注重电影教化功效的郑正秋以此为开端拍摄了许多以女性生活为题材的影片,抨击了封建社会对妇女命运的残害,表达了对她们的无限同情,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郑正秋的创作理念产生共鸣的洪深同样感到“电影比舞台剧更能深入民心,是更好的教育社会的工具。”
正当宣扬改良意识的社会片盛行之时,武侠神怪片以其独特的影像风格赢得了民众的普遍关注。明星公司于1928年拍摄的《火烧红莲寺》出现了“万人空巷,争先往观,收入一丰”的盛况。影片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既不同于娱乐滑稽片中女性的符号化,也不同于社会伦理片中女性的苦情模式,她们更多的是肩负了除暴安良责任的侠义之士,她们和男人一样具有了某种整治社会的权利,尽管这是建立在神怪想象基础之上的,却也给我们呈现出一类新的女性形象。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些侠女身上看到大众对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宽容度在放大。尽管后期效仿者众多,武侠神怪片的舆论影响却和“社会片”相差很大。“社会片”的题材内容符合官方提倡的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目的,从而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奠定了明星公司“领导者”的地位。武侠神怪片的舆论评价则褒贬不一,欣赏者认为此类电影包含了鲜明的草根意识和革命意识,赞扬了勇敢的国民精神;反对者则认为这种革命精神背后隐藏了对现行统治秩序的破坏,与政府试图营造的社会环境相抵触。于是《火烧红莲寺》遭到禁映,明星公司再次受挫。先不探究武侠神怪片的对错,单就塑造的女性形象这个角度来看,女侠形象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女性观众参与社会活动的愿望,是女性争取独立的表现。
总的来说,明星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作为电影市场发展的风向标为早期中国电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它的创作理念虽然受到社会改良思潮的影响,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明星公司创作人员的艺术构思仍然不能彻底摆脱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无论何种电影题材中的女性形象普遍遵循的还是传统伦理道德要求下的女性特质,个体独立的呼声始终无法推翻外界赋予的隐忍。她们依旧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被塑造成男性进步的垫脚石,而自身发展的权利并未得到平等重视。改良主义拯救不了中国,同样也阻挡不了“明星”市场竞争力下滑的趋势。到30年代中期,明星公司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启迪,开始和左翼文艺工作者合作,改变了原来的制片方针,人物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三、宣扬革命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左翼知识分子有组织的引导下,开始有规模的触及社会生活现状。创作者摒弃了原来儿女情长、神异古怪的题材选择,将镜头对准黑暗现实和贫苦民众,逐渐在电影界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电影第一次呈现出追寻时代精神与响应民心诉求的历史特征。
“九一八”、“一·二八”之后,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更加突出,中国电影业同样陷入迷茫期。明星影片公司从娱乐滑稽片到社会片再到武侠神怪片的拍摄路线再次令公司遭遇危机,而各大电影公司的激烈竞争渐渐动摇了“明星”领导者的地位,加之民众已经无法从这些电影中获取精神安慰,残酷的现实也已经容不得人们一再的麻痹自己。此时,左翼文艺工作者与“明星”的合作是多方作用下的结果。为了避免反动统治的迫害,当时电影中的革命色彩是隐藏在社会片的外衣下,通过剧中人物的生活经历反映出来的。女性作为社会片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在这个时期大方光彩,不仅自身形象突出,而且社会地位得到了明显的重视,与之前社会片中塑造的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动荡时期,电影镜头下的女性形象不外乎是依附达官贵人,或是历经生活困苦,或是勇敢投身革命事业。擅长女性题材的创作者往往以组合的形式让不同生活态度的女人们在剧中一同出现,通过进步女性和堕落女性的命运对比,为迷茫中的女人们指明道路。与社会伦理片中塑造女性形象的目的不同,左翼电影并没有将女性悲惨的命运作为吸引观众的噱头,而是让女性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尊重她们的独立和自由,呼吁女性们真正的参与到民族救亡中。左翼文艺工作者沈西苓创作的《女性的呐喊》就是此类影片的代表作之一。小资产阶级小姐叶莲虽然家庭被毁却仍然怀着自立自强的信念,即使是接二连三的打击也没有击垮她奋斗的决心。此时的决心来自影片中的另两个人,爱娜和少英是当时女性不同生活方式的缩影,前者安于享乐,后者投身革命,她们的生活轨迹为叶莲的人生指出了不同的道路。结尾少英那句“个人奋斗是会失败的,健实起来再奋斗”点明了电影宣扬革命的主旨。《姊妹花》虽然具有批评色彩却不是一部革命思想突出的影片。但是它的优秀之处在于剧中两姊妹重逢后姐姐大宝的一番话:“我自个儿心疼,我还替妹妹心疼,带好看的女儿出门,替好看的女儿打扮,是要靠的女儿升官发财。妹妹,你将来年纪大了的时候,那位大帅难保不再买几个女人,把你丢掉了,那个时候你吃了苦,那位靠着女儿发财的爸爸,他就不会来照顾你了。倒霉的是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呐!”大宝在父权社会中的声声控诉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剧作者写出的这番话让妇女隐忍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洗脱,她们敢于批判社会,批判不公的态度是社会进步,思想觉醒的象征。
尽管左翼思想指导下塑造的女性较之从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电影呈现出的类型化特点在某种程度还是局限了女性形象的塑造,使得革命精神洗礼中的女性略显程式化。
“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电影只是一个起步阶段,电影人只是从观看戏曲的角度去拍摄电影,用固定机位拍下故事即可,还谈不上对电影艺术的自觉研究、探索,商业利益驱动还没有转化为对艺术的渴望需求。”[2]到了 20、30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势头起伏不定,但总体来说还是取得了骄人的进步。这是因为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影响着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理念。娱乐追求和改良主义引导下的电影题材是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基础上的道德宣扬和社会改进。而左翼思潮引领着的电影创作更加呼吁民族崛起和民众反抗,因此阶级立场十分鲜明。明星公司电影创作理念的转变和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不同政治立场联系紧密,这即可视作主创人员的主动选择,也是观众需求下的合理附和。明星公司女性形象作为当时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代表,其演变过程恰是印证了这一特点。
[1]李道新.中国电影发展史[M].2005:75.
[2]周星.中国电影艺术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