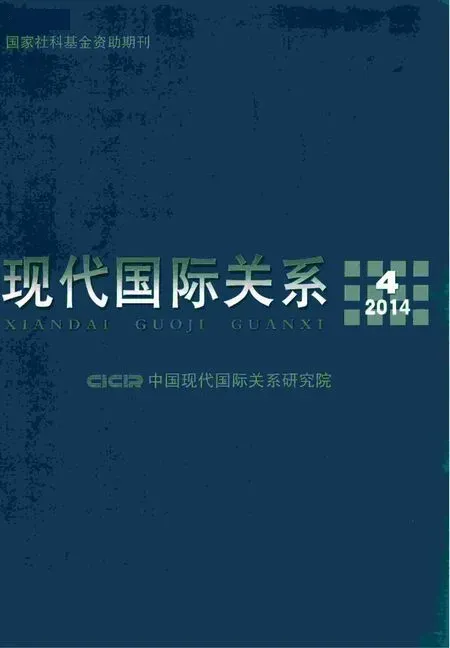宗藩体制:东亚传统国际安全体制析论
2014-12-09魏志江
魏志江
国际安全体制亦称国际安全体系,是由国际行为体按照一定的安全结构形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安全体系,即行为体通过一定的安全规范或机制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安全状态和安全结构。①参见刘鸣:《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的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张峰:《国际体系与中外关系研究》,中西书局,2012年,等等。东亚传统的国际安全体系,源于先秦时期以周天子为中心及周天子与诸侯、卿大夫之间层层册封和朝贡而形成的畿服制度,这种畿服制度在秦汉以后演变为规定中国与藩属国之间封贡关系的宗藩体制。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东亚的宗藩体制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②参见J.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68;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等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Morris Ro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中、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4、1995年;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等。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将宗藩体制视同于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天朝礼治体系等,并主要从朝贡贸易的视角进行探讨。本文则主要从宗藩体制作为东亚国际安全结构或体系的视角,剖析宗藩体制的渊源、构建条件、基本特征等,以就教于学界。
一、宗藩体制的渊源
关于宗藩体制的渊源,中外学术界一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宗藩体制起源于先秦时代的畿服制度,即西周时期周天子与诸侯、卿大夫等之间的册封和朝觐、聘问制度。周天子为天下之大宗,诸侯则为周天子之藩属,他们与周天子构成宗藩关系,并定期向周天子朝贡。③转引自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37页。西周时期,华夏与四夷交错而居,故五服亲疏的区别标准主要是与周天子宗族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远近,其中甸服、侯服、宾服属于华夏族,其与周天子宗族与政治关系亲近,故周天子以刑威或征伐手段要求其履行各自不同的朝贡义务,而要服、荒服由于与周天子宗族和政治关系疏远,故周天子不以刑威而以德化使其归附,即所谓:“先王耀德不观兵……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④《国语·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页。要服者为可以邀约羁縻之农耕民族,而荒服者多指游牧民族,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故而以德化感召之。其与周天子的关系除朝贡外,还承担拱卫周王室四裔即边境的安全义务,即所谓“天子守在四夷”。
西周的五服制到战国时代演变为九服制,即在五服制的基础上,由王畿向外依次五百里分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共九服。九服之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①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86页。《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7页。。五服制、九服制均是以周天子为中心,以宗族和政治关系的远近,构建成以周天子为中心、层层分封而形成同心圆式结构的等差体系。在此体系中,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华夏族居于天下之中,蛮夷、外藩则处于边缘,每一政治单位根据其与周王室的宗族和政治关系的远近承担定期向周天子朝贡等不同层级的义务。所谓朝贡,《周礼》谓:“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靓,东见曰遇。”②杨天宇撰:《周礼译注》,第277页。《礼记·礼运》,陈澔注《四书五经·礼记集说》,中国书店,1984年,第126页。《尚书》谓:“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③陈戍国撰:《尚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第36页。《尚书·益稷》,蔡沈注《四书五经·书经集传》,中国书店,1984年,第19页。孔颖达《五经正义》疏曰:“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④《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六,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朝贡关系构成宗藩体制的核心和运作基础。诚如梁启超先生所云:“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中央则以朝觐巡狩会同等制度以保主属的关系。”⑤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0页。然而,早在周穆王时期,由于戎狄等游牧民族叛服无常,“荒服者不至”。⑥《国语·周语上》,第7页。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春秋五霸的崛起,诸侯与周天子之间的朝贡关系也仅仅依靠春秋霸主和武力征伐而勉强维持。战国时代,在列国纷争格局下,“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朝贡关系失去存在的依据,而四夷被逐至周边地区,且与华夏长期对峙,外部的朝贡关系也就荡然无存”。⑦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9页。随着秦帝国的统一,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宗藩封贡体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但是,以畿服制大一统理念、华夷观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安全理念则延续下来,支撑着其后直至近代相当长时间里东亚地区的国际安全体制。这种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儒家天下一家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建构并维系了中国与周边各族、各国之间的同心圆结构。所谓大一统理念,起源于先秦的儒家理念,即《诗·北山》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⑧《诗·小雅》,朱熹注《四书五经·诗经集传》,中国书店,1984年,第102页。天下、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⑨《诗·大雅》,朱熹注《四书五经·诗经集传》,第148页。,皆为周天子之天下。可见,中国的皇帝作为天下的宗主,在政治上君临四海、一统华夷,从而实现了万邦来朝的大一统境界。正如《论语》所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⑩《论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中庸》亦云:“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①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86页。《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7页。由此形成家国同构的天下一家理念,即“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②杨天宇撰:《周礼译注》,第277页。《礼记·礼运》,陈澔注《四书五经·礼记集说》,中国书店,1984年,第126页。“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为帝臣”③陈戍国撰:《尚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第36页。《尚书·益稷》,蔡沈注《四书五经·书经集传》,中国书店,1984年,第19页。。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儒家的大一统理念成为中国帝王对外交往的基本政策理念,进而按照儒家礼治主义的规范建立起以中国帝王为中心、以藩属朝贡为基础的天下体系。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王朝支配下,中国帝王与周边四夷根据宗族关系、政治地位以及地理远近确定其尊卑、等级地位,分别承担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形成同心圆式的安全结构。
第二,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华夷观建构并维系了中国与周边各族、各国之间的安全秩序和安全关系。宗藩体制的维系与所谓华夷之辨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所谓华夷之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用夏变夷”,即在华夏族为中心的华夷观的基础上,以中原的华夏文化去改变、影响周边蛮夷戎狄的所谓野蛮文化;二是“夷夏之防”,尤其是在中原华夏族势力衰落时,防止周边野蛮民族对中原华夏文明的侵凌,即“蛮夷滑夏”,也就是华夏族需要防范的主要安全问题。西周末年,周王室为犬戎所灭,故时人甚为重视夷夏之防,以至于所谓“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①《春秋·僖公四年》,《四书五经·春秋公羊传》,中国书店,1984年,第156页。。齐国管仲改革,富国强兵,即以“尊王攘夷”为旗号,即尊崇周天子,抵御北部野蛮民族的入侵。孔子遂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②《论语·宪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9页。从此,“用夏变夷”和“夷夏之防”就成为宗藩体制下中国王朝的安全目标和安全政策。
在这里,夏夷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所谓“用夏变夷”,并非于夷狄之消极防范,而在于以华夏文明影响、改造蛮夷;或谓华夏与戎狄本同族同姓,因地域不同和文化差异形成不同族,华夷不同族之间的文化是可以转化的。华夷之辨,并非以种族和血缘关系为区别标准,而是以文化之高低为区分依据。春秋时代,孔子更以是否践行周礼为华夷之分野,这在后来成为华夷之辨的主要依据,即认同践行周礼即是华夏,反之则是夷狄。可见,华夷之间最初并无不可逾越之鸿沟。华夏以周礼规范国际秩序,以礼制德化、感召夷狄认同和接受周礼之政治和社会规范,即是用夏变夷。故唐朝时韩愈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至中国则中国之。”③韩愈:“原道”,《韩愈文集》,辽海出版社,2010年。所谓“进至中国”,即为“用夏变夷”。由于中国为华夏文化之核心,所谓“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④《春秋·定公十年》,《四书五经·春秋左氏传》,中国书店,1984年,第505页。故“用夏变夷”——以华夏文化改造周边夷狄成了华夷之辨在“夷夏之防”外的另一重要内涵。梁启超曾总结出:“封建制度最大之功用有二:一曰分化,二曰同化。天子不干涉侯国内政,各侯国在方百里或方数百里内充分行使其自治权……所谓同化者,谓将许多异质的低度文化,醇化于一高度文化之中,以形成大民族意识。”⑤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51页。“殷周之际,所谓华夏民族者,其势力不出雍岐河洛一带……及其末叶,而太行以南,大江以北尽为诸夏矣。我国所谓夷夏,并无确定界线,无数蛮夷,常陆续加入华夏范围内,以扩大民族之内容。”⑥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52页。
然而,华夷之辨不仅以文化之高低为依据,也以地理之远近为划分之标准。这始于春秋末期孔子的《春秋》,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⑦《春秋·成公十五年》,《四书五经·春秋公羊传》,第320页。,“即详周天子和鲁国而略诸夏,详诸夏而略夷狄,亲尊周天子与鲁国,次及诸夏而贬疏夷狄。随着夏夷限域由观念变为现实,建立在详略与亲疏原则之上的夏夷内外之分,遂成后人以地之内外划分夏夷的理论来源”⑧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202页。。此一理念也成为严“夷夏之防”、防止“蛮夷滑夏”的基本原则,从而奠定了东亚历史上同心圆式安全结构体系——以华夏中原王朝为天下之中心、夷狄位于周边四裔的宗藩关系且呈等差序列层层向外扩散——的理论基础。
二、宗藩体制的演进与东亚安全结构的形成
宗藩体制演进的过程,正是历史上东亚国际安全结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韩国学者徐荣洙教授在界定“朝贡关系”概念时曾指出:“一般来说,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是以政治臣属为前提,这一点见于历法或年号的采用,以象征和表示从属关系。随之是内政干涉及仪礼关系的建立,继而是宗主国向从属国收取方物的要求。甚至成为后者负担的一种经济关系。”⑨徐荣洙:“三国和南北朝交涉的性格”,载韩国《东洋学》,汉城,东洋学研究所编,1981年,第78页。这一关于“朝贡关系”的界定,恰恰揭示了东亚历史上宗藩体制作为安全结构的基本内涵。
首先,宗藩关系中的国际行为体实施了以册封和朝贡为基础的政治臣属行为。汉唐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始形成以中国帝王向周边国家册封,而周边国家通过向中国朝贡、称臣的臣属关系。汉初休养生息,改封建宗藩与郡县并存,故汉初之藩属,实为内藩(方国)和外藩(北方游牧民族和东夷南蛮以及西域、朝鲜、日本等)并存。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削藩,内藩、方国逐渐消失,故汉武帝时,汉朝之宗藩关系,实为汉朝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与外藩之关系。汉武帝北击匈奴、南征南越、东击朝鲜、荡平西南夷以后,开始建立起以汉朝为中心,周边的西域、匈奴、朝鲜、日本等藩属向汉王朝朝贡,并接受汉王朝册封为基础的朝贡关系。但是,西汉时期,宗藩体制的规范并不完善,周边藩属向汉朝朝贡也不需要以称臣、奉正朔等为前提,如汉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决定“称臣入朝事汉”①《匈奴传下》,《汉书》卷94,中华书局,1962年。,并遣其子入质汉朝。当时,汉宣帝采纳太子太傅萧望之的建议,待单于以殊礼,“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②《资治通鉴》卷27,宣帝甘露二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这显然不符合儒家“先京师而后诸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理念和宗藩体制的规范。显然,两汉时期,虽然周边藩属纷纷向汉朝朝贡,但是,并不具有宗藩体制的制度性规范,即并非朝贡方向中国王朝称臣的臣属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征服中原,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王朝被迫南迁。北魏和南朝宋、齐、梁、陈等政权,皆以华夏文化的正统自居,并继续维系以南北朝政权为中心的宗藩体制,但是,由于儒家的大一统王朝已经荡然无存,周边藩属如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几乎同时向南、北朝政权朝贡,并接受册封,形成东亚史上的多元朝贡关系。在“蛮夷滑夏”的严酷现实面前,儒家长期追求的“用夏变夷”和《春秋》大义所谓“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呈现巨大落差。这个时期,宗藩体制剩下的只有严“夷夏之防”的华夷之辨。值得注意的是,以臣属关系为基础的册封和朝贡制度正是这个时期通过高句丽向北魏的朝贡和日本向刘宋政权的朝贡关系而确立的。
其次,宗藩体制结构内的国家必须共建、共享安全利益,同时中国帝王应保障周边国家的安全即“天子守在四夷”。这是宗藩体制作为东亚国际安全结构全面确立的标志。以大一统为基础、以华夏文明为中心,共建、共享安全利益的宗藩体制得以全面确立,是从隋唐时期开始的。隋炀帝时期,为了打通丝绸之路,派裴矩重新经略西域,西域诸国以及东突厥启民可汗开始向隋朝朝贡称臣;隋朝为了西北安全,亦置四方馆负责管理朝贡事务。大唐帝国崛起后,声教远被,威加海内,“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蠹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庭”。③《新唐书》卷219,《北狄传赞》,中华书局,1975年。有学者统计,盛唐时期,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者多达“七十余番”。④转引自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36页。唐太宗作为天下华夷共主,被尊称为“天可汗”。至此,宗藩体制进一步完善,不仅封贡行为定期化,而且藩属国前来朝贡时亦经行专门的四夷朝贡道。⑤参见《地理志》,《新唐书》卷43,中华书局,1975年。此外,唐朝还在西南、西北诸番设置羁縻府州,实行“以夷制夷”政策,既保障唐朝边境安全,又维护、协调周边朝贡国的安全,实现安全利益的共建、共享。例如,同为大唐藩属国的高句丽侵扰新罗疆土,唐朝即以诏命形式加以调停,对拒不从命者,甚或以武力征伐,以维护藩属国的安全利益。不论是羁縻府州,还是海外藩属,唐朝均采用恩威并济的抚御方略,以维护周边安全,实现“天子守在四夷”的目标。因此,唐朝的宗藩体制安全结构是以唐朝中央为中心,以羁縻府州为外缘,以藩属国与唐朝中央的宗藩关系为框架的国际安全体制。对于虽向唐朝称臣但不接受唐朝正朔、历法的海外蛮夷诸国,唐朝仅以藩属国视之,双方关系只是单纯的朝贡关系,经济贸易的意义大于政治上臣属的意义,因而这些蛮夷国不应该纳入唐朝宗藩体制的范畴。
宋辽金元时期,东亚宗藩体制及其安全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宋朝丧失东亚国际安全秩序的主导权,建立在华夷大一统基础上、以中原汉族王朝为中心的宗藩体制发生重大转型,宋朝与辽金蒙古以及西域、大理、高丽、日本等政权成为对等的国家间关系。虽然宋初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是,随着辽、金、元先后入主中原乃至一统天下,以其为代表的所谓北族王朝取代了长期以来以汉唐宋为代表的汉族王朝在东亚的中心地位,并迫使高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而成为藩属国,尤其是澶渊之盟的签订,开启了东亚史上“所谓国与国对等的互相尊重的外交关系”①《姚从吾先生全集(二)辽金元史讲义——甲:辽朝史》,台北政中书局,1972年,第179页。。在历代正史中,《宋史》也开启了《外国传》编撰的先河。所以,宋辽金元时代,以中原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已经动摇,被视为“夷狄”的辽金元北族王朝取得了与素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宋王朝对等的国际地位。辽金元先后崛起为东亚国际秩序的战略中心,并与高丽、安南、西亚等周边国家建立宗藩体制,宗藩体制结构呈现出蛮夷-藩属国的所谓“华夷变态”的格局,并形成以辽金元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安全结构,以保障辽金元与周边藩属国共建、共享安全利益。
第三,藩属国自觉认同和接受以中国王朝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和礼治主义的价值观,强化了东亚国际安全体制存在的基础。明清时期,宗藩体制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文明形态重新得以恢复和确立,宗藩体制作为东亚国际安全体系的机能和理念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呈现出制度化特点。与一般的朝贡行为不同的是,明清时期宗藩体制下的朝贡关系必须以臣属为前提,贡期、贡道和朝贡品目等均由中国王朝礼部规定,不得随意变更,藩属国必须采用明、清王朝的年号、正朔等,中国的皇帝对藩属国国王继位等予以册封、赏赐,并对藩属国的朝贡物品加以回赐,双方之间呈现出典型的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和不平等地位。《明史》、《明会典》等史书中所载与明朝存在朝贡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总数达148个,②参见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68页。但是,明清时代,周边国家中与中国保留宗藩关系的臣属国只有朝鲜、安南和琉球三国。虽有大量朝贡国向明清王朝朝贡,亦接受明清皇帝的封号,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与中国王朝的关系并不具有政治臣属的性质,而仅仅限于朝贡贸易的经济往来。如暹罗、爪哇、苏门答腊等东南亚国家,与明王朝仅仅构成一般性朝贡关系,而非宗藩体制下的臣属关系。清朝中期编撰的《嘉庆会典》明确记载了朝贡国:“凡四夷朝贡之国者,曰朝鲜、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罗、曰苏禄、曰荷兰、曰缅甸、曰西洋。余国则通以互市。”但是,明清时代,随着欧洲势力东渐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宗藩体制下的朝贡国与平等的互市国逐渐区别开来。晚清时期,更进一步将朝贡国与邦交国并列,东亚的安全体系呈现出清朝的宗藩体制与互市国、邦交国并列的结构性特点。大清王朝所建构的宗藩体制与明王朝一样,除了朝鲜、安南和琉球三国以外,大多数藩属仅与清朝保持一般性的朝贡关系或者互市、邦交关系。因此,清朝以理藩院处理蒙古、新疆和西藏等藩部,以礼部掌管藩属国朝鲜、安南和琉球事务,而另设总理衙门负责办理与邦交国的外交事务。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清朝的大门,但是,宗藩体制的运行并未受到挑战和冲击,而是继续维持并主导东亚的国际安全格局,直到1880年代以后由于无法保障藩属琉球的安全方才开始丧失其主导地区安全秩序的功能。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被迫签署《马关条约》,清朝最后的藩属国朝鲜宣告独立,在历史上存续二千余年的东亚国际安全体系——以中外封贡关系为基础确立的宗藩体制终于土崩瓦解。
因此,在东亚宗藩体制下,“东亚国际关系因以朝贡关系为基础的统治关系而连在一起,在地域上,它形成了一个域内交易、情报、移民以及金银流动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中国起到了吸收和排除各种要素的中心作用,并与其周围诸国共有华夷观念,与它们构筑了朝贡-册封关系的实态。”③参见[日]滨下武志:《朝贡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尽管是不平等的国际安全秩序,但是在伦理上是以儒家的宗法制度和畿服体制为基础、以儒家的礼治主义为指导,该体系得以运作的政治基础是王道而非霸道。周边国家尤其是朝鲜、越南和琉球均自愿加入该体系,与中国的王朝形成宗藩关系,以宗藩体制保障国家的安全。
三、宗藩体制下东亚安全体制的特征
在东亚宗藩体制下,各国际行为体必须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以共同维护宗藩体制的运作。明清时代的宗藩关系,是东亚史上最为典型和规范的宗藩体制,其中明清王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无论从制度还是从实质看”,都“具备了最完整的制度和机能”。①[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5页。宗藩体制作为东亚传统国际安全体制的基本特征从中可见一斑。
一是以中国儒家礼治主义为规范的等级秩序。孔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②《左传·隐公十一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礼制作用是“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将礼制分为五种,即吉、凶、宾、军、嘉,凡都城、宫室、车旗、仪仗、器皿、坐位、用乐、揖让等均有等级之别。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③《论语·为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6页。荀子论及等级礼制时称:“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④《荀子集解·王制》,中华书局,1988年,第202页。他又说到:“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⑤《荀子集解·王霸》,第209页。中国王朝将儒家的礼治主义推广于东亚区域,就形成了宗藩体制架构下的君臣名分等级秩序,并以礼制和等级名分作为维系国际安全秩序的基本理念,以此保障东亚国际安全。“故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励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凌。此天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⑥陈澔注:《四书五经·礼记集说》,第336-337页。礼治主义的理念和原则虽然在国际关系上具有不平等性,但是客观上具有维护东亚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功能。因此,周边藩属国出于安全利益的考量,仍然愿意加入以礼治主义为原则的宗藩体制,并自觉接受儒家等级名分的规范。这表明,在宗藩体制作为国际安全结构的东亚地区,不论是中原汉族王朝,还是北族王朝的统治,中国始终在东亚国际安全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
二是“事大”与“字小”的安全结构。宗藩体制内的国际行为体相互共建、共享安全利益,并形成相互依赖的东亚国际安全结构。虽然中国是宗藩体制内的主导力量和东亚安全格局的战略中心,但是,中国安全利益的维护需要周边藩属国的协助、合作,进而形成安全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先秦时期的宗藩体制,即以藩属拱卫周王室,以达到“天子守在四夷”的安全目标;周天子以德化和征伐为手段,保护藩属国乃至夷狄之间的安全利益。诚如孟子所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混夷。为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⑦《孟子·梁惠王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79页。所谓“事大”与“字小”即大国通过册封、赏赐和出兵救助、平定藩属国内乱等手段,保障藩属国的安全利益,即“以小事大,保国之道。”如辽丽宗藩体制的维系主要是高丽出于国家安全之考量。⑧《高丽史》卷八《文宗世家(二)》,朝鲜古书刊行会本,1911年。朝鲜初期的性理学家郑道传从高丽时期国家安全的角度论证过高丽与中国构建宗藩体制的安全功能,指出:“金国暴兴,则排群意而上表称臣,自是世结欢盟,边境无虞……(迄元朝建立)世皇嘉之,至以公主归于王子,自是世结舅甥之好,使东方之民享百年生平之乐,亦可尚也。”⑨转引自陈尚胜:《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3页。因此,藩属国愿意向中国朝贡,并接受以华夏文明为主导的礼治主义规范,虽有“慕义”和“慕利”的双重目的,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与中国王朝建立宗藩关系,与宗主国共建、共享安全;藩属国通过宗藩关系对中国王朝朝贡称臣、秉承正朔以及入质、助征讨等手段,也有助于保障中国及其周边的安全,即实现“天子守在四夷”的安全目标。明宣宗曾经说过:“盖圣人以天下为家,中国犹堂宇,四夷则藩垣之外也……是故能安中国者,未有不能驭夷者也。驭夷之道,守备为上。《春秋》之法:‘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来则怀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穷追之,诚虑耗弊中国者大也……可为帝王驭夷之法。”⑩《明宣宗实录》卷38,宣德三年二月御制《帝训·驭夷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这反映了中国王朝利用宗藩体制的安全功能以实现“守中治边”的安全思想。
在东亚国际行为体的安全关系中,宗藩体制下的安全利益共建、共享以中朝(韩)关系最为典型。清朝作为宗主国,有保护藩属的义务,如清顺治六年(1649年)和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朝两次向朝鲜保证,如果宿敌日本来犯,清必当迅速出兵援救。①《通文馆志》卷九,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但朝鲜作为藩属国,亦须向清朝履行其出兵助征讨等义务。据台湾张存武先生统计,清朝征调朝鲜军助征讨,前后共有五次,前三次均为入关前征调鲜军助攻明朝和剿捕叛踞熊岛之瓦尔喀人;后两次则为顺治十一年(1654年)和十五年(1658年),先后调鲜军鸟枪手一二百名,前往松花江、黑龙江上游,协助清军征剿沙俄军队。②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7页。在663年唐罗联军与日本的白村江海战和1792-1798年明代朝鲜半岛的壬辰倭乱中,唐与新罗以及明与朝鲜均发挥宗藩体制的安全结构功能,以至于形成军事联盟,共同抵御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③参见《东夷传》,《新唐书》卷220,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外国传三·日本》,《明史》卷322,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因此,中国与藩属国构建的宗藩体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维持东亚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体系,这种体系所显示的安全理念就是“共享安全”,所遵循的安全关系是国际安全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所追求的安全目标是安全利益的“共优”和“共赢”。
三是以儒家的王道政治为目标,力行以德怀柔政策,辅之以武力威胁。其间,宗藩关系的维系及发展,主要依赖王道政治和作为藩属国对这一政治体系的认同或自觉接受。这是与西方近代殖民主义的根本区别,也体现了东亚史上儒家的王道政治与善邻、睦邻的和平主义价值取向。所谓王道政治,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④《孟子·公孙丑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02页。换句话说,宗藩体制运作的理念基础是孟子的“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藩属国接纳和参与这个体制及其中的等级规范、安全结构是主动自觉和心悦诚服的。荀子也对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进行了论述,其谓:“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 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文王以皜,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他故焉,以济义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⑤《荀子集解·王霸》,第202页。因此,于夷狄“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⑥《国语·周语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5页。朝鲜王朝时期,随着程朱理学的传播,朝鲜十分认同和接受儒家的王道政治,并进一步谨守“事大”之诚。如编撰《事大文轨》一书的卞季良主张削除《高丽史》中“诏”“朕”等尊称,以维护明朝天子于一尊的地位。他指出:“臣窃谓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之不可紊也,则事大之礼,固不可以不谨矣。大小之势,如白黑之不右以相混也,则事大之礼,亦不容于不谨矣。”⑦转引自陈尚胜:《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第284页。朝鲜王朝时期著名的实学家李珥即表示“臣闻下之事上,不以夷险而易其心,不以盛衰而废其礼……今夫以小事大,君臣之分已定,则不度时之难易,不摧势之厉害,务近其诚而已。”⑧转引自陈尚胜:《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第286页。不论中国王朝如何盛衰、兴亡,宗藩体制下的藩属国基本上都能遵循儒家的王道政治规范和君臣大义,对宗主国竭诚“事大”。也就是说,宗藩体制得以维系、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藩属国对儒家的王道政治与和平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和接受,而非宗主国的霸道政治或战争威胁。
综上所述,东亚历史上的宗藩体制起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畿服制度,儒家大一统的理念和华夷观构成了宗藩体制的理论基础,宗藩体制的结构演进过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呈等级差序不断向外扩散、形成东亚安全结构的过程。宗藩体制内的国际行为体之间,以王道政治和礼治主义为指导,建构起共建、共享东亚安全利益的安全秩序。因此,作为东亚历史上长期延续的国际安全体制,宗藩体制尽管在国际关系上具有不平等性,但在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以前一直是东亚区域国际秩序稳定与和平的保障。因此,其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功能及其践行的王道政治理念与善邻、睦邻的和平主义价值观,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