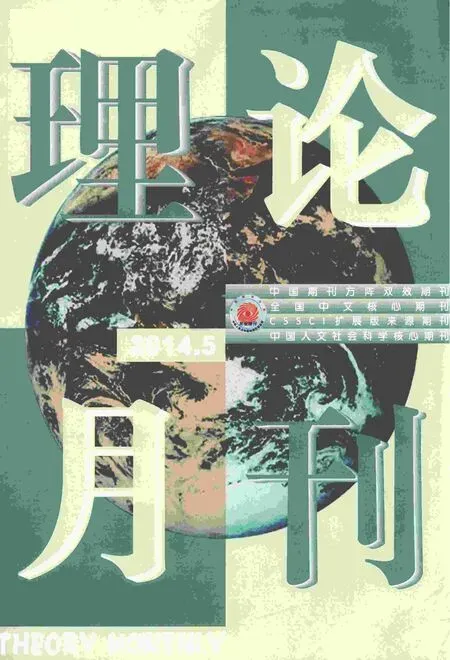当下中国社会民意的概念、特征与形态分析
2014-12-04张强
张 强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民意鼎盛的年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民意,即民众作为一个集合体的意见表达,从未像今天这般炙手可热和地位崇隆。民意,引领着政府进取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无可争辩地成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政府公共政策的制订、政治人物的雄韬伟略,无不以民意为依归。当然,在很多时候,民意也被异化为一种工具,被各种利益集团反复地利用,以达到各自的目的。无论如何,在当下中国社会,民意已经上升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志着权威主义时代无可挽回地式微,以及一个虽仍显粗砺却生机勃勃的大众时代的降临。
然而,在这个言必称民意的时代,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是,我们对于民意的认知事实上并不透彻,甚至完全不甚了了。我们对于这个经常脱口而出的词汇,所持有的理解常常是抽象而模糊的,是大而无当和缺乏内涵的。一定程度上,这种对于民意的肤浅体认,妨害公共理性的涵养,更阻碍国家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因此,透视和辨析民意及其表现出来的各种表征,显得必要又迫切。
一、民意的概念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系统而又富有创见地阐述了民意的概念。按照卢梭的分析,民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公意;一种是众意。公意是绝大部分或全体民众的共同意志;而众意则是个体的意志和团体的意志,二者可以合称为个别的意志。“人民的意志或主权的意志,这一意志无论对被看作是全体的国家而言,还是对被看作是全体的一部分的政府而言,都是公意。”[1]“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以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由此可见,卢梭对公意的推崇。
而另一方面,卢梭则对众意持有某种程度上的负面解读:“个别意志由于它的本性就总是倾向于偏私,而公意则总是偏向于平等。”[4]“公意与众意经常有很大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仍然是公意。”[5]
卢梭对于民意的概念性界定,最值得珍视的一点是,将民意细分为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派的意见,二者或有冲突,但都在民意概念的统摄之下。这对于我们系统而健全地理解民意,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国内一些学者对于民意概念的界定,往往是从卢梭“公意”的角度去阐发,而忽视了从卢梭“众意”的角度去观照。
比如:程世寿:“民意是人民意识、精神、愿望和意志的总和,作为社会真理的坐标,是判定社会问题真理性的尺度。”[6]吴顺长:“民意不单单是人民范畴中某个群体或某个个体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愿望,而是人民这个集合体的意向趋势,它所反映的总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7]
分析国内部分学者对于民意的定义可以看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卢梭民意概念中的一个方面,即公意,当作了民意内涵的全部。而且在他们的定义中,也假定民意天然地具有正义性和合法性,是毋庸置疑和无可辩驳的,是铁板一块和集体行动的。但事实上,这样的概念恐怕与民意的全部复杂性并不吻合,其间甚至有不可小觑的抵牾。
笔者倾向于认为,应该从一个整全性的角度,充分体察民意本身的全部复杂性与难以参透性,既要看到民意的主流,也要看到民意的各种支流,二者的有机结合才算是民意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尝试给民意下这样的定义:民意即公民基于自身的观点、立场和态度所表达的社会意见与社会愿望的总和,它是个体意见和群体意见、显性意见与隐形意见、主流意见与非主流意见,正义意见与非正义意见的激荡、杂糅与融汇。这样一种概念性定义的开创性在于:其一,以“公民”作为民意表达主体,强调其权利性与异质性,而不再以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人民”作为想当然的表达主体;其二,将民意视为一种发散型的网状结构,强调其层次性、多元性与动态性,而不再将民意视为一种单箭头的、先验的线性结构。笔者以为,这样一种概念更加符合现实与民意真相。
必须予以澄清的是,民意并不代表真理本身,它并具备真理性或者神性,不排除民意在某些情境下带有瑕疵甚至谬误。民意中的少数派,无论怎样都值得予以恰当地尊重,因为它们也是民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越是少数派的意见,越需要我们另眼相待。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文明社会的责任。
二、当下中国社会民意的时代特征
当下的中国正值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狂飙突进的同时,也充满诸多矛盾与纠结。反映在民意上,就是一边是激情澎湃,一边是哀怨丛生。时而悲观,时而乐观;时而坚强,时而脆弱;时而迷惘,时而清晰,常常呈现出社会转型期基于特殊国情的一些明显的时代特征:
1.“混沌—迷惑”性
事实上,尽管在我们的公共舆论中充斥着“民意”这样的字眼,但恐怕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民意是什么、民意的真正诉求又是什么。就像人民这一概念一样,我们在使用民意这一概念的时候,也往往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它,缺乏对其的精确界定与清晰表达。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民意都是复杂多样的,很多时候也是没有方向感的,尤其是在中国当下社会,当整个国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民意自然不可能是鲜明清晰和完全有迹可循的。在很多情况下,它是暧昧的、混沌的,需要仔细摸索和辨析的。
举例来说,以雅安地震后,身陷尴尬的中国红十字会为例:一面是名誉扫地、臭名昭著、遭世人唾弃;而另外一面则是收到5.66亿元捐赠款物,占所有捐款的53%以上。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合理却又不合理的结论:中国红十字会的恶浊形象似乎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它的信任度。由此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中国红十字会真的已经名誉扫地、被善良的人们弃之如敝屣了吗?
对此,青年时评家曹林先生在一篇评论中写道:“网络上一边倒地对红十字会喊‘滚’和‘捐你妹’,现实中的人们并不一定就都不信任红会了;网络上一边倒地反对水价上涨,其实现实中很多人是能理性地意识到资源性产品涨价的必要性;网络上一边倒地支持政府各种限购,现实中投票却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结果;网络上一边倒地反对政府取消长假,换个平台进行的民调结果却完全不同;网络上提起拆迁都是一片受害者的骂声,现实中很多人却寄望于拆迁改变自己的居住环境;网络上提起“高房价”好像人人都咬牙切齿,现实中很多有房者都期待房价上涨房产增值……”。[8]
显然,民意是混沌的,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虚假性和难以捉摸性。背后则反映出人们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缺乏坚定而自洽的立场,处于犹疑彷徨的状态,甚至人们自身也不知道该采取何种立场才是正确的,体现出一定的随意性与盲目性,如此这般,都导致了民意的混沌。
2.“多元—层次”性
民意绝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和通往一个方向,事实上民意是一个复杂多元、多方向、立体而丰满的网状结构,它远远不是一条“单向度的直线”的意象所能概括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不断涌现。而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民意的多元化。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取向,展开或温和或激烈的辩论,以期压倒对方的立场与利益,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与价值期许。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随着政治文明的演化以及媒体技术的空前发达,为不同民意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除了一些特定的敏感话题,人们可以借助各种平台,比较充分而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意见和观点,形成了一个纷繁芜杂而又生机勃勃的多元民意场。
此外,民意也是分层的。大体来讲,民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民意、群体民意与整体民意。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抑压,被抹杀。”[9]世易时移,现在不同以往,现在的公民个体勇于、敢于和善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构成一个个微弱却尊贵的个体民意,成为民意的最广泛的基础性要素。
群体民意也在成长,随着政治对社会的松绑,众多民间自治组织获得了快速发育成熟的机会。各种行业协会、公民组织、公益组织、社团组织纷纷建立和发展,它们的意见成为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体民意,只是一种理想性的民意。事实上,很难出现笼罩性的全体性民意,总有一部分人持不同意见,这是人性以及社会的复杂性决定的。著名学者刘建明认为,“把70%视为民意量度的临界点,反映了人口比例的绝对优势,无疑具有民意的品位。”[10]这似乎意味着,只要在统计学意义上超过70%的民众认同某一种观点或意见,就可以称之为整体民意。
3.“外强—内脆”性
当代中国,民意的确是一种耀眼的价值。任何人都无法忽视民意的存在及其强大的影响力。在官方的表达口径中,民意甚至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成为政治正当性的重要资源。江泽民曾经说过,“及时、准确地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多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安定人心的工作,努力为党和政府排忧解难。”[11]胡锦涛也曾经说过,“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切实转变作风,多做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的实事,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12]习近平同志更是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民意的重要性。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着重提到,“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13]
在网络民意场上,我们更是可以轻易便能体会到民意的喧嚣及其强悍的影响力。多少贪官是被民意送上法庭的,多少冤案是在民意的压力下沉冤昭雪的,多少善政是在民意的压力下慢慢出台的,历历在目,数不胜数。
然而,在一派繁荣而强大的民意表象之下,我们也不难窥见和感受民意的脆弱与无力。民意不是万能的,民意不能改变的事情要远远多于它能改变的事情,即使它改变的事情,也多是个案,远远不能改变整体形势与格局。民意把一个贪官送入了囚笼,但还有无数的贪官前腐后继;民意让一个冤案大白于天下,但还有很多的类似案例隐藏在铁幕背后;民意让一个善政浮现于公共领域,但还有更多的恶政挥之不去;民意或许能改变个案,但不能改变全部;民意或有助于一时,但无力裨益于长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民意千呼万唤,但终究无法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民意望穿秋水,但一次次折戟沉沙;废黜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民意已经过河,官方却还在摸石头。凡此种种,无不证明民意的脆弱性。
4.“撕裂—对抗”性
基于不同立场与利益的民意,自然会产生辩论和争执。在某些尖锐问题上,甚至会产生民意的撕裂,以至于激化成意见和行为的对抗。
当代中国社会,呈现出诸多方面的分裂:阶层分裂、城乡分裂、贫富分裂、精英与大众的分裂等等。这些形式的分裂,都会反映到民意的分殊与对抗上面。
比如关于“异地高考”的问题,就撕裂为两种截然相反又激烈冲突的民意。支持异地高考的民意认为,异地高考是一项不可褫夺的权利,它涉及教育公平与对外地人口的基本尊重,以宪法和教育法的名义,异地高考无论在现实中会遭遇多少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
但反对异地高考的民意则认为,如果彻底放开异地高考,北上广等教育发达的城市将不堪承受,汹涌而来的外地人口将彻底扰乱这些地区的教育秩序,分割当地原住民的本也不足的教育资源,此外异地高考还极有可能导致浩浩荡荡的高考移民,负面后果巨大,在目前状况下不具备实行的条件。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意见严重对立。在具有标本意义的“占海特事件”中,甚至引发街头对抗。2012年10月25日,支持异地高考的标志性人物占海特及其支持者在上海大沽路100号上海教委,与意见对立组织“守护者联盟”发生冲突,最终以占海特父亲被警方拘留而收场。由此可见,双方意见分歧之难以调和。
民意的撕裂和对抗首先造成的是一个劣质的舆论场和民意场,在这里人们基于立场而区分敌我,沉溺于单方面意见的表达与自我认同之中,并且倾向于强化既有的意见和观点,随时准备去征服别人,最终陷入难以沟通的偏执之中。这样的民意场中缺乏共识达成的条件和氛围,缺乏温和、理性和建设性的讨论空间,民意的撕裂和对抗,造成并加剧社会的撕裂和对抗,对转型中国而言,这是非常遗憾的一幕。
三、当下中国社会民意的基本形态
1.显性民意与隐性民意的统一
显性民意,即公开的民意,是公民借助各种平台,公开表达出来的观点和意见。现阶段,公民表达意见的平台和管道有很多,比如新闻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代议制平台(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信访体制、民间自治组织、民意调查机构等等。
民意通过上述管道而得到彰显,呈现在官方以及全体人民面前,成为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依据,也成为不同民意辩论、筛选和整合的前提。现代中国社会,早已不是一个万马齐喑的社会,官方应该充分鼓励民意的表达,畅通民意表达的渠道,及时呼应民意的吁求,只有如此才能赢得民意的信任。
当然,在中国还存在一种隐性民意形态。隐性民意的形成和存在,或者是因为公民缺乏表达的意愿和能力,或者是因为缺乏表达的渠道和平台,又或者是因为民意表达的成本和风险太高,以至于不得不三缄其口、静观其变。隐性民意虽然没有显性化为公共舆论,但它犹如暗潮汹涌,更值得当政者关切与回应。
事实上,真实而完整的民意,是显性民意和隐性民意的结合体,前者作为一种高调的民意,需要被看见和聆听,而后者虽然沉潜低调,但却具有更加沉郁顿挫的力量,更应被发现和体察,以有助于公共政策的全面性和深入性。
2.强势民意与弱势民意的统一
中国社会存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因而也就存在强势民意和弱势民意。一般而言,强势群体具备更高的智识水准,掌握更多的表达与传播平台,拥有更强大的左右公共政策的能力,遂成为强势民意。反之,则成为弱势民意。
强势或者弱势民意的形成,与历史、传统、财富、权力、地位、地缘、真理、良知、教育水平、公民素养等因素息息相关,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产物。而且极具相对性和更迭性,在合适的条件和土壤下,强势民意和弱势民意会在不经意间迅速完成转换。
一般而言,强势民意如下:城市民意、富人民意、原住民民意、网络民意、主流民意、正义民意、集团性民意等等。相对的,则属于弱势民意:农村民意、穷人民意、外来人口民意、线下民意、非主流民意、非正义民意、分散性民意等等。
强势民意与弱势民意之间的转换是微妙而迅捷的,以前段时间农夫山泉与京华时报的争执为例,以前者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为分水岭,民意舆情的转换就相当值得玩味:在这起已被定名为“华山之争”的论战中,2013年5月6日下午3时被证明是个民意反戈的节点,在那之前,京华时报总体占据上风,虽然诸多媒体同行都不再拥有持续追问的热情,但至少还算是静观其变;但在农夫山泉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舆情明显发生偏转,更多为农夫山泉鸣不平的声音冒了出来,一些媒体同行甚至已经开始拆台,拆京华时报的台。在微博上,在民间,甚至响彻着阴谋论的声音,农夫山泉被当成了遭到神秘权力打压的无辜者,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同情。一些微博大V,像周立波甚至公开表示支持农夫山泉,周有3000多万粉丝,他的号召力对舆情的影响不可小觑。
3.正义民意与非正义民意的统一
民意并不代表正义本身。人群的复杂性、利益的多元性,决定了所谓的整全性民意永远都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民意即残缺。因此,民意事实上不可能代表正义本身,民意也有可能是非正义的,事实上,常常存在这样的可能。
某种意义上,民意不代表正义这样的判断,简直是一个常识。在中日钓鱼岛风波引发的一些城市的“打砸抢”行为,难道没有民意怂恿的痕迹?在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案中,人们对这位未成年少年丧失分寸的口诛笔伐,难道不是民意高烧的结果?如麦迪逊所说,“在雅典的6000人公民大会上,即使每个人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也只可能是一群暴徒的大会。”[14]
我们要充分警惕民意的负外部性,尤其在极端环境下,民意滑向民粹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中亦有值得我们省思的论断。他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15]又说,“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经暂时搁置。”[16]
我们当然不能抹煞民意所代表的正义含量,它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以及所有合法性的基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体认民意非正义的一面,使我们既尊敬民意又不迷信民意,依靠民意又独立于民意,这样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才能永远保持审慎、谦卑、克制与理性。
4.主流民意与非主流民意的统一
主流与非主流仍然是相对的。不妨试着下一个定义:主流民意,就是那种相对多数的、相对正统的、相对稳定的民意。主流民意,与绝对无关,只与相对有关。它甚至都不意味正义和正确本身,它也只是民意之一种。
在缺乏科学有效的民意评价工具与体制之前,所谓“主流民意”经常陷入自说自话的局面。问题在于主流民意该怎么测算,谁有权力做出判断?主流的就一定是对的吗?非主流的就一定是错的吗?都未必。
正如南方周末一篇文章所写的那样,“科学的民意调查只要一天得不到充分发展,主流民意就仍是一个 ‘隐身人’,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发不出自己的声音。”[17]重要的也许不是谁赢得了主流民意,而是任何民意都值得倾听,不要以为非主流民意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必须要铲除而后快的。
四、结语
民意是一个迷人的字眼。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见证民意作为一种价值在当今的崇高地位。从权力神圣到民意神圣,是一个转型社会努力掘进的结果,是无数仁人志士付出勇气和行动的结果。
然而,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民意崇高,是它所代表的价值的崇高;民意神圣,是它所代表的精神的神圣。民意本身则是复杂而难以琢磨的,当我们从现实层面论及以及使用民意概念为我们服务时,我们得秉持十二分的谦卑和审慎,去对民意进行抽丝剥茧地理解和诠释。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意,既有一种普世性的民意特征,也有着基于特殊国情的特殊民意特征。一方面,转型期民意有着深刻的积极作用,但也有着完全不可小视的负面进攻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善如流,支持和皈依正面民意,阻止、引导和改变负面民意,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1][2][3][4][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79,21,32,3.
[6]程世寿.公共舆论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14.
[7]吴顺长.民意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7.
[8]曹林.别在被放大的网络舆情中误读中国[N].中国青年报,2013-05-03(A2).
[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259.
[10]刘建明.穿越舆论隧道:社会力学的若干定律[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171.
[11]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01-03-03.
[12]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N].新华社,2010-09-29.
[13]习近平.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新华社,2012-11-19.
[14]王怡.网络民意与失控的陪审团[J].百姓,2004,(02):60.
[15][1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36,48.
[17]李梁.主流民意是一个隐身人[N].南方周末,2009-0514(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