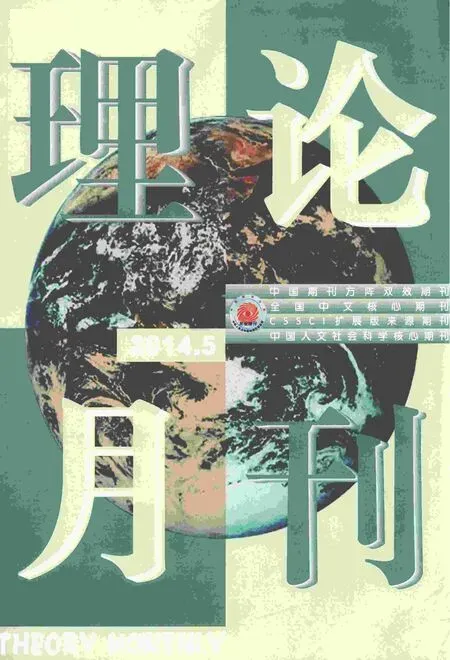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及其限度*
2014-12-04徐步华
徐步华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对象。然而“毫无疑问,主权国家并不是世界政治中惟一的重要行为体或角色”。[1](P212)除了主权国家之外,世界政治的舞台上还活跃着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是国际社会中彼此相对的两类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具有非国家性、独立性、跨国性等特征。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说,非国家行为体可以界定为国家之外的、所有独立进行跨国运作的国际行为体。一般来说,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跨国行为体。
目前学术界在非国家行为体的界定和分类方面已达成基本的共识,但在评价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却存在天壤之别。实际上,对非国家行为体的过分贬抑或者过度褒扬都会令人误入歧途。现有研究的一个关键缺陷是,对非国家行为体影响的限度问题鲜有论述。本文在梳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理想主义等国际关系流派有关非国家行为体之影响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非国家行为体对世界政治影响的制约因素和限度。
一、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褒贬不一的评价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中心,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的国家,除了他国的权力制约,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现实主义对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关系结果的最终仲裁者是权力,而结果一般会对最有权力的或最有效运用权力的国家有利。现实主义者还认为,在当代世界中,国家是拥有最多权力的组织。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它们是否能成功地改变最强势的国家的政策和偏好。[2]就政府间国际组织而言,它们是由国家缔造的,其规则是由主权国家制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依赖于国家的资助,而且只有得到大国的支持才会取得成功。政府间国际组织反映了现有的权力平衡和强国的利益,与其说它们是发挥着独立影响的独立的行为体,还不如说它们是国家权力斗争的工具。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现实主义者认为,它们要么是明显地掩饰特定国家利益的幌子,要么就是寻求削弱民族团结和国家体系稳定的潜在的革命者。跨国公司也并未取代国家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实质上是美国等大国权力和外交政策的工具。总之,现实主义坚持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尽管它并不否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但认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相对于国家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合作,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建立世界性组织(或世界政府)来实施集体安全,达到规范国家的行为、制止侵略和实现和平的目标。与理想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新自由主义,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尽管国家仍然理所当然地是强有力的行为体,但是,它们现在必须与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分享国际政治的舞台,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政治体系形成了冲击和挑战。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出现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全球化促使国际关系的多中心化,国家不再是国际关系唯一的行为体,国家过去拥有的许多权威逐步流入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手中。因而,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尽管国家仍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为体,且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重要性,“而广泛的非国家行为体则拥有着显著的、建构全球政治和经济的能力”。[3](P1)
建构主义批判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性原则,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机制、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影响正是通过对规范结构的影响或者说发挥其“软实力”来实现的。玛莎·费丽莫指出,权力并不像现实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总是在世界中起作用。像国际组织和市民社会组织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能够通过操纵观念、规范和价值而不是枪炮和金钱而变得强大。[4]凯瑟琳·辛金克指出,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规范结构或“观念分配”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的议题领域有着相当多的变化。一些地区的一些议题领域的确是以霸权规范结构为特征的,而另一些则处于规范激烈竞争的状态。这种随议题领域和地区的变化表明全球权力结构本身不足以精确地为全球的稳定和变革提供全面的解释,并且只有通过增加对规范结构的理解,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描绘出全球体系的结构。由于世界政治结构是特定的权力结构和目的结构的熔合体,也因为非国家行为体对新规范和话语的创造至关重要,因此,她认为非国家行为体通过改变全球治理的规范结构而促进了 “世界政治的重构”。[5](P302)尽管大多数跨国非政府行为体的力量相对薄弱,它们影响国际政治的能力经常是“基于运用信息、劝说和道德压力来促使国际机构和政府发生变革”。[6](P11)然而,在围绕特定的规范性诉求发起的运动中,关键的个人、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等非国家行为体扮演着“跨国道德事业家”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卡尔·马克思和戴维·米特兰尼到当代的理想主义者是对现存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更为激进的批评者,他们认为未来国家将会消失,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与互惠的全球市民社会。[7](P11)例如,全球化的拥护者认为跨国民间行为体起着建立跨国网络、促进共识、甚至促进国际团结的作用。主张全球治理的学者经常把非政府组织描述为正在兴起的挑战国家权威和国际资本权力的全球市民社会之先锋,一些学者甚至把非国家行为体视为“自下而上”抵抗全球化和国际机构的发起者,从而挑战了国家的权威和实践,塑造了全球治理的界限与特征。[6](P4)在他们看来,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的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8](P70)“由于行为体、机构、规范和观念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不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适当分析层次”,现在的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由国家和众多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所组成的 “跨国市民社会”。[9](P238)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活动“在现有的国家社会所提供的框架内,现在正组成一个国际社会,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全球社会”。[7](P4)质言之,一元等级制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已经演变为多元网络状的、以“复合多边主义”[10](P5)或者“多元化的全球治理”[11](P357)为特征的世界格局。
客观而言,关于非国家行为体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问题,一方面,我们既不能像一些现实主义者那样完全否认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数量和影响两方面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这是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渗透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对当代世界政治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首先,非国家行为体所掌握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对于民族国家在应付各种问题时可能很重要”;其次,非国家行为体“对政治话语、日程设置、法律制定和决策的影响力,以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起的公开作用”;最后,非国家行为体“本身就是国际体系中的政治、政策和制度安排之一部分”。[12](P3)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政治观察和研究都离不开对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考察,如果再固执地坚持绝对的国家中心主义论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像激进的理想主义者那样,过分拔高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影响力,甚至产生民族国家即将被取代或走向消亡的幻觉,这也是不得要领的。事实上,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是有限度的。
二、非国家行为体影响的限度
毋庸置疑,在全球化的作用下,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在日益增强,但我们也应看到非国家行为体影响的限度,这是因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和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首先,国际社会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制约。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衰是与“国际社会的扩展”相伴随的,且“依赖于国际体系本身的性质”,[10](P230)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参与是周期性的,往往是当国际社会处于衰落时期或者大国之间发生冲突与战争的时期,非国家行为体的生存都会难以为继,而当国际社会处于和平与稳定发展的时期以及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得到世界各国遵守的时候,非国家行为体就可能会迅速增长并扩大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时期都是非国家行为体蓬勃发展的时期。从历史上看,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衰是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和衰落相伴随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只有在一个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对国际互动的规则和国家单元的合法性拥有基本共识的国际体系中才能发展兴旺起来。
其次,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制约。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国家的性质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和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建立在有限政府原则之上的自由民主国家,从法律上对国家内部以及跨国交流中的政府和民间关系加以区分,这使得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公开地进行跨界运作。相反,挑战国际社会之主要假定的革命国家把包含和传播国际社会基本规则和价值观的民间组织当作非法的,然而这些国家自身支持的团体则旨在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集权国家否认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区分,排除了市民社会存在的可能;威权国家只是在严格的条件下允许不受其控制的民间行为体渗入其领土。[7](P4)另一方面,正如凯格利和韦特克普夫所指出的,由于国家几乎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和保留着塑造全球和国家福祉的巨大能量,国家“依然更多地塑造着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而不是相反”。[13](P196)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本质是“有时冲突,但经常依存”,[3](P6)然而这种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显然非国家行为体更多地依赖于国家,而不是相反。这种不对称的权力也表明了,相对于国家而言,非国家行为体的脆弱性及其影响的有限性。可见,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状态中的互补关系;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受到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行为体的控制和制约。
复次,全球化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全球化推动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14](P24)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至少在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了转变。民主国家已经从冷战后试图对相当大份额的国民经济加以控制的立场上退却下来,并且大大减少了跨国贸易、投资、生产和服务供给的障碍。通讯革命改变了非国家行为体发展和维持跨国联系的能力,并且大大降低了相应的成本。教育水平的提升、国际旅行的增加、全球媒体的兴起,大大拓宽了精英及其反对者的视野,极大地拓展了非国家行为体运作的空间。[7](P1)可以说,全球化的开放程度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的力量和多样化不断增加相一致。[15](P242)然而,全球化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及其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频繁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促使人们掀起一场限制相互依存的发展甚至扭转经济全球化的运动”,[14](P1)这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非国家行为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有利环境。
再次,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的掣肘。非国家行为体彼此之间并且与国家行为体之间发生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进而共同作用于当代世界政治。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主要的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运动不仅对国家而且也对跨国公司和政府间组织的合法性和许多政策发起了挑战。例如,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对跨国公司和政府国际组织 (尤其是全球三大经济组织)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发起挑战,力图构建一种更加公平、合理和民主的全球化,以实现全球正义和民主。而另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也会因争夺资金和支持而相互倾轧。因而,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影响的估量也要放在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和折冲的背景中进行衡量。
最后,非国家行为体自身存在的大量问题也制约了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主要有: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因为与国家权力相比,跨国公司掌控的是一种无责任的权力,它们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却无须承担社会责任,例如对环境污染、对当地社会和劳工的责任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民主赤字问题,联合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机构,对全世界普通大众的生活行使着巨大的权力,而它们却不对这些大众负责或者缺乏公民声音的渠道;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合法性问题和独立性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不过是发达国家对外渗透、干预和扩张的工具,而且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并非都是从事追求进步的社会变革,其中有一些则是非世俗的、非进步的,甚至是暴力和恐怖主义倾向的。这些方面不仅会影响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会使非国家行为体之“跨国道德事业家”形象大打折扣。
三、结语
总之,国际关系学者对非国家行为体的评价褒贬不一。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和激进主义者大多持肯定或褒扬的立场,而现实主义者则持贬抑或否定的态度。然而,现在只有最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才会否认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至少在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平衡所发生的转变。[7]虽然主权国家仍然在国际政治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许多问题领域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现在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任何理解和诠释都必须把跨国运作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考虑进来。
概言之,非国家行为体对世界政治的影响绝不能被忽视,但也不应当被夸大。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作用可能既不像一些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也不像一些全球治理和全球市民社会学者所认为的未来世界就是非国家行为体独当一面的“无政府的治理”。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它们的活动深深地受制于国际社会、国家和全球化的制约和影响,而且由于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难以撼动,也由于国际社会和全球化的发展都不是不可逆的进程,因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不可以高估,必须在国际社会、全球化和国家的背景中准确地理解和定位之。
[1]〔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研究[M].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S.Krasner.Power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C]//T.Risse-Kappen.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257-279.
[3]Richard A.Higgott, Geoffrey R.D.Underhill and Andreas Bieler.Introduction:Globalisation and Non-State Actors[C]//Richard A.Higgott, Geoffrey R.D.Underhill and Andreas Bieler.Non-State Actors and Authority in the Global System.London: Routledge,2000.
[4]〔美〕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M].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5]Kathryn Sikkink.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he Limits and Asymmetries of Soft Power[C]//Sanjeev Khagram,James V.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
[6]Sanjeev Khagram, James V.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From Santiago to Seattle:Transnational Advocacy Group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C]//Sanjeev Khagram,James V.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
[7]Daphné Josselin and William Wallace.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A Framework[C]//Daphné Josselin and William Wallace.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Houndm ills: Palgrave, 2001.
[8]〔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9]〔美〕玛格丽特·E·凯克和凯瑟琳·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M].韩召颖,孙英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Robert O'Brien, Anne M.Goetz, Jan Aart Scholte and Marc Williams.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Multilateral Econom ic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1]L.Gordenker and T.G.Weiss.Pluralising Global Governance: Analytical Approaches and Dimensions[J].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5, 16(3).
[12]Bob Reinalda, Bas Arts and Math Noortmann.Non-stat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o They Matter? [C]//Bas Arts, Math Noortmann and Bob Reinalda.Non-stat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13]C.W.Kegley Jr.and E.R.Wittkopf.World Politics:Trend and transformation[M].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95.
[14]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导言[A].约瑟夫·奈和约翰·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C].王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5]戴维·布朗等.全球化、非政府组织与多部门关系[A].约瑟夫·奈和约翰·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C].王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