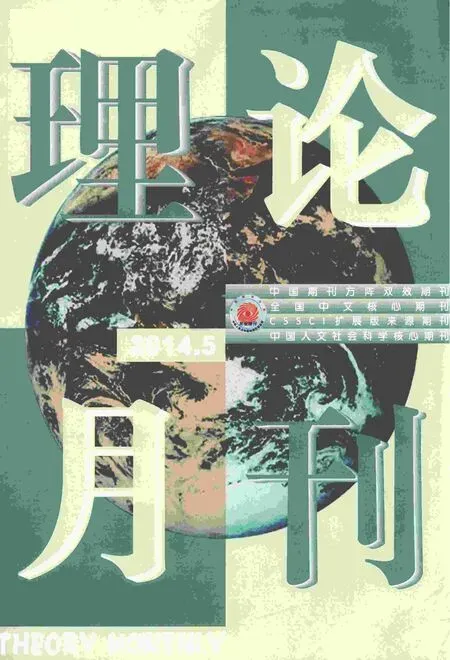社会历史之谜的解答*——《〈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交往行为理论》之比较
2014-12-04赵秀娥
赵秀娥
(广西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历史发展之谜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谜题。千百年来,许多智者和哲人一直试图破译和解答这个谜题,然而由于认知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所限,往往从这个迷误中走出又陷入另一个困境。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对历史发展之谜作出了科学的解答,解开了历史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历史必然性与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关系问题),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创立。马恩身前逝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质疑和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最直接地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对话并试图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当推哈贝马斯。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交往行为理论》分析历史的不同视角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历史,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向,探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历史的一种哲学——历史学解释。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上升阶段,资本家的剥削赤裸、残酷,工人及社会底层人群生活窘迫、疾苦。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就发现研究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是了解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的必由之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1](p591)因此他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然而,19世纪40年代末欧洲的革命形势迫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这一研究,被迫侨居伦敦。1850年,马克思开始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和摘录经济学资料,还系统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在1851到1853年间写下了24本经济学摘录笔记《伦敦笔记》,并在1853年决定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经过15年的研究和探索,马克思在1858年5月完成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创立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1859年2月为这篇巨著作序,在序言中第一次完整系统的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称这是被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证明和揭示的,是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结果”。恩格斯认为这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后来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述,他说:“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2](p509)
哈贝马斯对历史所做的是一种哲学——社会学的分析。哈贝马斯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和马克思有巨大的不同。历经20世纪初的严重经济危机、30年代的法西斯暴政和两次世界大战,破坏掉启蒙原则,践踏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物化生存是哈贝马斯随处时代的人们面临的生存困惑。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已经过时了,留下的只有马克思的批判的精神。哈贝马斯从社会学的角度,主张重建交往理性。他认为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活世界”应重新整合其结构,才能克服现代性危机,使“西方民主制度”重新获得稳固的基础。应让理性“以主体间性为中心”代替“以主体为中心”,只有建筑在三大有效性要求之上的话语共识才能改进和完善社会的规范体制,并以这种规范体制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人的平等、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公正。
哈贝马斯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批判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释失效,主张用 “新进化论”和结构主义的观点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 ”[3](p71)实质上他就是要用基于交往行为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进化理论来取代马克思基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基础之上的社会革命理论。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交往行为理论》对历史发展的不同解释
不同的分析视角,不同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就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形态等问题上都对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首先,对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不同阐释。在被称为对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原理进行高度概括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p597)马克思还分别界定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内涵以及社会存在的根源性,社会意识的派生性的关系。与此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应是交往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用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的发展过程来解释。他把 “劳动”和 “相互作用”区分归结为工具性行为和交往性行为。他还进一步界定了交往行为即是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交往活动。他认为这种相互作用理解是必须同时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与承认,并遵守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的规范。在《交往行为理论》书中,他通过对“世界”概念的反思,将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他认为,“世界观的分三化”应当成为“世界观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5](p14)哈贝马斯还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关于人的科学。他认为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工具活动,抹煞了经验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因为就在社会实践的名义下,马克思把人与人的 “相互作用”(交往)与作为工具行为的 “劳动”混淆了。
其次,对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不同诠释。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6](p32)这是对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科学概括。这里指明了社会生活的三大基本领域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它们总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且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在这里还指明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基础领域并非总是与经济系统相一致,并提出社会一体化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变革的内在机制。社会一体化,就是指一个社会中人们行为结构、世界观结构、以及法律制度结构和道德约束机制诸方面相互适应并处于同一水平。在哈贝马斯看来,生产方式的危机产生于社会经济基础领域,而解决危机需要整个系统的进化。而系统的进化便是出现新的组织结构和以新的组织结构为基础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在关于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上,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关系,而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生活世界和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矛盾。生产关系属于劳动领域,而“社会的制度结构”是在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规范中产生,是与前者有区别的领域。
再次,对社会发展动力的不同阐述。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7](p32)以上的表述说明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即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引用“学习机制”来解释社会发展动力。他把社会进化过程理解为两个向度,其一是 “目的—理性行为”合理化过程,其二是交往行为合理化过程。哈贝马斯认为“目的—理性行为”合理化过程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它是社会进化必不可少的动力;交往行为合理化过程则意味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它也是社会进化不可或缺的动力。这种“学习机制”不是单纯的学习生产知识的机制,而是包括道德——实践知识在内的整个生活世界的知识。社会传承不是生产力的传承而是整个生活世界的传承。他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就是社会系统或社会再生产发生了问题,随即社会变革的问题也就产生了。社会变革就是进入一种新的学习水平,形成一种新的规范结构。这种新的规范结构是通过学习机制完成的。这种新的规范,实现了社会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有效性,保证了交往行为的合理性。
第四,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不同解释。马克思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p592)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在马克思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9](P413)而哈贝马斯是用“社会的组织原则”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不是基于宏观主体,而是基于类主体,即通过主体间性形成的单位。他主张把“一般的行为结构”、对道德和法律起作用的“世界观的结构”以及“制度化的法律结构与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观念结构”是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准。他依据这一标准把迄今为止的社会形态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新石器社会”、“早期文明社会”、“发展了的文明社会”和“现代社会”。[10](p164-170)
第五,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不同看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1](p33)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并被之取代。马克思就是通过这些表述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也预测了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革命前景。相对之下,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科学技术已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使阶级斗争不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的决定力量了。他认为矛盾的焦点发生了变化,新旧政治格局转换,社会运动不再以阶级为单位,而是以各种不同的交往共同体为单位进行。他其实预设了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相异的第三条道路。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在各自理论的基础、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形态和社会的基本矛盾等问题上都对社会历史发展有不同的解释。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交往行为理论》对历史发展解答的时代意义
1.几种对两种理论的评价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解释历史发展之谜的一把钥匙。恩格斯曾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 ”[12](p597)他认为这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并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表述。列宁称历史唯物主义为 “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但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典论述曾被认为是模式化、教条化,即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随后在第二国际后期,一些理论家过分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和人的历史能动作用,把唯物主义历史观曲解为“经济决定论”,使历史唯物主义带有一定的机械论和宿命论色彩。
哈贝马斯是“重建”不是“复原”和“复兴”历史唯物主义。他把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行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用“劳动”和“相互作用”(交往)代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用交往行为代替生产方式,用“系统”和“生活世界”代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哈贝马斯就这样以新的理论框架来实现了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深层次的理论转换。对他理论的正面评价是:哈贝马斯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协调提供了规范的前提,他期望在此基础上建构文明的基本规则。他认为,交往理性包含着人与人之间和不同的合理性的相互接纳、是接纳型的理性。以往信奉的理性都是排斥型的理性,如新保守主义坚持工具合理性,排斥道德实践和美学合理性;后现代主义坚持从个人自发的审美形象排斥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哈贝马斯认为,自己引进的交往理性概念超越了意识哲学理性概念的困境,既克服了新保守主义狭隘的理性观,又克服了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但是哈贝马斯的理论也遭到批判,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无论国家或个人都在争夺各自利益的社会,他所构造的只能是一个乌托邦。不过这些批评也不无道理。
2.两种理论的现时代意义
一方面,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论述有个正确的认识,进而驳斥错误的攻击。“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批判斯大林和苏联哲学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他们强调了意识形态特别是 “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特别是论述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甚至指责“正统马克思主义”就是“经济决定论”,忽视和否定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多学者已经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忽视甚至否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哈贝马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错误的归结为劳动;萨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人学空场。因此,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论述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两种理论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高度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原理,规定了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采取的积极、稳妥、渐进方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根本动因原理,指明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前进方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突出了在改革和建设中要充分发挥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原理,给出了认识和解决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深层次问题的“钥匙”;与此同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给予我们一些的启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阶段,在处理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人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等方面问题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主体间、社会一体化和学习机制或许有助于我国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应给予思考和借鉴。他的这一构想,也许不能完全实现,但确实可以看作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家园。
[1][4][8][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美因河畔 /法兰克福,1981.
[6][7][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