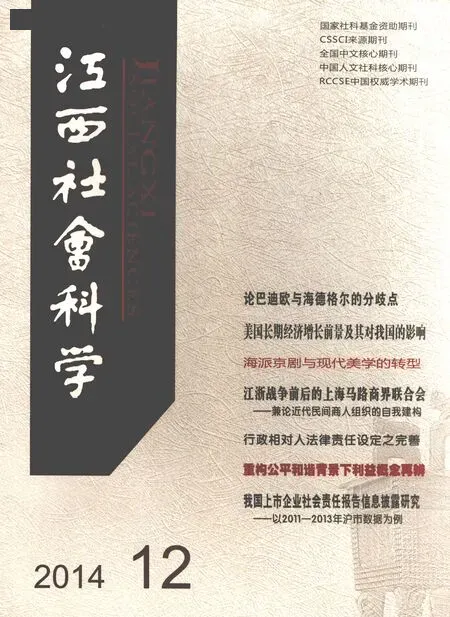老子身体观视域下的“大”概念
2014-12-04■石超
■石 超
“道”,是《老子》书中的高频词。若不对其特别加以说明,则往往会被当作最高范畴之名。然而,老子又常有“未知其名”[1](P283)、“无名”[2](P113)、“不可名”[2](P31)等判断。这种叙述方式,不免使人费解。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达,却体现了“道”内涵的丰富性和层次的复杂性。就其内涵之丰富性而言,玄、深、大、远、微、朴、母等,可用来指称和描述最高范畴之某一面相,但并不能将其全部涵盖;就其层次之复杂性而言,“道”不只是高悬物外的绝对超越实体,更是能够“生一”、“生二”、“生三”,乃至“万物”的特殊存在。[2](P117)而且,一切位阶的具体存在,均是“道”之不断下陷过程的结果。“道”在“生万物”的同时,乃至“之后”,也仍然蕴含、体现于“万物”之中。面对老子“道”论如此深刻之奥义,笔者不揣浅陋,选取集中论述“大”概念的《二十五章》①进行研究,以期获得新的诠解。
一、“字之曰道”与“强名曰大”
首先,让我们讨论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老子是如何对其最高范畴进行命名的?他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P63)可见,该命名方式,同时采取了两种方案,即“字之曰道”与“名曰大”,并在后一种情况下使用了“强为之”的限定语。而两种方案之不同,又集中体现在“名”与“字”的差别上。
提起“名”与“字”,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古代礼制中一个人“幼名,冠字”[3](P296)的生命历程。而老子此处言“字”、言“名”,正是对前句之拟人化修辞(“为天下母”)的进一步展开。因此,对名与字在古代礼制中的联系与区别的说明,恰可辅助我们阐发老子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说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段注:“冥,幽也。”[4](P57)意即日落天黑不能相互辨认,则以口自称,所称即“名”。此就“名”之功用而言,即一种使自己与他人区别的声符。当然,这符号并非随意“自命”,而是“父名之”,“子生三月,则父名之”[5](P951)。又《礼记·内则》载:“三月之末,……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3](P1159)可见,一个人的名,原则上必须由其生父来拟定,并于其出生后的“三月之末”命之。至于“字”,王充说:“其立字也,展名取同义,名‘赐’字‘子贡’,名‘予’字‘子我’。”[6](P1034)意即先将“名”转成它的同义词,再据此以取“字”。《白虎通》亦载:“闻其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7](P411)可见,先有“名”后有“字”,“名”为“字”之本意、根据,“字”为“名”之扩展、代替。故“字”又称“表字”。同时,“字”的拟定仪式是古代成年礼之中的重要环节。《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冠而字”,郑玄注曰:“成人矣,敬其名”;又载:“女子许嫁,筓而字”,郑玄注曰:“以许嫁为成人。”[3](P69)而以字代名,主要是为了显示对其成人身份的尊重。《仪礼·士冠礼》载:“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郑玄注曰:“名者质,所受于父母②。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贾疏曰:“云‘冠,成人益文’者,对名是受于父母为质,字者受于宾为文,故君父之前称名,至于他人称字也,是敬定名也。”[5](P77)质言之,名与字的区别,实即古人“本名”与“表字”的不同。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名”是由其生父拟定的,“字”则是由参加成年礼的“宾”,受主人之托而代为拟定的。
显然,《二十五章》中,所谓“字之曰道”,表达的是老子以“宾”的身份对拟人化的最高范畴之“尊称”、“代称”,并非其“定名”,而是仅“以称可”[2](P63)。所以,“道”之为“字”,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高范畴的某些特性,但毕竟非其“定名”。至于“名”,王弼《指略》曰:“名也者,定彼者也……名生乎彼”,[2](P197)而“寂兮廖兮,独立不改”的最高范畴,[2](P63)是没有区别、无分彼此的。亦即,对于最高范畴来说,并无一个“彼”为其命名。换言之,就是《老子》的作者,亦不具备随意为最高范畴“定名”的权利。故而,与“道”一样,“强为之名曰大”,也只代表最高范畴诸多面相中的一种而已。退一步讲,即便最高范畴有“名”,也只能是由其“父名之”[5](P1159、P1163),只有其“父”知道。可惜帛本《四章》曰:“吾不知其谁之子也,象帝之先。”[8](P242)对此,王弼注以“帝”为“天帝”,[2](P11)即古代宗教中的至上神,同时也是常人眼中世间万物的根本。而“帝之先”,却是“根本”之根本,是产生一切具体存在的抽象存在。它本身,则不被产生,更不会被命名。由此观之,老子为了封堵、取消人们对最高范畴进行定义、命名之行为的可能性与合法性,竟然不惜剥夺至上神之无上权威。因此,老子哲学之最高范畴,是既“无名”,又“不可名”的。换言之,无论是“强名曰大”,还是“字之曰道”,都是受于他人的代号,而非最高范畴之本身。
明白了这个道理,再看《二十五章》,我们不禁要问:老子既已“字之曰道”,为何还要“强为之名(勉强形容)③曰大”,而“大”字是否暗含了某种特殊的寓意,它是否集中体现了老子对其最高范畴的独特体验?为回应以上疑问,我们有必要对“大”字,进行深入探究。
二、“大象人形”与“天人之际”
对于“大”字的解释,历代注释比较一致,均作“伟大”、“广大”解。今存较早的,见《河上公章句》,其曰:“不知其名,强曰。大者高而无上,罗而无外,无不包容,故曰大也。”[9](P102)即是以“大”为一形容词,作“伟大”、“广大”解。王弼注曰:“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责其字之所由,则系于大。夫有系则必有分,有分则失其极矣,故曰‘强为之名曰大’。”[2](P64)今人从此说者,有代表性的,如陈鼓应注评:“大:形容‘道’的没有边际,无所不包。”[10](P161)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引蒋锡昌解“大”字,亦从此,其曰:“道既大而无所不包矣。”[8](P351)对此,刘笑敢说得更明白:“为什么只能勉强名之曰‘大’呢?这是因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之‘大’,是超出我们个体、乃至全人类的认知能力的。”[1](P295)综上,不难看出,以“伟大”、“广大”解“大”概念的传统,当肇始于《河上公章句》。对于《章句》提供的这种理解,笔者并无异议,因为《老子》书中之“大”概念,本来就具有“伟大”、“广大”之义。
但注意到成书早于《章句》的《说文解字》中对于《二十五章》之“大”字的不同解释,便不能不使我们对此处的“大”概念加以重新审视。《说文》曰:“‘天大,地大,人④亦大’,故‘大’象人形。”[4](P496)段注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按‘天’之文从一、大,则先造‘大’字也。‘人’、‘儿’之文但象臂胫,‘大’文则首、手、足皆具,而可以参天地,是为‘大’。”[4](P496)这里的“大”字,不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象形字,其所象之形,正是“首、手、足皆具”的“人形”。有趣的是,许慎所以得出“‘大’象人形”之结论,正是以《二十五章》为据。若依许慎之说,则“道大,天大,地大,王(人)亦大”之“四大”,[2](P64)皆以“人形”为象。而此思想,绝非孤例。相反,它很可能就是古人看待天人之际的普遍思维模式。考察《文子》、《淮南子》,其中对于天人以“人形”相际的论述颇多,其中要者如下:
头圆法天,足方象地,⑤天有四时、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有取与喜怒,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12](P116)
跂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13](P126)
不难看出,所谓“人与天地相类”,实际是人们“将自己⑥的结构赋予世界和他者:身体通过将自身普遍化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普遍性……通过用自身的存在方式去契合这种风格,来与被知觉事物相联系。”[14](P251)当这种“普遍性”与“契合”在古人头脑中形成一种稳定的观念后,便出现了倒果为因的现象。意即将人的身体所具有的“大”形,看作是对天地之形的复制。对于“天地之形”,《文子·下德》是这样说的:“天地之间,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形也。”[12](P397)而对于人身之所以具有此“大”形的根据,董仲舒说得非常明白:“人之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天之副在乎人。”[15](P318)显然,这里所表达的,分别是宇宙的身体性与身体的宇宙性。这就意味着在古人的头脑中,宇宙大化被想象为一个活的机体;而每一个本己身体,又对应着整个宇宙,或可称其为宇宙的全息投影。重要的是,绾结两者的,正是“大”概念所蕴含的“人形”之象。这种“天人同形”、“同构”的理论,发展到汉代,被以融合百家著称的董仲舒演绎、丰富为“天人感应”的学说。而从前文所论来看,董氏亦是在继承前人,甚至直接改造道家思想的基础上,才进而提出此说的。其思想之萌芽与基本形态,早已在《老子》书中有所体现。
可见,在许慎看来,老子所谓“大”,是为了说明天、地、人之间的同形、同构。那么,作为形容词的“大”,与作为人之象形的“大”,两者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笔者以为,前者之意义的获得,亦根源于一个与身体相关的简单常识:近大远小。对“我”来说,一事物的大小,取决于它与“我”的距离。距离变远,事物变小;距离变近,事物变大。当以上两种情况达到无限远与无距离的极端时,就会出现如下情况:前者,意味着事物对“我”来说,趋近于消失,无异于“虚无”;后者,意味着“我”与事物融合为一,成为一个绝对充实、自为的在世主体。而这与“我”合一的事物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决定“我”之所是的身体。显然,在此意义上,身体已成为对“我”来说意义最为重大的事物。这也正是老子批评“万乘之主”“以身轻于天下”[1](P358),而主张“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2](P29)的根本原因——与身体的“近”、大相比,天下是远、是小,老子怎会教人舍近求远呢?由此观之,形容词的“大”与人之象形的“大”,均可统一在老子贵身思想当中。而将人与道、天、地合称“域中有四大”,则可看作是一种为身体之贵寻找形上学根据的理论建构。可以说,后世所谓“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均与老子贵身思想密切相关。而天人之感应、合一所以可能,全赖身体之宇宙性与宇宙之身体性的内在统一。
基于以上理解,我们认为,老子之所以用“大”来“强名”最高范畴,正是为了突出一种天人之间的同一性。而对这种同一性的领悟,必然借助于反观自身的体察与觉醒。用老子的话说,就是“为道日损”,[2](P128)要“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因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2](P125-126)具体讲,既然最高范畴无所不在,那么对它的求索就应由近及远,最终还要复返其近。亦即《文子》所载:“夫道至亲不可疏,至近不可远,求之远者,往而复反。”[12](P356)而这至亲、至近的“道”,诚如前文所论,它“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身,身得则万物备矣”[12](P162)。其中,所谓“身得”即得“道”。得者,德也。《韩非子·解老》亦载:“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16](P370)因此,笔者以为,《二十五章》中的“大”,是一个用以体现最高范畴之根身性面相的哲学概念。换言之,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无法被他人所告知的,而是需要每一个人回观自己的身体、内在,去加以体验。
三、“周行不殆”与“逝、远、返”
在将最高范畴勉强形容为“大”之前,老子还对其进行了一番现象描述。这一描述在王本、帛本、竹本中互有出入,今将三者具列于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王本)[2](P63)
两处明显的不同,将会影响我们对老子哲学最高范畴的理解。先看第一处,此句竹本作“又成”。其中,“又”通“有”,与帛本、王本无异。“”,整理者将其读为“䖵”,即“昆”,通“混”,亦与帛本、王本同。重点是“”字,裘锡圭与李零将其读为“状”。刘笑敢亦从之,并申论曰:“‘状’比‘物’更有原初、原始的意味,‘有状混成’比以后诸本的‘有物混成’更能体现‘道’似有非有、似无非无、亦有亦无的特点。”[1](P285)笔者亦同意此说。但与前引诸人稍有不同的是,我们注意到老子“强名曰大”之“大”字所具有的“人形”之义。而据《说文》段注解释,“状”字“引申为形状”[4](P479),即可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因此,“状”字与后文出现的“大”所具有的“人形”之义可以互相发明。故而,竹本、帛本此处用“状”,较王本用“物”于义理为优。
另外一处不同,即王本有“周行而不殆”一句,但竹本、帛本无。对此,高明、许抗生、刘笑敢等均以其为后人妄加。[1](P286)笔者以为,此说值得商榷。因为如果缺少此句,则《二十五章》对于最高范畴之论述将变得不完整。诚如“有状混成”可与“强为之名曰大”互相发明一样,“周行而不殆”亦与“字之曰道”内在关联。其关联点即在一个“行”字。为说明此论断,我们应首先分析:“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2](P64)(王本)句中的“反”字,陈鼓应认为当作“返”。[10](P161)所论甚确。于是,本句所涉及的三个概念——“逝”、“远”、“返”——皆“从辵”,⑨《说文》载:“辵,乍行乍止也”,[4](P70)而“行”,“从彳、亍”,[4](P78)“彳,小步也”,[4](P76)“亍,步止也,”[4](P78)意即是说,辵与行同义,均表示“人之步趋也”。[4](P78)
而“道”字,亦“从辵”。《说文》曰:“道,所行道也。从辵、首。”段注“所行道也”句曰:“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4](P76)此解将“道”字之义分为两层:一是“所行”,二是“行”。前者为静态、已然之道路,⑩后者为动态、未然之行动。另外,王弼注“大曰逝”句曰:“逝,行也”,[2](P64)再一次对“从辵”字的“行动”义进行提点。所以,“道”字“从辵”,就其构造来看,除表示已然之道路外,还含有身体之动态义。留意后者,我们发现,王本《四十章》载有“反者,道之动”一句,[2](P109)竹本作:“返也者,道动也”,[10](P434)即是对“道”及“从辵”字之内涵有行动义的说明。因此,在《二十五章》之语境中,“字之曰道”句所代表的,首先、主要是最高范畴的运动性,是对“周行而不殆”句的进一步阐发。而“道”字之古文有作“衜”者,其从行、从首之构造,更直观地展现了这种动态义。对于其中之“首”字,段注曰:“首者,行所达也。”[4](P76)此解虽确,但无意间掩盖了一个前提:即在确定“行所达”之方向前,“首”字所指认的,首先是作为“行”之承担者的“人”、“大”。而郭店楚简中屡屡出现的“(道)”字,其从人、从行的构造,恰可为以上论断提供形象的证明。⑪可见,《二十五章》中“周行而不殆”,“字之曰道”以及“逝、远、返”等语汇,前后关联,层层递进。其所阐发的,正是老子哲学最高范畴流行不止、生生不息的行动义。而这一行动义又与以“大”强名的混成之状密切相关,实为最高范畴一体之两面。质言之,《二十五章》篇幅虽短,但其中所涉及的“状、大、行、道”等一系列概念均能内在关联,自成体系。以此反观王本、竹本以及帛本,轻易否定其中任何一种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态度,应是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至此,《二十五章》还剩最后一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P65)此句王本、帛本、竹本完全一致,可以说,前面的所有讨论,都是为了对这一句话给出一种基于身体观的全新解释。而这一新解的关键,即在于对“法”字的理解。我们已经澄清,“天”、“地”在古人头脑中具有与人身同形同构之意象;而“道”在《二十五章》中,则是对身体(不仅指人的身体,亦包括天地之“大”)之行动义的一种引申。因此,“法”就不再仅仅是前者对后者的被动效法(followtheexampleof),而是兼具了“使之合法”(tomakeitlegal)的主动性。也就是说,“法”字所连接的前后两项之间,乃是相互效法、相互框范的关系。
重要的是,此种关系正是我们在世存在的某种“宿命”。具体讲,在对象作用于我们的身体之前,身体已经为对象的作用方式进行了框范;而我们反作用于对象的一切活动,均须依据此种框范才能得以展开。对此,可参看宁晓萌女士对梅洛-庞蒂哲学“身体”与“世界”两大主题之关系的分析:“‘身体’作为主体,作为在身体图式中‘朝向世界存在’的身体本身,则以其‘投身世界’与作为‘往世中去存在’之‘锚定点’两个面向的特征与‘世界’形成一种悖论的关系。即一方面作为主体的身体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但另一方面作为主体的身体又有着某种建构的能力(‘身体本身’乃是一种‘我能’),朝向世界去存在的同时,也在规定和建构着这个世界。”[17](P6)刘笑敢先生亦说:“当我们观测客观世界时,我们必须依靠一定的手段和工具,而我们的手段和工具已经影响或改变了观测对象的存在,这样,我们实际上无法完全观测自在的、本来的客观世界。”[1](P296)显然,刘先生所说的手段和工具,特指那些区别于、外在于我们身体的东西。而必须指出的是,决定我们之所是的身体,本身就是一种先于一切外在手段和工具的最原初、最根本的“手段”和“工具”。诚如刘先生所论,手段和工具将影响或改变观测对象的存在,而以身体这一原初“手段”、原初“工具”所观测到的外在之物、外在世界亦必然充满了身体性的框范。
总之,从身体观的角度看《二十五章》,我们会发现,老子为我们描述的,是一个处处留有人的痕迹,时时可见人的活动的世界。换言之,一个无人的、纯粹客观的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可想象的。
注释:
①按,以下所引《老子》,均略书名,只注篇名。
②按,贾疏曰:“《内则》云‘子生三月,父名之’,不言母,今云‘受于父母’者,夫妇一体,受父即是受于母,故兼言也。”
③按,此说参考高亨《正诂》。其曰:“名、容形近,且涉上文而诉。”并引三证作解。其论精到,对于此句义理多有契合。(高亨:《老子正诂》,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4页)但考虑到帛本、竹本此句皆作“名”不作“容”,故笔者不取高亨改字解经之举,但同意其以“容”释“名”之见解。
④按,“人”字王本、竹本、帛本均作“王”。陈鼓应认为当作“人”,其论曰:“本章两个‘王’字应据傅奕本改正为‘人’。通行本误为‘王’,原因不外如奚侗所说的:‘古之尊君者妄改之’;或如吴承志所说的‘人’古文作‘三’,使读者误为‘王’。况且,‘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后文接下去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从上下文的脉络看来,‘王’字均当改正为‘人’,以与下文‘人法地’相贯。”(陈鼓应撰《老子注释及评介》第163页)陈公所论,有理有据,可备一说。对于本文假设,亦起支持作用。但考虑到竹、帛本均作“王”,不作“人”,似乎径改经文之举,仍有待商榷。其实,此处作“王”、作“人”于义理并无根本之影响。因为是与“道”、“天”、“地”并称,所以无论是“人”还是“王”,均应当特指圣人、圣王。而在老子、孔子的那个时代,“圣”与“王”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没有完全分离。换言之,圣者首先为人,且必有王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王还是常人,他都首先要有一个身体(“人形”)。
⑤徐灵府注曰:“一人之身,万像悉备,不可轻也。”
⑥按,即身体自己的“人形”。
⑦按,本文所引帛本《老子》,均为综合甲乙两种版本而成。括号中的文字,乃为乙本不同于甲本者。
⑧按,此二字,可参考刘笑敢所引诸家之说。笔者从李零说,释为“寂寥”。(刘笑敢.老子古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85)
⑨《说文》曰:“逝,往也,从辵 折声”;“远,辽也,从辵袁声”;“返,还也,从辵 从反,反亦声”。(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1、75、72页。
⑩《释名·释道》曰:“一达曰道路。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蹈而露见也。”(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1页。
[1]刘笑敢.老子古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魏)王弼.王弼集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M].(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汉)郑玄注.仪礼注疏[M].(唐)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汉)王充,黄晖,撰.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清)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8]高明.帛书老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9]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汉)许慎撰.说文解字[M].(宋)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王利器.文子疏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法)埃马纽埃尔·德·圣·奥贝尔.存在与肉的共同深度[A].杜小真.理解梅洛-庞蒂:梅洛-庞蒂在当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5](清)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16](战国)韩非.韩非子新校注[M].陈其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7]宁晓萌.表达与存在:梅洛-庞蒂现象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