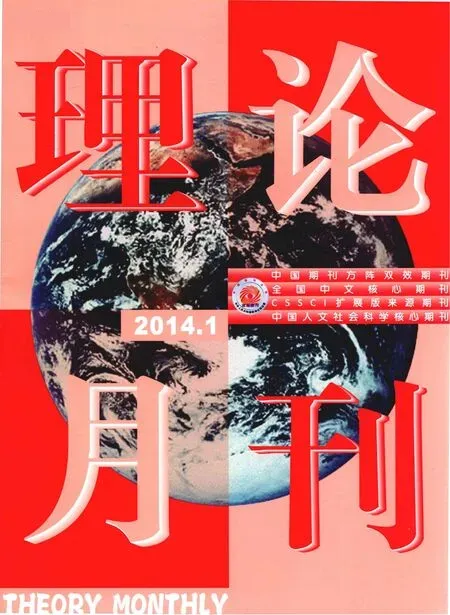素丝作画:墨家“染”德育方法体系诠议
2014-12-03杨建兵
杨建兵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墨学在先秦时期曾是与儒学比肩的显学,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思想道德资源之一,挖掘、整理、借鉴墨家的德育思想资源尤其是其德育方法对于当下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认识和把握墨家的德育方法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墨家道德教育预设了什么样的人性前提?即墨家认为其要进行道德教育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第二,针对这样的人,墨家提出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墨家德育的方法有何鲜明的特点?第三,墨家德育思想的现实价值如何评价?
一、墨家德育的对象:素丝无色
德育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其目标的达成以教育对象的思想转换为标志。德育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德育方法是否得当,是否与教育对象的性质相符。所以,对德育对象的性质即人性如何的不同体认就成为思想家们设计其独具特色的德育体系的首要前提,相应地,人性观也成为区分不同流派德育思想的重要因素。关于墨家的人性思想,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①比如,日本学者谷中信一认为,对人性问题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是墨家被世人遗忘的主因。(参见:谷中信一:《谈墨家的人性论》,载于《职大学报》2007年第1期第14页。)徐复观则断言:“墨家无人性论,但并不是没有此一问题”。(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7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笔者认为通过分析墨家伦理思想的逻辑结构与核心内容可以分离出其对于人性的基本观点。
墨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贵义”为宗旨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为它是孵出或者确证墨家其它道德命题的最高原则,在墨家伦理体系中居于核心的位置。②此一观点在拙著《先秦平民阶层的道德理想----墨家伦理研究》中有充分的论证,在此限于篇幅不再重复。(参看:杨建兵:《先秦平民阶层的道德理想----墨家伦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23-38页。)而在《墨子》文本中,这个最高原则作为一个道德命题的确证却只能是基于这样一个默认的事实,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是除“天志”以外的唯一充足理由。在墨家看来,如果不存在“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一基本的事实,那么,“仁人”(或称作“圣人”、“士”等)就没有必要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更不可能籍此成为令人称道的道德楷模而被贴上诸如“仁人”或者“圣人”的标签。墨家的主要道德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这样链接:“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以,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高尚的人(墨家称之为“仁人”、“士”、“君子”、“圣王”、“王公大人”等)应当“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满足天下人“趋利避害”的需求;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则必须“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可见,对于人的“趋利避害”之本性的基本体认是墨家道德思想的逻辑起点。
在《墨子》文本中,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多以人自然而生的各种欲望出现。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强调人生而就有满足自己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这种“基本欲望”,在生死观上具体表现为“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1]在物质利益观上表现为“欲福禄而恶祸崇”;[2]在爱情和生育观上则表现为“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3]在墨家看来,乐生厌死、男女之情、饮食之欲,这是如同“天在上,地在下,一年分四季”一样最自然不过的本原的人性。对这样的人性,我们当然既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所以,墨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人性作明确的善恶评判。而人性观一般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一,人性如何的事实性陈述;其二,人性如何的价值性评断。按照上文的阐述,墨家对人性的第一个层次的判断可概括为“人性欲利”,这是一个事实性陈述;墨家对人性的第二个层次的判断近似于又有别于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①部分学者认为,告子是墨家的弟子,笔者认同这种观点,但告子的人性观不能完全代表墨家。其细微的差别在于,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这是作出了明确判断。但墨家的立场是“无称善恶”,即“不要说是善还是恶”。关于墨家与告子人性思想的关系,请参看:杨建兵:《墨家人性论略》,载于:任守景主编:《墨子研究论丛》(九)第651-665页,齐鲁书社2011年版。可以概括为“无称善恶”,也就是不需要去分别善恶。在墨家的眼里,人之“欲利”好似布之“吸水”是自有的本性,无所谓善恶,更不需要强分善恶。两个层次的判断结合起来,墨家的人性观完整的表述就是:“人性欲利,无称善恶”。具体来说,墨家认为,人性如素丝(白绢),没有任何颜色(就像人无所谓善恶),而且,它具备吸纳、附着颜料颗粒的特性方便着色成画(就像人之“欲利”特性使道德教育有了着力点才有可能实现德育目标),所以,可以涂出你想要的任何颜色,画成你所构想的美丽图画。
二、墨家德育方法:素丝作画“染”为功
德育方法与人性观是相匹配的,既然墨家认为人性“无称善恶”,那么,人的德性关键就在于后天的“所染”。墨家认为,道德教育恰如在素丝上作画,画作的质量完全取决于作画者(教育者)“染”的功夫。墨家正是以“染”为中心构建其独具特色的德育方法体系。
《墨子·所染》篇云:“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
分析上段引文中墨家对 “染”的论述可总结出墨家“染”的德育方法论包含如下几个要点。
首先,“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是承接了上文所归纳的人性前提即“人性欲利,无称善恶”。因为只有一无所染之“素丝”才能随己之意“染”成自己喜欢的任何颜色(“苍”或“黄”),也只有非具“已然之善恶”(或“可称善恶”)的“素人”才能被培养成预定品质规格的任何人。在墨家看来,人的善德是在洁白的绢布上新“染”成的靓丽图画。它既不像孟子所说,是吹掉厚厚的灰尘后所呈现出的一幅价值连城的古画;也不似荀子所声称,是由一幅丑陋的旧画涂改而成,即所谓“化性起伪”。这是墨家与儒家的分歧。当然,墨、儒也有共识,比如都坚信“德行可教且必教”,这与老、韩之观点有本质差别。韩非认定人性之恶,如朽木不可雕,彻底否定道德教育的可能性;《老子》则认定人性是纯真至善的,根本否定儒、墨重视的,通过后天的、外在的道德教育转化人的思想的价值。
其次,“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这是说,人之亟待培养的善德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就像即将用于“染丝”的“五色”外在于“素丝”一样。在墨家看来,德育对人作用的过程就像是电脑录入或者画画写字一样,是由外到内的过程,只要成功地写入或者说只要教育对象接受了所宣传或者传授的道德知识,就可以看成是道德教育的完成和德育目标的实现,就象“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显然,这与儒家的“内求”和道家的“守”、“反”、“复”、“归”的道德修养的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孟子德育的基本方法就是“求”其“放心”,“养”其“浩然之气”。“良知”、“正义”、浩然正义的理性,不在人身之外,而于人的内心存焉,所以,不必“外求”。在道家看来,人的本性是纯真至善的,一切恶的、丑的东西全在乎人为。所以,其修养的方法就是“守”其“真”,“反”其“朴”,“复”其“初”,“归”其“本”。可见,由于对于人性有着不同的认读,墨家与儒、道修养的方法和径路就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
最后,“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这是说道德教育一定要慎重,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一定要进行全面的、正确的道德教育。墨家德育强调主动的、外在的道德灌输,并且,坚信道德教育的实效和对于国家人民的意义。墨家提倡“法先王,行仁义”,其德育的宗旨是要改造社会,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4]其德育计划的实施步骤是先国家、集体,再将个人包含进来;儒家行德教的步骤则正好相反,其顺序是:由“身”到“家”,再到“国”,最后是“天下”。 与儒、墨相反,道家反对外在的、人为的、主动的为达到某种社会目的而进行的教化活动,鼓吹以自然为“师”,推崇符合和顺应宇宙自然规律的“自化”,宁可回复“小国寡民”的状态。韩非赞成对社会的改造和变革,但认为达到这个目的只能依靠“刑”、“德”二柄,而不是所谓道德教育。
基于以上的认识,墨家提出三种主要的德育方法。
其一,物利引诱法(或称之为“物质激励法”)。墨家认为“人性欲利”,所以,劝人之善的基础方法就是“利诱”。这与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的儒家正好相反。对“诱”人向善之“利”,墨家也划分了不同等级。 “衣”、“食”这些最基本的物质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谈名誉、地位等;而音乐、娱乐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还耗费民力,浪费民财,是“害”非“利”。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墨家设计的“众贤之术”就是层层递进地提高贤人的待遇:“富之,贵之,敬之,誉之”,[6]做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7]以快速的可感、可视、可触、可握的“物利”吸引社会人群修德为“义”,从而达到短期内快速提升社会总体道德水平的目的。
其二,权力强制法(或称之为“示范教育法”)。对“欲利”之人诱之以利,这是墨家德育的基本思路。但是,墨家也知道,利益有大小,处于不同阶层的人对同一标的物价值的大小,看法是不尽相同的。而且,如何分配“利”才合乎“义”,不同的利益主体也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甚至会出现“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8]的情况,这就存在一个统一标准的问题。墨家主张通过权力来强制统一标准,统一思想,即所谓“尚同”,具体来说就是“上同而不下比”,[9]强调下级单向学习和绝对服从上级而不能相反。通过权力强制来保证德育行为和德育目标的双重实现。当然,这种强制的前提是“官上”的德性足以为“众下”的表率,所以,墨家设置的最高一级的长官兼为“上同”的终极标准是至德至明的“天”。
其三,天鬼监督法(或称之为“威慑教育法”)。墨家深知对于本性“欲利”的人来说,最渴望的情形就是:自己假装道德,在口头上道德,甚至于满口仁义道德,同时盼望其他人都真道德,并且都能落实到行动上,这样,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如果没有确有实效的措施打消人们的这种恶劣的“念头”,根除这种假道德现象,那么,道德教育的目的就会彻底落空。然而,鉴定和监督所有人思想、行为的善恶、真伪,显然超出普通人(也包括贤德的官员)的能力范围,所以,墨家请来一对无所不能而且不知疲倦的监督者“天鬼”,全时段全方位地监视所有人的行为。在鬼神的强力督促下,没有人能够偷懒欺骗,只能全心全意地践行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道德原则。总体来看,墨家以“人性欲利,无称善恶”为其立论前提,“外染”为显著特征,以“物利引诱”、“权力强制”和“鬼神监督”为具体方法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德育方法体系。
三、墨家德育的现实价值:白璧有瑕
墨家在深切体认德育对像即人的本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德育方法,不仅自成体系,而且,确曾在我国历史上取得过一定的成效,在创派之初就营造出令儒者生畏的显荣景象,奠定墨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今天,我们重视道德教育,对待像墨家德育思想这样的传统文化资源,我们要在全面认识、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
对于墨家的德育思想,从其积极的一面来看,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墨家重视德育的价值,认为 “德行可教且必教”,并提出了明确的德育目标,这种对待德育的态度是我们要大力弘扬的。《墨子·修身》开篇即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紧接着就提出君子修养的目标是“四德”:“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墨家认为,道德教育就是要培养具备 “廉”、“义”、“爱”、“哀”四种德性的君子。他们所提出的“四德”培养目标与儒家所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以及柏拉图的“四主德”一样,都是人类文明早期对道德生活所设定的目标,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生活模式的追求,都是人类德育宝库中的明珠,及至今日仍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第二,墨家“四德”之中的“廉”德性和“哀”德性对当今中国的道德建设尤其具有补缺的价值。《墨经》对“廉”的释义是:“廉:作非也”;[10]“廉:己惟为之,知其(左思右耳)耳”。[11]这里的“作”通“怍”,是惭愧之意;“(左思右耳)”是“耻”的异文。可见,墨家对“廉”德性的最基本的定位是道德主体在思想上“明是非,有羞耻心,有耻辱感”。墨家还认为,同样是“廉”的德性,在官民、男女各种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不同身分的人,其“廉”的判断标准就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求道德主体不去贪占自己不应得的利益,甚至连这种想法都不应该有,因为,对于具有“廉”德性的人来说,有这种想法都是一种羞耻,是否有羞耻之心是“廉”的最深层特征。墨家推崇“廉”德性,将它放在“四德”的首位,并且明确其最深层次的心理特征是“明是非,有羞耻心,有羞耻感”。这在一方面提醒我们,培养安守清贫的生活习惯和道德情操是治贪倡廉的关键;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养“廉”的本质在于培养官员的“羞耻之心”,如果官员内心真正“以贪为耻”,不管是否有人监督,贪腐的概率都会大为降低。
墨家之所谓 “哀”德性首先是要最大限度地挽救生命,包括节约资源以救助冻饿者,援助被欺凌的弱者和被侵略的小国。对于已死者,一是要表现出尊重与哀悼,另一个就是对其后事的处理也要服从节约的原则,而且,前者是第一位的,因为,“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墨家的“哀”德性,其深层的内涵是体现了其对于人命的珍惜,是一种“敬畏生命”的博爱情怀,是一个人人文素质的重要体现,而我国现有的德育体系中却缺少相关的内容,尤其缺乏“哀伤素质”的教育和辅导。所以,重温墨家的“哀”观念对当下的道德教育不无启迪和补充价值。
另一方面,对于墨家的德育思想,以下几方面的消极因素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警觉。
首先,墨家对人性的设定是“人性欲利,无称善恶”,这样的人性定位,表面看来尊重事实,不偏不倚,客观上却为自利者提供了隐性的理由,为德育的顺利展开设置了重重障碍。因为,“人之欲利”既然是无可厚非的,那“欲利”的人为何要放弃“一己之利”,而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呢!墨家的回答是:“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12]“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13]而对于真正“欲利”的人来说,最佳的人生策略莫过于对别人高喊“兴天下之利”,同时,自己却一心一意地经营“一己之私”,这样,既可以获得现实的物质利益,在心理上也没有任何愧疚之意。墨家为德育设置的人性前提使其道德推理变成了赤祼裸的“利叙述”,而仅以“利”为理由是没有办法说服人放弃利益去追求道德的,更不可能说服“欲利”而且认为“欲利”是正当的人,为“天下之利”而放弃一己现实的利益。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当我们以“众利”、“公利”为借口而倡导“功利主义”时,“物质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就会大行其道。可见,以“人性欲利”为起点的墨家伦理叙述在现实的德育实践中会遇到不可克服的操作障碍。墨学曾千年中衰的历史也似警告我们:道德教育这种伦理叙述不宜以“利”为核心和起点。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工具理性恶性膨胀的时代,进行道德教育更应当避免一元化的“利叙述”,而应当多强调“义务”和“责任”,并辅之以榜样的示范和吸引,才有可能收到教育的实效。
其次,墨家以“外染”为特色的德育方法论,过于强调外在的道德知识灌输的重要性,忽视德育对象的内在心理需求,似不利于教育对象道德自觉的唤醒,从而影响其道德情感的培养和自律精神的养成。
道德教育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又回复主观的双向作用过程,德育目标的实现以主体道德自觉和自律意识的形成为标志。如果不考虑教育对象的主观因素,德育的过程完全依赖外力的引诱、强迫和恐吓,其成功的可能性当然就很小。墨子本人也绝不是在利益的引诱、权力的强制和鬼神的威胁之下才成为墨子的,其克己利人的高尚节操的锻造,一者是受了前辈大禹高风亮节的人格吸引,二者是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使然。墨家在设计其德育模式和社会教化方式的过程中,沿着其“人性欲利,无称善恶”的人性理路将教育的重点放在“外染”的道德知识灌输上,在不知不觉中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连陶冶性情的音乐也要废弃,使人完全工具化,这就极易使道德教育陷入悖逆人性,一味强调利诱、强制、威胁和蛮干的盲动中。总结墨家的德育思想,我们得到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德育过程应当是道德知识的外在传授和灌输与道德情感的内在唤醒和培养并重,在德育领域,“主知主义”和“主情主义”各有偏颇,二者的共同出路在于相辅互补,辩证统一。
最后,墨家德育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都各有其优点和缺陷。上文第二部分,我们已总结了“墨家德育三法”的特色和优势。对于当今的德育工作者来说,更应当看到其缺陷,引以为戒。“墨家德育三法”的局限性在于:第一,“物利引诱法”过于看重物质的激励作用,轻视人的精神需求,尤其忽视了音乐、娱乐对人的德性的陶冶功能;第二,道德教育的成功最终有赖于人的道德自律的形成,“权力强制法”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会影响道德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墨家思想中专制独裁的因素;第三,如果是在古代,先民们还残存有若干“天帝”、“鬼神”的观念,“天鬼监督法”也许可以部分地实现其目的;时至今日,这种方法所唯一昭示的是墨学保守、顽固的一面。
[1]墨子·尚贤中[M].
[2]墨子·天志上[M].
[3]墨子·辞过[M].
[4]墨子·尚贤下[M].
[5]论语·里仁[M].
[6][7]墨子·尚贤上[M].
[8]墨子·尚同中[M].
[9]墨子·尚同上[M].
[10]墨子·经上[M].
[11]墨子·经说上[M].
[12]墨子·兼爱中[M].
[13]墨子·大取[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