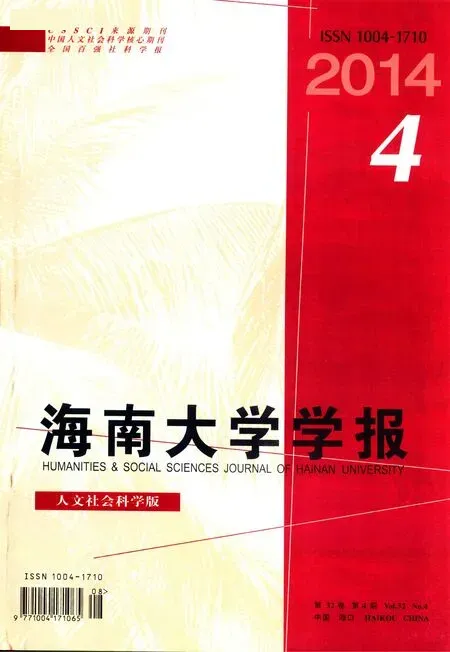黎锦筒裙人形纹研究
2014-11-27孙海兰
孙海兰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口570228)
在黎族各方言黎锦筒裙上,常会出现具有人形特征的纹样,这些纹样或以单独的人形纹出现,或以具体的人物活动和生活场景纹样出现。有的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的基本特征,如美孚方言黎锦筒裙上的人骑马纹、哈方言黎锦筒裙上的手持工具纹等(见图1),这些生动形象的纹样不仅具有装饰美化的作用,还蕴含着深刻的涵义,寓示随着社会的发展,黎族的宗教信仰已从早期的图腾、生殖崇拜阶段,发展到祖先崇拜阶段。
在黎族各方言黎锦筒裙中,皆织绣有大量人形纹样,不同方言黎锦筒裙上的人形纹有着很大的差异。润方言黎锦筒裙上的人形纹造型夸张,尚保留有不少蛙形特征,如繁复的蛙蹼;哈方言黎锦筒裙上的人形纹较为生活化,除了人物身上有明显的装饰物外,还有人物生活场景纹;杞方言妇女筒裙上的部分人形纹除了有明显的腰部形态和直立特征外,部分人形纹还织绣有装饰物;美孚方言黎锦筒裙上的人形纹特征相对抽象,但如果就人骑马这一特定的纹样内涵而言,其简化图案应为人纹;赛方言黎锦筒裙上的纹样呈紧密分布状,其纹样细小,但如果细致观察,也有许多人形纹存在。

图1 美孚方言、哈方言人形纹
一、黎锦筒裙人形纹的分类
黎族各方言黎锦筒裙人形纹可分为蛙姿人形纹、具象人形、简化人形纹三种形式。
1.蛙姿人形纹
此型的基本特点是还保留有蛙纹的某些外在特征,如留有蛙纹的菱形体型特征和四肢弯曲的动作特征。除此之外,有的人形纹上还有青蛙的蛙蹼,有的双足微张呈用力蹬地状,保留了青蛙腾空跃起的姿势,见图2。

图2 哈方言、杞方言蛙姿人形纹
尽管如此,此型仍明显表现出人的基本形象:已呈现出人的站立状,具有完整的头、身、双臂、双腿,最为重要的是与蛙纹的前肢向前跃起不同,此型的主要特点是:较为清晰地显示出由蛙纹向人形纹的过渡。
在所采集到的531种黎锦筒裙纹样样本中,此类人形纹共有40种,占所有纹样的7.53%。
2.具象人形纹(含复合纹样)
此类型纹样虽然在形状上留有蛙纹的某些特征,如菱形构图、四肢弯曲,个别手脚还保留有蛙蹼,但已经在蛙姿人形纹的基础上清晰地呈现出人的基本特征,不仅形象上更接近人,而且纹样中已明显出现了代表人类活动的某些基本特征,比如佩戴耳环、文身、持工具(武器)等,见图3。

图3 杞方言、孚方言具象人形纹
除此之外,黎锦筒裙纹样中还有一种复合人形纹,主要以具象人形纹为主,这类纹样的表现内容主要是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譬如骑马、耕耘、赶牛、婚礼、居住等。一方面,由于这些纹样所表现的活动场面明显与人物有关,另一方面,这些人形纹在形象上基本与上一种纹样一致,因此,可将此型纹样也归入具象人形纹当中,见图4、图5。

图4 哈方言婚礼复合人形纹

图5 美孚方言耕耘复合人形纹
在所采集到的531种黎锦筒裙纹样样本中,此类人形纹共出现12种,占所有纹样的2.26%。
3.简化人形纹
此种纹样已经完全呈现出人的形体特征,简化即只表现人的基本形象,忽略具体细节,多数纹样蛙蹼已逐渐褪去,只用简单的线条来代表人的双臂和双腿,见图6。
在所采集到的531种黎锦筒裙纹样样本中,此类纹样共出现31种,占所有纹样的5.84%。

图6 简化人形纹
二、黎锦筒裙人形纹的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黎锦筒裙上的人形纹具有以下特征:
1.人形纹在各方言黎锦筒裙上普遍存在
在所采集到的531种黎锦筒裙样本中,人形纹有73种,占13.75%。其中润方言18种,哈方言23种,杞方言19种,赛方言9种,美孚方言4种,见表1。

表1 黎锦人形纹统计表 单位:种
2.某些人形纹呈现黎族先民独特的生产生活习俗
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黎族儋耳习俗的记载:比如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南经》之“离耳国”云:“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在珠崖海渚中,不食五谷,但啖蚌及薯芋也。”[1]杨孚《异物志》云:“儋耳夷,生则镂其皮,尾相连并;镂其耳匡为数行,与颊相连,状如鸡肠,下垂肩上。食薯,纺织为业。”[2]850作为黎族的一种传统习俗,历史上并非只有妇女佩戴耳环的习惯,在古代,黎族男子也有佩戴耳环的传统。“老人们回忆说,至中华民国初期,除了石碌、重合、江边等地小部分男子还保留佩戴耳环的习惯外,绝大部分地区的男子已不再佩戴耳环。民国21年(1932年)抚黎专员陈汉光到琼……凡他所到的地方,都曾强令革除黎族妇女纹身纹面和男人佩戴耳环的习俗,并极力提倡改着汉装。从那以后,石碌、重合、江边等地的男人也逐渐地不再佩戴耳环,绝大部分地区的美孚方言黎族男人陆陆续续改穿汉装”[3]。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黎锦筒裙的人形纹并不一定都是女性,也有可能是男性。
关于文身,也有很多记载,如杨孚《异物志》云:“雕题国,画其面皮,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锦衣,或若鱼鳞。”[2]849明代学者顾山介 在《海槎余录》记载:“黎俗,男女周岁即文其身,自云:不然,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2]659部分学者已注意到黎锦筒裙上织绣有文身图案,《黎族妇女服饰》一文中在介绍黎族妇女服饰纹样种类时,提到文身纹样:“花草纹样和其他纹样(字纹、雷纹、星光、文身、几何图形等)。”[4]秦寄岗在《从黎族服饰图案看黎族人民的审美意识》一文中也提及妇女服饰图案中有文身图案:“除此之外,黎族的文身在服饰图案中也有表现。”[5]这些黎族生活习俗在黎锦筒裙纹样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3.蛙纹到人形纹的过渡痕迹
黎锦筒裙上的人形纹带有明显的从蛙纹过渡而来的痕迹:人形纹的基本形状保持了蛙纹的菱形体型特征;尽管简化人形纹的双臂已经明显地转变为向下的姿势,但在蛙姿人形纹中,青蛙上肢向上的姿势仍然得以保存,说明蛙姿人形纹是介于蛙纹与人形纹之间的过渡纹样;在蛙姿人形纹和具象人形纹中,保持了蛙纹的某些细节特征,主要表现在对蛙蹼的刻画上,从图谱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尽管一些纹样通过佩戴耳环、手持工具等方式已经显示出人的基本特征,但在表现人的手足的时候,仍采用蛙蹼的形态。
4.创造了人形大力神纹样
大力神纹,是黎族润方言黎锦筒裙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纹样,这一纹样的基础是简化人形纹,但它已经在简化人形纹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于大力神纹,《黎族传统织锦》中表述是:“黎族织锦大力神纹样,造型刚健有力,气势磅礴,给人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整体纹饰构图巧妙、奇异、抽象,人形纹非常特别和复杂,有一种超现实的幻想。大力神人形纹构图装饰非常独特,从头、手到脚,各部位图案的装饰和一般的人形纹图案的装饰相比大不一样,增加了许多夸张、抽象形式的装饰图案。头部装饰很像宇宙太空人的头饰,双手的装饰像个很大的飞行器翅膀,可自由地升空而去穿云而来,双脚的装饰呈现巨大的鱼尾形状,能在海河中自由遨游。”[6]大力神纹,不仅在形象上具有高大、魁梧的特征,重要的是它在黎族润方言人心中具有特殊的精神意义,明确地呈现出祖先崇拜的基本特征。
黎锦人形纹特别是大力神纹的出现,反映出黎族社会内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原有的母系氏族社会开始解体,父系氏族社会逐渐形成,黎族原始宗教也已由早先的生殖崇拜转向祖先崇拜。
三、黎锦筒裙人形纹的祖先崇拜内涵
关于祖先崇拜,阿朝东认为“有广义、狭义之分。作为广义的祖先崇拜,除人类先祖崇拜,尚包括图腾崇拜等。而狭义的祖先崇拜则仅仅指人类自身的崇拜。”[7]该解释尽管非常简单,未对祖先崇拜的内涵、特征等作充分的解释,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祖先崇拜具有广义、狭义之分,这种划分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狭义的祖先崇拜作出详细解释的是葛季芳,她在《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生殖崇拜》一文中认为:“祖先崇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祖先崇拜是死后的灵魂,但不等于氏族中所有死者的鬼魂,都被当作父系氏族共同体的祖先来崇拜……祖先崇拜就本质来说,是鬼魂崇拜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开始时,氏族成员曾把那些生前强有力的,对氏族作过贡献的酋长,死后的鬼魂当作氏族共同的祖先崇拜,认为这样的鬼魂生前为氏族作过贡献,死后的鬼魂亦能保护氏族的利益是可信赖的。但认真说并不是真正的祖先崇拜,因为死者与崇拜者并没有直系的血缘关系。可是它的发展导致了血缘关系的祖先崇拜,主要是这时期氏族部落出现了剩余价值,随之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9]葛季芳不仅将祖先崇拜放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分析,重要的是,她指出祖先崇拜的对象,是有着间接血缘关系、历史上有过功德和威望的人。即将祖先崇拜的对象具体化,更多地指向英雄崇拜,而不是笼统地指死去的祖先亡灵。当然,这仅就原始先民们可能崇拜的对象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分化,部落、家庭也日益分化,祖先崇拜的对象亦有所变化,在直系血缘亲属中,原本共同崇拜祖先的团体,随着人口的繁衍、变迁和家庭的分化,又不断派生出不同的直系血缘祖先。
在此采用狭义的祖先崇拜概念,主要因为在该概念中:祖先崇拜是一种对人自身的崇拜;祖先崇拜的本质是血缘崇拜;祖先崇拜的外在表现是英雄崇拜;祖先崇拜与父权制等社会现象的出现具有高度关联性。
1.黎锦人形纹中的祖先崇拜
人形纹在黎锦筒裙上往往占据突出和醒目位置。由蛙纹演变而来的人形纹是黎锦筒裙的主要图案之一,在哈、杞、赛等方言黎锦筒裙上,往往会留出一个单独的位置来表现这一主要的纹样。这些纹样之间一般有较大的隔离带,使主体纹样以独立的形态、通过放大的方式,织绣在筒裙最显眼的位置。关于蛙纹与人形纹二者的关系问题,由于没有相关的历史文献作为参考而无法确知,但存在以下两个基本事实:一是黎锦筒裙纹样的基础是菱形纹,这种菱形纹更接近于蛙的形象而不是人的形象;二是这种菱形纹不仅存在于黎族各方言黎锦筒裙上,还同时出现在广西壮族的织锦图案中,并且普遍存在于其他西南少数民族织锦中,只是由此演变出的人形纹在其他西南少数民族纹样中却极为少见。
从以上两个事实出发,按照文化变异理论,可以推测黎族文化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曾经与西南少数民族有相同的情形,但在其后的历史发展演变中演化出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原始信仰形式。基于这两点,大致可以推测:黎锦筒裙上的人形纹是由蛙纹演变而来的。关于这一点,在黎族民间神话《蛤蟆黎王》中可以看到蛙纹向人形纹转变的影子:一个长着一身蛤蟆皮的年轻小伙通过帮助黎人打败官兵,被黎王招为女婿,最终推选为新黎王[10]159-160。
在这则故事中,黎族的祖先被塑造成一个英雄式人物,他通过自己的勇猛和精通巫术打败敌人,成功继承了黎族王位。但他是一个亦人亦蛙的复合形象,白天为蛙、晚上为人。蛤蟆黎王的神话一方面显示出黎族氏族社会统治权的更迭,有时是通过武力方式来完成的;另一方面,这则神话暗示了蛙纹向人形纹的转变,即原始的生殖崇拜被祖先崇拜所替代。
此外,某些方言黎锦筒裙纹样已经在人形纹基础上演变出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力神纹。如在黎族润方言黎锦筒裙上的人形纹,已经开始演变出具有神灵性质的大力神纹样。大力神纹样较之于普通的人形纹,体积更为庞大,形象更加威严,色彩更为艳丽,构图更加精致,已经远远不同于其他普通纹样,而具有了特殊的文化意义。从这一点看,黎族对人自身的崇拜已经基本成熟,预示着向神灵崇拜过渡。由这些图形及其所包含的意义可以看出,黎锦筒裙上的人形纹反映了以对人自身崇拜为核心的祖先崇拜。
黎锦筒裙纹样上的人形纹在黎族各方言中一般都具有明确的含义,比如在润、哈、杞方言中被称之为祖宗图,在美孚方言中称之为祖先鬼。因此,人形纹就被黎族赋予了祖宗的内涵,而祖宗这一观念在黎族民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氏族的象征,类似于氏族的保护神。黎族传统观念认为,人是有灵魂的,死后会变成“鬼”,在其信奉的众多“鬼”中,“祖先鬼”亦称“父母鬼”,是地位极高的崇拜偶像。“黎族人普遍认为祖先鬼比其他鬼还要可怕,平时禁忌念祖先的名字,怕祖先灵魂回到人间,导致家人生病。甚至有的还认为始祖和二三世祖先鬼是最大的恶神,严重疾病或生命处于垂危状态,都是这些祖先鬼作祟的结果”[11]。祖先鬼控制着人的生死康疾、荣衰祸福,因而,凡事必须求巫作法,求佑于各自隶属血缘的“祖先鬼”。
此外,黎族妇女文身的纹样也被普遍认为是用来区分氏族血缘的,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的关联。据刘咸1934年所做的黎族调查,关于黎族妇女文身的起源一共有三种说法:“(1)黎人祖先概行文身之俗,子孙守祖宗遗制,依样葫芦,若生时不文身绣面,取具本支本族或本家之特种标识,则异日死后,祖先因子孙太多,难以遍观尽识,倘不幸祖先不认为嗣孙,则将无所归属,永为野鬼。盖黎人心理,以为生而为黎,已属不幸,死而为鬼,兹可惧也。(2)文身之始,由于上古时族类互残,每俘掠妇女,载之俱归,为战利品。因此各族妇女,于将成年时,均默面文身。族各有图识,所以免族类混嚣,易于辨识,及去女子之美妍,藉免为俘虏,意盖两善。(3)上古之时,天翻地覆,世界生物尽被淹埋,人类同遭此厄,仅遗一姊一弟,相依为命。然姊弟虽情亲手足,终不可以婚媾,于是姊觅夫,弟觅妇,分道扬镰,各自东西,久之各无所遇,终乃姊弟重逢,如此者再。雷公知其事,化为人身,下凡谓弟曰:‘今予在此,汝二人可结为夫妇’。弟曰:‘姊弟不可以婚姻,否则必遭雷公打。’雷公曰:‘我即雷公,决不打汝’。弟仍坚持不可,重出觅妻,于是雷公将姊之面划黑。无何,弟再遇姊,不识为谁,以为必非己姊,可以求婚,于是姊弟结婚,繁衍生殖,而得今之黎人。”[12]此三种说法即为谨遵祖制说、俘虏说和人类起源说。
波里尼西亚语(Polynesian)之文身起源的传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承祖先遗制,依样为之,俾死后祖先易于辩识,收为子孙。(二)古时天灾流行,地球覆灭,仅遗母子出人(一说姊弟),但不得婚媾,于是上帝降旨,命母涅面文身,不复相识,遂相为婚媾,繁衍世界之人类。”[12]这两种说法即为谨遵祖制说和人类起源说。
以上诸种说法尽管内容差别很大,但本质上都强调文身的基础是氏族血缘关系的标识,即认为只有同一氏族成员的鬼魂才能相互识别,因而需要以文身来作为同一氏族成员的标志。文身纹样的功能作为氏族标志以区分不同的氏族,划下各氏族之间的界限。这些说法体现出的是以血缘崇拜为内涵的祖先崇拜,是对已鬼灵化祖先的尊崇和敬畏。
在人形纹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黎族润方言黎锦筒裙上的大力神纹,呈现出威猛、高大、神武的形象。大力神在黎族民间神话中是一个英武神勇、法力无边的祖先的形象,不仅帮助黎人把炙烤人类的六个太阳和六个月亮都一一射落,而且把天上的彩虹取下来当扁担,把地上的道路拾来作为绳索,去海边挑来成堆的沙子造山垒岭,把自己梳下来的头发撒向群山变成茂密的森林,用脚尖踢划群山凿通了无数的沟谷,其汗水流淌在这些沟谷里形成了奔腾的江河……最后,大力神临死前,怕天倒塌下来,撑开巨掌把天牢牢擎住,黎族地区巍然屹立的五指山,就是大力神的巨掌[10]1-2。这则黎族神话塑造了一个开天辟地式的形象,是一个具有超强能力的英雄人物,具备了英雄崇拜的基本特点:无所不能、威力无比,是具有开天辟地能力、高大魁梧的男性祖先。这则故事说明此时黎族人类在面对自然灾难时,其愿望的诉求对象已经不是天上的雷神、地上的蛙神、鸟神等,而是转向了人类自身,是那些手持弓箭、具有超强武艺的男性英雄,呈现出了父系氏族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
2.黎锦人形纹中的父权制社会痕迹
哈方言、杞方言、赛方言的某些人形纹中,具有典型的男性特征,如图7。

图7 哈方言人形纹

图8 黎族杞、赛方言中的男性人形纹
该图案中的男性特征非常明显:一是织绣有非常明显的男性生殖器,二是手持弓箭。除此之外,其他方言中的纹样中也有类似的图案,如图8。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不仅体现在黎锦筒裙纹样中,在黎族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黎族村前一般都有土地庙,庙里不设神位也不摆香炉,只有一块雕刻的形如男性生殖器的石头,黎家称为“石且”,“石且”正是黎族父系氏族社会的标志。正如孟慧英在《父系氏族公社的萨满教》一文中所言:“父系血缘关系的确定和神化是父系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对这个基础的强化和神化是出自现实生活的必然要求……考古学证明,母系社会把对女性生殖力量的崇拜作为自己统治的观念基础,到了父系社会男性首先利用神化自己在人类繁衍中的祖先来建立男性独尊的重要思想,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是父权制在战胜母权制过程中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13]
因此,黎锦筒裙上的蛙纹向人形纹的过渡和转变、人形纹中男性生殖器的出现,反映了黎族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这种过渡特征充分反映在五指山麓黎族“合亩制”的独特生产方式中。在海南中部的黎族地区,直到解放前夕尚保存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合亩制。合亩,黎语“坟茂”,即合伙生产,一般由有血缘关系的3~10户组成。耕地为合亩所有或各家私有,合亩使用;耕牛和农具为各家私有。亩内有亩头,由辈份最高的男性担任,亩头主持亩内的生产和分配;播种、播秧、收获均由亩头或其妻下田先干,亩众方可动手,收获新谷时也由亩头先食用;发生纠纷时,亩头有权处理,亩头死了,弟继,无弟可传长子。由此可见,早期的黎族合亩制地区实质上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男性为生产生活的主导、共同生产、共同分配劳动产品的生产关系。这时父权制已经逐渐确立,男性已取代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在商议重大事件及举行宗教祭祀时,也主要以亩头代表的男性为主体,女性在生产生活以及宗教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黎锦男性人形纹所呈现的是以男性为血缘纽带的祖先崇拜。
人形纹在黎族各方言黎锦筒裙上的广泛分布,构成黎锦筒裙的一个重要纹样,它是黎族祖先崇拜观念的具体体现,据此可以推测,黎锦人形纹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黎族织锦的完善时期大约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约于距今3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后期。
[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69.
[2]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黎族古代历史资料:内部资料[D].1964.
[3]符兴恩.黎族·美孚方言[M].香港:银河出版社,2007:2.
[4]黄政生.黎族妇女服饰[J].装饰,1980(4):11 -17.
[5]秦寄岗.从黎族服饰图案看黎族人民的审美意识[J].装饰,1987(4):12-13.
[6]符桂花.黎族传统织锦[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286.
[7]阿朝东.从青海柳湾人像彩陶壶谈人类祖先崇拜现象[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32-34.
[8]葛季芳.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生殖崇拜[J].民族艺术研究,1991(3):61-68.
[9]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黎族民间故事选[D].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67.
[10]王学萍.中国黎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1]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M]∥詹慈.黎族研究参考资料选:第一辑.广州:广东省民族研究所,1983:167.
[12]孟慧英.父系氏族公社的萨满教[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37-42.
[13]董小俊.再论黎族“合亩”制的社会性质[J].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1):4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