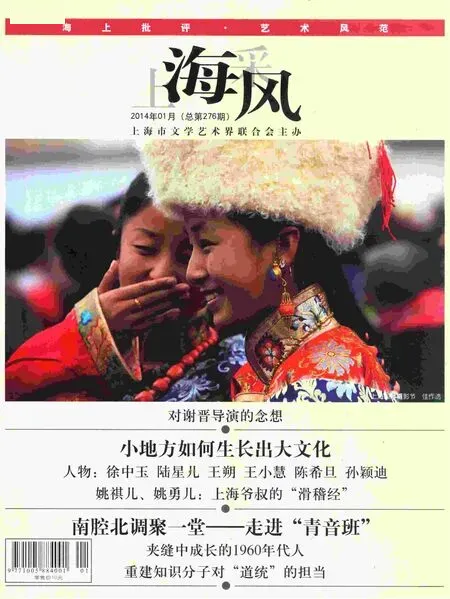观点集粹
2014-11-17
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
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在论及改革条件和目的时,把“解放思想”列于首要位置,并特别强调其“总开关”作用。如果说,过去的解放思想更多是“头脑风暴”,今天解放思想则要面对现实的利益博弈。一些人嘴上说思想解放,骨子里怕思想解放;一些部门抽象地赞成思想解放,具体地反对思想解放。说到底是一个利益问题。从调节分配到简政放权,许多时候,影响改革的思想障碍很多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尤其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羁绊。正因如此,中央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全局和局部、长远和当前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坚决克服地方和部门利益的掣肘。在新的时代场景中解放思想,不仅要有时不我待的历史主动,更要有自外于既得利益的政治担当。只有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改革者才能摆脱局部利益的狭隘,穿透短视思维的迷雾,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实现长远可持续的发展。试想,如果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破冰,怎么会有蕴藏于农村中的生产潜力的充分释放?如果害怕竞争拒绝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又怎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正是看到这一点,约翰·奈斯比特才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感叹:“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当然,敢于解放思想,更要善于解放思想。呼唤解放思想的勇气,激发大胆探索的豪情,并不意味着脱离实际、盲目蛮干。解放思想是探索规律、追求真理的过程,必然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解放思想,首先要有指导思想,如果不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所谓“解放”就可能走向反面;解放思想,为的是解决中国问题,如果只是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所谓“解放”不过是头脑发热。我们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即便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而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今天思想解放不可能是一声令下的活动,也不是靠等“指示”、等“批准”就能实现的。警惕解放思想“口号化”、“标签化”,不仅需要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具体而微的基层实践;不仅要冲破思想观念障碍,还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甚至还可能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从这个角度,解放思想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个人的勇气担当,也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35年后,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要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就要坚决破、坚决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只要有利于”,既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共识,也应成为锐意探索者的底气所在。
党内也有民粹思想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民粹情绪,不要说是底层社会,其实在执政党内也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民粹情绪和民粹意识,党内可能都没有清晰意识到。看我们在党内,我们对民主的理解这么简单,我们的政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把民主和民粹分清楚。受几千年的专制政治的文化传统影响,容易走向民粹而不是走向民主。比如,什么东西都是多数人说好,无论是选任和委任都在搞投票,表面上唯票是举,好像是搞民主,其实是民粹。表面上投票,但是并不当场公布,宣布的时候就借着多数票的名义,实际上仍然是少数人意志。把表面的多数票和骨子里的少数权力意志,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客观上形成的负面效应是非常大的。在干部问题上是这样,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为了平息民怨,立马就把一个干部免职,为什么?那么被处理的干部是不是有问题?不问体制机制的缺陷,把干部当成体制机制的替罪羊牺牲掉了。还有工程项目上,为了迎合社会公众的情绪,造成决策随意多变。骨子里是偏向于既得利益的,但是外在的处理手段,受民粹情绪影响,通过安抚、迎合,其实它是被民粹绑架,对不对?所以学者们担心,我也担心,官方和民间看起来对立,其实大家都是民粹思维。因为法制权威没有起来,没有形成不同利益群体在法制框架内理性博弈的机制,所以决策容易被既得利益和民粹绑架。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呼唤民主法治,但也不能不看到,资本对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压榨也是很残酷的。但现在的状况是不少底层民众对毛时代很怀念,推崇重庆模式,就是因为底层社会直接感受到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榨,他所希望的是比一般权力和资本更强势的更大权力,呼唤清官,呼唤明君。因此学者们要呼吁两个东西:一个是在权力面前,我们都应该朝着民主方向去努力。第二个是不能回避社会公正问题,要运用民主法治遏制资本对底层群体的利益侵占。
中国老人变“坏”了?
凤凰网关于“中国老人变‘坏’了?”的调查引起极大关注。目前关于老人的新闻层出不穷:先是唐山老人的广场舞打扰到附近学校,高中生站立抗议,却遭到了老人的羞辱;紧接着,广东汕头两名高三学生扶起了骑电动车摔倒的老人,反而被老人诬陷讹诈,报警后才获清白;更有甚者,西安一位老人因为女孩不肯为其让座,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大江南北,莫不如此,让人疑惑中国老人为何集体变“坏”了?于是,不少人开始怀念过去,怀念过去的老年人是多么有教养,多么讲道理,怀念过去的社会是多么的“平静与安详”,不似现在这般“赤裸裸”。而老年人不讲道理、“变坏”的原因也被归咎于社会的发展,认为正是因为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复杂甚至浮躁,才造成以前那么纯朴的老年人现在变得如此这般的不讲道理。可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教化并不差,现在的困境不能赖账到老祖宗;这也不能怪西方文化的传入,不能说改革开放让大家学坏了。随着越来越多人出国,大家都知道了西方社会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并不低。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老人变“坏”呢?
老人变“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长时期他们的生活、经历已经所接受的教育,而把责任推给他们成年后的社会开放,显然是不公平的。众所周知,近几年出现的“新晋老人”大多出生于1949年前后,在他们的成长时期,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匮乏”。在他们长身体的时候,却正好遇到“三年困难时期”,食品短缺和饥饿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物质观念的形成。哪怕到了物资充裕的时期,记忆中的“匮乏恐慌”还是会使他们试图占有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源,而为了物质甚至不惜大打出手甚至铤而走险。与物质相对应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在物质长期匮乏的背景下,人类的活动唯一目的几乎就是生存下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且伴随着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国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被打破,而新的道德观念又不存在,为了生存下去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环境下,这一时期的人们也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他们是喝着狼奶完成启蒙和基础教育,得到的是一种丛林里比划谁的拳头大的价值观。而最要紧的是,没有什么禁忌也没界限。想想看,道德的底线在哪里?尊老爱幼,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这些就是底线。很不幸,老人家们成长的年代正是恶没有底线的年代。而狼奶教育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理智和知识的缺陷。老人家们都不适应多种声音的局面,不知道如何理性地辩论,他们习惯一人独语的一言堂。诉诸理性,宽容异己,这种理智和道德上的品质,恰好是洞穴教化无法造就的。而知识上,老人家们当年成长时期的中西经典诵读几乎空白,没有一点诗书礼乐的熏陶,这导致他们的粗野无知。
当初种下的恶果,如今就到了“收获”的季节。于是,他们不觉得广场舞可能会对他人造成困扰,不觉得让座是一种关爱而并非理所应当,甚至可以颠倒是非、诬陷他人,成长时期基本公共教育的缺失,使他们认为一切都理所应当,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的利己。
当然,除了教育之外,还与另一种他们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政治运动,把人性中最恶的部分激发了出来。很不幸,老人家们成长的年代正是恶没有底线的年代。历次的政治斗争激发出人性中最恶的因素。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师长都可以批斗,连同床共枕的夫妻之间都可以相互揭发,还有什么可以信任?还有什么坏事不可以做?无论他们之后还经历过什么,在价值观形成期所经历的一切已经足够影响到他们中的很多人了。人,是看着父辈的背影长大的。品行的教育,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和周围的长辈言传身教,靠的是耳濡目染。恰恰是这一代人,成长期间有许多空白,也有很多盲点,最该接受道德哺育、情操导引、汲取文明的时候,不是浩劫,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结果,等到当了父母辈或者祖辈,以身作则,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为老不尊,则更成了一景。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老干部的“两头真”现象
文史博览刊文说,“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