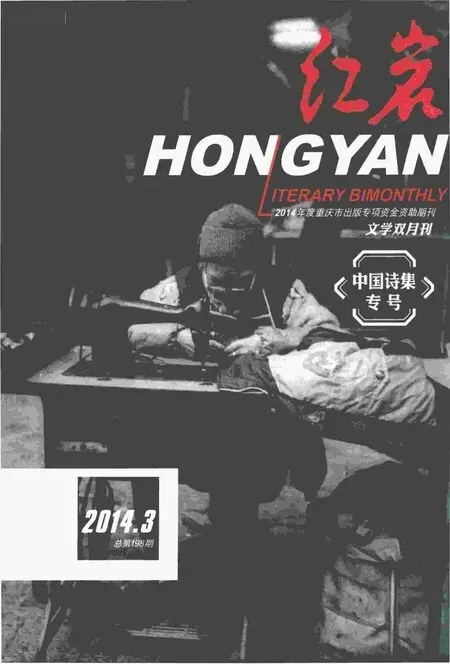王家新诗集
2014-11-15王家新
野长城
在这里,石头获得它的分量
语言获得它的沉默
甚至连无辜的死亡也获得它的尊严了
而我们这些活人,在荒草间
在一道投来的夕光中,却显得
像几个游魂……
冬日断章
在这个冬天我最大的渴望
就是阅读一只闪光的冰斧
和它带来的仁慈。
醒来
你为什么醒来?
因为光已刺疼我的眼皮,
因为在我的死亡中我又听到了鸟鸣,(那又是一些什么鸟?)
因为我太疲倦,像是睡了好多年,
因为我听到了,在一条柔嫩的枝头上
有一阵光的晃荡,
然后是钢水般的黎明……
因为我睡了这么久,睡得这么沉,
(像是中了什么咒语)
就是为了在这个陌生的、让我流泪的
语言的异乡醒来。
清晨,惊闻希尼突然逝世,来到爱荷华河边
现在,我能做什么?
现在,在一棵挺拔的白杨和一棵
弯斜向河面的老榆树之间,
让我来把那座老铁桥赞颂—
每天每天,车流从它的上面驶过,
光膀子的青年跑过,穿球衣的女生跑过,
同性恋、异性恋情人们手牵手走过,
校车、邮车、货车、载重卡车和工程车驶过,
桥以它刚强的石头桥礅和拱形铁臂
一次次撑起了这一切,
—即使在这个悲痛的
呯然一声落下的早上也是如此!
而我知道了什么叫“承受”。
我知道了什么叫“生生不息”。
我还知道了我所热爱的诗人为什么会说:
“我在两者之间成长”。
只是,我的老铁桥!你在什么地方留下了
一阵坚固而轻微的
颤抖……
参观安迪·沃霍艺术馆
还没走近那些“电椅”
我就听到了
一声烧焦的惨叫
而在四周
在更近处,在更远处
在我来的那个兵马俑的国度
在火花四射的短路里
回声传来
不断传来
红色、蓝色、暗棕色、灰烬色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那么多
仅仅—
作为伴奏
在爱荷华
在爱荷华,
早上使我欣喜而黄昏
使我软弱。
在爱荷华,
我需要发明某种仪器,来记录那道
来自“未来”的光。
在爱荷华,
每天我和树上的一只小松鼠
相互瞪视,
而不需要翻译。
在爱荷华,
在一个深夜,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
听见了一声
鱼的“泼刺”声……
黄昏或黎明
在爱荷华,从早到晚,我在河边散步
我听着清晨的鸟鸣
我观看夕光怎样透进松林
(在草坡上留下幽灵般的倒影)
有时我想到我自己的国家、我的遥远的童年
有时我想到更加迷茫的未来的某一天
现在我要问自己:你要做一个黎明的诗人
还是一个黄昏的诗人?
做一个黎明的诗人
你能否像那个晨跑青年一样,每天从这片惠特曼歌颂过的大陆跑过?
你是否还有力量从另一个早上重新开始?
而做一个黄昏的诗人
当那颗命定的星辰升起,你是否还会流泪?
是否还有勇气接受黑夜的邀请?
啊,我的星辰
我的像处子一样安静的黎明
我的说来就来的黄昏
你们都在我的身体中活着
你们都在要求我赞美
现在,我再次来到你的门口
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
来,把你自己完全献給黑夜吧
你的路还只走到一半
此刻为你闪现的长庚星
也许就是你未来的启明星
它神秘而又忠诚!它在等待着你—在黎明到来时和你一起隐去
一个人的河流
1
在秋天,爱荷华的太阳更温和了
而它投在河水中的波动
像是泪光
2
在爱荷华,在它镜子一样的河流里
一只灰褐色的野鸭
像一艘巡航舰一样驶来
双翅在水面上划出一个银光粼粼的“V”
3
青铜的十月,女孩们躺在草坡上
叉开光亮的双腿
这是她们向太阳致敬的一种方式
而在走过她们时我的步子放慢了
这是我向时光致敬的一种方式
4
在爱荷华,河流无风而汹涌
因为这是我的河流
这是我在河边读老杜时感到的河流
5
在爱荷华,我们赞美黎明
可是除了那些在树上筑巢的鸟
谁能看到那一道
柔弱展翅的光?
6
而到了秋天,人就有点想流泪为那些遥远的事物
为蟋蟀的最后一阵歌唱
为河水中露出的那几块光洁的还散发着热气的石头
为一个夏天的烘烤
哦,现在,阳光使我有点发冷
7
在爱荷华,总是在无人的时候
我向河边的那棵大橡树走去
在那里,在小松鼠黑珍珠般的眼睛里
有着无敌的光和寂静
在圣地亚哥—给金重
圣地亚哥风起云涌的天空让人流泪,
圣地亚哥的朋友也让人流泪;
圣地亚哥的屋檐下挂着几个谁也舍不得吃的中国东北家乡的柿子,
圣地亚哥成了流浪者和诗人的家。
圣地亚哥的大海和那些尖叫的迎风飞起的鸥鸟
让我多少年来第一次张开双臂想要欢呼,
圣地亚哥的庭院永远摆着几把空椅子。
圣地亚哥的朋友送我到机场,临别时紧紧拥抱了一下,以至于我的胳膊到现在都疼。
圣地亚哥屋檐下的柿子,会永远在风中摇晃,
像几个温暖的汉字,
像一盏盏吹不灭的灯笼。
在纽约—给一个人
纽约让我有点伤感。
纽约让我知道了我终归是个异乡人。
来到纽约,我知道了我还有许多诗未写,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喜欢纽约。)
在纽约我爱在大街上漫游。
在纽约我知道了我迷失得还不够。
在纽约我爱在星巴克坐下,
来一杯咖啡,为了它的热气,
也为了自己替自己付账。
在纽约,什么也不会发生。
在纽约,有那么多美女擦肩而过。
在纽约,只有一次,也只是那么一瞬
当你裹着黑色长风衣匆匆赶来
我差点愣在那里——那是你吗?如果
(多少年前?或多少年后?)
你就是那个在我的远轮减速、靠岸
在码头上为我出现的人……
旅途散记
1
这是从杭州到北京的高铁
坐在上面的你是不是
还是那个在苏堤上散步的人?
2
松江,虹桥……
发电厂巨大的烟囱
仍在喷吐着灰烟
它似要瞄准
太阳中的黑子
3
时代在提速
但你真正能看到的东西
却是在减速的那一刻
而我们似乎已不需要去看
我们只需要一个更伟大的荒漠
供我们打盹
4
进入北方
一望无际的冬小麦
像是又一茬年轻诗人
在霜寒中发愤抒情
为什么你要醒来?
仙人掌的尖刺
在一个梦中刚刚展开半径
5
车厢暗下来
有人靠近了他看的书
这嗡嗡的静音
也正是此刻,东坡居士
我们拥有了
和你的不一样的寂静
另一个故事
要讲出这个故事你得回到一个梦中,
或是被那个梦再次梦到。
似乎最初是和翻译有关:
一位诗人前来同你谈些什么,
因为她要到俄国去。
而在黑暗的山洞前,
人们燃起火把,唱着山西梆子,
成群的人,不,成群的幽灵
绕着火堆,在用单腿蹦跳,
蹦……
(那火把映出的黑暗
在一只非洲狮疲乏的眼中晃动)
而你在梦中紧紧抱住了她:
“那时你还很瘦,
但你的皮肤
是那样光滑……”
翻/译。
翻/译。
无人会感到一种语言的舌头
是怎样抵及到另一种语言的上颚。
醒来,莫名的痛苦。
(但这只是一个梦。
有什么从你的怀中永远溜走了,
有什么用单腿
突然蹦跳到你的面前—
如此而已。)
你在傍晚出来散步
你在傍晚出来散步,其实也不是散步,
只是出来走一走,像个
放风的犯人。没有远山可供眺望。
四周是高楼。
腊梅的幽香也不会为你浮动。
又是十二月,树梢上
孩子们留下的喧声也冻僵了。
你走过街边的垃圾筒,
那些下班回家的人们也匆匆走过,
也就在那一刻,你抬起了头来—
一颗冬夜的星,它愈亮
愈冷。
写给未来读者的几节诗
1
在这个雾霾的冬天所有我写下的诗,
都不如从记忆里传来的
一阵松林间踏雪的吱嘎声。
2
玛丽娜用鹅毛笔写作,
但有时她想,用一把斧子
也许可以更好地治疗头疼。
3
昨晚多多在饭桌上说:“写一首
就是少一首。”
我们听不懂死者的语言,
活人的,也听不懂。
在伟大的诗歌中(之二)
在伟大的诗歌中
有一只乌鸦,一群麻雀
在同一雪地里散步
在伟大的诗歌中
我遇上了突然插嘴的石头
在伟大的诗歌中
语言同我们嬉戏
如同一个幽灵
在伟大的诗歌中
我们找不到它的压舱石
我们自身的分量不够
在伟大的诗歌中
晚脸是一个词
站台和光流量也是同一个词
在伟大的诗歌中
我梦到了钢轨上的黎明
也梦到了断头台上的黎明
我们不是和曼德尔斯塔姆而是
和一只金丝雀一起翘起了脑袋
在伟大的诗歌中
我们会忽然怀念起多年前
那刮来的一阵穿堂风
马
有时我们看到的马有一双孩子的眼,
有时我们看到的马有一双囚犯的眼,
有时我们看到的马,一转眼化为树木和岩石,
有时我们看到的马,比天使还要羞怯……
但此刻,我的马,你从雾霾中向我们走来,
在你的眼中我看到一场燃烧的火灾!
献给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一张书桌
这里是献给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
一张书桌,
以悲痛的大理石制成,
书桌面对一张窗户,
窗户边有一棵花楸树,更远处是但丁消失的密林;
书桌上,一个烟灰缸和一杯
不断冒着热气的中国绿茶,
还有一把沉甸甸的橡木椅子,
一支拧开一个大海的钢笔,一支陡立的“压向未来的笔”—
写吧,灵魂已呼啸在空中!
写吧——即使死亡的狂风
也吹不动那纸页,
写吧—即使你永远也不会
出现在那里。
在伟大的诗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