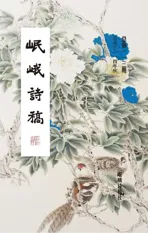一言难尽说清诗
2014-11-15滕伟明
滕伟明
一言难尽说清诗
滕伟明
清朝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朝代,这个朝代兴过文字狱也编过《全唐诗》。清人好学习,连皇帝都是博览群书,出口成章。如果客观地考察,只要你不写『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胡儿)搁半边(徐述夔)』那样的诗,一般也不会杀头。比起明朝,清朝好像还宽容一点。因此,清诗是有成就的,它远远超过了明诗。从内容上看,清代所有大事几乎都得到反映。从形式上看,清人的技巧还超过了宋,已达到十二分的圆熟。但是,清诗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没有产生大家。清代名家辈出,但就是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那样的大诗人。清人赵翼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新岂易言!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为嫌,是必拾人牙后,人云亦云;否则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是尚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瓯北诗话)稍后的王国维说得更清楚,不能『感自己所感、言自己所言』,就不配叫做大家。为什么,因为清诗『不新』。唐诗有面目,宋诗有面目。有人说清诗是『唐神宋貌』,『唐神宋貌』适足证明其无面目。如此努力经营过,还是沦为第三,实在叫人惋惜。
清代的确有不少好诗人,就是随意在路边冷摊上淘得一本清人诗集,起码也是可读的。但读着读着,就有一个感觉,他们的思想,还是唐宋的思想;他们的辞藻,还是唐宋的辞藻,只不过句法更加圆熟而已。当我们读到黄仲则的《绮怀》:『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时,非常佩服他能如此细微地捕捉心绪的变化,但我们一比较范成大《秋前风雨顿凉》:『但得暑光如寇退,不辞老景似潮来。』就发现他们的路数都是一样的。再看赵翼自己,《赤壁》:『千秋人物三分国,一片河山百战场。』很欣赏他句子的洗练。但比较黄庭坚《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就发现赵翼的功力也不过如此。如果选一本清诗三百首,结果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几首就打发了。要想找到李白、杜甫、白居易那样的标杆式人物,那是很难很难的。
现在就来逼视一下有可能成为大家的人物。龚自珍《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差不多成为龚自珍的名片,一说龚自珍就想起它。但《己亥杂诗》三百余首,可选的也就四五首,就是这一首,走的也是『气骨』的路子,『万马齐喑』是虚象,『不拘一格降人材』是直说。这种呼喊当然很好了,但都这样写,也未免有些苍白。《夜坐》:『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以楚骚入诗,芳草美人,箫心剑气,却也瑰奇,但与现实就隔着一层。何况这种手段,黄仲则也有。龚自珍仍然只能算是名家。
黄遵宪发起『诗界革命』,被目为革新派的领军人物。也看他的《己亥杂诗》:『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当时看是很新的,但一味直说,未免枯燥,而且他的心史也未应验。《夜起》:『千声檐铁百淋铃,雨横风狂暂一停。正望鸡鸣天下白,又惊鹅击海东青。沉阴曀曀何多日,残月晖晖尚几星。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写日俄战争,被目为黄遵宪的代表作。细看诗中意象,差不多都是旧的,只有『海东青』新。而这个『海东青』却害死人,原来它是辽国民歌,此处代表辽宁,又特指日俄战争所在地旅顺。鹅当然指俄国了。本欲翻新,结果弄得更复杂了。所以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心』只是口号而已,他自己也未实行过。黄遵宪也只能算是名家。
最后就是陈三立了。一九三六年,中国推举陈三立、胡适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笔会,被邀请的还有印度的泰戈尔,但未成行。胡适的《尝试集》当然赶不上陈三立,但陈三立也赶不上泰戈尔。泰戈尔是大家,是国际公认的大诗人。陈三立已经很不错了,但还只是名家。清人对封建时代的诗歌作了一个很不错的总结,但他们无力突破,也无基础产生但丁式的伟大人物。中国的国情,实在一言难尽。
从形式上说,清诗似乎选择了一种更古、更艰深外衣(当然不是全部),有故意卖弄学问的嫌疑。翁方纲的『肌理说』,笔者是不大赞成的,因为他反对『诗有别才』,鼓吹义理(即肌理),所以不讲它。但要考察清诗的倾向,还得拈出他的『学人之诗』,不然无法认识清诗的主流形态。清人有学唐的,有学宋的,翁方纲对王渔洋、沈德潜不满,力主学宋,于是按自己的需要把历代诗人重新作出归类。他说:『有诗人之诗,有才人之诗,有学人之诗。齐梁以降,才人诗也。初盛唐诸公,诗人诗也。杜则学人诗也。然诗至于杜,又未尝不包括诗人、才人矣。』 (复初斋文集)诗本来只有一种,就是诗人之诗,但他抓住了杜甫的复杂性,把他作为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的总代表,这就为以学问入诗找到了借口。我们曾经说过,唐人是『风人』,宋人是『文人』。风人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文人是『好发议论,崇尚气骨』。清人呢,继续走宋诗的路子,但变本加厉,不光好议论,而且还要求议论时显出学问,不会用典,你就下去。这就是『学人之诗』了。我们如果比较一下唐诗、宋诗和清诗,就会惊奇地发现,唐诗最浅,几乎不用注。宋诗稍微深一点,要加点简注。清诗不得了,不加注你就读不懂。我们看清人的集子,发现很多人都是自己先注了,有的还是一句一注,因为他生怕后人读不懂。这就怪了,唐诗离我们最远,反而易懂;清诗离我们最近,反而不易懂。这就是『学人之诗』给我们带来的负担。下面我们就以席子研为例,看他是如何表现中法战争的前期状况的,括号内是他的自注(边事感怀)。
专征假节拜宸宫,旗鼓堂堂仰召公。(甲申春初,朝旨命湘抚潘鼎新出关,旋授桂抚。)裹甲将军来树下,从征僚佐赋桑中。(时提督杨玉科、苏元春皆寄居湘省,募军投效,随员幕友皆携眷而行。二月杪潘公抵粤,次日策马遍览风洞山、独秀峰诸景,越日启节。)谢安先着游山屐,李广谁传射虎弓。(巡检李某上书,能造档牌,可御洋炮。其法……)河上逍遥惊虏至,可怜回马太匆匆。(法人知其无备,骤然攻击,北宁、谅山失守,提督杨玉科殿后,阵亡……)
你看怪不怪,诗写的是一回事,注释是另一回事。离开了注,这样的诗就成了『天书』。事情还没有完,如果要完全读懂这首诗,恐怕还得请人对他未注部分『作笺』,因为『召公』 『树下』 『桑中』 『游山屐』 『射虎弓』这些辞藻还未弄懂呢。可见,『学人之诗』把我们带入了迷途,清诗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光是白费了,而且是误人的。
当然,清诗也不完全是需要一句一注,一些高手还是努力做到流畅自然。但是,有一个毛病是共同的,就是在他们心目中,不用辞藻和典故就是『白』,就不是好诗,因为他们在无形中已经认同了『学人之诗』。现在我们来看看清季的『同光体』,这个被誉为『超唐迈宋』的诗派究竟如何。
沈曾植,同光体浙派领袖,《到家作》:『病与愁兼复几时,还家迢递一年迟。芜城剧有参军感,旧馆难为长史思。燕守空梁甘寂寞,莺依晚树话流离。此生行共飘摇尽,惭愧迎门稚子嬉。』这是清亡后回家之作。『梁燕』 『流莺』都不讲了,要读懂这首诗,起码要搞清颔联是什么意思。『芜城剧有参军感』,这是把自己比作鲍照(他曾任参军),鲍照写有《芜城赋》,对比广陵的繁华和荒凉,不胜故国之思。沈曾植肯定是对鲍照的『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豆剖而瓜分』深有同感,才用『参军感』来代替自己的感受。『旧馆难为长史思』,这里又把自己比作孔稚圭(他曾任长史),孔稚圭写有《北山移文》,表明自己坚守归隐之志,讨厌再做官了。诗好,也有真情实感,但读者首先也必须是一个『学人』才读得懂。这个路子是不是太窄了点?
陈三立,同光体江西派领袖,《晓抵九江》:『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鼾声邻榻添雷吼,曙色孤篷漏日妍。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雁万峰巅。』这首诗写于《辛丑条约》之后,那种悲愤之情使人久
久不能平静。我们应该承认,这已是清诗的最上品了,但要读懂它,你仍然必须是个学人。『藏舟夜半负之去』,就是说一夜之间,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搬到九江了,但因是学人的原因,他还是用了庄子的典(夜半负山去)。『鼾声邻榻添雷吼』,表面上是写旅客的酣睡,其实是写列强的猖狂,这里又用了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那个典。『琵琶亭畔客』就不说了罢。我们不是说陈三立是故意卖弄学问,他是无意的,他不知不觉,就选择了清诗的主流形式(学人之诗)。直到现在,如果要表现高格,我们往往也仿照陈三立的写法。看来要构建当代诗词的全新面目,还有好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