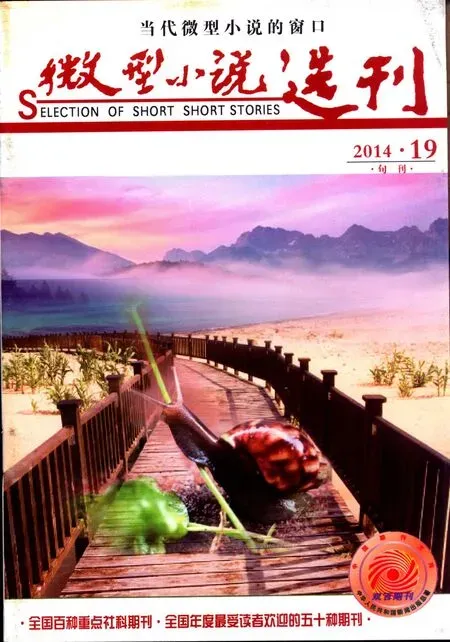最后的秧歌
2014-11-15徐建英
□徐建英
最后的秧歌
□徐建英
正月十五闹花灯,鄂南人爱热闹,大多地方都兴耍龙灯,舞狮灯,唯独那湖村人,一代一代的,唯独只对船灯情有独钟。
湖村船灯一般以竹篱或木条制成的船形,在船体上蒙画布,左右开一孔小圆窗,四周挂上小灯笼、小流苏之类;舱内和外四角装上彩灯,点蜡烛,由一名年轻力壮的男子,藏在船舱内,以安装的挎带肩扛起船身,不停地左右、前后摇摆,表演船在各种江河中航行的动作。船头船尾上各站一人,船头的扮丑角,叫艄公,持花桨摇船。船尾的扮艄婆,打着花扇边扭边唱灯歌。
离元宵夜节还有好几天,鄂南各村各寨的花灯开始沿村耍灯拜年。湖村的船灯每到一地,得到的喜礼都会多过别村灯队。县里一年一度的元宵夜花灯大赛,湖村的船灯也是年年独占鳌头。所以每年湖村开灯河,十里八乡的大人孩子都赶着看,花灯闹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更多的,他们是为了看湖村的艄婆,看那扮艄婆的姑娘水仙。
水仙姑娘扮艄婆,嗓音好,歌声亮,腰肢活。那小步一错,身段扭扭,扭得老人齐叫好,娃娃们笑翻天,女人回到家跟学样,更扭得不少老少爷们心猿意马痒得慌。
随着一曲:正月哪个里来是新哪个春,家家呀户户戏花呀灯……船灯缓缓飘了过来,在一片鼓乐伴响中正式拉开了帷幕,只看那扮艄婆的水仙摇着花纸扇,错着小步一路飘过来。那扮艄公的正权,头戴一顶破草帽,脚趿一双旧球鞋,满脸抹着东一块西一块的烟灰渍,手里拖着花桨左一划,右一摆地跳进了场。水仙唱一句,他插科打诨的调侃立即就加了进来:啊哟,这是哪里来的妹子呀……不时地上蹿下跳,手里的花桨拍拍敲敲,左一桨右一桨,跟着花灯调唱起来:看花是假意哦,依呀嘿,看妹是真情哪……俩人的配合,直引得围观的人喝彩连连,笑声在整个正月里回转。
脱了艄公衣的正权,洗净灰渍也是模样周正的俊后生,种地打庄稼,在湖村是一把好手。当年湖村人选水仙做艄婆挑大梁时,他就争着抢着扮丑角做艄公。他们从冬月开始排演,到唱完正月十五元宵夜,双方也有了好感。
水仙娘看着花一样的女儿经常悄悄往后门溜,忍不住抹眼泪跟几个要好的姐妹叹:闺女大了,事儿由不得娘做主!正权那孩子呢,好是好,只是可惜啊,精精壮壮的后生家,扮个艄公闹着玩了也就罢了,怎就骨儿里也跟着戏里像打丑的呢?话也就这么随口叹叹说说,却不知被谁添油加醋地传,变了味传到了正权娘的耳朵里。
那正权娘在湖村本是要强的狠角子,听罢,感觉自家孤儿寡母受了辱,就气愤地拎着菜刀菜板,站在湖村的公众晒谷坪上边剁边骂:自家屁股流脓血,咋还乐意给别人诊痔疮嘞?都说装旦的不嫌打丑的,自己大姑娘家家的,成日屁颠屁颠扭屁股唱出搭人,脊梁骨也不晓得几时给人戳穿了。这种货色,倒贴给我做媳妇,我还嫌亏呢……
水仙娘在屋里听到正权娘的骂街,越听越不是滋味,忍不住拍手打掌跟出来接口应骂。只是这一接骂不打紧,本来好好的两家人,当村一顿大骂后,从此就断了来往。水仙在娘含泪百般催劝下去相了亲。嫁人后的水仙,从此远离了花灯。而湖村的船灯,还是一年一年地在正月里沿河沿村耍灯拜年,艄婆的角子,湖村人又挑上村里年轻漂亮会唱调的小媳妇来演,只是大家发现,湖村的艄婆小媳妇都只是唱唱,就唱唱,脚不开错,腰不扭摆。
再后来,湖村的小媳妇也不知咋回事,跟约好了般,没人再愿意来接艄婆这个角子。湖村人只得让俊秀的后生化着浓浓的彩妆尖着嗓子来演。那一上一下的喉结,在沿村一声又一声的叹息中打着颤音,直到村里来了一群陌生人。
那伙人的来到,在湖村掀起了一层巨波—湖村的船灯将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派代表去外地演出。
湖村沸腾起来,这祖辈传下来的船灯,如果能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村人祖祖辈辈的骄傲啊!可是,如今的船灯还能去演出吗?艄婆角子一角稳全局,谁来演呢?湖村论唱腔,比扭秧,还有谁能胜过水仙?可是水仙嫁了,水仙嫁时当村发誓—此生不做艄婆。
那一晚,水仙娘的院子里坐满了湖村人。那一晚,正权娘约了水仙娘,两人在河边坐了半宿。
水仙被娘召回了湖村。可水仙说:娘,我发过誓!水仙娘说:气话能作数?不作数!不作数!一屋子都附和。水仙仍是垂头不语,手指绞着衣襟,一下又一下。直到一个声音传来:大侄女,婶子我这样扮艄公和你一起演,你看,还中不?正权娘此时头戴正权的破草帽,脚趿正权的旧球鞋,抹着东一块西一块的灰渍笑嘻嘻进了屋。一屋人面面相觑,水仙娘在一旁跟着扯水仙的衣角。
湖村再次热闹起来,在一片鼓乐声中,一个清亮亮的声音踩着小步又扭了起来。
(原载《打工文学》2014年3月16日 作者自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