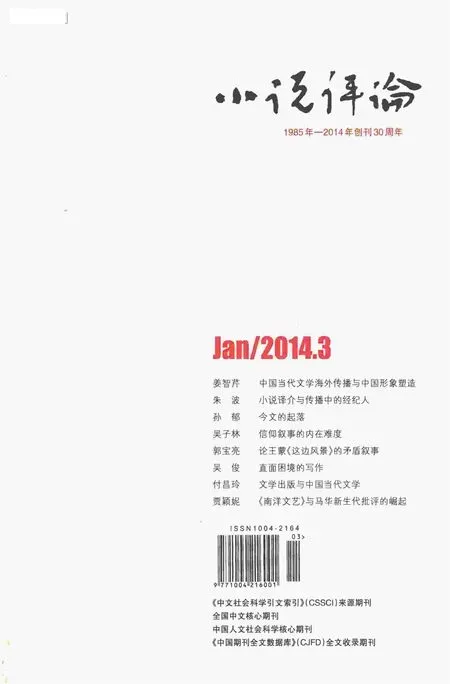直面困境的写作——关于余一鸣的小说
2014-11-14吴俊
吴俊
读余一鸣的小说非始于近年,但他是个大器晚成的作家,给人的印象似乎他是一个最近才出现的新人。但你读过他的小说就会了解,他其实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老作家。他保持了文学写作关注当下的当代传统,使他在新世纪的写作能够与新时期的文学精神直接续上了血脉;他的批判立场则使他的小说能够承袭更为深厚的文学脉传,成为一种自觉担当社会使命的思想性写作;而他的“保守”的写实手法,又最能显示他挑战文学难度的自负和自信。与他的同龄作家相比,他是一个迟到的作家,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起点是在哪里,但我们只有在终点才能知道谁是那个最先撞线的人,谁是坚持跑完全程并留下记录的人。
读过他近年的一些小说后,我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他的写作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也开始显出了一种明显的困境。这种困境看似叙事策略问题,实恐主要是观念或写作姿态问题。但在细说这写作困境之前,还得先说说他的写作的一个基本品质——余一鸣的写作是一种直面困境的写作。
何为困境?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无法摆脱的困难处境。我说余一鸣的写作是直面困境的写作,既是指他的小说内容,更是指他的写作态度;或者是由他的小说而看到的他的写作态度。余一鸣的写作因对当下困境的觉悟而获得动力,文学表达便成为他直面困境的方式;他在呈现困境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写作无形中成为一种困境的真实体现。这就在更深的意义上彰显了所谓困境的必然性。这是作为写作者、批评者或人文研究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如他所说,“如何通过小说的形式处理好当下的题材,也是一种挑战难度的写作,能在现实题材当中体现出小说的技巧性来,那更是考验。”
当下的困境是什么?余一鸣的作品里就有过多种回答。他的作品多有新时期、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当代的传统政治底色已经相当的模糊,代之而起的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社会的表达空间。他纠结的不再是人间关系中关涉到重大现实政治矛盾的冲突,而主要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生活对于当代社会和人性追求的颠覆性冲击与重塑,并由这种冲击和重塑产生的种种当下性困境。其中既有主要体现为一般生活层面的困境,也有较深层的精神性困境,甚至还有更倾向于抽象性的关于基本人性和未来命运的困境思考。直面困境的写作,赋予了余一鸣小说的现实感。——我们几乎不能把握自身的现实依附究竟何在,即一种可谓丧失了理性自觉的现实自信的迷失感,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现实。这是现实无疑就是一种困境。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动机思考。余一鸣小说中的人物各有不同,但在其行为动机中都可以看到利欲的冲动和追逐如何影响了人性和道德的表达。余一鸣的小说不是在单面、单向地对此进行价值评判,而是深入地写出了两者的复杂性,即道德如何深陷在困境的泥淖之中。
利欲的冲动和追逐并非就是负面人性的体现。在社会底层、乱世江湖谋生乃至挣扎过活的人,如果能够过上一般正常人的生活,就已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他们要么默默地沉沦,在无望中耗尽自己的生命;要么铤而走险,伤人害己,走上凶险的不归路。更多的是已经在江湖上趟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但因为不可遏止的利欲的冲动和追逐,在人生的走向中更加激烈地展开了道德意义上的矛盾和冲突。余一鸣的小说就由这种人物的道德表达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深陷其中的一种救赎无望的存在困境。
余一鸣将他的代表作组成的中长篇集命名为《淘金》三部曲,淘金二字正是所谓利欲的冲动和追逐的一种表达。但淘金二字的倾向性显示的更为清晰——他的小说主人公多是各种意义上的淘金者,淘金者既可是社会人间的底层受苦者,也会是犯罪者的滋生源,特别是经由淘金而获成功的暴发户土豪,或是不惜代价专心布局经营仕途的各级官员,更是无不经历了道德的拷问——但没有一个人是经得起拷问的,他们(包括我们)怎么办呢?这是余一鸣小说所呈现并追问的现实问题。
就以《淘金》为例,其中的《入流》写的是长江上采沙和运沙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离开了农村土地外出打工谋生的农民,这会让人联想到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变:农民变成了农民工,农村渐渐向城镇靠拢,城镇化的建设和社会的整体转型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改变了原先的人际亲缘和社会关系,而且更加彻底地改变了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甚至是在最彻底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人性。这种变化意味着当下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已经使人难以准确定义我们的社会身份——这就在客观上使得道德成为一种有时需要悬置的模糊、暧昧的存在。重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成为重建社会道德的过程。但在这之前、或者过程中,我们首先经历的是道德的崩塌或弃置。这正是余一鸣小说所直面的当下困境。我们很难用既定的道德标准来评判白脸、罗老大、拴钱们所作所为的是非,尤其是在三宝之死中作为哥哥的拴钱究竟是个什么角色;善恶的评价在这些人物行为的身上已经不能得出单一的结论。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善恶的区分,而是因为善恶判断的模糊和暧昧,已经使得道德意识趋于瓦解,道德成为一种不需要顾及和思考的问题——道德不再是个问题。这却正是我们当下这个社会和人心的可怕性所在。道德意识和道德标准的崩塌,最终使得作恶才是成功的投名状成为社会的约定俗成或潜规则。如果利欲的追逐和财富的增长需要人性付出这种代价,那么所谓的社会进步又将如何体现呢?我们究竟有无可能抵达文明的彼岸?能否阻止或挽救人伦的堕落和沦丧?我们对于财富的不可遏制的追逐,如何才能体现出文明和人性进步的意义呢?这一切现在都找不到答案。
《淘金》中的《不二》更加典型。东牛、红卫、秋生、孙霞都是建筑工程或建材的包工头,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同时也在重建自己的生活、重塑着自己的人格。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层面中看到他们的情感流露和生活方式,也可以在经济生活的时代大潮中看到他们的人生波折、命运起伏,他们不是一群单纯的人,尤其是主人公东牛,是一种有着多种思考和人生智慧的时代弄潮儿。但是就是这种能够体现社会发展的角色,却在基本的道德考验面前陷入不可收拾的溃败。他与孙霞本来似乎可以朝着一般预期的理想化的方向发展,建立一种新的人生及生活方式。但作家显然已经彻底看透了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和人性真相,不是作家的无情和残酷,而是对于当今社会的利欲价值观的洞察,他只能使东牛亲自将孙霞送给了银行行长。这还不是结束。送出了孙霞的东牛,回到工地疯狂砌墙,将自己砌在了围墙中。他不是不觉悟或没有觉悟,而是觉悟之后的无法选择。他眼看着自己将最宝贵的情感和道德价值弃之不顾,他只能在亲手做成的围墙中囚禁自己。所谓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东牛的人生无疑便是一种悲剧了。更大的悲剧是这种人性基本良知的溃败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再构成道德的挑战。人性的堕落使得人伦的禁忌在一瞬间便可轻易地跨了过去。余一鸣的小说常在这些地方使我感到恐惧,他逼使我必须直面自己所处的困境,明白自己只是个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假装沉睡的人。
但余一鸣到底还有所不忍。他想流露出一些善意来拯救眼前的现实,收拾一下人心无可救赎的溃败。这使他的小说出现了叙事逻辑上的某种软肋。被东牛当做礼物送出去的孙霞,后来的去向有点像是个谜了,小说最后的桃花源暗示,多少带了点一厢情愿的乌托邦似的想象。她要拯救别人,首先能拯救自己吗?——救赎的主题在《淘金》三部曲的《放下》中是最明显的。
这部小说也是余一鸣自己谈得比较多的一部作品。“我没有理由不让人家搞养殖,经济要发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既然山水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能不能想好了保护根本再想发财?我们是不是在这方面也应该放慢脚步,等一等我们心中的良知?但是没人愿意等,等不及了,人性的贪婪和卑劣在追逐利益的狂欢中已成脫缰野马,人们心田的一汪清水已卷入浑浊的疯狂的深不见底的旋涡。”《放下》写的是在利欲驱动下自然生态遭到的巨大灾难,但贪婪却使人心在灭顶之灾降临前对之浑然不觉,所以作者说“这比生态的破坏更可怕。”只有从心里放下利欲的执念,我们才能解脱报应惩戒的轮回。作家把希望寄托在了谢无名、刘清水这样的人物身上。“我把希望寄托在谢无名这样的聪慧者身上,我相信,一个有眼光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潮中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后,良知的复苏会走在别的暴发户前面,但是他失败了。我把希望又寄托在清水这样的地方官员身上,我愿意相信,每个人的心田都需要留一角清水,每一个水分子本身是纯净的,是人性的污秽将它们变成浑浊的泪滴。及时觉悟是一方水土之幸,更是人们的灵魂之幸。”
不过,救赎是很难的。在绝对意义上,救赎是上帝的事,凡人无能为力。小说家让刘清水充当一个救赎的角色,显然也是勉强的。刘清水是当地党委的宣传部副部长,这个角色曾经为了仕途而将自己的身体按照预案的设计送给了顶头上司——她能够付出的代价足以使我们相信她的道德底线已经不复存在。她的善念只能像砌墙时的东牛一样,尽情宣泄悔恨自责之情,但绝不会改变初衷。她会是一个可以使人信任的救赎者吗?当她按照自己的预案与上司互相追逐游戏时,我们不能不佩服作家深入人心的笔力真是冷静到无情刻骨的程度。她对谢无名的情感寄托同样能使人理解,这无碍于一个年轻乡镇女干部的正当道德选择。这也是刘清水们还能保持一点美好自信的最后的理由。但是问题出在最后,也就是在小说的结尾处。谢无名自己是“放下”了,他促使刘清水也能够“放下”,但谢无名终究已经无力救世,他把一切托付给了刘清水。结果刘清水利用自己的职权便利,在网络上开始了对于世道人心的救赎。我的疑问不在刘清水的行为是否合理,而在很难相信刘清水如此利用网络的可能性——她这样做只会以最快的速度毁灭自己。这不是一个真实可信的细节,但我能理解作家救赎人心世道的用心,只是还没能设计出一个合理的技术性细节。这种叙事上的软弱实则是当下人心欲念还不能“放下”的文学写照,在这一点上小说还没有完全背叛作家的基本价值立场,只证明了他希望的某种政治正确在文学上是走不通的,当然首先我以为也是作家本人不愿如此廉价就能肤浅地相信的。
从人物和情节走向上看,许多小说的结局都能见出作家尝试救赎的苦心孤诣,哪怕因此留下叙事上的勉强痕迹。比如《拓》中徐安全的幻听,作家将写作的旨趣和“正确”的价值观借助本来就是虚构的人物“梁山时迁”之口来表达,在小说叙事上或许并不觉得突兀,不算是个破绽,但对一篇写实性的小说来说,这种手法总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现实中的无解,乞灵于虚幻的力量固有其文学的逻辑,批评家不能因此有充分的诟病理由,但显然同时也失去了现实的力量感。
《我不吃活物的脸》就更加明显了。这本是一篇极具冲击性、震撼性的短篇小说。故事由一个工地上的伤亡事故引发,围绕着赔偿的利益博弈,各类人物纷纷登场亮相,活现一幅世态众生相。一切都可以算计,包括生命的价格,惟有道德是不必算计的——道德是用作践踏的。在对此的一切做了极致的描写之后,作家的不忍之心就占据了上风。凶险社会中未能尽泯而潜伏留存着的善念人性,寄身在了做豆腐的赵先生身上,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阴阳先生,这使他的行为含义有了一种神秘超凡的意味,让人有所敬畏。果然,丁良才就在赵先生的点拨下,多少能够从世俗的浑浊甚至罪恶中拔出脚来,回归到救赎的希望之路上。对此,我只能说作家的立意可感,无可厚非,但具体的叙事策略并不算上乘。人心的救赎应该依靠真实的善念觉悟和价值信仰,而且,这种善念觉悟和价值信仰还应该有真实的社会条件的支持,即所谓救赎应该是世俗性的,也才是真实的。借助于非日常的、超能力的想象而获得救赎的希望,只能说明救赎的虚妄,在文学叙事上表现出的则会是一种非真实感的软弱性。
还有一个中篇《淹没》,通过一个叫木木的农民进城寻妻的经历,写出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变迁,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生活方式和人性价值观的巨变。乡村的年轻男女不堪生活的艰辛而进城务工,结果所操职业多难启齿,木木却是其中的幸运者,因为他碰到了在城里发迹了的老乡金宝(李国才),故事的曲折性就围绕着后者展开了。城里的生活将原来乡村里的朴实人心都淹没了,甚至连每个人本身都淹没不见了,木木到哪里去寻找他的妻子小香呢?他只能跟着金宝(李国才)谋生,也就目睹了金宝(李国才)的“淹没”生活。这或是小说名为“淹没”的用意。最后,淹没者必须获得某种拯救。小说开辟了陈洁的线索,特别是用陈洁偷孩子的情节起到棒喝人心改恶从善的转折作用。但这种救赎人心的方式同样不足以彰显人心善念的强大,它太过孤立,其实说服不了已经淹没多时的灵魂。说到底,余一鸣还没有将他需要拯救的小说人物放在善恶交织的绝境中去反复煎熬,他还是有些不忍。他太同情于笔下的人物,不忍他们的万劫不复,因此总显得过于急切简单地要将他们脱出道德和命运的堕落苦海。这显然有损于他的小说的力量感。或许归根结底是因为作家对所身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不忍吧。
现实的利欲的追逐改变、扭曲了人性,同样,在虚拟的世界里同样可以满足利欲的另类想象,最后导致罪恶。《愤怒的小鸟》是一篇网络题材的中篇小说,而且故事的主人公多是初中生。这群现实生活中的弱者,却是网络世界里的强人,他们叱咤风云,自成江湖,除了技术,也靠诡计。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的世界其实已经分裂成两个互相交叉却又互相隔绝的空间,成人很难进入网络世界,而现实生活在网络规则看来更像是虚拟的世界。并非网络世界与实际生活合二为一了,而是两者的边界都变得模糊了。于是,在网上可以杀人如麻的快感,轻松地入侵到了现实生活中,由此改变了人性的基本价值观。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将郑婷婷意外致死之后,三个少年还能如此无动于衷地冷血。网络少年的杀人故事或许看起来有些极端,但在网络生活成为常态的当下,现实发生的一切只会更加残酷。这篇小说的挑战性应该并不亚于《淘金》三部曲,而且写得更加从容。
有评论说余一鸣是位书写生命痛感的作家。读过《沙丁鱼罐头》(中篇)也能了解这句评语的准确性。与其他几篇“进城”发生的故事不同,这篇小说是城里人“下乡”的故事,写的是知青的生活。因为小说取的是一个小孩的叙事视角,故事的进展显得不动声色,某种情感的表达总是被压抑着,让人释放不开。这种紧张感一直持续到了最后,当李大卫回城之后有了一点预兆,接着便是白瓷的死亡。这是一篇不能不令人感到隐痛的小说。余一鸣显然是个对底层遭遇有着深刻同情的作家,他对知青生活的观照,重点在于这个人群的失落感和被边缘化,而这恰恰就是这个群体在中国的历史宿命写照。他们最终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回城了的李大卫和死于农村的白瓷,演绎的是一代人的无奈归宿和生命陨落。与那些在江湖上行走的农民工相比,两者的生命轨迹截然不同,面对生命的姿态也完全两样,但在人生历练的的残酷性方面,两者却显得如出一辙。活着,挣扎着,却与生命的尊严、价值和意义无关。
社会的变迁在不断地改变、重塑着人性,人性的表达方式则是社会道德的真实体现。如果道德的溃败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也是我们每个人无以自处而放纵自己堕落的结果。余一鸣的小说让我们再度直面自己的生存方式,反省自身的道德困境。大凡指向当下的文学,其关怀的往往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自身的境遇。余一鸣的小说因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及精神状态有着切肤般的联系,才会使我们读了如此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