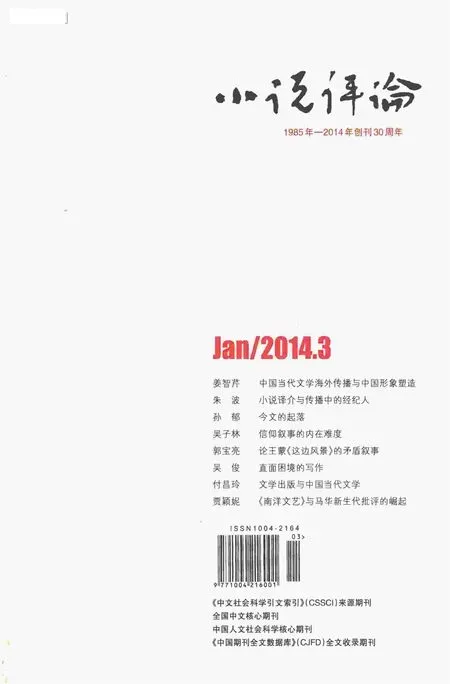噤声时代的文学记忆——王蒙新作《这边风景》略论
2014-11-14温奉桥李萌羽
温奉桥 李萌羽
王蒙与新疆是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话题。自70年代末从新疆“归来”后的王蒙创作了《歌神》、《买买提处长轶事》、《杂色》等一系列描写新疆伊犁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与《在伊犁》系列小说,更是构成了王蒙新疆小说特别是“伊犁叙事”的“双璧”。
一
王蒙的《这边风景》是一部命运多舛、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说,抛开小说的具体内容不谈,单就这部小说的“身世”而言,也颇具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
为了改变自“文革”以来文艺界的全面凋敝状态,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的短评,从1972年开始,文学创作的氛围开始了稍稍松动。此时,身在新疆正接受“劳动改造”的王蒙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特别是在他受到安徒生描写一个人一事无成的童话“刺激”后,产生了写一部反映伊犁农村生活的“大长篇”的愿望并“悄悄地”开始写作,王蒙所说的“大长篇”就是《这边风景》。
《这边风景》酝酿、写作于“文革”年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部小说的艺术风貌和审美取向。崔瑞芳曾谈到王蒙创作这部小说时的情景:“当时,‘四人帮’正在肆虐,‘三突出’原则统治着整个文艺界。王蒙身受20年‘改造’加上‘文革’10年教育,提起笔来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作品中的人物又必须‘高大完美’,‘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写起来矛盾。在生活中,他必须‘夹起尾巴’诚惶诚恐,而在创作时又必须张牙舞爪,英勇豪迈。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得提神运气,握拳瞪目,装傻充愣。这种滋味,不是‘个中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虽然王蒙具有杰出的文学才华和深厚的生活经验,但《这边风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不得不暂时搁置。1977年寒假,崔瑞芳从新疆回京探亲,趁此机会把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黄伊,1978年,王蒙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到北戴河对这部小说进行了修改,“虽花了很大力气”,但终因“整个架子是按‘样板戏’的路子来的,所以怀胎时就畸形,先天不足”,不得不“报废”。1979-1981年间,王蒙再一次试图对这部小说进行“起死回生的拯救”,小说的1-2、3-5章曾分别在1978年7、8月号的《新疆文艺》上发表,《东方》1981年第2期也曾以《伊犁风情》为名发表过小说的部分片断。虽然发表了部分章节、片段,但终因《这边风景》的整体内容和思想意识无法适应新时期以来变化了的新形势,最终还是难脱“因政治可疑而被打入另册”的命运,不得不再次搁置起来。2012年,搁置多年的《这边风景》偶然的机会重被发现,从“坟墓中翻了一个身”,走了出来,作者在“基本维持原貌,在阶级斗争、反修斗争与崇拜个人的气氛方面,做了些简易的弱化”的同时,进行了两次校订、修改,并增加了每章后面的“小说人语”,终于在时隔近40年后以新的面目“重见天日”,最终完成了“从遗体到新生”的过程。在当代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部小说像《这边风景》这样,从写作到问世经历过如此曲折、反复的过程。从《这边风景》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更多的前世今生。
无论是遗忘还是“捂盘惜售”(徐坤语),在尘封了近40年后《这边风景》的出版都是一件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甚至,其意义可能超越了这部小说的自身价值。就王蒙个人创作谱系而言,《这边风景》无疑填补了他创作的一个空白,使王蒙横跨60年的文学创作链条得以完整,在王蒙整个创作链条上,《这边风景》占有一个特殊的承上启下的位置:一方面它内在地承续了50年代《青春万岁》的理想主义的余绪,使王蒙50年代和新时期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写作得以连接和延续,从而使王蒙不同历史阶段的创作风貌得以清晰完整地呈现;更为重要的是,《这边风景》暗含了王蒙新时期小说变革的“基因”和可能,在《这边风景》中可以隐约发现王蒙后来“季节系列”小说的某种因缘和内在根据。其二,就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前的文学而言,《这边风景》的出版,则具有某种“考古学”的意味。在以往的当代文学史中,“文革”时期的文学基本是空白,即使偶尔提及,也大多是作为某种概念化的反面典型,很少正面论述其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这边风景》让我们有可能重新反思既往文学史的某些“定论”,重新审视、评价包括“文革”文学在内的整个新时期之前的文学创作。如果将《这边风景》置于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整个生态系统和价值坐标值中来考察,无疑会对整个当代文学整体艺术风貌和美学价值特别是“文革”文学的整体认知和评价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边风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独特的历史境遇造就了《这边风景》,并赋予了这部小说独特的艺术和审美品格。王蒙从一开始就对这部小说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解释为何是“大长篇”时坦言:“因为当时政治上的陷阱太多,越写的短越会顾此失彼。只有写大了,才好设防。”王蒙“大长篇”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按照王蒙当时的设想,《这边风景》所要描绘的是“伊犁农村的风土人情,阴晴寒暑,日常生活,美丽山川,特别是维吾尔人的文化性格。”应该说,作者的“初衷”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出色达成。客观而言,这部创作于“文革”期间的小说,由于当时作者基本处于“半地下写作”状态,只能“悄悄地”写作,文学创作上的各种框框严重束缚着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而,《这边风景》难免带有那个时代激进政治特别是创作上“三突出”的影子,无论是小说的故事构架还是人物设置,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此类小说的规格化、模式化以及“观念论证式的结构”的流行模式,对此,王蒙并不讳言:“这篇小说很注意它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下的‘政治正确性’,它注意歌颂毛主席与宣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它注意符合在‘文革’中吹上天的‘文艺新纪元’种种律条。……小说人没有可能另行编码,只能全面适应与接受当时的符码与驱动系统,寻找这种系统中的靠拢真实的生活与人、当然也必会有的靠拢小说学的可能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当时特殊政治语境下不得不如此的无奈、游移而又心有不甘。但如果轻率地把《这边风景》仅仅看作是“过时”的“文物”,就会失去对这部小说的美学及文学史价值的正确认知和判断,当然,如果将它与王蒙或其他作家的当下写作置于同一评判尺度下,也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就整体而言,《这边风景》在可能的程度上最大限度地保持和体现了某种“文学性”,保留了更多的生活质感以及作家的个体经验和文学想象,特别是对伊犁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诗意描写和对生活细节的精微刻画,展示了作者超强的写实功力,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历史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并赋予了这部创作于“文革”期间的小说某种超越性审美品格,这正是这部小说在今天得以出版并被广泛接受的前提。
二
在《这边风景》这部小说中,王蒙从伊犁农村生活的切身经验出发,通过对跃进公社爱国大队两条路线斗争以及生产生活的描写,立体地全景式地向人们展示了上世纪60年代初新疆伊犁农村的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是一部描写新疆伊犁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从故事层面而言,《这边风景》虽然写了1962年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1964年的“四清”运动等政治事件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与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宏大叙事相比,《这边风景》更是一次充满了生活质感的诗意叙事。
《这边风景》的美学价值首先表现在作者对边地伊犁自然景物、民风民俗、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性格的生动描绘。在这部小说中,王蒙以丰实饱满细腻缜密的笔触,出色地原汁原味描写了新疆伊犁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族农民真实鲜活的生活以及独特的文化个性,这构成了这部小说持久的艺术魅力。虽然从一开始王蒙首先考虑特别注意这部小说“符合政策”,但勿庸讳言,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和魅力当然不是来自“政治正确”,甚至相反,在审美效果上小说对生活的描写反而把两条路线斗争压倒或者说消解了,正如作者所言:“万岁的不是政治标签、权力符号、历史高潮、不得不的结构格局;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倾吐,是世界,是鲜活的生命。”更确切地说,政治性书写仅仅构成了这部多声部小说的一个声部、一个维面,而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才是作者真正描写的所在,正如作者在谈到另一描写伊犁生活的小说《在伊犁》所言:“虽然这一系列小说的时代背景是那动乱的十年,但当我一一回忆起来以后,给我强烈地冲击的并不是动乱本身,而是即使在那不幸的年代,我们的边陲、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么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每个人心里竟燃着那样炽热的火焰,那些普通人竟是那样可爱、可亲、可敬,有时候亦复可惊、可笑、可叹!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重的岁月,生活仍然是那样强大、丰富、充满希望和勃勃生气。”无论什么时候,生活才是文学表现的中心,对生活自身而不是对阶级斗争的痴迷和眷恋,正是《这边风景》与同类小说相比“胜出”的根本原因。
王蒙曾多次谈到对生活的“入迷的‘不可救药’的兴趣和爱”,这是王蒙的“主义”和宗教,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深层根据和动因,这在客观上帮助作者完成了对“政治”最大限度的突围,从而在可能的程度上赋予了这部小说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坚硬的生命质感。相对而言,《这边风景》与创作于“文革”期间的同类作品相比,概念化、模式化的东西相对较少,这一方面源于王蒙杰出的艺术才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源于作者对生活和文学的爱和信念,与某些政治“信条”相比,王蒙更感兴趣更痴迷的是生活本身,是伊犁农村那些日常的琐碎的切肤的日子即“亲切的令人落泪的生活”,还没有哪一部小说像《这边风景》这样如此丰富真切而又细致深入地描绘了伊犁农村维吾尔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雪峰、草原、牧场、河谷、果园、高大的白杨树、潺潺流淌的渠水、大片的条田等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打馕、刷墙、赶车、看磨坊、修水渠、扬场、打钐镰,抓饭、奶茶、酥油馕、酸马奶、土造啤酒、大半斤、米肠子、拉面条,坎土镘、抬把子、生皮窝子、热瓦甫、都塔尔等具有充满了民族特色的衣食住行,以及喜庆、祝祷、丧葬,甚至颇具宗教色彩的乃孜尔、托依等都进行了细致精微的描写。
三
不止一个人谈到王蒙的“诗人气质”,陆文夫很早就说过“王蒙首先是个诗人”,“诗人”的确构成了王蒙创作的某种挥之不去的底色。《这边风景》同样打下了“诗人”王蒙的鲜明徽记,回荡着诗人的激情,《这边风景》是噤声年代罕有的激情写作。
在《这边风景》这部以朴实健朗风格见长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依然可以看到王蒙50年代特别是《青春万岁》的影子,理想主义在这部小说中并未完全褪隐,王蒙的“挚诚”——“少共”之心依然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这部小说独特的审美气质和美学风度。从审美风格和内部构成而言,《这边风景》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传奇性和抒情性。小说的传奇性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了:反颠覆斗争,粮食被盗,死猪事件,四清斗争,都颇具传奇性,库图库扎尔、里希提、伊力哈穆等人的成长故事,也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特别是小说的下卷基本围绕泰外库的“情书事件”展开故事,则不仅具有传奇性,更有结构上的考量。但真正构成这部小说灵魂和魅力的还不是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而是小说的抒情性,这决定了《这边风景》的浓郁的诗意和深情的笔致。
《这边风景》的诗意首先源于对爱情的书写。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压倒一切、政治消解了一切的年代,爱情已成为某种文学禁忌。《这边风景》中对爱弥拉克孜与泰外库、雪林姑丽与艾拜杜拉、米琪儿婉与伊力哈穆的爱情,以及吐尔逊贝薇与雪林姑丽、狄丽娜尔之间胜似姐妹般的友谊的描写,曲折委婉,幽雅深致,表现了特殊年代爱情的美好,生活的美好,人性的美好,为小说平添了许多浪漫气息。
除了爱情,小说的诗意更表现为对劳动的激情书写。就小说情节而言有坏人有斗争有阴谋,但小说充满了热爱劳动、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开阔刚健、明朗乐观的格调,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诗性光辉。王蒙曾说,整部小说虽然写得处心积虑、小心翼翼,但仍不失为一次“生气贯注”的书写,最“生气贯注”的是小说对对劳动场面的充溢着圣洁和诗意光辉的礼赞和书写。第二十一章,对伊力哈穆“夏夜扬场”的描写:
忽然,一阵小风,伊力哈穆一跃而起,天已经大黑了,满天的繁星眨着眼。伊力哈穆拿起了五股木叉,先扔了两下,试了试风向和风力,然后旋即拉开架子,一下接一下地扬了起来。风很好,扬场像一种享受。本来混杂了那么多尘土、秸秆、毛刺、碎叶的,扎扎蓬蓬、不像样子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脏东西,轻轻一抛,经过风的略一梳理,就变得条理分明、秩序井然、各归其位。星光下,一团有一团的尘土像烟雾一样地伸展着身躯飞向了远方。秸秆飘飘摇摇、纷纷洒洒、温柔地、悄无声息地落在场边。麦粒呢,在夜空中像训练有素的列兵一样,霎时间按大小个排好了队,很守规矩地落在了你给他们指定的地点。
这是诗!是美!是闪光的文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东西值得反思,但是这样一种对于劳动的圣洁无比的情感,无论何时都不会过时,都值得尊重和怀恋。巴赫金曾说:“乡土小说里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改造:日常生活诸因素变成为举足轻重的事件,并且获得了情节的意义。”这里对于劳动的描写,没有后来小说的惩戒性、自虐性内涵,劳动不再是苦难叙事的必然所指,而是充满了真诚、快乐和激情,洋溢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与美好,且具有了某种精神性即马克思所说的“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这既是劳动的过程,更是美的享受,充满了创造和自由的愉悦,在这里,劳动、美、自由与创造完全融为一体。《这边风景》中对于劳动场景的描写,并不是一种特殊语境下的政治性想象,而是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创造、激情与诗意的内涵,王蒙在这里所描写的已经不单纯是劳动场景,而是通过劳动场景的书写,努力发掘社会主义新生活带给农民的精神世界之美。如果《这边风景》的写作看作是“幽暗的时光隧道中的雷鸣闪电”,那么小说中关于劳动场景的动情书写则是整个“文革”文学中最酣畅的“雷鸣闪电”。
美、健康与劳动结合在一切,这是对劳动的礼赞,也是那个单纯年代的最圣洁的情感。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这是一种单一的情感方式,也是一种纯洁无瑕的情感方式,多么可爱的夏夜,多么可爱的劳动场景,多么可爱的王蒙!王蒙小说的这种如此简单而又圣洁的描写,在其以后的小说中似乎并不多见了。
四
《这边风景》是当代文学一次跨文化写作的成功试验,是一部跨文化写作的经典范本。
王蒙是当代汉族作家中仅有的精通维吾尔语的作家,新疆16年生活,给予王蒙最大财富是他熟练掌握了维吾尔语,使他有了“另一个舌头”,不仅能够与当地维吾尔农民毫无障碍交流,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一把走进维吾尔族历史和文化的钥匙,能够透过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价值观念,进而走进了维吾尔人的生活和心灵世界,正如维吾尔诗人热黑木·哈斯木所认为的:“汉族作家反映维吾尔生活,能让维吾尔读者称赏叫绝,说到底,就因为王蒙通晓我们的语言文化,懂我们的心。”美国作家阿瑞尔·道夫曼曾说,“作家”的题中之义就包涵了“不适”,如果对现实安之若素,他的笔将就此枯竭。也许王蒙是个“例外”,王蒙多次强调他在新疆的生活是“如鱼得水”,正是这种“如鱼得水”,才有了《这边风景》以及后来“复出”后的《在伊犁》,因为,它们都充满了王蒙对这块土地的深沉的理解、爱和感激。德国哲学家乔治·齐美尔提出了文化上“异乡人”的概念,就文化身份而言,王蒙之于维吾尔族文化无疑是个“异乡人”,这种“异乡人”的身份使王蒙对两种文化的差异格外敏感:新疆“使我有可能从内地——边疆、城市——乡村、汉民族——兄弟民族的一系列比较中,学到、悟到一些东西”,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王蒙的“比较”视野源于对维吾尔族生活和文化的热情,源于作家对维吾尔人的爱,是爱使王蒙从一个文化的“异乡人”变成了真正的“巴彦岱人”。
王蒙对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人的生活和文化具有深刻的了解,他曾广泛阅读维吾尔族的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并翻译过维族作家马合木提·买合买提的小说《奔腾在伊犁河上》以及诗人铁依甫江等人的作品,所有这些都养成了王蒙的跨文化视野,王蒙说:“绝大多数情况下,题材、思想、想象、灵感、激情和对于世界的艺术发现来自比较——对比。了解了维吾尔族以后,才有助于了解汉族,学会了维吾尔文以后才既发现了维吾尔文的也发现了汉文的特点和妙处。了解了雪山、绿洲、戈壁以后,才有助于了解长安街。”这种自觉的跨文化意识无疑给王蒙提供了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开放的文化心态,可以说,没有对维吾尔语的学习和掌握,就不会有《在伊犁》《这边风景》等深得维吾尔族生活真味的作品。
维吾尔族一个是具有鲜明气质和文化个性的民族,《这边风景》没有猎奇,没有热衷于奇闻异事的描写,而是怀着尊敬、喜爱、欣赏的心态,以跨文化的视野透过维吾尔人日常生活的描写,表现他们独特的生活情趣和文化心态:如当地居民习惯于把窗子开到临街的一面,以便透过精美的挑花窗帘可以欣赏繁华的街道和过往的行人,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美”和情趣,家家院子里都有葡萄架、苹果园、玫瑰花,不但窗帘、床围子、餐单、箱子、毡毯上绣有精美的挑花,甚至打馕包包子上也有花纹图案;穆斯林文化特别讲究生活的清洁和卫生,维吾尔人每年粉刷两次至少一次房屋,家家院门外都有供夏季乘凉用的土台子;维吾尔少女喜欢用奥斯玛草涂染墨绿色的长眉毛,用凤仙花涂染红指甲、红掌心和红脚心。在长期的历史文化中,维吾尔人养成了独特的生活观念:维吾尔人认为新鲜空气对人的健康十分重要,只要天气允许要尽量在室外“吃空气”;维吾尔人十分“崇拜”夏天,认为夏天越热,出汗越多,身体就越健康,心情就越舒畅,没有夏天的汗流浃背,疾病就不能排除。同时,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也形成了一些独特文化观念或文化禁忌:维吾尔人普遍对粮食充满了敬畏,认为粮食是真主赐予的,一定要保持“清真”,牛奶不小心洒在地上,一定要用土掩埋起来,饭前一定要洗手,严禁随地吐痰、擤鼻涕、放屁;即使在日常饮食方面,维吾尔人也有自己独特的规矩:许多食物的吃法、摆法、切法,都有固定的规矩,在吃馕和馒头的时候,决不允许拿起一个整的张口就啃;马是干净的合格的,而驴是不洁的违规的,因而穆斯林对马驴交配十分反感,与驴交配后的马是不能食用的,维吾尔人甚至认为羊肉的味道与屠宰的手艺有关,一个手艺高超的屠宰者通过他的妙手能使羸弱的瘦羊的肉变得鲜嫩肥美。
《这边风景》的跨文化视野,更深层地表现为维吾尔人独特的语言方式:如维族人常常用“白”来形容女人的漂亮:“白媳妇”“洁白的女儿”,“甜甜的好女儿”,这里的“白”“甜”并不是指颜色、味道,而是“漂亮”的意思。爱弥拉克孜与伊力哈穆的对话:“爱弥拉克孜姑娘,这是您吗?您在吗?”“伊力哈穆哥,您好,还能不在吗?”小说描写迪丽娜尔的歌声:她唱起来的时候,燕子都不在高飞,羊儿都停止了吃草;描写乌甫尔的妻子莱依拉能干:“她的家总是拾掇得如细瓷碗一样的干净”,形容乌尔汗的头疼“好像有一条蝎子钻到脑袋里”,形容一个人红光满面像一个“刚出炉的窝窝馕”,这些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语言及话语方式,是维吾尔族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以及心灵世界的独特表达。如果把王蒙比喻成一颗大树,那么它的根深深扎在了伊犁维吾尔族生活和文化的最深处,王蒙走进了维吾尔心灵世界的最深处。
新疆是王蒙“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新疆在诸多方面对王蒙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王蒙之为王蒙诸多的规定性之中,伊犁永远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王蒙让“巴彦岱”从一个地理名词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存在,“巴彦岱”就是鲁迅小说中的“鲁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伊犁是王蒙心中永恒的“桃源”。《这边风景》是王蒙这位赤子唱给伊犁母亲的最深情的赞歌,王蒙说《这边风景》“是戴着镣铐跳舞”,在那个独特的历史语境中,镣铐是难免的,但是,王蒙“舞”出了他的精彩,“舞”出了他的非同凡响。
注释:
①②崔瑞芳:《我的先生王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第110页。
③④⑤⑦⑧⑫⑭王蒙:《这边风景·后记·情况简介》(下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704页,第704页,第701页,第704页,第543-544页,第702页,第702页,第702页。
⑥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页。
⑨王蒙:《王蒙文存》(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37页。
⑩《王蒙致何士光》,《当代作家评论》1984第4期。
⑪王蒙:《这边风景·前言》(上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⑬[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页。
⑮楼友勤:《维吾尔友人谈王蒙》,温奉桥编:《多维视野中的王蒙——第一届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⑯王蒙:《文学与我——答〈花城〉编辑部××同志问》,《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0页。
⑰王蒙:《萨拉姆,新疆!》,《王蒙文存》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⑱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⑲温奉桥、温凤霞:《从伊犁走向世界——试论新疆对王蒙的影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