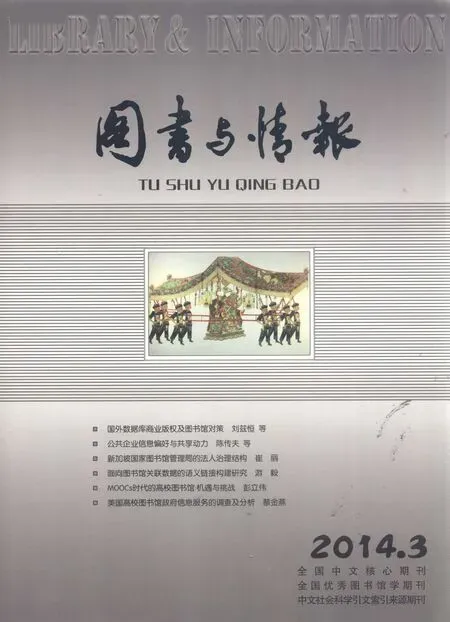中国古代王朝图书事业中的若干政治心态管窥*
2014-11-14陈谦
陈 谦
(青岛大学文学院 山东青岛 266071)
以往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研究成果,总体上客观地展现了历代王朝在图书编纂、出版、流通、搜求、整理及收藏等方面的活动,使我们从中看到历代王朝对图书事业重视的总面相。本文则换一个视角,即通过对历代王朝图书活动“言”与“行”的观察与分析,总结古代王朝关于图书事业中的若干政治心态,以期对“文化传统”取向型的中国古代政治在图书事业上的表现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 图书一统——“大一统”观念的文化表达
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在古代政治思想中,“大一统”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大一统”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关于国家、政体的主要思路。有学者将古代大一统理论体系详细分为天道一统、江山一统、治权一统、政令一统、帝位一统、王道一统、文化一统、华夷一统及天下一家等主要论点。其中思想文化一统是大一统理论体系之一。先秦诸子普遍主张圣者为王,圣者为师,主张“执一”、“定于一”、“一天下之义”、“作一”。而所谓“一”,从大的方面说,就是政治一元化、集权化的“大一统”。政治大一统,要求“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为法”,这种“圣王之制”应囊括人间一切,自然也包括学术文化。有着圣王理想或以圣王自许的君主,无不尽其所能,在学术文化上涵摄一切。在对待图书典籍态度上,他们大都希望尽可能最广泛地搜括旧籍、编纂新典,这些除了能在一般意义上说明古代君王重视文化建设外,从深层次上说,是在丰富“一统”的内涵。
在图书搜求方面,历代有文化理想的君主往往广事搜求,不遗余力,甚至频下诏令,督促臣下搜括亡遗。汉武帝面对“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的局面,“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成帝因为“书颇散亡”,便“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并且指令专人整理旧籍,编订书录。东汉光武帝更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四方鸿生钜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
隋代牛弘感叹历代图书之厄,认为图书乃王朝政治必操之物,图书之厄是政治衰败的象征:“以经书,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图书“兴集之期,属膺圣世”。认为“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但“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在牛弘看来,大隋在政治一统之外,尚有缺失。希望隋文帝能够通过天下士民广献图书典籍,从而完成图书一统。隋朝虽立国仅短短三十余载,却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图书搜求活动,藏书一度达三万余卷。而且还进行了书目编纂和图书修纂活动,成果巨大,史载“共成书三十一部,万七千卷”,俨然文化典籍一统之气象。
在改朝换代过程中,新崛起的统治者往往非常重视对前朝图书典藏的搜括。如李渊起兵一举平定河东各县,继而进军关中,攻克长安,“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图籍”。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攻克洛阳,“入据宫城……一无所取,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宋太祖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不断收缴图籍,在击败后蜀后,“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书经籍、引篆赴阙,得蜀书一万三千卷”。多数统治者认识到,武力征服取得政权,仅获得了部分权威,要想使政治权威牢不可破,非得建立统治的合法根据不可,统治合法性可凭借的资源包括多个方面,享有文化上的权威是其最为重要的合法性因素之一,而图书典籍则是文化权威的象征物。
一统天下之文的心态,在历代不少王朝强盛时期的修纂活动与言论中也有所体现。唐代太宗朝、玄宗朝都修纂过大型的图书典籍如《五经正义》《艺文类聚》等;宋代盛世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极力做到“广疏于九经,较阙疑于三史,修古学于篆籀,总妙方于释老。洪猷丕显,能事毕陈。”明成祖时期修纂的超大型的图书——《永乐大典》,更是空前绝后。修书之时,成祖的言论就明确地表明了一统文化、一统学术之意:
明永乐元年秋七月,上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籍,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再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大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一书,毋厌浩繁。
成祖好大、好全,囊括宇内文化的心态,在“毋厌浩繁”的谕旨中表露无遗。在《永乐大典序》中,其对修纂《大典》的意义有更为明确的说法:“尚惟大有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修《大典》,“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精粗,粲然具举;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复见。盖纲罗无遗”。
概而言之,“圣”王乃人道之极,不但是为政之“君”,也是人伦之“亲”,更是以道德、学术化育民众之“师”。“师”者,自然应囊括“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籍,这样就仿佛占领了道德、学术的制高点,与君王的身份相匹配。当然我们看到,尽管历代君王多数难堪“圣”任,但自汉代以来,人们(包括君王)几乎无不公开表明对此理想的追求。这既是文化理想,更是政治共识。
二 典籍资治——强调图书政治功用
古人对图书典籍政治功用的认识可谓由来已久。《汉书·儒林传》谓:“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光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唐玄宗也曾宣称:“国之载籍,政之本源”。
(一)治政依据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图书文籍作为治政决策的信息参考,说明在官僚制度体系中,图书文籍对于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关于史官掌书的政治地位,《隋书·经籍志》称:“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不过有学者指出,萧何毕竟出身法吏,“尽管知道图书的实用价值,却没法了解文化传播的真正意义”。所谓“文化传播”的意义,于政治而言,不仅只是作为行政管理的具体参考,还有承接道统、政统,规戒君臣,建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等诸多政治效用。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被抬升到崇高地位,具有了法典性质。无论是皇帝的诏书,还是大臣的奏议,大都要引经据典。正如皮锡瑞所言:“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汉代以经典为依据处理政务并解决疑难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甚至在司法实践中“以《春秋》决狱”,如武帝时“使仲舒弟子吕步舒为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又如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
后世虽少有以经典决狱的记载,但以经典作为治政依据或参考的事例与认识并不鲜见。《隋书·经籍志》即言,所著录典籍“虽未能研机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主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
(二)教化之本
古人在进行图书编目、修纂及典藏时,还经常从教化的角度说明图书典籍存在的意义。比如《汉书·儒林传》云:“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光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而在解释孔子编辑整理先圣旧籍“述而不作”的原因时,也指出是为了垂法先圣之教:“(孔子)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唐人毋煚也讲经籍“垂教”:“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
然而,圣人制典籍垂教后世,主要指的是旧典传延的历时性的信息传递。在每一朝代,朝廷大都非常重视图书典籍广教化、美风俗,进行共时性的信息传播。当然,每代的情形不同,化风俗、行科举等方面的标准教本各有不同,但总体上是沿着旧有经典的统绪进行传承的。
(三)历史鉴戒
“史鉴”是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常常被提到的话题。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是周初的政治家召公奭,他告诫成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有殷”,一定要吸取夏、商灭亡的教训。后代大凡理性的政治家,都极力宣扬在政治活动中以史为鉴。历代王朝在编纂、收集、整理史籍活动中,史鉴观念多有体现。如贞观十年,房玄龄、魏征等人修成《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诣阙而上,太宗勉励诸史臣言:“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史鉴观念在《资治通鉴》修纂活动中表现得比较集中。宋神宗在为《通鉴》所作的“御制序”中说: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繙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託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资治通鉴》的主要编纂者司马光也同样表达了史鉴思想。他说:“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于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古代王朝对史书的重视还表现在另一种借鉴,即史书对当下君主及政治运行的监督。《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不少朝代还制定了君主不能参阅国史实录的制度,意在通过它造成“历史评价压力”,达到监督君主政治正常运行的目的。
三 不惜代价——典籍的价值高于一切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治一乱,而图书典籍也有一聚一散,这似乎成为规律。每当新朝确立、大搞文治之时,作为治政之具与政治象征的图书典籍则往往残破不全,需要尽力搜求。而君主也往往怀着急迫的心情,希望聚拢天下载籍,“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
为了尽可能多方搜求图书典籍,历代王朝往往想尽一切办法。如隋文帝时,“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唐初,秘书丞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中唐肃宗朝,太常少卿于休烈上疏要求搜求遗散于民间的前朝国史实录,建议“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宋代君主特别重视奖励献书者,不是许以官阶,就是重赏金帛。如宋乾德四年,太祖发布诏令购募亡书,对献书人许以官阶:“献书人送学士院问吏理,堪任职官者,俱以名闻。”宋太宗更是规定了比较具体的奖赏措施:“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俱列其名;于待漏院出榜,告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馆阙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宋真宗曾诏令“所少书有进纳者,卷给千钱,三百卷以上量才录用”。宋高宗“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将遗书“悉上送官,多者优赏”。
明清时期依然重视奖励献书行为,如乾隆十五年,御史王应彩建议乾隆皇帝:“请敕下内外大臣,细加搜访,上其遗书,果能斟酌群言,阐明奥旨者,量予旌奖。”为了鼓励民间献出珍本秘籍,乾隆提出“以书易书”的奖励办法,即对进献图书500种以上的,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献书百种以上的,各赏《佩文韵府》一部。
以上这些搜求图书的奖励规定与活动,一方面说明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另一反面反映了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崇高的政治任务,故不惜代价,尽其所能。这种不惜代价的心态在几处史料中也有所显示,可与上引史料相印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宋高宗曾谓秦益公曰:“监中其他缺书,亦令次第镂板,虽重有所费,盖不惜也。”又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明成祖永乐四年,为了修纂之需,“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其中,“不惜”、“勿较值”就是指镂板雕造、搜访遗缺不必过多考虑花费。可见,为了集中天下之书,一统天下之文,或者说为了“教政”之需,经济帐是不用细算、不必计较的。
四 盛世修书——政权强盛心态的表征
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有成功”与“有文章”相对举,可以看出孔子认为政治之事功必有“文章”之光彩相匹配。
《宋史·艺文志》云:“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八万卷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宇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这分明是说,盛世典籍浩繁,而五季乱世王化尽弃,就连图书也所存不多。宋景德二年,真宗到国子监视察书库,询问国子祭酒邢昺书库有多少书版片?邢昺回答道:“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宋真宗高兴地说:“国家虽尚儒术,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所谓“四方无事”即盛世,图书事业的兴旺,可谓正当其时。清代乾隆皇帝在采办、搜求图书以纂集《四库全书》时,强调要通过修书“用昭我朝文治之盛”,“以彰右文之盛”,并认为,“此采择四库全书本指也”。以上这些言论都表明图书事业兴盛与政权兴盛的关系。
历代典籍就像政权的兴衰轮回一样,聚聚散散,然而政兴之后必有书盛。“尽管图书聚积和散失率极大,但人们坚信‘书籍聚散自有一定不移之数,一聚必有一散,乃物之常理’。‘一旦治平,当有兴集’。”书籍的聚散存佚与王朝的兴衰轮替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五 结语
据实而论,政治与文化从来都不是相脱节的,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历史文献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并不仅仅是个文化技术的问题,而是负有‘正纲纪、弘道德’的政治和道德的使命。”包括图书事业在内的文化事业从来没有游离于王朝政治之外,它是教化政治的重要手段,与自西周以来逐渐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乐形式的书面化、孔子的提倡及编纂实践等等息息相关。汉代政治家通过对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深刻反思,逐渐形成了重视文化、重视传统、重视教化的政治选择。于是“教政”得到发扬,对图书典籍的搜求、编纂、整理、收藏受到重视,甚至形成象征性的崇拜。
艾森斯塔得(S.N.Eisenstadt)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指出,中华帝国的政治目标属于文化传统取向型,帝国的政治得以维护的重要因素是注重文化传统的延续,同时这种取向的政治制度极其重视通过文化建设来维护统治合法性及进行社会整合。笔者在以往的古代王朝政治传播制度研究中,将其总结归纳为政治传播制度之一——“政治文化传统的信息存续与维护制度”。就图书事业方面的表现来说,历代王朝普遍建立修史机构,设置修史人员,通过官方修史延续政治统绪,表明合法性。除了修史外,还重视其他图书典籍的出版、校勘、编目、收藏。其意义主要在于延续文化,自我确认为文化传承的担当者,并通过这些活动间接地实现对社会舆论、知识、信仰的控制。历代王朝大规模的图书收集、编纂、收藏活动既可以被认为是实现理想“王政”目标的途径,也可以被认为是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又是通过控制图书来控制思想文化的措施。利用图书进行教化传播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播的重要方面,它是维系政治统治、传承政治文化、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它像一张无形的政治之“网”,潜移默化地控制着社会。
我们不难理解,古代王朝为何如此重视图书的编纂、出版、发行(流通)、搜求、整理(包括校勘、编目等)及收藏等方面的活动,因为这种文化活动更被自觉地当作一种政治统治手段,是一种上至君主下至臣民广泛认可的“软性政治”。因此,本文关于中国古代王朝图书事业中的若干政治心态的观察,就是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特点的另一种说明。
[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3.
[2]张分田.秦始皇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7-273.
[3]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1.
[4]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545.
[5][7][32]魏徵.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906,908.
[6]魏徵.隋书·牛弘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00.
[8][37]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06,1510.
[9]欧阳修.新唐书·高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5.
[10][25][33][34]刘昫.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1965,2597,4008.
[11]徐松辑,苗书梅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231.
[12][13][14]袁詠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15-116,119,120-121.
[15][24][3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589,1715.
[16]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商务印书馆,1959:264.
[1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014.
[18][23]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992-993,909.
[19]陈正宏,谈蓓芳.中国禁书简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20.
[20]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3.
[21][22]班固.汉书·五行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33,2639.
[26]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召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309.
[27]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M].北京:中华书局,1960:3797.
[28][29][44]袁詠秋,曾季光.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09-110,110-111,131.
[31][38]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761.
[35][36]程俱.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0:254,44.
[3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四[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9.
[40]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44.
[41]朱熹.论语集注[A].四书章句集注[Z].济南:齐鲁书社,1992:80.
[42][4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5032,12798.
[45]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37.
[46]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6.
[47][以]艾森斯塔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30-232.
[48]陈谦.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J].广西社会科学,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