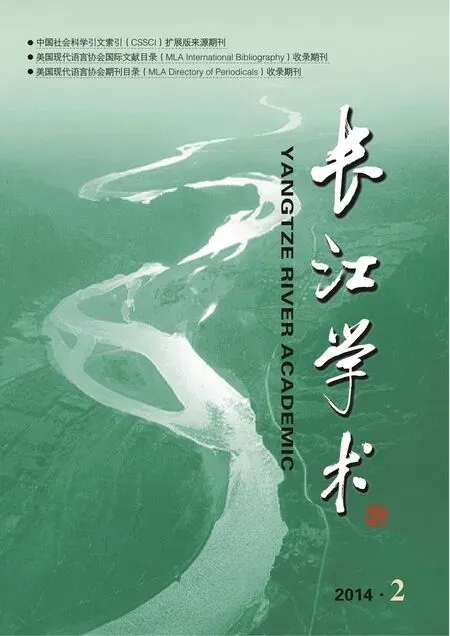被闯入:百年乡村的历史书写
——读莫言小说《丰乳肥臀》
2014-11-14朱厚刚
朱厚刚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被闯入:百年乡村的历史书写——读莫言小说《丰乳肥臀》
朱厚刚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以乡村社会被外部力量如战争、国家权力等塑造与改变及其后果为结构主线,串联起中国乡村在20世纪整个百年的变迁历史,对农民被安排的生活与被改变的命运进行了集中的书写。这是《丰乳肥臀》的价值所在,也是莫言大部分小说的核心内容。借此可对莫言的整个创作有更为贴近的理解。
《丰乳肥臀》 闯入者 乡村社会 饥饿 命运
莫言称《丰乳肥臀》是一部告慰母亲在天之灵的长篇小说,因为“人世间的称谓没有比‘母亲’更神圣的了,人世间的感情没有比母爱更无私的了,人世间的文学作品没有比为母亲歌唱更动人的了。”但该作问世后毁誉参半,一面获得“大家·红河文学奖”的十万元奖金,一面被斥“玩史不恭”与大写性变态而遭禁,在九十年代对北京市进行的“被访者最反感的书”的调查中榜上有名。2002年,莫言说:“最近我把《丰乳肥臀》润色了一下,做了一些技术性的删节,当时写得太仓促了。在修改的过程中,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丰乳肥臀》是我的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老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一部试图“借此歌颂天下的母亲”的小说,怎会有如此遭遇?莫言将小说写成了何等面目?即便莫言曾说,“小说根本没有界限,历史小说、现代小说、军事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都没有界限,完全可以打通。”我们也依然能够确定《丰乳肥臀》的故事内核。五十万言的小说铺排的其实是高密东北乡大栏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与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发生的悲喜剧,即中国乡土社会百年的沧桑变迁。各种外部力量介入对乡村产生的多重影响是小说的重点,而这背后,作家思考的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贡献与牺牲常遭忽视的问题。
一、乡村社会的闯入者
《白狗秋千架》中的文艺兵蔡队长是乡村社会的闯入者,激起了暖从军的愿望,有论者指出,暖的命运故事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闯入者,“‘秋千架故事’中的不安全感,是旷日持久和疯狂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直接带来的。它意味着饥饿、死亡、贫穷和丧失尊严等等东西。”在《丰乳肥臀》这部“具有总结性”的作品中,乡村社会闯入者的身份越发明显,是小说结构的主动脉,主要有战争对乡村的破坏与影响,国家政权对乡村的管理与控制及后果,乡民在商品经济时代的反应与迷失。故事开始于日本军队踏入高密东北乡大栏镇,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乡村,小说通过母亲之口讲述了这个村庄的历史:司马家族其实是高密东北乡的“先祖”,司马大牙于清朝咸丰年间到大栏定居,继而有了儿子司马瓮,孙子司马亭、司马库。上官家族一脉是官府的移民,到上官寿喜已经历了三代繁衍。高密东北乡的这些先祖们也曾经自发地抵抗过德国军队的入侵,虽败犹荣,显然留下了抗拒外敌的传统。这是一个两个大姓家族繁衍组成的自然村落,该村落地理上并不封闭,铁路也已然铺设在这片土地。上官家是一个以上官鲁氏为血缘中心形成的颇大的家庭结构,第四代有姐弟九人,第五代有沙枣花、司马凤、司马凰等七人。家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细胞,在乡村社会中有保护各个成员的功能。金童对母亲的过度依恋,上官家的女儿们都将后代送给母亲抚养皆是证明。
日本鬼子进村时,母亲正在分娩,终为上官家再添两丁。这是村民的日常生活,也是乡村社会内部正常的新陈代谢。传统中国是一个“家族结构式的社会”,虽不能说大栏镇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家族文化,但司马、上官等大家庭的确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点。“相对于狩猎采集社会的帮团(band)以及游牧社会的部落(tribe)而言,村落是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它相对于前两者而言,更具有时间与空间的恒久性,如果没特殊的外力作用,一个村落的人口可以在其边界范围之内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上官吕氏对男性这种“必要的人口”的期待,就是“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的重要依托,由此便能理解她为何对上官家的女儿们了无好感。乡村的封闭性也使得村民中互助的风气代代相传,如樊三大爷为驴接生并牺牲自己救了村人的性命;孙大姑即便与上官吕氏有过节,但还是给上官鲁氏接生而为此命丧日军枪口。乡村用礼俗建立起一整套的社会秩序,乡民从容安详,生生不息,从乡村的房子布局也可见一斑。“福生堂的房子一排十五间,共有七排,院院相通,门门相连,层层叠叠,宛若迷宫。”这样的格局既体现了某种等级,也有灵活的沟通,显出一种绵延的稳定感,构成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它是大栏镇的标志性建筑,是故事展开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地点,也是各方争夺的重心所在。从随之而来的战乱看,这意味着稳定;由集体化时代返观,这意味着乡村社会的私人空间。
大栏镇的历史就是被外界力量无数次闯入的历史,概述其要为:首先是日本侵华,造成了上官金童的祖父、父亲以及众乡亲的惨死,其中司马家族19口人被杀,人头被悬挂示众。接着沙月亮成立的黑驴鸟枪队入村,导致了母亲被强奸、生身父亲马洛亚坠楼身亡,全家一个月里仅以“雪水煮萝卜”这一味菜维持生命。随后铁路爆炸大队进驻村庄,虽换来了全家人活命的机会,却使上官家房屋被占用、三姐被孙大哑巴奸污。鲁立人率领的独立团进村导致二姐、六姐双双丧命。在大撤退途中,上官全家都经受了磨难,三姐的孪生儿子被炸死。强制推行的寡妇改嫁运动将母亲嫁给司马亭,破坏了乡村社会伦常。阶级成分的划分使得乡村社会的流动性与开放性被阶级关系的介入阻断,某些革命功臣开始借助政治资本为非作歹,大姐被孙大哑巴奸污即是一例;农业在不切实际的实验中举步不前,饥饿成为可怕的梦魇,上官玉女为此丧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曾被分产到户恢复起来的对土地的热爱,很快被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一空,人心涣散、乱象纷呈,婚姻等亲缘关系被利用,生态环境遭到毁坏,大栏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的村庄”,“他看到张牙舞爪的大栏市正像个恶性肿瘤一样迅速扩张着,一栋栋霸道蛮横的建筑物疯狂地吞噬着村庄和耕地”(第446页)。
就是战争这“特殊的外力作用”扰乱了乡村社会场景,稳定被外力打破,因为“历史上没有在动乱时期村庄可以成功地‘自我封闭’的先例。”战争其实是对资源的掠夺与急速消耗,显然不利于乡村的稳定,造成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如铁路爆炸大队跟沙月亮的伪军一场恶战之后,俘虏欲认亲却被对方拒绝(第115页),又如上官金童在大撤退途中看到的战役即景:
一个小兵打不过一个大兵,小兵悄悄抓起一把沙子,说:“大哥,论起来咱俩还沾亲呢,俺堂哥的媳妇是您的妹子,你别用枪托子擂我好不好?”大兵说:“算了,饶了你吧,我还到你家喝过一次酒,你家那把锡酒壶做的有机巧,那叫鸳鸯壶。”小兵突然扬起手,把沙子打在大兵脸上。大兵眼被迷住了,小兵偷偷地转到大兵脑后,一手榴弹就把大兵的脑袋砸得葫芦大开瓢。(第206页)
这种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乡民间的自相残杀,实在破坏了乡村伦理与血缘亲情。对大栏镇而言,几支部队的你来我往无疑都是争权夺利,“两党战争说到底还是农民子弟跟农民子弟在打仗”,各种集团势力都想借机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村民却要承受兵荒马乱的消极后果。大栏镇是一个自治组织,司马亭担任着镇长职务,显然是村庄的领袖与保护人,利用自家与村外的关系(福生堂家大业大,有在外当团长的叔伯,有在城当警官的表亲)建立起威信,司马亭曾提醒乡民将有外敌入侵,在村庄被洗劫后,他又组织人员收尸安葬,这也算是乡村社会的自我修复机制:
司马亭对姚四说:记上记上,听明白了没有?但姚四仅仅在上官寿喜的名字上圈了个圈,并没记录他的死因。司马亭抡起锣棰,敲打着姚四的头,骂道:你娘的腿,在死人身上还敢偷工减料,你欺负我不识字吗?姚四哭丧着脸,说:老爷,别打了,我都记在心里了,一千年也忘不了。司马亭瞪着眼道:你咋那么长的命,能活一千年,是乌龟还是王八?姚四道:老爷,不过打个比方。您这是抬杠——谁跟你抬杠!司马亭又打了姚四一锣棰。(第38页)在略带戏谑的场景中,一种仇恨与痛心的情绪也弥散开来,接续上了先祖抵抗外敌的传统。“一般说来,中国农民是很麻木的,不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不真把他们惹火的时候,他们绝对都是羔羊。”前述一连串因闯入带来的变故定会激起反抗,司马库的形象也正是在反抗闯入者的层面得到高度赞扬,既有母亲、上官金童对他的认同,在他们看来公审大会就像登基大典;也包括作家对他的赞美,莫言声称“喜欢他敢作敢为的性格”。
通读小说可以发现,在对乡情的维系与对土地的守护上,母亲、司马库、上官金童其实是同一个人物系列,他们的行为浓缩了百年乡村变革史上农民体验的重要部分,他们判断事物的标准是内心的爱憎与亲亲仇仇。在大姐与沙月亮私奔之后,“司马库趁此机会对我二姐说:‘你是老二吧?回家告诉你娘,总有一天我会把沙月亮那个黑驴日的打垮,把你姐姐夺回来还给孙大哑巴。’”(第67页)他插手维护的是一种伦常。当家人因他遭到毒打折磨时,“司马库抓起巫云雨,一字一顿地说:‘小畜生,跟村里那些土鳖们说,谁要敢欺负我司马库的亲人,我就杀他家个鸡犬不留!你记住我的话没有?’”(第235页)由于阶级成分问题,社会体制不可能对上官家提供任何保护,反而要进一步惩罚: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随时要受贫农出身的人欺负,因此司马库的保护就显得十分必要。在上官鲁氏希望他远走他方躲避时,“他拍拍怀里的机枪、腰间的德国造大镜面匣枪还有护身的勃朗宁手枪,说:‘俺那个老丈母娘竟让我逃离高密东北乡,我为什么要逃离?这里是我的家,这里埋着我家亲人的尸骨,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亲我,这里好耍好玩,这里还有你这个烈火一样的狐狸精,你说我怎么离开?’”(第247页)都足见他对血缘亲情的重视。与前次在亲人的协助下成功逃跑相比,司马库的最终难以逃脱表明了政权在农村的建立以及控制的加强。
上官金童是一个不能找到平衡的人,他落落寡合的一生是家族意识与阶级意识在其身上进行拉锯战造成的,他的意识深处是排斥阶级意识的。如当知道沙枣花能通过高明的偷窃过得很好时,“他有些欣慰地想到,上官家的又一杆猎猎做响的大旗,竖起来了。”(第310页)当他回忆八姐的往事时说“你摸索着走出家门,这家门进出过英雄豪杰,这家门进出过泼皮无赖,这家门已经破败不堪,”(第425页)“家门”一词的反复出现,足见他对家庭的看重。因为家门不仅表明血缘关系,也是一种生产方式,家户势力的强弱在乡土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家门在遭遇战争后又受到国家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改造,“土地国有化和集体所有制使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不再与家庭联系在一起,这取消了家族或家庭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上官家越发变得支离破碎。母亲维护的也是家庭,她说:“我变了,也没变。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儿孙浮上水来那一天,你们都要给我争气!”(第251页)希望“儿孙浮上水来”是家庭意识强烈的表现。母亲声言“死也要死在自家炕上”,在撤退途中,“母亲执拗地把我们带了回来,明天,我们就要穿过蛟龙河北岸的盐碱荒原,越过蛟龙河,回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回家,家。”(第199页)“母亲说:‘我糊涂了半辈子了,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枣花是我养大的,我舍不得给别人。’”(第108页)母亲不管世事的变迁,对故土、对血缘的认同始终不变。长时间吸食母乳的上官金童“遗传”了母亲“守土”的品质。结束15年的牢狱生活,“当他走过墨水泥小桥、翻过墨水河南堤、望见高地上那座严肃的七层砖塔时,已是苍茫的黄昏时分。砖塔在火红的夕阳下熠熠生辉,塔缝里那些枯草,像燃烧的火苗一样。一群白鸽围绕着砖塔飞行。一缕洁白的、孤独的炊烟从塔前草屋上笔直地升起来。田野里一片寂静,身后建筑工地那儿的机器声显得格外清晰。上官金童感到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热辣辣的泪水流进了嘴里。”(第324—325页)他成为城市化的高密东北乡的游荡者,无土可守。
将战争、国家权力的深入等因素视为乡村社会的“闯入者”,并非认为乡村社会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它的自组织机制具有修复功能;村民也并非“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常有自然迁徙与流动。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走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路途中,经受着多种力量的冲撞与闯入。由于现代化的需要,使得闯入者获得了居留此地的权利,但闯入是强制性的,没有拒绝与排斥的可能,对被闯入者而言就是一种冒险,不管是乱世日本兵的入侵,还是建国后的乡村管理活动,因为这将会带来诸多难以预测的副产品。闯入之后带来的改变、误会以及由此牵扯出的故事,便是《丰乳肥臀》关注的重点。这种闯入既给农村的自然环境带来压力,带来诸如饥饿、灾荒等问题;也改变着生活于其中的村民的命运轨迹,尤其是女性村民。
二、饥饿与被安排的生活
饥饿是莫言小说的重要母题,如《黑沙滩》、《透明的红萝卜》、《老枪》、《五个饽饽》等均属此列,《丰乳肥臀》延续了这一母题。饥饿是灾变叙事的内核之一,也是乡村闯入者带来的后继事件。《丰乳肥臀》补叙的母亲的儿时经历,将故事时间提前至20世纪初期,小说因此获得辽阔的视野。因为20世纪初“可以说是中国政权进化中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在其后50年间乡村社会中的一系列变革都与这一时刻有关,如义和团的失败、列强的赔款索要、清政府的种种集权措施都对乡村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视野中,“和平年代”农业集体化道路上农民的饥饿体验得到强调。
母亲初为人妇时,“碧绿的庄稼和野草见缝插针、争分夺秒地生长,狭窄的小路几乎被野草遮没。”“路边的池塘连着沟渠,沟渠爬进池塘。一群群的小鱼,在透明的、淡黄色的水中漫游。鱼狗子蹲在草梢上,紧缩着脖子不动,突然像石头一样砸到水里,蹿起来时嘴巴里就叼着一条白亮的鱼。”(第408页)用小螺喂养的鸭子,“只养了五个月,便长得像小船一样”。打铁铺子是上官家的生活基地,洋溢着生活的气息,也带来颇为理想的收入。小说铺陈上官家的女儿们在日寇入侵前到河里抓虾的场景,暗示着高密东北乡生活物资的自给自足。战争对农村的破坏主要是没有粮食,“田鼠们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接下来便是野兔、鱼、鳖、虾、蟹、蛇、青蛙……如果不是大量的野菜及时长出,村里的人大半都要饿死。”(第80页)好在大自然的生物性、季节性特点拯救了乡民。在司马库组织的抗日胜利庆典活动中,“他们杀了几十口猪,宰了十几头牛,挖出了十几缸陈酒。肉煮熟了,用大盆盛着,放在大街当中的桌子上。肉上插着几把刺刀,任何人都可以前来割食,你割下一只猪耳朵扔给桌子旁边的狗也没人干涉。酒缸摆在肉桌旁,缸沿上挂着铁瓢,谁愿喝谁就喝,你用酒洗澡也没人反对。”(P126)司马库为上官念弟与巴比特举办了婚礼宴会,这里有必要列举一下酒席上的菜谱:红烧狮子头、铁扒鹌鹑、蘑菇炖小鸡、玻璃肘子肉、松鼠桂鱼,主食有水饺、面条、糕点,水果有葡萄、黄瓜、西瓜、鸭梨,还有巴西咖啡与葡萄酒,“沙枣花带头扔掉筷子,动了手,她左手抓着一条鸡腿,右手攥着一只猪蹄,轮番啃咬。”(第142页)这显然是颇为丰盛的食物。这既说明司马家族作为村里的首富,的确藏有不少粮食,更表明经受了炮火洗劫后,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亦能很快得到恢复。在新政权深入乡村的几十年里,饥饿笼罩着大栏镇的上空。直至八十年代,“上官金童看到了这个女人年轻的肥大脸盘,和那脸盘上油汪汪的短鼻子,还有从粉红衬衫里缝隙里露出来的打褶的白皙肚皮。”(第317页)“您走这十五年里,变化很大,人民公社解散了,地也分到各家各户了,都不缺吃穿了。旧房子都拆了,统一规划。”(第323页)这是农村改革起到的作用。九十年代,老金的废品收购站的看门狗,“它的面前,摆着整只的烧鸡和咬了一半的猪蹄。”(第332页)由此可简略看到百年来高密东北乡生产力发展的脉络及乡民所做出的牺牲。
小说中标示的日期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字词的提示,会让人将高密东北乡与当代中国进行互文性解读,即通过小说来读历史。“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继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的又一场重大的改革。”但是“这场运动的结局,却不似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所共同期盼的‘理想社会’和‘人间天堂’,而是整个农村、农业和农民径直跌入到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三年灾难性境地。”这也是《丰乳肥臀》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莫言从村民的感受与命运的角度,给出了“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理论更多是一种具有良好意愿的理想化设计,未必能够经受住现实经济生活的检验”的一种“读史者”的思考。
农业集体化运动是国家政权在“和平年代”对乡村的介入与管理的重要途径,日常生活被政权重新安排。这种介入是强调政治意义甚于经济意义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这样写道:“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和政治的斗争。”但对于“劫后余生”的人们而言,温饱问题仍然是人的第一需要,这对任何时代的乡民而言都是如此。农业合作化是农村现代化预设的方案,高密东北乡用政治动员与军事化管理的办法,将农村“工厂化”也并没有带来物质的丰富。上官金童在国营农场的经历,突出的是食物的匮乏:“饿殍遍野的一九六零年春天,蛟龙河农场右派队里的右派们,都变成了具有反刍习性的食草动物。每人每天定量供给一两半粮食,再加上仓库保管员、食堂管理员、场部要员们的层层克扣,到了右派嘴边的,只是一碗能照清面孔的稀粥。”(第297页)至于母亲及众女乡邻饿着肚子拉石磨粉碎粮食、姐姐求弟(乔其莎)用身体换几个馒头的经历也便不足为奇;在粮食定量由每天六两减到一两的时代,每人都想尽办法“偷”粮食,尤场长偷鸡、女工们偷吃鸡蛋。盲眼的八姐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人物形象,“其实盲人也有爱美之心,你心里有我们凡夫俗子看不见的风景。你走在这条演出过数不清的悲喜剧的胡同里,历史的味道扑鼻而来,历史的声音如浪涛涌起。”(第428页)八姐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见证了母亲呕吐粮食的细节:
你听到那些粮食扑簌簌扑簌簌落水的声响,清脆不悦耳,如同一枪铁砂子打在一只红皮大萝卜上。八姐的心就是一只红皮大萝卜。母亲第一次呕吐粮食时,八姐你还以为母亲病了呢。你摸索到院子里,凄凉地叫着:“娘啊娘,您怎么啦?”娘顾不上跟你说话,只顾用筷子探喉催吐。你用松疏的拳头,轻轻地捶着娘的背,你感到娘的衣裳被冰凉的汗水溻透了,你嗅到从娘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惊心动魄的血腥味道。你感觉到一股热流直冲眼底,于是你清晰地看到娘的孱弱的身体弓得如一只虾。娘双膝跪地,手抓着盆沿,双肩起伏,脖子探出又缩进,那么可怕那么惊人的美丽,那么庄严的雕塑。伴随着打雷般的呕吐声,娘的身体时而收缩成一块铁,时而软弱成一摊泥,粮食这些小畜生们如粒粒珍珠大珠小珠落入木盆里……后来借着梨树下微弱的星光,娘呕吐完毕,伸手到木盆中,捞起一把粮食——那天娘吐出的是豌豆——紧紧地攥住,又慢慢地松开,让颗颗浑圆的、黄橙橙的粒儿,叮叮咚咚地不情愿地落入水中。(第426页)
但凡有粮食果腹,母亲断然不会在严密的管控下如此“偷”粮,正所谓“贫穷生盗贼”,饿怕了的母亲对粮食有极大的好感,这是经历过集体化运动的乡村百姓的普遍情绪,“漏斗户主”第一个领到粮食的场景才会如此令人感动。
造成饥饿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乡村现代化若不从发展经济入手而过于强调政治,日常生活就会被置换。小说就侧重写了一些干部瞎折腾导致民众遭殃的事件,变成用政治热情去掩盖经济发展问题。中国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承受外来冲击的限度,因为“闯入者”会与本地村民展开一场资源争夺战,这牵涉到“人地的紧张关系”问题。战后的乡村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由于脱离实际的政策倾向,乡村经济遂遭受新的束缚。乡村社会中的非农活动是村民扩大生活资料来源的手段,面对人多地少的现实,寻求生存的冲动自然催生了这样的活动。农民对非农活动的热情及其经济效益在七十年代小说《虹南作战史》的小商贩身上可见一斑。《丰乳肥臀》中的王超就是一个靠剃头的手艺积攒起颇为可观的家财的人,他推着漂亮的胶皮轱辘小车行走在撤退的队伍里,后因小车被独臂领导征用而自尽。“在由权力主导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权力对生产过程乃至私人领域的集中和控制,并不只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有时甚至不考虑经济效益。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受制于社会历史环境,拾荒、经商等非农业活动被禁止,乡民的流动性亦被阻滞,如“卖炒花生是违法行为”,农民生计的多样性道路被阻断,生产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农村改革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允许农民跑买卖发财”,陈奂生也是在分田到户之后才逐渐富足起来并开始学着卖油绳的。
“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国人从此中断了进行现代化的上层资源,只能走暴力革命这条道路。但是以后通过暴力革命,历经三届政体完全不同的政府,比如晚清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有我们现在的政府,应该说除解决了西方列强的入侵问题之外,戊戌变法时期就存在的其他五个问题,如人口、教育、农业内卷化(边际效益下降)、政府腐败、社会不公正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反而以更复杂、更难解决的形式呈现在世纪末。”的确,莫言写作《丰乳肥臀》时,中国的“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站在乡村社会的立场看,百年来外部势力对乡村社会的闯入、管理其实收效各异,但农民要领承现代化的各种后果。莫言在2004年意识到,“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又是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的乡村生活,其实并没有得到深刻的表现,如果能把这五十多年写出来,肯定是了不起的,这五十多年发生了多少悲喜剧荒诞剧啊!写出来,很可能成为经典。”由此我们才能对莫言的历史观进行有效定位。显然,莫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后果非常不满,因为饥饿感在他童年时如影随形,这也是五十年代生人的普遍经验。“莫言的童年,正是中国农村最沉寂最萧条的时期,一方面政治稳定,虽然没有战祸匪患,个体人生的自由度在严密的现实关系束缚下,也变得日益狭小,更不用说先人所经历的激烈场面。另一方面,政策的失当导致长期的经济停滞,在贫困愚昧的基础上又极容易滋长封建特权。这种沉重的时代氛围,无疑都对幼小的心灵有着严重的影响,他在贫困与沉寂中度过的岁月,形成了对世界最初的印象。”切身体验使得他对此念念不忘,由此便能理解“这部书的腹稿我打了将近十年,但真正动手写作只用了不到九十天。”莫言在与王尧对谈时曾说:“究竟哪个历史才是符合历史真相的呢?是‘红色经典’符合历史的真相呢还是我们这批作家的作品更符合历史真相?我觉得是我们的作品更符合历史的真相。”据此可推知,1994年因《金光大道》全四部出版引发的“《金光大道》现象”及其中透露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该是《丰乳肥臀》出现“在创作之前所确定的主题,在小说中变成了副题”的原因之一。
三、“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有论者指出:“文学关注的是这个文化空间如何决定人们的命运、性格以及体验生命的特征。追溯历史,乡村的文化版图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边界,持续的建构隐含了乡村的复杂演变史,人们甚至积累了多种不无矛盾的想象。”莫言亦称《丰乳肥臀》写的是“山乡巨变”中人的命运。小说中写到司马库在被鲁立人部队抓住时,有一段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一向整洁漂亮、连每个纽扣都擦得放光的司马库一夜之间改变了模样,他的脸像被雨水泡胀又晒干的豆粒,布满了白色的皱纹,眼睛黯淡无光,粗糙的大头上,竟然已是斑驳白发。他托着流干了血的二姐,跪在母亲面前。”(第164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对乡民日常生活的破坏,司马库体面的生活就此终结,同时也看到了强力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命运具有外部性,“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且“以上四种力量与个人能动性的互动过程共同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每一种力量都不是绝对的。”上官家四代人的命运也正是《丰乳肥臀》着墨最多之处。莫言认为“命运是个庄严的词汇,某种意义上也是个苦难的词汇”,而苦难则来自于战争、国家权力、市场经济等外力的闯入。
母亲“非但小脚出众而且相貌超群”,“水面上映出了上官家女儿们的清秀面容,她们都生着高挺的长鼻子和洁白丰满的大耳朵,这也是她们的母亲上官鲁氏最鲜明的特征。”(第16页)上官家女儿们生理上比较明显的优势,既吸引着上官金童,也吸引着其他男性的眼光,牵引出一段段令人唏嘘的故事。乡村社会面临的战争等巨大变动打破了固有的宁静,村人惯常的生活状态也被改变,司马库的豪情、沙月亮的霸道、鸟儿韩的手艺都意味着新奇,陌生感使得上官家的女儿先后被不同的闯入者头领俘虏。姻亲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起着多重保障和联系作用,是乡村女性社会交往的重要部分。“母亲由于有大女儿嫁给汉奸沙月亮、二女儿嫁给国民党还乡团长司马库、五女儿嫁给共产党的蒋政委,也就与这几种政治势力有着特殊关系。”如果说战争时期的上官家女儿们的命运还有某种偶然性,是她们各自本无可厚非的选择。那么,这些亲属关系在和平年代就成为家庭出身的印迹,使得她们的命运更加跌宕起伏,政权的深入是她们命运故事展开的重要背景。新政权治理下的每一个村落几乎都与国家历史大变革紧密相连,国家成为乡村日常生活变动的重要外部因素,俨然一个庞大的闯入者。
略显随意的阶级成分划分让上官家一度蒙受委屈,后由于孙大哑巴抗美援朝的凯旋出现喜剧性的翻转,但这一切都是不管不顾地来临,被迫卖身为妓的四姐也被冷漠的政治害死。尤以大姐的命运最富传奇性,她的一段心理活动将她的命运做了无奈的梳理:
“她的思绪便飘忽到了三妹凤凰般的眉眼上。眼前这个男人,本来是属于她的,她本应是鸟国皇后,但鬼使神差,但阴差阳错,属于她的成了我的,属于我的,又成了谁的?随即她又想到了乌黑的沙月亮,想起了轰轰烈烈的司马库,想起了奸占了鸟仙的孙哑巴,几十年的酸甜苦辣涌上心头,想当年我也曾骑马挥枪闯荡天下,想当年我也曾穿绸挂缎吃香喝辣,那时马蹄如雪,披风似血,犹如凤凰展开翅孔雀开屏,繁华易逝,富贵如烟,自从沙月亮悬梁自尽,我上官来弟就走了倒霉的盘陀路,疯疯癫癫我,人皆可夫我,人人唾骂我,我这一辈子活得好不好?说好是没人可比的好,说坏是没人可比的坏,咬紧牙关横下心,跟着鸟儿韩折腾吧……”(第436页)
看似偶然的命运,其实是政治强力所致。母亲以亲生经历察知了沙月亮队伍的不堪而劝阻她嫁与沙月亮,但她不管不顾地说:“娘,您还要我怎么样?您心里装着的只有金童,我们这些女儿,在您心里,只怕连泡狗屎都不如!”(第59页)将责任推给母亲,似乎家庭的男性偏爱是她离家的理由,但深层原因是政治对家庭的渗入使她远离了安稳与踏实。“母亲尽管生了八个女儿,……只有一个玉女天天跟在母亲身边,但可惜她是个瞎子;也许正因为她是瞎子,才能在母亲身边呆得住。”即便瞎子也不能幸免,最终“上官家的这八仙女,就真正七零八落了”。
上官金童对各位姐姐的态度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理解他眼中盼弟的“叛变”也有助于理解命运的政治学。政权统一后,掌握村民或下一级干部的历史及其生活经历的流转变动,是包括乡村管理者在内的各类干部的首要任务。盼弟与鲁立人更改姓名的经历,就是通过“去历史”的策略划清与家庭、过往历史的界限,进而取得政权的认同。这一脱离家庭的举动招致金童的反感。她与鲁立人代表着乡村社会新的领袖与统治者,但他们并没有像司马库那样保护亲人,或者也是某种无能为力,他们无力挽救自己的孪生外甥,对母亲显得十分冷淡。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是当时政策的核心,而阶级是超家族的,家庭的能量被弱化,鲁立人自然无力保全自己的亲戚。类似乡村保护人的司马亭在“文革”中死去表明乡村基层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村社关系与乡村的自组织机制也被替换,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被政治化,亲情受到漠视与摧毁。“在华尔德看来,传统在集体化时代已经演变为了一种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即传统经过与现代因素的结合具有了新的形式与内容。这种新传统主义强调下层对上层、干部对国家、民众对干部的效忠与服从,而连接这种效忠与服从的是上与下之间的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这是一种工具性的私人关系。”这种新传统的等级性更强大也更无情,盼弟自杀就是这种工具性的体现,她当众不能对自己的亲弟弟有丝毫的照顾,乔其莎的“极右派”命运是马瑞莲(上官盼弟)对乔其莎(上官求弟)的强力赋予,都是政治对亲情的侵吞。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从这篇小说(指《透明的红萝卜》),包括他后来的《生死疲劳》等许多小说看,他对这种‘过于国家化’的乡村是失望的,尤其讨厌那些作为‘新的乡村保护人’的乡村基层干部。”这是上官金童不喜欢上官盼弟的主要原因。
生于斯长于斯的风姿绰约的上官家女儿无疑是乡土社会的可贵资源。福柯认为,性是没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忽视的资源。鸟枪队员强奸母亲、孙哑巴强奸三姐虐待大姐,都是以革命名义对女性身体的强行闯入;阶级教育展览上,做过妓女的四姐被批斗也是对女性身体的征用,家庭遗传的身体优势成为罪过。而上官金童对尤场长的态度与此正好形成对比,他没有因时代的混乱而放纵自己。司马粮的命运也是外力强行塑造的结果。至此,这种对命运的书写便具有了整体性眼光,揭示出乡民普遍的心理创痛,尤其对上官家第五代人影响巨大,司马粮在商品经济时代的表现就是这种心理后遗症的发作。集体化时代“运用高强度的政治手段来调控广大的乡村,使其完全与社会体制相对应。但是,这套体制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在经济发展列为主要目标之后,这套体制便需要加以改变。这时便出现了一个难题:在旧的体制被削弱之后,人们发现没有别的体制可以保证原有的整合,乡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离倾向和失控倾向。”的确,与集体化时代的饥饿相比,商品经济时代的社会总资源明显增加,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但也面临着严重问题。小说第六卷就集中写大栏市的无序与紊乱。社会的转型将大栏市搅了个底朝天,全民陷入金钱追求的狂热中,连杀兔子都会手软的上官金童也加入了竞争的行列。一些干部借着改革的名义,通过“野蛮的想象力”开发各种资源,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在吃喝享受上下工夫。村民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承受者,也是无权的被管理者,他们只能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取社会资源,因此“大栏镇的人,现在一半是贼”,他们“成箱的电焊条、钢筋、水泥,成捆的电缆线”都敢偷。造假之风甚嚣尘上,司马家大院子成了造假窝点;作为人体器官的乳房也出现了假的;乞讨少年通过明目张胆的欺骗获得财物。浪费风气蔓延,宴请官员的百鸟宴,通宵照明的广场,资源被过度消耗。环境破坏,贫富悬殊,物欲横流,人心异化,烘托出浮躁的社会风气与疯狂寻求补偿的心理。现代经济观念极大地冲击着家庭:鹦鹉韩领走房产变卖款并与母亲分家,只会在语言上孝敬老人;鲁市长穷奢极欲却从没有想过要孝敬姥姥;上官金童虽想报答母亲却总有心无力;母亲成为时代的弃儿与亲人的累赘过着凄凉的晚年生活,几乎死无葬身之地。人们依靠各种关系来扩大获得资源的渠道,甚至不惜利用亲情,耿莲莲利用舅舅与市长的师生关系捞取贷款,汪银枝利用婚姻将上官金童经营的乳罩店占为己有,“大栏市人现在正处在最文明也最野蛮的阶段”。
从物质匮乏时代走过来的人们对物质生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膨胀的物欲吞噬着迷失者的生命。鲁胜利的权力经济就很有代表性,她因血缘关系获得银行行长的职务,又抓住机遇升任市长,这背后是贪污腐败与拉帮结派,难逃法网。鹦鹉韩建起二百亩的“东方鸟类中心”,也是华而不实别有所图,终被判刑。南韩巨商司马粮财大气粗,花天酒地,不知所终。总之,上官家第五代几乎全军覆没。上官金童也“学会了抽洋烟、喝洋酒、搓麻将,还学会了请客送礼偷税漏税”。即便如此,他依然是社会的局外人并被视为精神病,实则他是清醒者。“上官金童的脑子又混乱不堪了,陈谷子烂芝麻,千年百年的事儿,搅成了一团麻。”这未始不是中国农民面对农村发展前路的疑惑与迷惘。这是历史交替的时代症候,作家通过颇有历史感的书写表明:经济时代人们的种种作为跟历史有着莫大的关联。上官金童是这一切的见证人。对他而言,母乳是粮食是生命是幸存的机会,乳房是原初是自然是洁净的象征。他对乳房的痴迷其实是对乳房的疼惜,是对父亲上官寿喜折磨母亲、祖母残害母亲的一种抵制,体现出对女性的疼惜,因为他知道她们比男人苦得多,目睹上官求弟遭张麻子强暴他“眼睛里满含着泪水”。与对土地的守护与亲情的维系一样,他对家庭里的女性身体及命运都体现出明显的残破意识,面对社会的无所适从与举目无亲,都近于这种残破意识——家园毁坏、亲人离散、人将不人。小说第六卷结尾处他与同父异母兄弟相逢的场景,未始不是对亲情的呼唤。强调小说人物命运的外部性因素,并非要否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朴素道理。社会进程非个人力量所能阻滞,但《丰乳肥臀》以文学的名义对社会变革中未能预期的后果进行了思考。
Intruded:HistoricalWritingoftheCentennialVillage: OnMoYan’sBigBreastandWideHips
ZhuHougang
(SchoolofLiberalArt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MoYan’snovelBigBreastandWideHipstakestheshapingandchangingoftheruralsocietybyexternalforces justlikewarandstatepowerandtheresultoftheintrusionasthemainstructure,connectsthechanginghistoryofChinese villagesinthewhole20thcentury,andfocusesonthearrangedlifeandchangedfateofthepeasantry.Thisisthevalueofthe novel,andalsothecorecontentofmostofMoYan’snovels.Observingintruder’sroles,wecanachieveadeeperunderstandingofMoYan’swholecreation.
BigBreastandWideHips;Intruder;Society;Starvation;Destiny
责任编辑:萧映
朱厚刚(1984—)男,广西融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