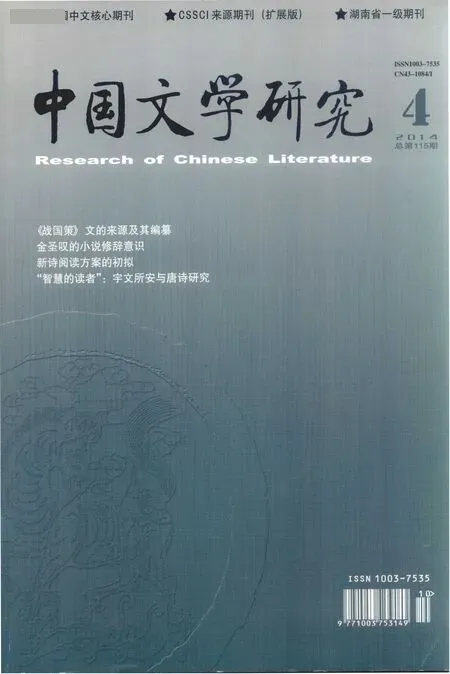艾芜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比较论
2014-11-14侯敏
侯 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 辽宁 鞍山 114007)
茅盾曾深有感触地谈到高尔基在中国新文艺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年轻的中国的新文艺,从高尔基那里得到许多宝贵的指导。‘五四’以来,我们的新文艺工作者在实践中曾经遇到好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找到解答。”“‘五四’以来,曾经有好多位外国的作家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但是经过三十年之久,唯有高尔基到今天依然是新文艺工作者最高的典范。”尽管茅盾的言辞略显夸张,但高尔基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30 年代的左翼文学产生过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在左翼的重要代表人物鲁迅、瞿秋白、夏衍、胡风、艾芜等人身上都能寻绎到高尔基的影响痕迹。但相对于左翼的其他代表人物而言,高尔基与艾芜之间的关系显得较为特别,这种特别就体现在:艾芜并不是像鲁迅和胡风那样从国民性和“人学”思想的角度、瞿秋白和夏衍那样从政治革命思想的角度接受高尔基,艾芜是从流浪经历、流浪汉小说创作及人道主义思想方面寻绎到了他与高尔基的共性特质。但目前学界对高尔基与艾芜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实际上,对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进行全面的研究与探讨是极其必要的,因为通过两人流浪汉小说的比较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清晰两人流浪汉小说的创作取向、文本内涵、风格特征和重要贡献,而且还可以对当下底层写作存在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
一
艾芜深受高尔基的影响。据目前的资料记载,艾芜首次提到高尔基是在1928 年。在这之后,他不仅阅读了大量高尔基的作品,而且还写作了关于高尔基大量的评论性文章。他不仅是《幽会》、《在草原上》等作品的热心绍介者,而且在《文学手册》、《高尔基的小说》、《读高尔基的小说》等文章中也曾多次提到高尔基。1956 年,艾芜在《我与苏联文艺》一文中写道:“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我最喜欢苏联文学。这不只是由于我爱苏联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而且还由于苏联以前的文学遗产,即俄国文学的那种热爱劳动人民的美丽的作品,那种同情被侮辱、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曾深切地吸引着我。许多年前读过的作品,科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屠格涅夫的《木木》、高尔基的《草原上》、果戈理的《外套》……到今天,那里面的人物还生动地活在我的记忆里面。……而在我从事文学工作和不断学习的路上,从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起,一直到法捷耶夫,可以举出一长串俄国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名字,来作我的老师。”1958 年,艾芜又在《人民日报》上明确指出:“由于有了流浪的生活,又有渴望自由的心情,一旦读到高尔基的初期的短篇小说,真如干燥极了的土地上一下逢着甘雨,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凡是翻成中文的高尔基作品,我都找来读,而且不止读一次,总是常常拿来读。甚至高尔基喜欢读的别人的作品,我也要找来读。……我觉得我自己曾经成了高尔基热烈的爱好者和追随者。”以上这些充分说明,艾芜接受高尔基的影响是出于一种自觉。而为什么艾芜会自觉地接受高尔基?其实在艾芜的言论中已经表述得很清楚,除了源于一种追求“自由”的渴望,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两人都有“流浪的生活”。
高尔基曾经三次漫游俄罗斯,而艾芜也是三次南行。可以说,他们的“文学道路都缘于流浪。漫游俄罗斯与南行滇缅成为高尔基与艾芜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正如高尔基在‘人间’读‘大学’,成为伟大的文豪”一样,流浪生涯也同样造就了“中国的高尔基——流浪文豪艾芜”。细读艾芜和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不难发现,相似的漂泊经历使他们有着诸多共同的创作取向与思想特质。他们在作品中塑造的多是强盗、小偷、乞丐、娼妓等底层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几乎都是被当时社会抛出“正常生活轨道”的“边缘人”,他们衣食无着、忍饥挨饿,过着朝不保夕的惨淡日子。这些人物对造成自身贫穷与落魄的黑暗社会现实和丑恶势力往往有着强烈的痛恨,这种痛恨之深甚至使他们的性格发生极度的扭曲。比如艾芜在《月夜》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的旅伴吴大林,说他所以干了这么一种牵羊拔牛毛的职业,完全由于他从小到大,都过着挨打受骂的生活。起初在鞋匠那里,挨着鞋底板和巴掌,继后又在打铁店吃了拳头和脚腿,终于从裁缝铺子里逃了出来,手臂上带着烙铁烙伤的痕迹。从此在街上变成流浪人,和扒手偷儿一道打堆,学会了牵羊拔牛毛的技术。……他对他的同道,极抱好感,碰着无业的人,也能彼此相合,可以称兄道弟,其余的人便都成了他的眼中钉,总是设法使他们受到一点损害。他的快乐,便是建筑在他们的悔恨和气恼上面的。他从小受到的苦难,深深刻印在心里,自然使他无法忘记,而每一次他在市集上的失败,给人抓在手里,打出鼻血,就又增加了新的仇恨。
高尔基在其作品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在小说《叶美良·皮里雅依》中写道:
“不管你怎么说,对着有钱人的脑袋来一下,倒是非常痛快的;特别是在把事情安排得巧妙的时候,”叶美良意外地说。
“你不要再瞎扯啦,”我说。
“瞎扯?!这怎么是瞎扯!这件事情是要实现的,请你相信我的良心。我四十七岁了,二十多年来我就一直在绞脑筋想这个办法。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狗的生活。没有一个窝,没有一块面包——比狗的生活还不如!难道我是个人?不,朋友,不是人,比虫、比兽都不如!谁能够了解我呢?没有人能够!不过要是我知道人们能够好好地生活,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生活呢?唉!让魔鬼抓了你们,这群鬼东西!”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位作者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黑暗的社会现实,并指出残酷而丑恶的“有钱人”才是造成人们贫穷、流浪和居无定所的罪恶渊薮。这无疑赋予了这些流浪汉畸形性格一定的合理意义,所以两人并未仅限于对流浪汉畸形性格的揭示,而是将笔触深入到这些流浪汉内在的精神现实,并试图挖掘这些“歪人”内面精神世界的“人性闪光”,对这些流浪汉人性当中内蕴的善良本性给予审视,从而使我们看到即使是强盗、小偷也有其善良的一面。这在艾芜的《荒山上》、《山峡中》、《流浪人》、《我的旅伴》,高尔基的《叶美良·皮里雅依》、《谢马加被捕记》、《科诺瓦洛夫》等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之所以体现出诸上的共性特征,与他们的流浪经历及由此生发的人道主义思想息息相关。艰辛的流浪历程,沦落底层的凄惨境遇,不仅使艾芜与高尔基切身感受到社会的黑暗,而且使他们深谙底层人民的不幸,并对底层人民产生了深深的人道主义同情。也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浓郁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才使艾芜和高尔基在流浪汉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关注底层、批判社会、讴歌人性之“善”。
二
虽然艾芜深受高尔基的影响,两人在流浪汉小说的创作方面也体现出诸多的共性特征,但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过程往往不是直线式的“传递”,也不是强硬的“灌输”,而是作家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影响对象作出选择与甄别,并将有用的部分纳入自己创作视野的过程。另外,每一部作品都不可能是他者的完全复制,它势必会打上写作者独特的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印记。那么,如果从这些角度出发来考察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创作,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艾芜与高尔基的作品除了共性特征之外,还存在某些差异,如果对这些差异进行归纳与总结,笔者认为,这集中体现在挖掘人性的深度、批判现实的力度、反抗意识的强度等几个方面。
在反映流浪汉的人性方面,艾芜着重表现的是流浪汉人性中的“善”。这样的人性之“善”在《山峡中》一文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作品中的“我”是个读书人,被世界所弃,混迹于一群强盗之中。这群强盗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心肠“干硬”。但是强盗首领的女儿野猫子,虽然也残忍冷酷,但并未完全失去人性的“光泽”,当“我”解救了她之后,却意外地给我留下三块银元,使我脱离了强盗的“魔爪”。在日常生活中,强盗难有善良本性,但在艾芜所生活的那样一个荒乱的年代,他能够挖掘出这样的人性之“善”,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肯定的。可值得注意的是,艾芜这种对“善”的执着描写,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他对人性之“恶”的客观审视。比如在《偷马贼》中,偷马贼老三因初次偷马而被人们在山上打得皮开肉绽,可看见老板悄悄派来送伤药的伙计,他头一句话却是担心大家没有认出他来,原来他偷马是为了别人能认出他,从而使别人恐惧,以获得吃喝的资本。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畸形性格的人,作者却用近于赞赏的态度描绘到:“这时,我蓦地感到这个弱小人物的高傲了。我蹲在他的身边,替他擦药,还对他有些同情,现在才觉得,在他身上升腾起了强烈的争生存的欢乐感情,是用不着任何人的怜悯的。”虽然在这段表述中,寄予着作者对人能主动争取生存权利的热望与期盼,但不要忽略这样的热望与期盼却是以掩盖与淡化人性之恶为代价的。
与艾芜不同,高尔基不仅表现了人性之“善”,而且还对人性之“恶”给予揭示,并且往往是将这种人性的“善”与“恶”放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加以展示。比如在《阿库莉娜奶奶》一文中,阿库莉娜奶奶是一位善良的“母亲”般的人物,她无私地照顾着酒鬼、流浪汉,小偷、娼妓等各种各样被社会遗弃的人,但她“却得不到受她恩惠的人们的爱戴”,在阿库莉娜奶奶讨饭不慎摔伤之后,她抚养的八个流浪汉不但不送她去医院,还向她要吃要喝,并无耻地剥夺了她买棺材的最后三个卢布。阿库莉娜奶奶就是在这样的冷漠中悄然地离开了人世,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人们就这样埋葬了阿库莉娜奶奶,埋葬了这个小偷、乞丐和阴沟街上的善人。”这种平静语调的背后,我们分明能够感觉到作者的无比痛心与愤恨。
在关注现实方面,艾芜往往陶醉于大自然当中,而“不愿意长久地审视黑暗”和“丑恶”。这在其流浪汉小说中有着鲜明的印记。比如在《山峡中》一文中,当受伤的小黑子被同伙残忍地扔到大江的第二天,作者就急不可耐地这样描写他无比热爱的大自然。
峰尖浸着粉红的朝阳。山半腰,抹着一两条淡淡的白雾。崖头苍翠的树丛,如同雨洗后一样的鲜绿。峡里面,到处都流溢着清新的晨光。……清亮的波涛,碰在嶙峋的石上,溅起万朵燦然的银花,宛若江在笑着一样。
对自然的崇拜与热爱,对一个作家而言,并无可指摘之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消解了作品的悲剧意味和批判现实的力度。
高尔基同样也热衷于描写大自然,但是他作品中的自然描写却不像艾芜那样“独立”与“纯粹”,而是紧贴现实,并为现实服务。比如在小说《切尔卡什》中,作者对乌云的描写就颇具深意,当切尔卡什去帆船上偷东西时,作者这样描写乌云:“大片的、沉重的黑云慢慢地移动着,从黑暗中散发出恐怖,准备用自己的重量把人压碎。一切都是冷冰冰的、黑压压的、不祥的。”而在偷盗成功以后,作者写道:“乌云在天空中向四外扩散,用一张均匀厚实的帐幕覆盖着大海,低低垂到水面上,一动也不动。”显然,作者在这里是用景物描写来衬托具体事件的,也就是说,作者虽然描写自然环境,但他的目的始终是在指向现实,并试图解剖现实的。也正是由于高尔基对现实的高度重视,因此他的作品往往能让我们体会到较强的批判现实的力度和解剖现实的深度。比如在《科诺瓦洛夫》一文中,当“我”漫游罗斯,看到劳动工人建筑防波堤时,不禁对于社会的丑恶投以深深的憎恶,而对贫苦的人民给予深切的同情:
他们只顾埋头建设,永远不停地劳动,他们的血汗就是大地上一切建筑物的混凝土,可是他们自己却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从事建设的永不衰竭的愿望——在大地上创造奇迹的愿望,但是到头来却没有给予人们以栖身之处,而且给他们的面包也太少了。
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有着许多这样的现实批判性的描写,而在这种描写的背后,我们分明能够看到作者那充满愤恨、悲悯、无奈和痛苦的表情。
艾芜与高尔基不仅在挖掘人性的深度、批判现实的力度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而且在人物反抗意识的强度方面也并不相同。在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中,他只是“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和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所以致使其作品中的人物虽也有对自己被压迫的不幸命运的反抗,但这样的抗争意识显得微弱。比如在《乌鸦之歌》中,面对一个本分的农民被地主逼疯的残酷现实,他的亲人只是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欺压,但却并没有激起人们对这种残酷压迫的反抗。另外,在小说《山峡中》一文中,在小黑牛被同伙无情地扔到大江以后,文中的“我”有这样一番感慨:
小黑牛在那个世界里躲开了张太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我不禁就由这想起,难道穷苦人的生活本身,便原是悲痛而残酷的么?也许地球上还有另外的光明留给我们的吧?明天我终于要走了。
尽管这段话体现出“我”对黑暗社会吃人本质的极度痛恨,以及对光明世界的热切渴盼。但一句“明天我终于要走了”,却使先前的悲剧性的力量骤然消解,因为这句话本身指向的不是对悲剧命运的反抗,而是“逃离”。或许正像有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象艾芜这样倾向热烈地赞美人生的作家”,“他在种种凶险可能的揣测面前扭过头去,不过是为了更专心地欣赏路边的溪水和林丛,他睁大眼睛到南方去寻找幸福,岂能让丑恶遮住自己的视线?”
高尔基与艾芜不同,文学对于高尔基而言“只是他介入、干预生活的一种方式”。他用这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压制人性,而首先是反对置人于死地的那些人”。正是基于此,高尔基的笔下才出现了那么多反抗强权与压迫的人物。比如,在《两个流浪汉》中的马斯洛夫就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他用行动来反抗“机器”对于人的压迫,文中写道:“他把谷穗摊成均匀的厚厚的一层送进机器,他乌黑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紧皱着眉头,心中充满着愤恨,这是那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复仇的、总是能够达到目的的愤恨。”尽管这样的反抗行为有些盲目,但它确实标识着人的反抗意识的觉醒。
三
以上结合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文本,对两人文本世界的不同之处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与分析。但是在阐释与分析之后,我们就势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文本世界的差异性?我想其原因,主要应该有以下几点:
第一、童年的经历不同。早已有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童年经历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和创作倾向,这在艾芜与高尔基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艾芜出生在四川成都平原上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当时的成都平原不仅经济富庶,而且还是风景秀美的圣地,幼时的艾芜常常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当中难以自拔。可以说,正是这段愉快的童年经历使他对大自然产生了一种由衷的热爱,也决定了他日后描绘世界与现实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向大自然投去深情的一瞥。与艾芜不同,高尔基没有艾芜那种优裕的家庭条件,更没有艾芜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高尔基出生在俄罗斯伏尔加河畔一个贫苦的木工家庭,在他四岁时父亲就因霍乱病去世,无奈之下,母亲带着高尔基来到了开染坊的外祖父卡希林家。卡希林家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家庭:愚昧、狭隘、自私、残忍……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甚至为一些小事而常常争吵、斗殴。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暴戾的外祖父常常毒打高尔基,并多次打得他失去知觉。高尔基就是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中度过了自己惨淡的童年,其后,母亲又去世,外祖父也不愿意再收留他,年仅11岁的高尔基只能孤身一人去漂泊炼狱般的“人间”。在漫长的漂泊生涯中,高尔基看到了社会上各种各样残忍、污秽、丑恶的事情,这“使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作家都更为真切地体验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不幸”。所以,高尔基不像艾芜那样热烈地崇拜与讴歌大自然,而是自从登上文坛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默默地谛视着俄罗斯这些“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实”,并渴望从这“丑恶”的“土壤”里能够“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出“善良——人所固有的善良。”
第二、所接受的文化传统不同。艾芜更多地关注人性之“善”,而缺乏对人性之“恶”的客观审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仁也者,人也”,直到宋明理学所倡导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等思想,一直都在强调“仁”的重要性,所以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艾芜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而艾芜的作品缺乏批判现实的力度,笔下人物少有反抗意识,与艾芜受到的中国道家、佛家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道家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佛家的“缘起性空”、“自性妄执”等观念,强调修身养性、顺法自然、与世无争,这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然艾芜也名列其中。另外中国“士”文化和“侠”文化也对艾芜的创作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童年的艾芜满怀兴味地诵读的充满“士”文化气息的“古代诗人歌咏柳絮清风的诗篇”,以及《三国演义》、《今古奇观》、《七剑十三侠》、《燕山外史》、《禅真逸史》等满含侠义色彩的书籍,不仅使其作品浸染了浓郁的浪漫色调,而且加强了作者凸显正义与善良的意识。最后值得强调的是,艾芜除了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他也秉承了“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衣钵”。“五四”新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试图摆脱“传统”,但又未能真正脱离“传统”;试图放眼“西方”,但对西方文化又未能真正消化与吸收。加之“五四”后战争频仍,作家颠沛流离,饱受战争之苦,难能对现实、人生作出深入而理智的思考。所以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先天就“营养不良”,后天也往往难以摆脱“稚嫩病”。这在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与艾芜所受的文化传统不同,高尔基广采博取的是西方各国的文化传统,从古希腊文明一直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他都有所涉猎。高尔基在流浪过程中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各特、龚古尔兄弟、大仲马、海涅等都影响过他。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俄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兴盛于19世纪40、50 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其主要特点是:作家往往以冷静、理智的眼光审视与批判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黑暗,解剖人性,从更现实的角度去寻求改善人类生存处境的途径。而俄国古典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几乎每个作家都有虔诚的宗教情结,他们“忘我地热爱伟大的生活,热爱文学,热爱辛劳困乏的人民,热爱自己凄凉的国土。”“他们是诚实的战士,为真理而死的伟大的殉道者”。所以,俄罗斯文学的主色调往往不是“明快与乐观”,而是“沉郁和苍凉”。那么,高尔基为什么能够较为冷静、理智地辨析人性的善与恶,为什么能够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性和反抗意识便不难理解了。
第三、流浪的心态不同。艾芜的流浪是出于自觉。由于艾芜在童年时期就对大自然和外面的世界满怀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憧憬,使他从小就强烈地渴望走出家门,去打量外面五彩斑斓而又神秘新奇的世界。所以“一旦生活终于向他露出卑俗的嘴脸”,祖父卖掉最后十亩田,又给他包娶了一位不识字的农家姑娘作妻子的时候,他就急不可耐逃开了父辈们为他安排好的生活,离开了家乡,义无返顾地踏上了他的寻梦之旅。从这一角度来看,艾芜的流浪其实是源于他对儿时诗意梦想的追寻,所以尽管他在流浪的途中也体验到了现实的残酷,人性的丑恶,但艾芜却往往不情愿因此而破坏自己内心的浪漫诗意,他要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侧过脸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要么尽量回避人性中的丑恶而极力去挖掘人性中的善良。与艾芜的这种自觉的流浪意识不同,高尔基的流浪是源于被迫。高尔基没有艾芜那样令人艳羡的童年生活,也没有艾芜那种浪漫新奇的想象,当高尔基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抛入到了残酷现实的洪流,而在之后的流浪岁月里,他又饱尝了无尽的人世的艰辛与磨难,这使他深刻地体验到了现实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所以他绝不会像艾芜那样以新奇的、浪漫的、善意的眼光去打量世界,他只会以憎恨的、愤怒的、批判的眼光来谛视与反抗现实。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艾芜的童年生活令他感到无比快乐,而高尔基的童年生活使他倍感痛苦;艾芜主要接受的是儒道佛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高尔基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与充满“沉郁和苍凉”文化底蕴的俄国古典文学的熏染;艾芜的流浪是出于自觉,而高尔基的流浪则是源于被迫。不同的童年经历、文化传统和流浪心态,使艾芜虽然始终注视着“现实的大地”,始终描绘着“真实具体的人性”,但往往不由得向浪漫主义倾斜。而高尔基虽然以浪漫主义的姿态登上文坛,但他却始终以忧郁的眼光、深沉的姿态默默地谛视着现实,从未“脱离现实,忘记现实”可以说,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使他们在书写流浪汉小说时,提供给我们两个不同的文本世界。
综上所述,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书写一方面存在着诸多的近似之处。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不同的童年经历、文化传统的熏染和流浪心态的影响,又促使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不同的文本世界。而在此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的关注点各有侧重,但他们却以流浪汉小说确立了自己在文坛上的重要位置,并为流浪汉题材小说的发展开拓出了新的空间。可以说,他们的流浪汉题材小说,不仅在各自国度的文学语境中是全新的,而且在整个世界流浪汉题材小说的创作中也是较为特别的。因为尽管流浪汉题材小说有着漫长的历史,但却几乎没有哪个作家像艾芜与高尔基那样去真正深入流浪汉群体内部,去设身处地地体验他们的生活,去充分挖掘他们的“人性闪光”。因此,尽管在世界文学中不乏流浪汉小说佳作,但往往因缺乏真实感和对流浪汉人性的挖掘而失去说服力。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当下的底层文学写作,如今每年都有大量的关于底层的文学作品问世,但能够真正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现在许多书写底层文学的作家大多都身居都市,他们缺少像艾芜与高尔基那样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切身体验,他们不能洞察与揭橥底层民众的人性的真实,导致他们的作品往往只是源于“虚构的热情”。这样的作品虽然在形式上眩人耳目,但其内容却常常流于浮泛,难有让人为之振奋的东西,我们也感觉不到作者灵魂的重载!所以笔者认为,要想使底层文学焕发生机,作家就必须要像艾芜与高尔基那样,深入底层人民的生活,切身体验、深入在场,否则一切都将可能成为空谈。
〔注释〕
①这一年艾芜刚刚从四川新繁老家逃婚到仰光,初到仰光的艾芜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艾芜在英文报《仰光公报》上首次看到了介绍高尔基的文章,并将其译成中文在《仰光日报》上发表。
〔1〕茅盾.高尔基和中国文学〔A〕.茅盾全集(第23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艾芜.我与苏联文艺〔A〕.毛文,黄莉如.艾芜研究专集〔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3〕艾芜.高尔基永远走在我们的前头〔A〕.毛文,黄莉如.艾芜研究专集〔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4〕张建锋.艾芜与高尔基反思国民性的比较〔J〕.成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5〕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
〔6〕艾芜.艾芜文集(第1 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7〕〔苏〕高尔基.高尔基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苏〕高尔基.高尔基文集(第2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0〕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A〕.鲁迅全集(第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1〕〔苏〕高尔基著,汪介之选编.高尔基读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2〕〔俄〕瓦季姆·巴拉诺夫著.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M〕.张金长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13〕汪介之.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4〕〔苏〕高尔基著.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M〕.刘辽逸、楼适夷、陆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15〕〔苏〕伊·格鲁兹杰夫著.高尔基传〔M〕.辛守魁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6〕〔苏〕高尔基.论文学(续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7〕汪介之. 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关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8〕艾芜.读高尔基的小说〔A〕.罗果夫、戈宝权编.高尔基研究年刊〔C〕,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