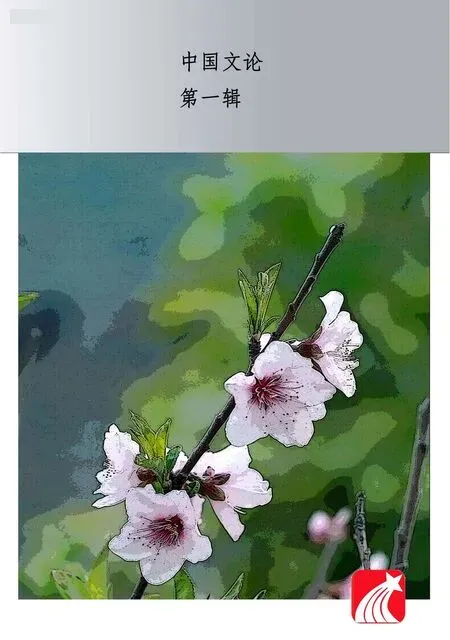文如其人
——从《文心雕龙·程器》篇看文品与人品之争
2014-11-14邹广胜
邹广胜
文如其人——从《文心雕龙·程器》篇看文品与人品之争
邹广胜
人品、文品之争乃是中西文论史上的老问题,从朗加纳斯的《论崇高》开始,到《文心雕龙·程器》篇,再到钱锺书的《文如其人》等,都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中,这个问题时刻都存在着,只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方面与特征。重新思考这个历久弥新的老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文心雕龙;文品;人品;文如其人
人品、文品之争乃是中西文论史上的老问题,从朗加纳斯的《论崇高》开始,到《文心雕龙·程器》篇,再到钱锺书的《文如其人》等,都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中,这个问题时刻都存在着,只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方面与特征。时至今日,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中国学术界,重新思考这个历久弥新的老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克尔凯郭尔通过他的两则寓言也阐明了这个问题。其一是《宫殿旁的狗窝》,它讨论的问题是:“思想者建立的体系与他的现实处境之间的关系应作何比喻?”其寓言为:“一位思想者建立了一座庞大的建筑,一个体系,一个包容万有及世界历程等等一切的体系。然而,假如我们考察他的个人生活,会发现一个可怕而荒唐的事实:思想家并不居住在这座恢弘、高大的宫殿之中,而是住在旁边的马厩里,或者在一个狗窝里,或至多住在一个脚夫的草屋里。假如有人提醒他注意这个事实,他就会发怒。因为他并不惧怕生活在幻想之中,只要他能够完成这一体系——这也同样借助于幻想。”此则寓言讨论了哲学家,自然也包括文学家及各式各样的艺术家,他们为世人,也为自己筹建了各式各样美好的理想,许下了各式各样令人神往的承诺,然而这些理想不过是幻想,而令人神往的承诺也不过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更为重要的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正如在盗跖看来,孔子为世人许下的各式各样的美丽谎言一样,又有哪一样兑现了呢?无论是大同世界,还是小康世界,无论是仁义道德,还是礼义廉耻,都无法兑现这些哲人此前曾许下的诺言,虽然他们自己也许曾经一度相信。如果此则寓言讨论的是“言说”和“信”的问题的话,也就是哲学家艺术家是否相信自己的言说。第二则寓言《复活的路德》则是讨论“言”和“行”的问题,哲学家所说的和他所行的是否一致,克尔凯郭尔把这个问题命名为“没有不惜身命的奋斗,真正的信仰能否存在?”他在寓言中说:“设想路德从坟墓里复活,一连数月,他都在我们中间,尽管无人察觉,他一直在观察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留意所有的人,也包括我。我想有朝一日他会向我打招呼,对我说:‘你是不是信徒?你是否有信仰?’作为一个作家,所有熟悉我的人都会承认,就此类考试而言,我毕竟可能是那个成绩最好的人,因为,我常常说:‘我没有信仰。’就像一只小鸟在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面前急切地逃遁,我也表达了对那种狂乱之困惑的不祥的预感,‘我没有信仰。’我可能会这样回答路德。我可能说,‘不,我亲爱的路德,我至少已经向您表示了敬意,就是说我宣布我没有信仰。’然而我不愿意强调这一点。所有其他人都自称为基督徒和信徒,我也同样会说:‘是的,我是信徒。’否则我就无法明了我想要明白的事体。于是我回答道:‘是的,我是信徒。’‘那怎么会呢?’路德道:‘我没有发现你有任何信仰的迹象,而我已经观察了你的一生。而且你知道,信仰是一件烦恼的事。你说有信仰,信仰又是如何使你烦恼的呢?你何时曾为真理作证?你何时曾揭穿谬误?你曾做出何种牺牲?你曾为基督遭遇受何种迫害?在你的家庭生活中,你又曾显示出何种自我牺牲与克制?’我回答道:‘我庄严宣告我有信仰。’‘宣告,宣告,那是什么话?如果有信仰,就不需要任何宣告;如果没有信仰,任何宣告也无济于事。’‘是的,但我只要你愿意相信我,我可以尽可能庄严地宣告……’‘呸,别再说这些废话!你宣告又有什么用?’‘是的,可你要是读过我的一些书,你会知道我是如何描述信仰的,所以我知道我一定有信仰。’‘我觉得这家伙是疯子!确实,你懂得如何描述信仰,这只是证明你是一个诗人;如果你描述得很精彩,说明你是一个出色的诗人;但是这并不证明你是信徒。也许你在描述信仰时可能会哭哭啼啼,这只是说明你是一个好演员而已。’”克尔凯郭尔异常精彩地说明了哲学家与真正有信仰的人之间的根本差别,也就是“言”和“行”的差别,正如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道德的一定有美好的言论,有美好言论的不一定有美好的道德。仁义的人一定勇敢,不勇敢那能行施自己的仁义呢,不能行使又与空谈有何区别呢?勇敢的人有为己为人之别,为己者不过是一己之勇,是自私的勇敢,像动物争夺食物一样,而为人者则是真正的勇敢,他不为己,如苏格拉底的勇于赴死、释迦牟尼的离家出走、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孔子的颠沛流离,所遭受的各种屈辱又有哪一个是因为自己的呢?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他的“一以贯之”不仅仅是指把一个根本原则贯彻到整个理论之中,使自己的理论能够自圆其说,而是把自己的根本原则同时贯穿到理论与生活之中,并贯之以一生。《论语·里仁》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可见,孔子是将他的理论贯穿于他的一生的,不管是人生畅达,处于富裕和显贵的时候,还是人生穷困,处于贫弱和低贱的时候,都把自己的理论当作生命的根本,君子依靠的是自己的仁德,离开了仁德,哪还称得上君子呢?君子一刻之间都不要离开仁德,即使在匆匆忙忙的时候,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何曾背离自己的原则呢?但一般的人都是在需要仁义的时候拿着仁义当作骗人的幌子来使用一下,等达到自己的目的后就随意地放弃了,正如作家在创作时,客观的需要使他选择了一个高尚的主题,但在他的内心又何尝相信呢?等他离开了自己的创作,离开了大众的视野,当他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当他名利双收自感到安全的时候,他便展露出真正的自我,那自我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正是被压抑的本能。但圣人没有本能吗?圣人不过是能根据理想的原则来控制自我罢了。可以想象如果庄子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好色贪财之徒,释迦牟尼是一个贪恋世俗权力与名利的俗不可耐的庸人,孔子是一个蝇营狗苟斤斤计较的势利小人,如果他们自己不以身作则,不以身证法,他们又怎能说服无数的跟从者,从而使他们前赴后继赴汤蹈火呢?然而克尔凯郭尔正看到了并不是任何哲学家与艺术家都言行如一地生活着,却常常存在着事实上的言行不一,虽然这种言行不一是经常存在的,特别是在普通人身上,但普通人的言行不一不如哲学家与艺术家的言行不一更具有哲学意味,因为哲学家与文学家呈现在世人眼中的更多的是言,而不是行,况且哲学家也懂得如何以人品、文品之争的另一方面来为自己辩解:世人能否因人废言,或因言废人呢?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不是讲过“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吗?君子不因为人家话说得好就提拔他,也不因为否认他的为人就不信他的话。可见孔子还是承认除了以道德的层面来判断哲学家和文学家之外,还要以智慧,甚至是审美的层面来判断哲学家与文学家,而这正是他们在世上得以存在的理由,哲学家与文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比世人具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为自我辩解的能力。所以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今日中国则常反其道而行之,损失不小。唯近世以还,操守缺而学问显,人品残而声名著者,盖已多有,岂亦‘不以人废言’之谓乎?固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之又呈现也。然秦桧、严嵩,阮大铖、汪精卫诗卒不流传。伦理命令至高无上,可不惧哉。学者盖三思焉。”可见,李泽厚把人品文品的问题上升到“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的问题,虽然很多人能够凭借一时之巧飞黄腾达,但最终还是要接受伦理最高命令的惩罚而遭到历史的唾弃,这也是康德所说的求真与求善的根本不同吧。
《文心雕龙·程器》分两部分讨论了作家及政治家的人品问题,如果政治家的政治作为也算作他们的作品的话。第一部分首先讨论了文学家的人品。《程器》的一开始就根据《尚书·周书·梓材》提出了自己的标准,他说:“《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梓材》中周王说:“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彟。”周王说教化民众就像优良的木材制作器具,不仅要辛勤地削皮加工,还要涂上红色的颜料加以装饰,以达到既要实用,又要有文采的效果。也就是《论语》中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如李泽厚解释的,“‘质胜文’近似动物,但有生命;‘文胜质’如同机器,更为可怖。孔子以‘礼’‘仁’作为中心范畴,其功至伟者,亦在此也:使人不作动物又非机器。”可见刘勰的论士“贵器用而兼文采”与孔子的“文质彬彬”是一致的。然而在刘勰的时代却并非如此,而是“近代词人,务华弃实”,再加上魏文帝“古今文人大都不顾小节”的观点,以至于韦诞对很多作家都一一作了批评,后人也随声附和,视听混淆,不一而足了。这就是刘勰的写作目的:为了纠正当时文坛流行的关于作家人品的不正确的观点。所以接着刘勰就列举了历代文人们的各种瑕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锐以躁竞,孔璋惚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潘岳诡诪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司马相如勾引卓文君私奔而又受贿,扬雄因嗜酒而生活混乱,冯衍、杜笃都不守规矩,贪得无厌;班固谄媚窦宪,马融投靠梁冀:都作威作福,贪污受贿;孔融、祢衡都以自己的傲慢狂放而招致杀戮;王粲、陈琳都是草率轻疏之人;丁仪、路粹都是乞货贪吃的小人;潘岳陷害愍怀太子,陆机攀附贾谧、郭彰:都是阴险狡诈之人;而傅玄和孙楚都刚愎自用,反叛上级。如此等等,都是文人的毛病。由此看来,刘勰主要是以儒家的道德观点来判断作家的人品及行为的。但是正如牟宗三所说:“孔夫子讲仁,并不是单单对中国人讲。孔子是山东人,他讲仁也不是单单对着山东人讲。他是对全人类讲。”对此,我们也可以讲,刘勰的《程器》篇也并非仅仅针对他所提到的这些文人,而是针对所有的文人,自然也包括今日的文人。关于这个问题,周振甫在《文心雕龙今译》中说:“本篇讲作家的品德,既是从‘负重必在任栋梁’着眼,不是从品德同创作的关系着眼,那么从创作的角度来考虑,对这些问题,本可存而不论。只是刘勰既经提出来了,也可以说一点,即他所指责的,有的不是品德问题。像扬雄嗜酒而少算,孔融的反对曹操,祢衡的傲视权贵,王粲的轻锐躁竞,陈琳的草率粗疏,傅玄的攻击台臣,孙楚的跟石苞互相控诉,相如跟卓文君同归,都不属于品德问题。此外,还可指出一点。他说:‘彼杨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认为他们的品德不好,所以不能任栋梁。那末古代的将相的品德也不好。他指责古代将相的品德,实际上是为文人抱不平,也是感叹自己的不得志。”既然刘勰是按照儒家的价值观来判断作家的品格,他甚至在《序志》里把自己写作《文心雕龙》的缘起归结为梦到孔子,把写作《文心雕龙》的根本目的看成是对孔子志向的继承,所谓“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所以像“扬雄嗜酒而少算,孔融的反对曹操,祢衡的傲视权贵,王粲的轻锐躁竞,陈琳的草率粗疏,傅玄的攻击台臣,孙楚的跟石苞互相控诉,相如跟卓文君同归”之类,无论是在孔子,还是在刘勰看来都是有很大问题的,也是一个儒家君子所不可取的。“嗜酒”、“傲慢”、“狂妄”、“轻浮”、“草率”都不符合刘勰的“负重必在任栋梁”的基本观点,因为这不符合从政所需要的基本品格。我们从孔子反对子路的刚烈性格也可看出这一点,他说子路:“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他甚至预测了子路的不得好死:“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他也不认为子路是他最好的学生:“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所以他在给子路讲话时都是与别人不同的:“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甚至有时候还笑话子路,当别人问他为何笑话子路:“夫子何哂由也?”他回答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所以当季康子问孔子:“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路是否适合于从政时,孔子便自然回答:“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他不适合从政,子路的死也印证了孔子的话。甚至朱熹也继承了孔子的这个观点,他在《孟子序说》中引用了程子的话来评价孟子与孔子的不同,他说:“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可见,这种内涵的中庸之道是儒家“一以贯之”的。刘勰对文人的批评,我们在孔子对子路的批评中都可看到,虽然刘勰自己也遭受不公,没有“负重任栋梁”的机会,才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但他认为这并不是由于自己的品质,或是自己的才能,而是由于自己的出身,所以他才说:“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鲁迅《摩罗诗力说》中也说刘勰的这句话“东方恶习,尽此数言”。刘勰甚至在《史传》篇中也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中的虚伪所表现出来的对权势的阿谀逢迎做出了尖锐的批评:“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文人写传记愈近当代愈是虚假,即使如孔子这样的圣人在记述鲁定公与哀公的事时都不能免俗,这也是他历来就主张为尊者讳,刘勰所谓“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的理论主张所决定的,其实这也关联着现实的利害。在刘勰看来,文人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即使是庸俗不堪的小人也要尽力地加以拍马逢迎,而对那些暂时失势的君子,则打击嘲笑,无所不用其极,文人的一支笔既像春风春雨一样,又像北风寒霜一样,时代遥远的模糊不清,时代太近的又不敢讲真话,有谁能靠内心的真诚来判断事理呢?像刘勰这样出身微寒的士人虽然在理论有“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设想,而现实也只有“穷则独善以垂文”等着他。我们只要看一下《梁书·刘勰传》的记载就明白了刘勰为何在《文心雕龙》里反复发出这样的感慨。刘勰的出身是“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这样贫穷的人在刘勰所描述的“文士以职卑多诮”,“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的门第等级森严的世界里,又哪有什么“达则奉时以骋绩”的可能呢?所以当他写完《文心雕龙》后,“未为时流所称”。刘勰虽“自重其文”,然无可奈何,便只好按照流行的方式去做:“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经过了这番经历后,刘勰写出“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这样以己度人的话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陆侃如、牟世金在《刘勰和文心雕龙》中说:“对于班固、陆机等人的丑行,刘勰的批判是对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身居将相,担负国家重任的人尚且品行不端,何况那些官卑职小的人和穷困的书生呢!将相虽然品行不端,仍然算是儒林名士;一般文人却遭到过多的讽刺。这不过是因为‘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罢了。这是极不公允的。刘勰这样的揭露,在门阀森严的六朝时期,是有一定意义的。”
紧接着刘勰又论述了武士的缺点,所谓“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古代的将相很多人都有毛病:管仲偷盗,吴起财色俱贪,陈平行为不检点,绛灌则逢迎拍马、嫉贤妒能,有这种毛病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可见将相与文人只不过在职业上有别,在人品上则相类似,可谓斑瑕互现。但刘勰又为普通文士的缺点与不得已做出了说明:“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孔光位居相位还逢迎董贤,何况班固、马融、潘岳这样的小人物?王戎为开国元勋竟也买官卖官,随波逐流,何况司马相如、杜笃、丁仪、路粹这样一无所有的人?至于孔光依然被尊为名儒,王戎被列入竹林七贤,都不过是因为名声太大,无人讽刺打击他们罢了。古今的历史哪个时候不是“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江河腾涌,涓流寸折”呢?但是刘勰并没有到此为止,他最后又提出了更富有挑战的问题:人们都常用“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这样的话来为他人辩解,同时也自我安慰,但是不是所有的文人都像刚刚列举的那些人一样以“为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来解释自己的难言之隐呢?刘勰并不认为如此,他说:“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看看屈原、贾谊的忠贞,邹阳、枚乘的聪慧,黄香的孝顺,徐幹的淡泊,并不是只要是文人就必然有缺点的,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随波逐流,被别人的权势与自己的所谓苦衷所驯服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知识分子都做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依然有少数人能坚持自我坚持真理并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至于那些反复为自己辩解的人,在刘勰的观点来看,有些是可以理解的,但那并不能成为为低俗开拓的借口,因为依然有人能达到文人的最高理想。所以刘勰又重新回到了儒家对于文人的理想要求上:不管名声的高低与职位的大小都应该“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所谓“以成务为用”就是要“治国”“达于政事”,而不能像扬雄、司马相如这些人,只有文人的才能,而没有从政所需的道德品质,所以一辈子碌碌无为,得不到任何显要的职位,而应该像庾亮一样不仅文章为时所称,而且能身居要职,虽然官职的显赫盖住了文章的才华,如果他不从政,同样也会以文章名世的。如果能像郤縠、孙武那样文武兼备,左右开弓,那就更能达到文人“蓄素弸中,散采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的最高理想了,写文章的目的在于为国为政,而从政就要勇于成为栋梁之材,时势来时就要建功立业,时势去时就独善其身,这样又重新回到了孔子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所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观点上了。当然刘勰在这里仅仅是讨论了文人的个人品质,而不是讨论文人的个人品质与作品内容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的《辨骚》、《明诗》、《才略》、《体性》、《风骨》等诸篇中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则分别讨论了作家的才能、创作的风格、文体等具体的文学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刘勰是怎样看待文人人品与文品基本关系的。当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首先,刘勰在评论作家作品与评论作家人品时采用相同的标准吗?当然文品主要是指作品艺术形式的特点,而人品主要是作者现实中的行为表现,然而两者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一致吗?《周易·系辞下》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在《周易》看来,可以从语言上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有叛乱之心的人,是否是一个内心疑惑的人,或是一个诋毁善人的人,一个人的性格也是可以从语言上看出来的,是善人,还是焦躁之人,都一目了然。然而,《周易》也仅是从理论阐明两者的关系而言,既然言辞“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也就是“称名”与“取类”及“旨”之间有“小”、“大”、“远”的矛盾,“言”与“事”也有“曲中”与“肆隐”的矛盾,那两者的统一,也就是无论在表在里的统一,就很难了,不仅言谈者很难达到表里统一,就听者而言,就更难了。所以《周易》不仅指出了言意一致的问题,更强调了言意不一的问题,所以《周易·系辞上》又明确指出:“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种矛盾性与张力关系正是中国传统文论“言意之辨”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而《易经》作为中国文化初创时期的经典著作深刻地认识到言意关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老庄对此问题讨论得更多,已成为中国文论史上的常识。孟子也继承了这个观点,他在《孟子·公孙丑上》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其内容基本同《易经·系辞下》中孔子的话。至于扬雄《法言·问神》中所说的,更是众所周知:“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则根据言意一致的关系讨论了作家与他们的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体性》篇讲:“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在刘勰看来,每位作家的风格是不同的,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他把不同作家的风格区分为八类:“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并对每一种风格的具体含义作出了分析,并最终指出:“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我们从刘勰对八种风格的描述中就能发现他对这八种风格的取舍是很鲜明的,例如他说“典雅者”是“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儒门是刘勰的根本宗旨,他在《文心雕龙》一开始就讲,要“原道”、“征圣”、“宗经”,所谓“道”、“圣”、“经”都是儒家之“道”、“圣”、“经”,所以他把“典雅者”归结为“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是对“典雅”的一种褒扬与认可。至于他把“新奇者”定义为“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把“轻靡者”定义为“缥缈附俗者也”,都显示他对“新奇者”与“轻靡者”的否定。所以他对八类进行对举以显示其对立的根本特性,就为了彰显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判断。我们在刘勰对具体作家的评论中也可看出这一点。他说“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贾谊英才超群,所以文章高洁而风格清新。我们从《才略》中他对贾谊的评价“若夫屈贾之忠贞……岂曰文士,必其玷欤”就可看出他对贾谊毫无疑问的赞扬了。至于他说“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司马相如狂放不羁,文理都很浮夸,这也是他对司马相如的基本评价。当然,刘勰考虑到作家自身个性与创作的复杂性,并没有绝对地对一个作家进行黑白分明的区分,所谓“志隐而味深”、“趣昭而事博”、“兴高而采烈”等都不是明确的价值判断,但这绝不意味着刘勰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两可的,他的价值标准是很明确的,并不像《文心雕龙今译》中所说的:“陈望道先生讲四组八体彼此相反,没有贬低其中的任何一体,这是对的。刘勰讲四组八体彼此相反,贬低其中的两体,这是不恰当的。因正与奇反,有正即有奇,两者都需要,不应该贬低奇。刘勰把奇说成‘危侧趋诡’就不好了。”当然,文苑中风格的多样性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但文苑不可能是没有主调,这至少是在刘勰看来如此。刘勰为何对这八种风格进行价值判断呢?因为刘勰最终考虑的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美学价值,或者是阅读时的快感,而是作品最终对读者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与对读者的行为所最终产生的影响,所以,他对风格的描述基本上与对作家品格的描述是一致的,贾谊的“俊发”与“文洁而体清”和司马相如的“傲诞”与“理侈而辞溢”都是文品与人品统一的,这与他在《体性》一开始所提出的“因内而符外”,在逻辑上也是一致的。
然而,作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毕竟和作家所处的现实世界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两者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作品的世界不仅是作家所处现实世界的反映,更是作家想象与客观叙述的结果,即使是作家所处现实的反映,也不一定是作家真正行为与真正内心世界的反映。所以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反对那种把小说中所描写的世界与作者世界混为一谈的做法,他说:“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况且“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加缪更举出了叔本华的哲学理念与生活逻辑相反的例证,他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没有一个人把否定生活意义的逻辑推理发展到否定这个生活本身。为了嘲笑这种推理,人们常常举叔本华为例。叔本华在华丽的桌子前歌颂着自杀。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笑的。这种并不看重悲剧的方法并不是那么严重,但用它可以最终判断使用他的人。”至于海德格尔在1933抛弃黑森林的世袭财产,充当新纳粹政权的臭名昭著的宣传者,又何来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呢?由此来看,作家生活的现实世界与他在小说与诗歌中创作的艺术世界或体现的人生与艺术理念是根本不同的两个世界。只有在理论上正确地区分此两种世界的差别,才能真正区分艺术世界中的作家与现实生活中的作家。钱锺书在《文如其人》中,就作家的个人主张和作品之间的矛盾关系讨论了作家的人品与文品相分离的问题。钱文针对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之六“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而发,而元诗又是针对扬雄《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而发,郭绍虞认为元好问的这首诗是“主张真诚,反对伪饰”,他说:“元氏除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分析其正伪清浊之外,特别重视作诗的根本关键。他感慨地指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伪饰。而对陶诗的肯定,恰正是因为它的‘真淳’。正面主张‘心声只要传心’了,出于真诚的才是好诗。元氏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说:‘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居相为一。……夫唯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正是这诗的最好注脚。”由此看来,元诗并不是反对诗歌应该真实地反映诗人的内心情感,而是认为客观地存在很多诗歌并没有真实地反映诗人的真实内心世界,读者应该看到这个问题,不应该被作家虚情假意的伪饰所迷惑,而应该结合作家的作品及他的人格,也就是他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来判断作家的真实人格。既然潘岳为谄媚贾谧竟望其车尘而拜,这样的人还写出了《闲居赋》,明阮大铖为魏忠贤奸党,却在自己的《咏怀堂诗集》里模仿陶渊明的《园居诗》自比清高之人,奸相严嵩在《钤山堂集》中却自称晚节冰霜,所以《庄子·列御寇》中孔子讲:“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钎。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人心比山川还要凶险,他的期望比天还高,而且往往厚貌深情,无法测量,更重要的是人还往往表里不一,外貌憨厚而内心奸诈,外貌柔顺而内心刚直,外貌美善而内心残忍,外貌清高而内心贪婪等等,不一而足,因此读者仅仅靠简单的“言为心声”来判断人,判断作家的人品及人格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像孔子这样综合地深入分析作家的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所以钱锺书说:“‘心声心画’,本为成事之说,实尟先见之明。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也就是钱文所引魏叔子《日录》卷二所谓文章“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日夕揣摩,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语。虽孟子知言,亦不能以文章观人。”由此看来,写文章不仅仅是一种内心世界的直接抒发,还有写的方法与技术,这就是历代八股文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写文章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模仿的,不仅是思想内容,语言风格都是如此,所谓“日夕揣摩”,正如演员的演出一样,它们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相似,而内在却有着根本的差别,所以钱锺书又说:“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譬如子云欲为圣人之言,而节省助词,代换熟字,口吻娇揉,全失孔子‘混混若川’之度。柳子厚《答韦珩》谓子云措辞,颇病‘居滞’。……阮圆海欲作上水清音,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虽然作品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作者的真实品格,但要完全掩盖也是不可能的,其揭示的程度也是作家极力掩盖与读者尽力探究互相博弈的结果。但有时候文中所表达的作者与真实的作者不同,并不仅仅是作者欲掩盖真实的自己,而是要表达自己的愿望,也就是自己所想,甚至是梦想成为的样子。一个是作者的真实人格,一个是作者羡慕梦想成为的理想人格,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作家的真实人格始终和他自己创作的艺术世界所体现的人格相游离。所以钱锺书对这种所谓的言行不符现象说:“文如其人,老生常谈,而亦谈何容易哉!虽然,观文章顾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为及欲人视己为何如人。”“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时遂失初心。不由衷者,岂唯言哉?行亦有之。安知此必真而彼必伪乎?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见于行事者,往往为随众俯仰之我。皆真我也。身心言动,可为平行各面,如明珠含利,随转异色,无所谓此真彼伪;亦可为表里两层,如胡桃泥笋,去壳乃能得肉。……亦见知人则哲之难矣。故遗山、冰叔之论,只道着一半。”这就是指人的内在矛盾性,人格的多重性。钱锺书评嵇康说:“以文观人,自古所难;嵇叔夜之《家戒》,何尝不挫锐和光,直与《绝交》二书,如出两手。”嵇康的《家戒》和《与山巨源绝交书》都是嵇康性格的真实表现,是嵇康真实的不同侧面,没有所谓真假之别。所以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嵇康的这种双重性格说:“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稀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无论怎样,作品总是能从不同的角度给读者提供作者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及个性,这种性格及人格的复杂性直接来自生活与现实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通常所谓的“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自我夸耀和靠修辞革命来自我炒作的手段根本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复杂的现实直接造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复杂的心态。徐复观关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复杂的个性与心态说:“在上述的现实面与理想面的历史条件中,一般知识分子,多实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即是有的为了现实而抛弃理想;亦有的因理想而牺牲现实,或者想改变现实。不过自隋唐科举制度出现后,知识分子集团的由现实下坠,直下坠到只有个人的功名利禄,不复知有人格,不复知有学问,不复知有社会国家的‘人欲的深渊’里去了。……科举遗毒,深中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髓;其最显著的形态是:一不择手段以争取个人升官发财的私利,而毫不顾惜公是公非。口头上可以讲各种学说,但在私人厉害上绝不相信任何学说。”以此,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在两个月前,我收到汉密顿(G.H.Hamilton)老博士为大英百科全书一九六八年版写的熊先生小传时,引起我许多复杂地感想。熊先生在学术界,一直受到胡适派的压力,始终处于冷落寂寞的地位。谁能想到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部,请年届八十五岁高龄的汉密顿博士,为熊先生写此小传,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是‘佛学、儒家与西方三方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是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由此可以了解西方人的学术良心,实远非中国西化派所能模拟于万一。”所以他又说:“我国知识分子,抑压于专制政治之下,非旷代大儒,即不能完成人格精神之独立自主;而政治主动性之被完全剥夺,更无论矣。才智之士,依附于一二悍鸷阴滑之夫,以成其所谓功名事业,则饰其所主者曰‘圣君’,而自饰曰‘贤相’;圣君贤相,乃中国历史中最理想之政治格局,固不知此种格局之背后,实际藏有无限之悲剧。中山先生年少上述李鸿章,其内容姑不论,要其时之精神尚未脱离传统之政治羁绊,则彰彰甚明。……中国知识分子,必先有此一精神解放,乃足以进而正视中国之问题,担负国家之使命。”徐复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专制体制直接造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的畸形化,顺势者飞黄腾达,逆势者则处江湖之远,还有如屈原、司马迁、刘勰等甚或自杀、甚或出家、甚或忍辱负重以待来世。即使如勇斗智斗者鲁迅,也逃不过此种命运,所以他三次被通缉,晚年还被国民党特务列入严厉制裁的黑名单。至于他的译、著作品被反复禁、删更是常事。鲁迅生前发生过无数次的文坛之争,以至于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收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然而一直到鲁迅去世半个多世纪,这样的书都没有成功问世。特别是郭沫若以笔名杜荃等发表的攻击鲁迅的文章更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大景观,正如孙郁所说的:“在攻击鲁迅的文章里,郭沫若是最锋芒毕露的。他在这一年《创造月刊》二卷一期上,以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篇文风极不友好、笔触相当刻薄的文章,对鲁迅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且试图以此宣判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死刑’。……郭沫若以诗人的浪漫情绪代替了政治意识,他对鲁迅的著作所看甚少,仅凭一点印象,就信口开河,这完全是一种非科学的武断的批评态度。在政治生活中,支撑郭沫若的有时是某些非理性的情绪和直觉,他的缺少理性的直率之作,客观地说,对后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鲁迅是由于现实的斗争教育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及现实,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品格的深刻认识,所以他应《京报副刊》的征求讨论“青年必读书”时直接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认为儒家,至少是当时很多主张儒家学说的人有很多是虚假的主张,所以便劝人不读中国书,但难道儒家书中就没有可取之处了吗?这是鲁迅极而言之,是气话,但这种气话在现实的生活中也许比仅仅从纯粹的理论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更有合理性,这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之中的思想者得出的结论。正如罗宗强指出的:“我国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是历代治国的思想主流。我国古代士人出仕入仕,与政局有千丝万缕之联系,一部分士人既是文学作品的作者,又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官员,定儒学于一尊之后,宗经致用的思想为他们之所共同遵从,工具论的文学观为他们所接受,并且成为公开场合论文时之主流话语,这是很自然的事。”传统知识分子极力追求权力就在于他们欲把自己的知识与权力密切结合以彻底控制社会,知识分子在文章中所极力美化的人品与文品合一的观念就直接来自中国传统的知识与权力密切结合的传统。正如罗宗强所说:“大多数文体的产生,皆出于功利之目的。刘勰论及81种文体之产生,多归结为实用。文之工具性质,在汉代定儒术于一尊之后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与圣人崇拜、内圣外王的观念的建立有关。与此一种观念之联结,促使文与政教形成更为紧密的关系。黄侃就曾说过:‘夫六艺所载,政教学艺耳。文章之用,降之于能载政教学艺而止。’文的政教之用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它与内圣外王的观念是不可分的。”当然内圣外王的思想也并不是一开始就统治中国政坛与文坛的,自从孟子之后,圣人就被儒家所占有。罗宗强说:“圣人专指儒家,从孟子始。孟子才提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的圣人统系,这是特指一个行仁政、施仁义的圣人系统。他甚至把伯夷、伊尹、柳下惠也列入圣者的系列,因为他们的道德品格、他们的行为属于‘仁’。到了荀子,就把圣与王联系在一起了:‘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到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的《白虎通德论》,圣人与经书、与治道便成了三位一体,崇圣宗经、内圣外王,成了后来文的工具角色的思想观念的源头。”而这也是《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但在我国文化的早期百家争鸣的时期,儒家还必须经过艰苦的辩论与斗争来争夺地盘,为自身绝对的合法性寻找论据,那时关于人的道德理想的圣人还不仅仅为儒家所专有,老子、庄子的圣人就不可能是儒家,因为他们的争论从未断绝过,看看《庄子·盗跖》篇对孔子的讽刺与打击就可明白了,虽然很多理论家把老子当作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一个阴谋家,因为老子《道德经》三十六章中讲:“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其大意是:要收敛的必先扩张,要衰弱的必先强盛,要废弃的必先兴旺,要夺回的必先给出。不仅是按照道家的哲理,即使是按照常理也是这样:不先扩张又怎么收敛呢?不先强盛又怎么衰弱呢?不先兴旺又怎么废弃呢?不先给予又怎么夺回?看似高深不测的哲理又怎么会遭到古人及今人反复的误读呢?正如陈鼓应所说的:“本章第一段乃是老子对于事态发展的一个分析,亦即是老子‘物极必反’,‘势强必弱’观念的一种说明。不幸这段文字普遍被误解为含有阴谋的意思,而韩非是造成曲解的第一个大罪人,后来的注释家也很少能把这段讲解得清楚。然前人如董思靖、范应元、释德清等对于这段话都曾有精确的解说,下面引录董思靖与释德清的解说以供参考。董思靖说:‘夫张极必歙,兴甚必夺,理之必然。所谓“必固”云者,犹言物之将歙,必是本来已张,然后歙者随之。此消息盈虚相因之理也。其机虽甚微隐而理实明者。’(《道德真经集解》)释德清说:‘此言物势之自然,而人不能察,天下之物,势极则反。譬夫日之将昃,必盛赫;月之将缺,比极盈;灯之将灭,必炽明。斯皆物势之自然也。故固张者,翕之象也;固强者,弱之萌也;固兴者,废之机也;固兴者,夺之兆也。天时人事,物理自然。第人所遇而不测识,故曰微明。’(《老子道德经解》)”他们两者都直接从老庄的思想来解释老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并没有解释清楚“欲”是什么意义?“欲”是谁的“欲”,是道的“欲”,是自然界的“欲”,是作者老子的“欲”,还是人的“欲”?而人的“欲”在读者解读时可以随时解读为自己的“欲”。无论“欲”是解释为“欲望”、“爱好”、“想要”、“应该”,还是“将要”都无法回避“欲”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如果主体是人,那“阴谋”的意味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自然”与“道”,那万事万物自我兴衰的过程就呈现出来了。当然,自然虽然没有阴谋诡计,但人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最终还是要法自然,自然的兴衰,人不仅可以自己利用,也可用来征服对手,何况人类的竞争历来就如同自然界的竞争一样无法摆脱,就《老子》的接受与效用来看,被阴谋家所偏爱也是他自身的特点所造成的。所以刘笑敢在《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说:“朱熹也说:‘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支吾不知,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学。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合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这都是以历史上的政治和军事谋略来解释老子以反求正的思想,这种解释自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很容易把人误导到阴谋诡计的歧路上去。对老子思想的这种解释一方面忽略了老子讲以反求正的历史环境,另一方面也把以反求正的一般性方法局限到了政治军事争斗之中,把丰富生动的老子哲学引入了狭窄的政治、军事阴谋之途。以反求正的辩证方法与阴谋诡计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说,以反求正的方法有可能成为阴谋诡计的工具或被理解运用成狡诈的阴谋,但老子的以反求正的思想本身决不是阴谋诡计,而只是根据客观事物辩证运动总结出来的一般性方法。这种方法好像是为弱者设计的,实际上可能对强者更有意义,这就是‘知其雄,守其雌’的道理。老子哲学有可能被利用成阴谋诡计,老子要不要对此负责呢?一般说来,我们是不应该为此而责备老子的。正如科学家可以发明原子能并用来发电,战争狂人却可以用原子能来制造大规模毁灭性的杀人武器;发明刀子可以用来做饭做手术,歹徒则可以用刀子做谋杀的凶器。我们怎能因此而责备发明家呢?”可见,刘笑敢把老子表达的哲理当作一种中性的知识,对正反双方都可使用,正如智慧都可被坏人与好人同样使用一样。但如果他们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如何被使用呢?阴谋家与军事家是否可以用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的理论来谋一己之私呢?正像孔孟之道也被经常当作工具来使一样。哪个人,特别是阴谋家,不宣称自己的动机是高尚的呢?所以韩非对老子的解读虽然与众不同,遭到了道家学派的不满,但司马迁在《史记》中还是把老子与韩非放在一起,称为《韩非老子列传》,并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可见司马迁是看到了韩非与老子的内在一致性的,虽然老子在司马迁看来也是“隐君子也”,可见老子也有他内在的不一致性。所以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区分老庄之别时说:“故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鲁迅也同样看到了老子内在的矛盾性,也就是老子在贯穿自己的道的哲学时,在自然的道与人间的道之间所无法统一的矛盾性。总之,老子的哲学也常常为那些追求外圣内王的人提供理论根据的,但庄子却是坚决反对所谓内圣外王的,我们在《庄子·列御寇》中对权势的挖苦与痛斥就可看出。庄子讲宋人曹商为王出使秦国,开始只有几辆车,后来得到秦王的喜欢便获得了百辆车。因此便到庄子那里来炫耀自己的成功。他说:“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处在穷街陋巷靠织鞋为生,面黄肌瘦,忍饥挨饿,苦不堪言,自己不如庄子,但能得到君王的欢喜,有百辆之重的随从车马,这也是庄子所不及的。其对庄子清高自居,坚忍不出的高洁的蔑视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庄子却并不以为然,他说:“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秦王有病请医生,破除脓疮的得车一乘,舔治痔疮的得车五乘,谁治的病低下,谁得的车就多,你大概是添治痔疮的吧,不然怎么会得到这么多的车呢?古今中外对权势之批评,无有比此更为激烈的。由此可见,庄子之圣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内圣外王之人。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据我心中的
道德法则。”然而康德并没指出所谓艺术家所苦心经营的艺术世界给我产生这样一种崇高的美感。无论艺术家创造了怎样的艺术世界,他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艺术不仅仅能带来直接的审美快感,它最后还必然导向人的行为世界。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的:“真正的崇高必须只在判断者的内心中,而不是在自然客体中去寻求,对后者的评判是引起判断者的这种情调。谁会愿意把这些不成形的、乱七八糟堆在一起的山峦和它们那些冰峰,或是那阴森汹涌的大海等等称之为崇高的呢?但人心感到在他自己的评判中被提高了。”崇高的真正根源还是在观赏者自身的道德感之中,所以无数的人在看到高山大海时并没有什么崇高之感。所以康德后来又强调:“所以崇高不在任何自然物中,而只是包含在我们内心里,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对我们心中的自然、并因此也对我们之外的自然(只要它影响到我们)处于优势的话。这样一来,一切在我们心中激起这种情感——为此就需要那召唤着我们种种能力的自然强力——的东西,都称之为(尽管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崇高。”根本意义上的崇高乃是自然与人类伟大的道德行为。正如卡莱尔在《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中所说的:“在我看来,真诚是伟人和他的一切言行的根基。如果不以真诚作为首要条件,不是我所说的真诚的人,就不会有米拉波、拿破仑、彭斯和克伦威尔,就没有能够有所成就的人。应该说,真诚,即一种深沉的、崇高的而纯粹的真诚,是各种不同英雄人物的首要特征。……我希望大家把这作为我关于伟人的首要定义。”这与《易经》中孔子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进德修业中外都是一致的。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孔子、庄子,哪一个不是进德修业、言行如一的人呢?只不过区别在进谁的德,修谁的业,忠信于谁罢了。那些仅仅依靠所谓智慧为一己之私尽力打造的虚假艺术与虚幻人生又能在世人持久的注目与反复审视中坚持多少呢,而这也正是刘勰《程器》篇所讨论的根本出发点与最终归宿。
邹广胜,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