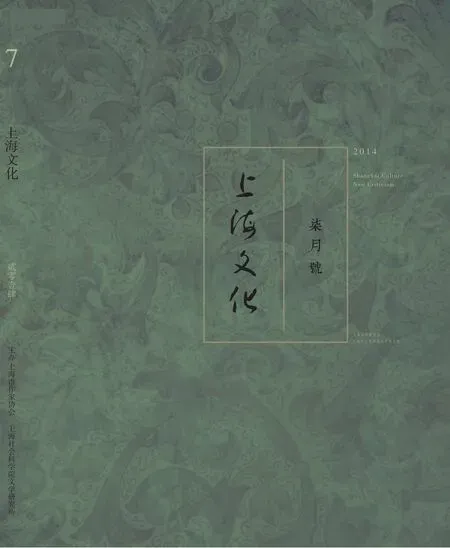《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四)
2014-11-14张文江
张文江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四)
张文江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从司马谈跳回到司马迁,此处发生的转换,在章法上就是所谓交脱,交脱有衔接、继承的意思。太史公不参与管理百姓,政治地位并不高。掌天官是天文,却依然关乎人间,所谓“天人之际”。治史和治民有其思想上的联系,此即《论六家要旨》所谓的“务为治”。
“有子曰迁”,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有子”用《易经》蛊卦初爻爻辞:“有子,考无咎。”孩子有出息有能力,可以弥补父亲的过失。中国人几乎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后代争气,将来出人头地,就是所谓的“有子”。司马迁写下这句话非常自豪,言下之意为我是对得起父亲的。道家往往从无的一方面考虑,儒家往往从有的一方面考虑。实际上自己的孩子有发展前途,对父母的精神是莫大的安慰。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司马迁出生于龙门,龙门即龙门山,在陕西韩城县东北三十公里,以后司马迁的祠堂和墓地也在此地。我读到这里,感到很好奇,民间传说“鲤鱼跳龙门”是不是和此处有关联。查考古代地名,有两个龙门。其中一个在河南洛阳伊河的两岸,一边是西山,就是龙门石窟;一边是东山,就是白居易晚年居住的香山。另外一个在陕西的韩城县,两山壁立,河出其中,相传为大禹治水所凿。《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六引《三秦记》曰:“每暮春之际,大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者化为龙。”又引林登曰:“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刘庆柱辑注《三秦记、关中记》,三秦出版社,2006,95页)可见“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出于后者,确实来自司马迁的家乡。
“耕牧河山之阳”,河就是黄河,山就是龙门山。山南水北为阳,也就是说在龙门山之南,黄河之北。“耕牧”,家中从事农牧业。“年十岁则诵古文”,古文是六国传下来的文字。过去常常看到一句话“耕读传家”,中国两千年最基础的生产力是耕,扩大而言是耕牧,最先进的思想是读,了解传统的圣贤言行。这是古人抓住的两个最要紧的纲,在中国维持了两千年。近代五四运动为什么发生“打倒孔家店”,原因之一在于耕已经不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了,于是跟生产力相应的读也起了变化。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跟今天有所相似,也是在变化之际。当时有今古文的变化,好比现在的文言文变成白话文。古文变成今文,为什么国家还可以稳定呢,是因为那套读的文献基本保存了下来。而文言文变成白话文,原来的那套经典系统完全拆散了,至今还没有自然而然地形成新的系统。
在军事上汉和匈奴是大敌,要是打仗一对一,匈奴对汉肯定是胜多负少。匈奴军事上虽然彪悍,但是没有获得耕读力量的支持,长期博弈下来,最终还是走向消亡。所以单单骁勇善战还不行,必须要有持久的生产力和文化凝聚力。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主要就是从西方吸收新思想,然而吸收到了某个阶段,还要反过来研究中国文化形成期发生的事情。研究这些事情干什么呢,就是认识你自己。中华民族要成为政治成熟的现代民族,就必须形成民族的自我认识,这就脱离不了研究乃至反思古代经典。而理解中华学术的原创性和革命性,非走到先秦时代不可。中华民族形成期的胎教,不是那些凝固的文字,而是经典中活生生的内容。只有这样,你才能认识西方文化的源流演变,才能吸收真正好的东西,重新焕发出民族的生命力。
“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司马迁年少颖悟,读书十年,把古典文献基本了解了。我们现在从小学读到研究生,时间远远超过十年,然而只是知道某个专科大体应该读些什么书。至于了解整个社会应该读些什么书,还没有自然而然形成的系统,所以获得学历并不能等同于成才。当时的聪明人通读古典文献,甚至不需要十年,传说像东方朔就是“三冬,文史足用”(《汉书·东方朔传》)。李白少年时也是大约读书十年,就了解了一生的基本知识。“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
文言文变成白话文,原来的那套经典系统完全拆散了,至今还没有自然而然地形成新的系统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这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亲身经历中国的广大疆域。他最初从西北到东南,南游长江、淮河流域。然后去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体验了中国文化的主干。
“上会稽”,就是绍兴。“探禹穴”,应该指会稽山的山洞。“窥九疑”,九嶷山在湖南,《五帝本纪》谓舜南巡崩,葬于此。“浮于沅、湘”,沅水、湘江,也是在湖南一带。从长江的中游再往北走,到了黄河的下游。“北涉汶、泗”,两条河都在山东。“讲业齐、鲁之都”,在人文荟萃之地,跟儒者讨论学问。“观孔子之遗风”,到了曲阜,感受孔子家乡的风俗。“乡射邹、峄”,乡射是古代的礼节,又邹为孟子的出生地。“戹困鄱、薛、彭城”,这是山东、江苏一带。以戹困为言,相应于孔子厄陈蔡,司马迁大约在那里受了些挫折。彭城在今江苏徐州,项羽曾定都于此。“过梁、楚以归”,梁就是河南开封,魏的都城。然后再到楚,楚为长江流域。
壮游了大半个中国,然后官职也升了一级,郎中是皇帝的侍从官。“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皇帝派他出使,沿长江往源头方向上走,到了四川(重庆、成都)、西康、云南一带。“还报命”,完成后回来交代任务,不辱使命。
青年时代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剩下来没有走到的地方,入仕以后又补充了一些。脚踩各地不同的地气,好比孔子周游列国,兜了一个大圈子。到鲁国讲业的经历,可以参考《孔子世家·赞》:“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心驰神往,衷心赞叹,融合了当时留下的直观印象。
这是司马迁一段春风得意的时期。人生应该有这样一段青年时期,意气风发,享受生命的美好。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转折,他在历史上也可能是留不下来的。但是如果生下来就是受苦,那也太悲惨了。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这时候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生命轨迹就此转折。
“始建汉家之封”是汉武帝封禅泰山,下诏改元,那一年是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封是封泰山,祭告天,禅是禅梁父,祭告地。梁父是泰山旁边的一座小山。封禅大典向天地祭告自己的丰功伟业,是非常隆重的宗教仪式。中国的封禅仪式来自原始宗教,由山顶洞人那些祭祀逐步变化而来,一直到宋代都有封禅。《封禅书》引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追溯极其之远,直达于上古。“太史公留滞周南”,因为太史公职掌天官,封天禅地正好跟他的职务有关。不让他参加,强烈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司马迁后来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诗经》中“周南”是十五国风之首,在这里指洛阳。于是“发愤且卒”,身体一下子不行了,很快到了临终时刻。
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
司马迁正好从四川一带回来,和父亲在河洛之间相见。其实会面地点就在洛阳,司马迁称“河洛之间”,气象非常开阔。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重复讲列祖列宗的功德,试图从时间中获取能量。“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就是重黎后面的羲和。颛顼时的重黎有神话成分,虞夏时的羲和基本上靠得住。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巫史传统一代代衰落下来,难道到我这里就消灭了吗?你一定要接续祖宗的功业。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接千岁之统”,千岁差不多要推到虞夏。虞夏之后再来一次这样隆重的封禅大事,我不能跟随前往,真是命啊,真是命啊,不能怪我不努力。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你子承父业当了太史,不要忘记我心心念念想写的东西。论就是排列、研究,著就是著作。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孝有三个境界。初等的境界,奉养父母;中等的境界,把对于家的感情推广到国;高等的境界,使自己有所成就,扬名于后世。这是最大的孝,那父母真会高兴。“终于立身”只有三条路,立德、立功、立言。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扬名于后世”,时间最厉害,对所有的人都公平,无论你自以为如何了不起,一点都不容情。你造纪念馆也好,印多少书也好,怎样炒作也好,时间就是使你留不下来。经历淘汰而留下来的人,一定有其不可磨灭的道理。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把父母烘托出来,这才是最大的孝。所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是命宫的保存,“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性宫的保存。
一本真正跨越时代的伟大的书,往往一个人完不成。像《史记》,就是两个人完成的。像《红楼梦》,也是一个人完不成。《史记》这本书特别了不起,还因为它综合了儒道两家变化时期的思想,所以说这本书划出了时代。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史记》这本书特别了不起,还因为它综合了儒道两家变化时期的思想,所以说这本书划出了时代
这里提出了周公,叙述的是《诗经》。“论歌文武之德”,就是《雅》《颂》。“宣周邵之风”,就是《周南》、《召(邵)南》,所谓正风,为十五国风之首。十五国风结束于《豳风》,描述祖先怎样艰苦开创事业:“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太王、王季是文王的父亲和祖父。公刘是后稷的曾孙,开始居于豳,也就是陕西的旬邑县。太王受到狄戎的逼迫迁居岐山,也就是陕西的岐山县。最后追溯到源头,后稷是尧舜时的农官,周最早的祖先,被认为开始种稷(谷子)和麦的人。《尚书·舜典》:“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
孔孟的提法是宋代才固定的,以前主要提的是周孔。周孔是完整的王家文化序列,孔孟是王家文化到民间文化的系列
幽王和厉王之后,是东西周之交。前面提出西周周公,这里提出东周孔子,两个人是儒家经典序列的完整表述。我觉得,也可以把孔孟两个人拆开来理解,孔孟的提法是宋代才固定的,以前主要提的是周孔。周孔是完整的王家文化序列,孔孟是王家文化到民间文化的系列。孟子本人还是非常好,但是毕竟越来越弱。
所以我说有两种不同的精英。孟子的精英在于贤,孟母三迁,要有好邻居,读的是贵族学校。孔子的精英在于圣,“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他在生活中高级和低级的事情都做过,在底层的环境中一点点磨砺自己,最后集大成。孔子的弟子像颜回、子路、子贡,个性都很鲜明。孟子的学生公孙丑和万章把老师的讲话抄下来,但是自己没有特殊的东西。
六经之类的王家文献在东周,主流意识形态也已经不珍惜了。这些老掉牙的竹帛,放在那边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一般人或许会选择丢弃。孔子把这些东西救出来整理好,保存了古代思想的血脉,对中国文化起了大作用。每一代人总会扔掉些旧的东西,如果选择其中真正好的保存下来,一旦和新的东西结合,那就比新的东西还要新。
“修旧起废”,可以参照下文“补弊起废”,保存不同的物种或者文化。现代人用技术培育良种,然后推广到全国,有一定的危险。一旦这个品种衰退,或者出现某种病虫害,就可能缺乏抵抗力,产生大面积的危害。文化上教材统一,思想统一,如果杜绝竞争,以人工推广统一,就会有极大的问题。
幽厉之后,周道衰了,政治上平王东迁,没有开出来新的气象。但是文化上孔子起了大作用,在西周衰退的时候拚命努力。如果一直是西周的政治,那也就是没有孔子。正因为西周衰退下来,就给了孔子显现的机会。
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论《诗》《书》”,论是排列、研究、整理,《论语》所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孔子真正花工夫是在《春秋》,对历史有自己独特的心得,所以称为“作”。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离娄下》)。又引述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滕文公下》)。谁要理解我,懂我这个时代,一定要理解《春秋》。谁要批评我,也要理解《春秋》。为什么呢?《春秋》应该成于王家人士之手,不应该成于民间人士之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孔子以后四百多年了,诸侯互相兼并,史书记载流失的流失,消灭的消灭。从这里的“史记”可以看出来,指的不是司马迁写的这本书,而是指史官保存下来的记载。“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这里司马迁跳跃了两步,其实要套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的话,就宣称四百余岁,实际上是三百七十一年,打了相当的折扣。他不好意思说五百岁,就讲四百多岁,稍微有些夸张。
“获麟”是《春秋》的结束(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麟是瑞兽,据说出来的时候天下太平,当时捕捉到了麟,对孔子产生了大刺激,那就是所谓的“绝笔获麟”。不写了看似消极,实际上是孔子相应于更深的地方,找了一个借口来停笔。孔子明白《春秋》再写也写不完,他不再看某一个局部好或坏,而是看整体的自然变化。自然界永远有新生的东西,孔子看大化无形,正是他的积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时代无情,不停地淘汰,时代淘汰别人,还要淘汰你。你把前人推出了局,而把你推出局的人,此刻正站在你的身后。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就是司马迁的使命感。他在前面提到了孝,父亲给了他一个任务,做出自己独特的成就才是孝。独特成就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两个最高的榜样,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孔子。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迁一边低着头一边哭,接受父亲临终前的最后嘱托。“小子不敏”,我虽然很笨,“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你编辑的那些过去的记载,我会完全整理好的,不敢有所遗漏。司马迁答应完成先人的遗愿,为此奋斗了一生。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司马谈死去三年之后,司马迁子承父业,担任了太史令,这一年是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紬就是缀集,把竹简编撰好,读书理出头绪。“石室金匮”是皇家藏书的地方,把皇家的材料整理起来。
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又过了五年,是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这里有一次大的改历,过去沿用的是秦历,这时候才开始用汉历。汉代改了历法,旧的统就完全换掉了。太初改历定岁首为建寅,就是我们现在的春节,形成了汉民族的风俗。“建于明堂”,在明堂颁赐新历于诸侯,天下更始。《礼记·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为群神之主,“诸神受纪”,意味着诸侯都接受了。以后历法多次改动,但是以建寅为岁首不再改动,相比秦历用建亥,相差有四个月。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自然界永远有新生的东西,孔子看大化无形,正是他的积极
所谓“绍明世”,就是能继往开来,对得起伟大的时代,使时代发出光芒
这里用的是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真正的王者必须整理文化。按照我的理解,六经可以有两个层次,《易传》和《春秋》是一个层次,《诗》《书》《礼》《乐》是一个层次。《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世家》记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以《诗》《书》《礼》《乐》教”,《易传》和《春秋》可能属于更深入的课程。所谓“绍明世”,就是能继往开来,对得起伟大的时代,使时代发出光芒。在孔子卒后五百年,这个人整理前代的典籍,在时间中显出不朽的东西。孔子编订六经,怎样把六经用到时代中去,和时代相结合,就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心思就在这里啊,心思就在这里啊。“小子何敢让焉”,这是谦虚的讲法,意思是我当仁不让。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重言咏叹,就是司马迁的使命感,把父亲的志向变成了自己的志向。“先人”应当指父亲,也暗含接通重黎以来所有先辈的血脉。五百年不是确切数字,是借助它所包含的力量,然后得到血缘和非血缘两路文化的支持,当仁不让,陈述出他本人的判教。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