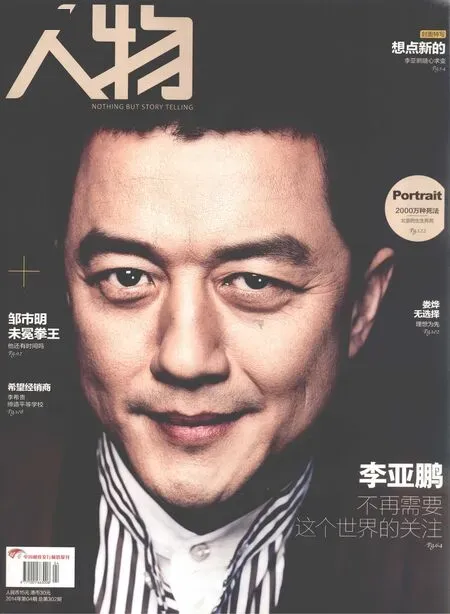唐荣尧:宁愿不拍,也别太近
2014-11-07艾江涛
文|艾江涛
唐荣尧:宁愿不拍,也别太近
文|艾江涛
一位同行站在水洞口的一处土堆上拍完一段古长城后,一脚把那个地方踩掉了,别人再也拍不上了。“这叫什么?这叫自私,我宁愿拍不出片子,也不愿这样去拍”。
2006年10月,唐荣尧再次来到云南泸沽湖一带,第一次在这里拍到摩梭人古老的木头房屋时的那种震撼引诱着他。“这里即使是最穷的家庭,建筑都特别宏大。我就想普通人家房子盖这么大干吗呢?泸沽湖的建筑给我第一眼的感觉,真的像皇家建筑。”
作为一个常年拍古建筑的摄影师,他对取景框中这些古老建筑的形态极为敏感:这里的房子都为木结构,一般是二层楼甚至三层楼,建筑过程中不用铁钉或胶之类的东西,木头与木头之间完全依赖榫相接,非常大气,“根本没有一丝平民色彩”。唐荣尧之前在东北大兴安岭一带考察过俄罗斯人用圆木头垒起来的木刻楞,中间也有接的地方,但不是很严谨。
“榫这样的建筑结构,是老祖先流传下来特别棒的一个东西,好多东西在现在看来都是反力学的。”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古建筑,是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的应县木塔,当梁思成在1933年夏天第一次见到这座我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时,“半天喘不过一口气来”。
经过研究,唐荣尧认定这些建筑正是当年流亡的西夏后裔(其中不乏王公贵族)所建,绵延至今。
除了摄影家,唐荣尧还有记者、诗人、学者、行者一堆头衔。十几年时间,近20个省份,十几万公里行程,5本专著,将他与西夏这个业已消亡800多年的王朝紧紧联系在一起。某种意义上,对古建筑的拍摄与记录,始终伴随着唐荣尧的西夏探求之旅。逶迤荒凉西部的这些神秘古建,几乎是消失在历史上的党项人唯一能证明其湮灭轨迹的历史证据,凝结其上的智慧与勇气更让他震撼。
在四川大金河与小金河交汇处神秘峡谷的两侧山岭上,矗立着一座座高达数丈的石碉楼,对这些“东方建筑史上的奇迹”,早在20世纪初就有史学家认为是当年西夏后裔撤离宁夏平原南逃时所留。
2005年11月末、2006年5月初,唐荣尧两次深入丹巴“美人谷”,拍摄、研究这些碉楼。丹巴的这些古碉,多高达二十多米,有的高达三四十米,全部用一块块石头砌成,平整规则,有四角、六角、八角,乃至十二角、十三角。唐荣尧将从冬坡格绒家一座古碉上取下的一截木头寄往美国实验室进行碳14鉴定,结果证明这段木头为将近800年前的东西,时间恰在西夏灭亡前后。历经地震泥石流,这些古碉楼依然安然无恙。在四川桃坪羌寨,这类碉楼还有人居住,“迷宫”般的结构和便利的暗沟水道令人称奇。碉楼多建筑在山顶,“瞭望敌情、军事防御”的建筑目的不言而喻。唐荣尧的实际调研有力佐证了当年史学家的观点。
令唐荣尧称奇的是,这些羌寨古碉在建筑时一不放线,二不用脚手架,全部用反手墙,却将如此多角的外墙面砌得光洁平整。古碉内部结构则按八卦方位布局,“走进去会迷路”,唐荣尧指指眉角,曾在古堡中狠狠摔过一跤,“血流满面,差点毁容”。
唐荣尧还在康定发现全部倾斜的古碉,“现在从力学角度无法解释”,“党项人是极其聪明的民族,不要以为他们只会打仗”。
唐荣尧是木匠的儿子,家里除了父亲,两个叔叔也都是木匠,哥哥就读于有“中国建筑学黄埔军校”之称的长春建筑专科学校。父亲雕刻过许多工艺品,包括木制的自行车。“家里小到柜子、炕桌、门箱,大到自己的房子,父亲没让别人占过便宜,很多活全是自己做的。” 初中一放学,哥仨就去拉大锯,将圆木分解成一块块木板,用那些木板做成的家具,现在仍完好地保存在老家。
最早接触到摄影,还是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唐荣尧从哥哥订阅的《辽宁青年》上翻到一则相机广告,只要8元钱。喜欢折腾的哥哥很快买了一部,自己弄相纸、显影纸、定影粉,很快就可以帮毕业班的同学拍毕业照了。唐荣尧跟在旁边,边看边学,有时也想玩一下,很快被哥哥喝止,那时候的胶卷很宝贵,一卷126胶卷,最高的水平也只能拍326张照片。
十几年前开始走西夏之路时,唐荣尧随身带着一部1000多元的胶片相机,直到2004年,他才换了一个3000多元的数码相机。“相机是个无底洞,好相机永远是小三,看得见,摸不着,总是别人的。”
没专业学过摄影,唐荣尧自称是中国最笨的摄影者,只靠着对光影的敏感,去记录征途中宝贵的资料。有时候,拍摄古建筑意味着一种缘分。除了风沙岁月的缓慢侵蚀,天灾人祸往往对古建筑带来快速伤害。唐荣尧曾拍摄过玉树州结古镇附近的禅古寺,这座拥有近800年历史的古寺,在2010年玉树地震后损毁,“再去的话就拍不了了”。
2013年,唐荣尧参加了雪花纯生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第一次知道古建筑还能这么拍,“每天晚上都有讲座,清华大学研究古建筑的教授,还有摄影学院的专家,从建筑学角度,从摄影的角度给我们讲,以前我们拍,一下拍到了,现在可能就是通过一个屋檐的角,通过一个僧人的视角,怎么看蓝天白云。”
一路行走,一路拍摄,古老建筑与其背后蕴含的精神,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唐荣尧。
2008年9月底,唐荣尧来到觉扎山,这里是藏传佛教康区36座神山之首。道路艰险,“一边是汹涌的澜沧江水,一边是刀削斧砍般的悬崖,中间就这么一点点路,前边来个车怎么办?司机开得哪是车,简直像骑马一样。”一路上,同行的两位女记者都快把唐荣尧的胳膊掐烂了。
转过山脊,澜沧江边觉扎寺八层楼高的藏经阁,如同天降,即使从最近的地方拉建筑材料,也要“翻过2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
深山险谷中忽然出现一座八层楼高的藏经阁,是什么感觉?历代高僧大德写就的经卷就藏在楼上,钥匙由4个活佛共同掌管,必须由4人共同开启。大堪布(给活佛上课的经师)一辈子就在山里修行。一路行走,唐荣尧内心深处的底片仿佛忽然得到“感光”,他一瞬间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皈依。他接受上师灌顶,得到一个“达玛西然”的法名,意即“通晓智慧的王”。此后,他在这里待了两个月,白天给周围的孩子上课和拍照,晚上抽时间去附近的觉扎寺修行,或者写作《西夏史》。
拍摄也罢,探究也好,都是皈依于自己的心灵。唐荣尧认识一个摄影师,“为了拍佛家建筑,自己皈依了,然后把天台山的建筑全部拍下来了。”
玉树州佛学院的建筑,在唐荣尧看来也很传奇。佛学院的建筑历史并不太久,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是一座麻风病院,后来一位英国的活佛出了几十万元,在其基础上捐建了一座经堂。在玉树地震中,“玉树州州府内所有的钢筋建筑物都毁了,就这个佛学院内的建筑安然无恙,包括那些看起来破败不堪的平房。非常不可思议,地震发生后,州政府机关包括抗震指挥所就搬到了佛学院内,2012年夏天,我去玉树时,看到那些机关还在佛学院内!”
建筑学家楼庆西在《古代建筑二十讲》中即提到古建筑“墙倒屋不倒”的特殊建造,“这就是古建筑这种力量,不是说我们现在站在迷信角度去说。”
“翻开中国的古建筑历史,能保留下来的,多数都是宗教建筑,因为它是用心去构造的,而不是作为一种简单的需要。”唐荣尧走得越多,拍得越多,心中的触动越多,敬畏也越多。
1932年,林徽因在《平郊建筑杂录》一文中提出“建筑意”的概念,以说明建筑在诗意、画意之外传达给人那种直接、明锐的感受。
在诗人的眼光里,建筑还应包括动物的建筑。法国导演雅克.贝汉所拍反映鸟类迁徙的《迁徙的鸟》,“是人类历史上最棒的一部纪录片”。写作《青海之书》时,唐荣尧注意到每年翻越高山,到青海湖繁衍的黑颈鹤,在短短几个月里,这些鸟要垒窝、找配偶、孵蛋、训练雏鸟,它们的巢穴也是建筑,但“我是永远给不了照片的,也希望大家以后别拍,一拍就打扰它了”。一次唐荣尧去内蒙古鄂托克旗的阿尔寨石窟拍摄,无意中在洞窟东侧的一处山坡上,看到雏鹰在母鹰搭建的草窝里安详地静卧,在草原、蓝天、草窝合构的立体画卷里,一只雏鹰享受着暖阳。“我努力阻止自己拍照,它们要的不是通过我的镜头展示,而是安静。”
古建筑亦然,固然“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还不够近”,可它们往往经不起这种靠近。有一次,一位同行站在水洞口的一处土堆上拍完一段古长城后,一脚把那个地方踩掉了,别人再也拍不上了。
“这叫什么?这叫自私,我宁愿拍不出片子,也不愿这样去拍”,唐荣尧一脸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