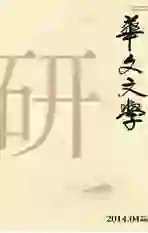“诗言志”变:抒情的发明
2014-11-05杜晓杰
杜晓杰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范畴研究一直占据主导,命题研究相对处于弱势。但是作为对文学进行整体评判和规约的文论命题,对于把握古代文论的整体特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诗言志”这一中国古代文论“开山的纲领”的研究方面,朱自清以扎实的考据功夫,在《诗言志辨》中还原了其“志”“道”合一、“都关政教”的历史语境;身处海外的王文生,同样以扎实的文献梳理为基础,在《诗言志释》中却还原了“诗言志”作为中国抒情传统重要源头的诗学内涵。二者同途而殊归,反映了不同的学术语境对于同一命题的不同发覆,也反映了海外学人在建构中国抒情传统过程中的为抒情而抒情、整一性的“东方想象”等问题。
关键词:“诗言志”;朱自清;王文生;抒情传统;东方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4-0054-07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范畴研究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源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一批奠基人的身先士卒,如郭绍虞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小说月报》1928年十九卷第一期)、《神韵与格调》(《燕京学报》1937年第二十二期),朱东润撰写的《古文四象论述评》(收入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印行之《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则源自于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传统文化热潮而出现的对于范畴研究的大力倡导。在研究成果方面,不仅有以蒋述卓的《说“飞动”》和《说“文气”》等为代表的对中国传统文论范畴进行挖掘、阐发的论文,还出现了以袁济喜的《“和”》和赵沛霖的《兴的源起》为代表的专门探讨某一文论范畴的专著。
与文论范畴研究的如火如荼相比,对古代文论话语表述另一种组成形式——命题的研究,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言志”和“诗缘情而绮靡”等,则显得相当寥落。在这种情势下,一些专门探讨文论命题的文章和著作就显得尤为意义宝贵,并能给我们带来不小的启发,比如朱自清出版于1947年的《诗言志辨》和王文生出版于2012年的《诗言志释》。前者是第一部针对“诗言志”这一中国文学批评的基础性命题进行梳理的专著,后者则是在海外汉学建构的中国抒情传统的谱系中对该命题的全新解读。透过这两个文本,我们可以梳理出“诗言志”的内涵从政治教化到思想感情直至纯抒情的发展过程,并可以窥视出不同语境下的学者建构中国文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以及所谓抒情传统对中国文论的发覆之功与遮蔽之过。
一、“志”“道”合一:《诗言志辨》的发生与接受
1947年,朱自清的《诗言志辨》由开明书店印行。虽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批评史的清理和研究早在1927年就由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日人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1925年即问世,但1928年才由孙俍工选译到国内)发其先声,但《诗言志辨》仍称得上古代文论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
《诗言志辨》的出现,与当时学术发展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新文化运动为国内学界带来了体系化的西方学术体系,将这种结构化、逻辑性的学科意识引介到传统学术研究活动中,便成为中国现代学界的工作重点。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原本在文化体系中叨陪末座的诗文评被重新梳理,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学科的雏形,大量中国文学批评史性质的书籍开始涌现。经过新文化运动的破旧立新,传统文学研究的这种复兴之态当然是有着深厚国学根基和学养的朱自清所乐见其成的——他为郭绍虞等人的批评史专著所撰写的专评就足以为证。但是,正如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所言:“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以认真地仔细地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①他一方面肯定了诸多学人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对批评概念、范畴确切内涵的清理工作寄予厚望。这种看法,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或许也是对于早先由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关于“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可参阅刘绍瑾教授发表于《学术研究》2001年第8期的《“整理国故”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兴盛》一文)和由顾颉刚等人领衔的“古史辨”运动的回应,以整理和考辨的态度介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清理。但从更切近的原因看,应该是对于当时部分学人运用古代文论术语不谨慎或者全随己意、颇多望文生义的现象的批评——更切实的,应该是针对周作人所发表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作“新文学的源流”的演讲,并于当年9月汇编成书出版发行。在这本书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史视为“诗言志—言志派”和“文以载道—载道派”两种潮流的更替起伏。②对于“言志”和“载道”的内涵,周作人其实并未作切实的阐发,但是在论述清代各种文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差异时,他将内容分为志(情感)和道(思想),俨然将“志”等同于“情感”。③
“志情合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对于“志”的内涵的一种解释,标举者不在少数,攻讦者亦大有人在。周作人在复杂的学术史中选取了主情派的观点来为自己“人的文学”的理论背书,固然有其主观的理论目的,但是这种理论的择选并未建立在扎实的学术史梳理工作之上,在朱自清看来,应该是有些粗暴和随意的。因此,为了批驳周作人对“诗言志”的误解,朱自清用大量原始文献为材料,从“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和“作诗言志”四方面分析了“志”在其原初语境中的意思。朱自清从诗歌在古代的“献”、“赋”、“教”、“作”四种存在状态入手,认为古代诗歌的诞生都是带着强烈的政教目的的:从创作者的创作目的来说,“这些诗的作意不外乎讽与颂,诗文里说得明白”,并且是“讽比颂多”;从听诗者的角度来说,由于诗歌的接受者大多是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而他们搜集诗歌的目的主要是“观志”和“观民风”,所以即便是对《诗经·伐木》这样“缘情”的宴飨诗,也不会作情感的理解,而是将其作为了解民风民情的一种途径。在论及“骚人”出现之后创作的“言一己穷通”的诗歌的时候,朱自清认为这批作者多是士大夫之流,所以他们的穷通出处也都与政治抱负和政教理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原不相同,究其实“都关政教”。④
当然,朱自清也注意到中国诗歌史上抒情诗兴起这一事实,但是,一方面,这种为了抒情而抒情的诗作实属后起,已经难以改变“诗言志”在历史语境中的政教内涵;另一方面,为了因应创作实际的这种发展,“志”在后世的发展中也有了数次内涵的扩张。不过,“‘诗言志的传统经过两次引申、扩展以后,始终屹立着。‘诗缘情那新传统虽也在发展,却老只掩在旧传统的影子里,不能出头露面”,这种局势一直维持到袁枚将“言情”纳入“志”的范围。而周作人之所以将“志”等同于“感情”,乃是受到了袁枚以及近代西方抒情观念的影响,但是,朱自清着重强调的是,“词语意义的引申和变迁本有自然之势,不足惊异;但我们得知道,直到这个新义的扩展,‘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其实原一”⑤。
作为第一部对“诗言志”命题进行学术梳理的著作,《诗言志辨》无疑有着丰厚的学术内涵。朱自清先生虽然是用学术史的眼光观照这一诗学命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但是最终目的仍在于还原“诗言志”的原初内涵,力图将对这一命题意涵的阐发限定在本义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将其当代化,抽空这一诗学命题的历史内涵。《诗言志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一则是其确立了“诗言志”作为中国文论“开山的纲领”的地位,更重要的则是他对于“诗言志”的考察,还原了“言志”说的历史面貌,并倡导了一种扎实的学风。但是这一结论并未得到学人的传承,在后来的学术谱系中,对于“诗言志”的解释,大多遵从了周作人(以及后来罗根泽等人)的意见,将其释为抒情——至少是广义的人的思想感情。
比如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1999年初版,2011年修订),虽然重视了“志”在战国中期的意义扩展,但仍认为,“‘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⑥,这与周作人的理解几乎别无二致。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建构中,朱自清先生对于“诗言志”的考辨成果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概念的原初义并不能框定后人对之的灵活运用或泛化处理,所谓的“起源不等于本质”,因此才有了数千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纷纭聚讼;另一方面,将统摄了中国文论史数千年的“诗言志”定为“都关教化”,无论是对于身处“反传统”历史背景中的“五四”一代学人,还是身处西方文化大举传入造就身份危机、文化危机的当代学人,都有些难以接受。对于浸淫国学的“五四”学人来说,虽然对传统文化有过激的批判,但大部分人在文化情感上仍以传统文化为依归,如鲁迅对魏晋风度、中国小说史的热心考辨,傅斯年、闻一多对先秦文史的追索等。若将“诗言志”等同于政治教化,那就意味着数千年的文学史都在否定之列,极易滑向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深渊。而对于当代学人来说,过于强调“诗言志”的教化意味,也等于将中国文学史从纯文学体系中完全剥离开来,在与西方文学一较高下的紧要关头,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毁长城。朱自清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容抹杀,但后世学人对之的无意甚或有意遮蔽,也有其不得不为之的无奈处境。
从朱自清明确“诗言志”的政教本质,到后人乃至时人对这一结果的回避态度,已经彰显了中国诗学研究者努力扩充“志”的内涵背后隐藏着的建构中国抒情诗学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在海外学者特殊的文化处境的刺激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升。
二、抒情诗学:中国抒情传统
建构中的《诗言志释》
随着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日益兴盛,标举中国诗学独异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特征,成为海内外学人戮力共襄的盛举。这种诗学特征乃至文化身份的建构,对于身处海外的华夏学人来说,显得尤为紧迫。经过陈世骧、高友工、孙康宜、吕正惠等人的努力,中国文学中的所谓“抒情传统”逐渐形成了脉络清晰的体系,抒情也成为与西方叙事比肩而立的中国传统。在半个多世纪的拓殖之后,中国抒情传统形成了自己绵延的学脉,“专指20世纪后半叶以来,缘起于海外华人学者,后延伸至港台的一个从整体文学层面考察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研究取向”⑦。
在这些前辈学人的抒情传统建构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他们大多或以某种诗歌类型(如叶维廉对于山水诗的独好)、某一时期的诗歌实践(如高友工对于唐诗、宋词的阐发)为基础,或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将纷繁的中国诗学实践纳入到抒情体系之中,建构中国抒情传统或阐释自己对于中国诗学抒情特色的理解。前者虽然有扎实的诗学实践作为基础,但是以某类、某期诗歌实践指称中国抒情传统,显得有些头重脚轻;后者虽然对于中国诗学有整体上的把控,却有先入为主的嫌疑,削足适履地将中国丰富的诗学实践纳入单一的抒情传统体系,难以服众。
在这种背景下,王文生先生的《诗言志释》就显得尤为意义重大。作为王文生规划的“中国抒情文学思想体系丛书”的扛鼎之作,《诗言志释》与早先出版的《论情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一系列论文一起,构成了其对于中国抒情传统的整体思考。《诗言志释》之于中国抒情传统的意义在于,它以“诗言志”这个中国诗学的关键命题为切入点,从真正诗学的高度确定了中国诗学的抒情特色。虽然“文论概念却是从特定思想史的背景出发而对特定文学现象做出的理论概括,它的义涵应历史地由特定思想背景和特定文学现象的关联中抽绎而出”⑧,但是文论概念一经形成,就会超越其赖以建构自身的具体文学实践,而对整体文学的发展有了强大的规制力,像“诗言志”这样对于中国诗学有举足轻重意义(如朱自清所言,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的命题,更加具有这种全局性的影响力。
而从“诗言志”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王文生的《诗言志释》同样不容小觑。在国内,自朱自清的《诗言志辨》之后,再没有产生以这一命题为研究对象的专书。虽然国内相关论文层出不穷,但都未能穷尽这一命题所涵盖的问题,有如散金断玉。而海外关于“诗言志”的零散研究,则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从言意关系出发,将这一命题纳入言意之辨的框架;二是从抒情传统的角度,提及这一命题的抒情性质。刘若愚认为,将诗视为“普遍人类情感的自然表现”的理论可称为“原始主义”⑨诗观,并称“古代中国的原始主义诗观结晶于‘诗言志这句话中”⑩,较为粗略地涉及了“诗言志”的抒情特质。高友工先生则将“诗言志”与“歌永言”合而论之,认为大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足之蹈之也”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中国抒情美学的宣言”{11},明言这一命题对于中国抒情美学的意义。但是,这些对“诗言志”抒情特征的论述都稍显薄弱,也未能以这个关键命题统摄抒情传统的建构。
在此种背景下,王文生的《诗言志释》不仅以专书形式接续了朱自清开创的学术传统,更从“诗言志”的产生时代、“志”的真正内涵和“言”的表述实质等方面作了详实的论证,系统地坐实了“诗言志”的抒情本质,并在与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代表的西方文论传统的对比中彰显了东方诗学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诗言志释》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不仅对于“诗言志”命题的研究有参考价值,更能从方法论的高度启发我们对比较文艺学学科的反思。
首先,与朱自清主要从历史文献的阐释入手确定“志”的确切含义不同,王文生从人类精神活动的组成以及发展进程出发,论证“志”指的是“知”、“情”、“意”中的“情”。朱自清在阐发“志”的内涵时,主要是从《诗经》诗作本身以及《左传》等典籍中的记载为文献基础。而王文生的逻辑起点,则是后世对于《诗》的笺注。他认为,历代注《诗》,对于“志”的解释虽然纷繁复杂,但实质上都近似于朱熹所言“心之所之谓之志”,即把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视为“志”。基于此,王文生借助现代心理学对人类精神活动知情意的划分,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视为整体,认为后者“概括起来,就是注意表现形式的节奏感和音乐性”{12},而知情意三者中较为倚重音乐性的,只有“情”。之所以《尧典》没有明言“诗言情”,乃是“当‘诗言志这个纲领出现的时候,人们对于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志的认识还停留在粗略而一般的水平上”,因而将知情意全部涵纳进了“志”的范畴。{13}而到了汉代,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人们对于知情意的认知有了较为明确的意识,因此汉魏文献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情”的论述,也出现了“诗缘情”的命题。但是到了宋,大多数诗人又接受了“诗言志”即是“诗缘情”的共识,导致“诗缘情”未能对“诗言志”取而代之。
较之于朱自清的文献互证法,王文生所采用的心理学方法具有相对的优越性。作为传统学术路径的代表,文献互证极易陷入阐释循环的怪圈,而且选取不同的文献极有可能使得研究者对同一问题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基于此,王国维先生才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弥补文献互证的缺陷。在“诗言志”研究的历史上,学者们依据的主要文献都大同小异,却催生出两派难以调和的主张,文献互证法的弊端难辞其咎。而将以逻辑性和结构性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心理学的明晰化研究成果,引入混融的原始思维所促发的早期诗学命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具有敞亮的作用。王文生的高妙之处,更在于能将特定时期人们的精神发展阶段与当时的诗学论述结合起来,以诗学主张印证精神发展进程,又以精神发展阶段特征描述诗学主张的确切内涵。自文学理论发生心理学转向之后,论述文学创作心理、接受心理的著述层出不穷,但真正将心理学与诗学命题结合得滴水不漏、相得益彰的学者或成果却寥寥无几。王文生以心理学剖析“诗言志”的内涵,无疑具有相当的首创意义。
其次,从诗乐相近的角度,论证“诗言志”之“言”是抒情的表现而非叙事的模仿。以往关于“诗言志”的研究多集中于“志”的阐发——朱自清也概莫能外,而王文生见人之所未见,从“言”入手,与“志”相和,共同佐证这一命题的抒情本质。
“诗言志”是舜与夔讨论乐教诗提出的一个命题,“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共同组成了以舜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对于乐教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因此,要想廓清“诗言志”的内涵,必须回到乐教这个大的语境中。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虽然也注意到诗乐的分合对中国诗学产生的影响,但他主要是将诗乐分离视为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受到重视的历史节点,并未将诗乐问题与“诗言志”内涵的揭示联系起来。王文生则见人之所未见,从中西诗学、文化学的共识切入,认为中西都存在诗乐并置的现象,因为诗歌与音乐“同是内在感情的直接流露”,“使用表情的媒介都是以声为主”,“在创作上是表现而非模仿”。{14}通过对诗乐同源的论证,王文生成功地将音乐的抒情性、表现性置入“诗言志”的“言”中,将“言”定义为表现,间接地证实了“诗言志”命题的抒情性。
除此之外,王文生还认为:“‘诗言志、‘赋比兴都是‘诗经的创作经验的总结。前者标明诗的本质;后者概括了抒情诗的表现手法;二者联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抒情诗的文学思想体系的核心。”{15}
最后,与朱自清努力将“诗言志”的探讨限定在中国古诗领域的做法不同,王文生从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进程出发,论证了中国文学整体的抒情性以及“诗言志”作为抒情纲领的统摄地位。海外学人虽然标举抒情传统应对西方的叙事传统,但是这种标举行为一直饱受诟病。学人——尤其是大陆学人——诟病抒情传统的一个原因就是,只讲抒情传统其实无视了中国文学中绵延不绝的叙事传统,而将叙事诗、小说等明显带有叙事印记的文类纳入抒情体系,无疑忽视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针对这一点,王文生以小说为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古典小说在明清两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红楼梦》甚至成了世界级的巅峰作品。然而它们的成就,并不体现在西方叙事文学所擅长的情节创造上,而在于融抒情叙事于一体,冶外在行为描写与内在情感表现于一炉的民族特点的形成。而这一点,恰恰是古典小说作者运用中国抒情文学经验和追求情味价值观念于叙事文学创作实践中而得到的丰硕成果。纵观元、明、清三代文学的历史,南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并不是如同闻一多说的,偏离抒情文学为主流的路线而转向。相反地,这条路线是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了。{16}
与大多数支持抒情传统的学者一样,王文生也将中西文学史视为分别以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为主流的截然不同的文学发展史,并以此论证中国诗学的抒情特色。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王文生先生对于“诗言志”命题的研究是全面的,不仅用跨学科的方法阐明了“志”的情感本质,而且对前人未曾留意的“言”也进行了抒情性质的剖析,并以文学史为证,构成了基本能自圆其说的“抒情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同样存在着破绽。
首先,在对诗大序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像高友工一样,王文生也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视为一个整体,这本无可厚非,但是王文生在接下来的阐释中,却将这个整体视为了对于“诗言志”这一命题的具体阐发:
尽管《尧典》没有明确说明“诗言志”的“志”主要是知(knowledge)、情(emotion)、意(idea)的哪一方面,但是,什么样的内容才需要用拉长了的声音(“歌永言”),高低、长短、轻重的节奏(rhythm)(“声依永”),和不同声调(tone)、调质(tone quality)的变化和谐(“律和声”)去表现它呢?“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概括起来,就是注意表现形式的节奏感和音乐性。音乐节奏,由于它是传达人的内在感情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媒介,因而被称为形式化的情绪。这样依赖于音乐节奏的“志”,自然不可能是“知”和“意”,而只能是“情”了。{17}
我们在上文曾提及,舜与夔的这段话,是对于乐教内容和形式的规制。在“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论述中,“诗言志”关涉内容,其余的都是对于音乐形式方面的要求,两者本就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是在王文生的论述中,“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形式成了专门为“诗言志”这一内容服务的订制形式,这其实是一种误读。而拿形式的抒情性来反证内容的抒情性,同样也是说不通的,因为抒情的形式同样可以用来讲故事,而叙事的形式同样可以用来抒发感情。
其次,将“诗言志”的抒情性视为不仅仅是对中国诗歌的概括,更是对整体中国文学的概括,失之武断。朱自清撰写《诗言志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认为周作人将“言志”的指涉范畴从中国诗歌扩张为对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的做法不甚妥当。而王文生也同样重蹈了周作人在20世纪初的覆辙。将中国文学史视为抒情文学史,将西方文学史视为叙事文学史,本身就是武断的。《红楼梦》固然有很强的抒情性,但是作为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它的首要任务也是将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出来。女娲补天、绛珠还泪、宝黛爱情的三重叙事结构,目的也在于更好地呈现叙事内容。草蛇灰线以及遍布全书的暗示、双关等叙事技巧,也是为更好地讲故事而非抒情服务的。而西方文学史固然是以叙事文学偏多,但是湖畔派、意象派等诗群的绵延不断,也显示着抒情传统在西方文学中的不绝如缕,且不是能轻易忽略的文学存在。以大而言之的态度生硬切割中西方文学,背后隐藏的乃是西方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思想。对立虽然有助于人们认清对象的身份界限,却遮蔽了所谓“整一性”中鲜活的同质化因素。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早有评判,此不赘述。
三、余论:为了抒情的抒情
从朱自清到王文生,“诗言志”这一统领中国诗学的命题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易筋洗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无法评判二者的“原初”哪个才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从这一命题的演变轨迹不难发现抒情传统的建构由隐而显的崛起过程。
对于中国诗学抒情传统的建构,虽然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显在的潮流,但是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有了对于“诗言志”的抒情化解读。
与《诗言志辨》同时出版的傅更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虽未明说“诗言志”就是“诗言情”,但是却通过对大量古代诗学主张的情感化解读,切近了“志情合一”的核心,同时明言:“文学创作既所以抒情,则必有其情者始克有其文。无其情而强以为文,如不实之花,无源之水;中乏其情而冀以其伪者感人,能为所动者鲜矣。”{18}
可见,对于“诗言志”的抒情解读早已有之,但是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的建构之所以引人瞩目,一方面因之人数众多,另一方面则因其理论多有极端。海外学人身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异域,再加上在西方高校从事中国文学、诗学的教职,不得不标举中国文学、诗学大异于西方文学、诗学的特征,本有情可原,但是若将二者的区别过分夸大,就会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用“东方主义”的目光审视中国,将中国文学、诗学视为与西方迥异的铁板一块,用“抒情”的大帽子掩盖了中国文学、诗学的丰富内容和特征,将活态的中国处理为“想象的东方”。相较于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东方想象,华裔学者对于中国的东方想象显得危害性更大,因为这种东方想象实际上在确证西方学者本已出现偏差的论断,使得对中国形象的扭曲有了更理直气壮的依据。尤须引起警惕的是,华裔学者的这种东方想象更有从学术策略滑向政治策略的危险。
相较而言,王文生在海外学人中算是持论公允的一位。针对西方理论大行其道的现状,他在《中国美学史》前言的最后疾呼:“在本书脱稿之时,我想向我的同行发出由衷的呼吁:无需寻求中国美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无需寻求美学话语于别的文化系统。而要集中力量去发现中国美学传统,抢救传统,弘扬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中国自己的美学体系,并用它去引导中国新文艺朝着具有民族特点的方向发展。”{19}从《论情境》到《诗言志释》,王文生一直立足于中国诗学的实际,以西方文论和方法作为辅助,努力廓清中国诗学的核心问题,并且建构了具有浓烈中国特色的抒情诗学体系,其功不在小。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强烈警醒意识的学人,为了构建中国抒情传统体系,也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处,可见用一个体系来涵盖丰富的文学、诗学实践,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困难,才诱惑着一大批学人前赴后继地为着这一目标尽心尽力。比较诗学学科的推动者叶维廉曾经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的宏愿,而且这个愿望也被视为比较文艺学的重要目的之一,但是,从“诗言志”这一命题的学术史就不难看出,文化背景或时代背景是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学者对同一问题的审视眼光。个案研究尚不免乎此,更何况是体系庞大的中西诗学研究?岂能不慎之又慎?
我们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海外学人建构中国抒情传统的努力,因为与西方文学、诗学相比,中国文学、诗学在抒情方面确实显得较为突出;而且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抒情传统的持续阐扬,也确实为我们敞亮了此前受到忽视的某些诗学问题,使得中国诗学在世界诗学体系中有了坚实的立足之地。但是,在建构抒情传统的过程中,万不能为了抒情而抒情,为了体系化的建构而曲解、误读、遮蔽中国文学、诗学的复杂生态。任何体系化的努力,都需要建基于对文学、诗学实践的尊重之上,只有这样的体系,才能具有超越性和指导性。相较于体系弘大的理论抽绎,微观地审视具体的诗学问题,从问题出发,走向求同存异的跨文化交流,也许更应该成为比较文艺学所追求的学术愿景。
①④⑤ 朱自清:《诗言志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第5-26页;第33-35页。
②③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7;第31页。
⑥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⑦ 李凤亮等:《移动的诗学: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观照的海外视野》,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⑧ 萧驰:《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对时下中国传统诗学研究四观念的再思考》,《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
⑨⑩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第101页。
{11} 冯若春:《“他者”的眼光——论北美汉学家关于“诗言志”“言意关系”的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61页。
{12}{13}{14}{15}{16}{17} 王文生:《诗言志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0页;第54页;第75-78页;第90页;第139-140页;第50页。
{18} 傅更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6页。
{19} 王文生:《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category, the study on literature topic is weak. But literature topic, like Poetry Speaks the Mind, is a judgement and definition about the whole literature. By means of these literature topics, we can understand the whole literature of Chinese more accurately. In the book of Differentitation of Poetry Expressing Mind, Zhu Ziqing considers that Mind means Moralization. But Wang Wensheng, the famous overseas scholar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nfuted this opinion. In his book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Speaks the Mind, Wang Wensheng deems that Mind means Emotion. From this evolution, we can find that how violent the context of learning has changed the field of vision of the scholars of different ages.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also find such a f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the scholars of overseas Chinese are lost in the trap of lyric for lyric and Orientalism.
Key words: Poetry Speaks the Mind, Zhu Ziqing, Wang Wensheng,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Oriental Imag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