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50后作家遭遇80后批评者
2014-1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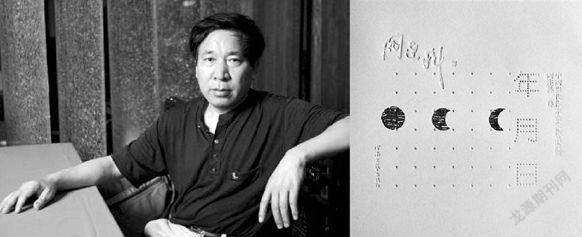
邀请80后评论家参加阎连科创作研讨会,是阎连科自己的主意。他很看重年轻一代如何理解他的作品,因为他们对文学更敏锐、更新鲜。“其实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评论者,年龄大了之后都会有疲劳感、厌烦感”。
在这次研讨会上,这群年轻人当面对他进行了一番“批评”。比如,在获得2014年度卡夫卡奖后,阎连科曾在本报发表文章《神实主义,探求“不存在”的真实》,以“神实主义”来概括自己的创作,但80后评论家并不完全认同这一命题。这是一场内部讨论,本报得到阎连科先生授权,刊登本次研讨会的部分观点。
中国作家集体罹患现实
写作焦虑症
作为中国最具争议的小说家阎连科一直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邱华栋最近在肯定阎连科和余华小说的现实精神的同时也指出,《炸裂志》、《第七天》因为迎合国际市场而在写作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中国作家很容易原谅自己”。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西方评价话语与本土评价话语之间的区别。
在国内,阎连科被誉为“中国的卡夫卡”、“荒诞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等等。中国的评论家称《丁庄梦》为“中国的《鼠疫》”、“中国笛福的《大疫年纪事》”,《年月日》被誉为中国版的《老人与海》。这实际上是文学评价和传播、译介交互的不对等状态造成的。这体现出来的是中国文学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极其不自信,媒体和评论家西方情结淋漓尽致。这不仅体现了批评家们的失语和批评的无能,也体现了在世界文学体系下的本土焦虑。
先锋文学到今天已经快十四年了,而很多小说家的身后却仍然站立着西方文学大师们的身影,本体身份和本土写作仍然没有真正完成。
当前很多所谓的汉学家并非真正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场域,而他们所携带的“国际话语权力”却导致了很多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和全球化幻觉中过于依赖于这些汉学家的评价标准和口味。这难道不是本土写作的悲哀吗?难道不是汉语的悲哀吗?即使在汉语创造力极强、想象力超群的文体小说家(如索源体、絮言体)阎连科这里,也仍然有着“世界性文学的焦虑”。需要追问的正是,为什么中国小说家的身后总是站着西方作家的身影?
我还注意到同一题材在不同文体那里体现出的时间差问题。比如,艾滋病题材的小说,《丁庄梦》出现于2006年,而实际上在2004年70后诗人沈浩波就写出了《文楼村纪事》。同一题材的作品,在小说家和诗人那里,在小说评论家和诗歌评论家那里类似于绝缘体一样自说自话。我希望写作者和评论者多对此现象进行“沟通”和“互文性”阅读,这无论是对于写作者和评论者而言都是有益的。
日前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对中国作家过于依赖现实的批评我倒是很认同。当下中国作家对“现实”和讲述“中国故事”投入了空前的热情,阎连科等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不满与批判,小说家集体患上了现实写作的焦虑症。似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写法和精神在今天的小说家那里都失效了。他们在寻找处理“现实”的新途径以及文本自身的逻辑。而无论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 ”,古巴卡彭特尔的“神奇现实主义”,还是阎连科的“神实主义”都构成了一些特殊国家本土作家写作的文学史谱系。请注意三者背后的民族和国家特征,文学的政治地理学仍然是值得谈论的话题。但是,我仍然想追问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在当代中国真的就无效和死亡了吗?当年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柳青、路遥、陈忠实的写法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延续?乡土写作的可能性是什么?此外还有乡土小说经验对当代小说家的挑战。当下很多乡村写作表面上看是涉及当下和历史的,实际上却只是停留于历史经验,真正的当代性的乡村书写仍然缺失。也就是说乡土小说的当代性非常不足,更多的是仍停留于现代乡土文学经验,区别在于只是手法上不断更新罢了。
此外,对于像阎连科这样的“先锋作家”而言,当先锋的方法论不再是问题,那么以什么材料来构筑文本就显得格外重要(典型的例子是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和徐冰的装置艺术《凤凰》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各种令人震惊的、超出了作家想象力极限的新闻现实的语境下,小说材料以及作家对材料的理解和重构就显得格外重要且具有超出以往的难度。对现实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更多的是仿真性现实、伦理化现实、道德化现实、社会化现实,相应缺失的是文本性现实、语言性现实、精神性现实和想象性现实),重构文学的乡村和乡村的文学,如何呈现看不见的现实和看不见的历史,小说的能见度问题,这仍然是阎连科等作家必须正视的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阎连科多年来的写作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不断的震撼性的启示——最荒诞的最真实,最抽象的最真切,最寓言的最现实。他的残酷叙述,苦难想象,癫狂和病症修辞(性病,艾滋病,男人的早死病),小说家的“医生”身份,恶心抒写,狂欢的寓言化细节,荒诞性的奇观与猎奇,身体的政治学,方言性写作都呈现了近乎百科全书式的能力。这种“非正常”的震惊式阅读效果仍离不开政治寓言抒写的情结。一定程度上,性欲和政治仍然是中国读者的阅读欣快症和小说家的伦理。
以艺术之假写历史之真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目前,评论界对阎连科的争论特别集中于一种当下性,即,他写作的内容和题材与中国现实政治之间的一种奇怪的对峙关系,以至于媒体夸大其词地宣传阎连科是中国遭禁最多的作家。我想说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政治一直是文学的核心内驱力,在一些投机取巧的作家那里,政治甚至变成了文学的春药。但就阎连科的写作意识和写作姿态而言,政治固然是理解阎连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却过于简单化或者二元化,简单到我们认为只有政治正确或者政治不正确,比如西方的汉学家可能认为阎连科批评了中国的体制,所以政治正确,而我们的批评家可能认为这种批评不符合实际,所以政治不正确,这特别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论。
当我们局限在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的二元逻辑中,我们已经是在把“意识形态”灌输给我们的观
念,我们不知不觉地成了我们要反对的东西——同时也是阎连科批判的东西。因为只有在意识形态中,政治才有正确和不正确,历史才有正确和不正确,现实也才有正确和不正确。而阎连科的写作,恰好是要颠覆这种“正确/不正确”、“真/伪”普遍化的陈述。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要从精神和美学的内里去理解阎连科写作的政治学。
看阎连科近些年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历史和现实在这里是同构的: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我们经常谈论的“历史”可以分几个层次:一是指在过去某个时刻“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二是历史的叙述,主要通过教科书和大众媒体进行传播,这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第三是对于这一叙述的再叙述,文学叙述基本上属于这个层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革命历史小说和上世纪90年代的所谓新历史主义小说,其本质上都是对于意识形态化历史的再叙述,不管其是认同还是反对。阎连科的写作往往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写作的一部分。但我认为阎连科突破了这种框架,他试图用中国的卡夫卡式的方式努力回到历史的第一个层面,即对“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进行解构,也就是直接从根部着手,以艺术之“假”(寓言)来书写历史之“真”。于是,“真”变成了“假”。以真来写真,这是新闻,是纪实,是非虚构;而以“假”来写“真”,这才是小说,是艺术,是伟大的文学道统。
神实主义的血管里仍是
现实主义
饶翔(青年评论家)
阎连科提出“神实主义”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实践已经溢出了既有文学观念的解释范围;现实与写作的关系,现实背后的真实要求,当下中国呈现出来的逻辑,这些都需要新的解释范式。
“神实主义”的定义是: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
其中包括几个要素:追求——看不见的真实,所谓“内真实”与“灵魂真实”;遵循——事物内部的逻辑,所谓“内因果”;技术——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如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
以出版方认定且必然获得阎连科认可的“神实主义的力作”《炸裂志》为例,寻找当代中国三十余年的发展模型,给出一种解释向度。“炸裂”由村而镇、市、超级市,不可遏制地发展。经济发展的躯体下,拖曳着漫长的由荒原与垃圾场所构成的坟地的阴影。炸裂的发展是活脱脱的丧德史,传统道德序列中最低贱的男盗女娼成了炸裂的发展永动机。它的逻辑是,当下中国无所不在、战无不胜的拜金主义,“笑贫不笑娼”,“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其背后隐含的逻辑:物质必然使人疯狂,在物质的驱动下,个人必然丧失主体性与尊严感。
在技术层面,作者找到的“内因果”不断简化、放大、重复,让人由震惊(惊喜)到疲乏,最终是全面的贫乏感。很难断定这种贫乏感是阎连科的主动追求,但技术层面的单一与丧失生命力,确实与全书刻意营造的“荒原”、“垃圾场”、“坟地”相适应。
再来谈谈世界观,“神实主义”缺乏对世界的整体把握,不是对“现实—文学”关系的新定义,基本上只是一种“文学观念”,甚至更准确地说,只是一个“文学提法”。换句话说,“神实主义”主要以对现行文学的反动来确立自己。而这种反动常常针对的是现行的文学体制及其产生的压力,而非文学观念。“神实主义”概念的提出更多是出于作家自我认同的焦虑与需要,而不是真正“发现了小说的新大陆”。没有新的世界观,也就必然对应着写作层面“专利技术”的阙如。“神实主义”的武器库里,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诸般兵器都身份混杂,甚至称不上是纯粹意义上的“技术手段”。
阎连科自称“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这句话或许最为准确地概括其写作。他可以更名改姓,以“神实主义”来指认自己的写作,但根本上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现实主义的血液,他的写作仍是现实主义的子嗣。
